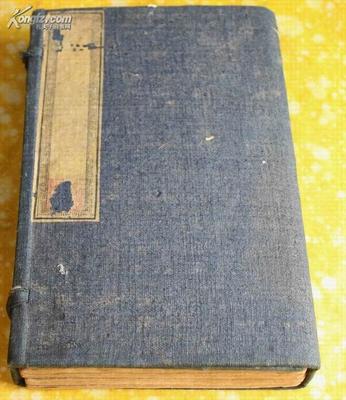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收在这一文集中的文字并非是我所写文字的全部,但它们已基本可以说明我的文学理念和我的写作状态了。
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我的处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心绪,常常会使我无端地想起儿时在田野上独自玩耍的情形——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稻田,穿过一片林子,走过一汪水平如镜的池塘,走过一座细窄摇晃的木桥……
就这么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芦苇叶上有一只呜叫的“纺纱娘”,我先是一阵出神的凝望,然后将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鸟喙状,弯腰缩脖,双眼圆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就在微微张开的“鸟喙”马上就要啄住它时,它却振翅飞走了。于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捉它在阳光下飞过时变成精灵样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绿闪动着,在空中悠悠地滑过,终于飘飘然落在大河那边的芦苇叶上。我望见先前那片单薄的芦苇叶空空地颤悠了几下,不由得一阵失望,但随着“纺纱娘”的叫声怯生生地响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觉中游走开了……
一群鸭子从水面上游过,我先是看它们争先恐后地觅食,用嘴撩水洗擦羽毛,再看雄鸭追撵母鸭,弄得水上一片热闹。过不多久,我就暗暗生起恶念,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团泥块,身子后仰,然后向前一扑,奋力将泥块掷向鸭群。随着一片浪花在太阳下哗哗盛开,鸭子呱呱惊叫着拍着翅膀四下逃窜,我的心头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再歪头看时,只见正悠闲地坐在小船上抽烟的放鸭老头忽地站起,小船晃悠着,他也晃悠着,用手指着我怒吼——声音也在晃悠着。我捏着鼻子朝他哞哞几声,然后再捡起一团泥块更加用力地掷出,也不看一下水上的情景,就撒腿跑掉了。晃悠的怒吼追了过来,在我的耳边震荡着,我的心里却荡开莫大的愉悦……
我在田野上走着,看一只瘦长的河蚌在清清的浅水中于黑泥上划出一道优雅的细痕;看一只只肥肥的野鸭笨重地落进远处的河水中,犹如一块块砖头从天而降咚咚砸落;听天地相接处断断续续地传来吆喝水牛的苍老声音;听大河中不知从哪里来的大船上异乡女子呵斥她娃的清脆嗓门……
看不够听不厌的田野,勾着魂,迷着心,让我痴痴地走,痴痴地耍。但,就在这不断上演的田野好戏让我流连忘返时,忽地就有孤独悄然攻上心来,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后来,我爬到一座大坟的高顶上,在寂静的天空下转动着身子,觉得孤独犹如迷雾从四面呼呼涌来,我不由得大声尖叫;叫了一阵,就见恐惧从远处林子里正朝这边走来。我哆哆嗦嗦地坚持了一阵,终于仓皇冲下坟来,朝着家的方向落荒而逃……
然而,过不多久,我又会被田野吸引着而重新回到田野上。继续重复那个过程、那些游戏……
这些年来,总有这少年时田野上的感受:兴奋着,愉悦着,狂喜着,最终却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独,甚至是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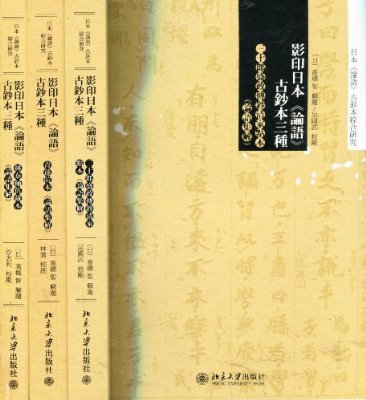
我常常突然怀疑起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由怀疑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而怀疑自己的感觉、见识、思维方式,甚至是智力。
就像魅力田野一般,文学还是不可抵抗地迷惑了我——更准确地说,那些文学理念还是迷惑了我,使我无法自已。就像在完成一个谎言,我也一直为我所认同的理念进行着理论和逻辑上的完善。我一直企图要让我的文学理念成为无懈可击的、圆满的、合法的言说,因此我可能是一个更喜欢在大庭广众中诉说自己文学理念的人。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在试探他人的认同,最终是想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诉说而使自己的理念更趋完整和完善。但我很快发现,那种在高深处建立理论王国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再后来,我选择了一种朴素的思考和论证,我开始经常性地进行原始的、常识性的,同时也显得有点儿过时的发问和诉说——
“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来确立的?”
我曾在中韩作家论坛、中日作家论坛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问道:“是中国人吗?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学在经过各路“憎恨学派”对古典形态的文学不遗余力的贬损与围剿之后,现在的文学标准,也就只剩下一个:深刻——无节制的思想深刻。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标准,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舔脚丫子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这一标准,成为不证自明的甚至是神圣而庄严的标准,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优美平衡,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新兴文学中被彻底打破了(那时的文学是由深刻的思想、审美、悲悯等诸多维度共同组成的),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学朝圣者,气势非常壮观。
可是,韩国、日本、中国在数千年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先辈们于长久的文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维度吗?没有——尽管在它们的文学中一样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深刻。
就中国而言,它在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用的是另样的标准、另样的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情调、性情、智慧、境界、意境、格、格调、滋味、妙、微妙……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艺术门道,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审美境界。“深刻”一词不知是何时才出现的?有谁向我们证明过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价值上来得低下呢?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证明。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所谓‘深刻’作品,我们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朴素却也最能使人暂且停下前行脚步的发问。那些以揭示人性的名义而将我们引导到对人性彻底绝望之境地的作品,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犹如深陷冰窖的作品,那些暗无天日让人感到压抑想跑到旷野上大声喊叫的作品,那些让人一连数日都在恶心不止的作品,那些夸示世道之恶而使人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下作的作品,那些使人从此对人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那些对人类的文明进行毁灭性消解的作品,那些写猥琐、写浓痰、写大便等物象而将美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作品,我们真的需要吗?
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糟糕。日子过得本就很压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压抑。难道费时费神地阅读文学,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阅读效果吗?难道阅读者也与那些文学一样喜欢阴沟与苍蝇、喜欢各种各样的变态情趣吗?文学在引导人类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是要将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它?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现在文学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
“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不只是“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探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更何况,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的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
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的尸体、被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微、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落后和贫穷,可怕的是展示我们在落后和贫穷状况下简直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你可以有你的不同政见,但不同政见并不能成为你不顾民族最起码体面的理由。
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的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是为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