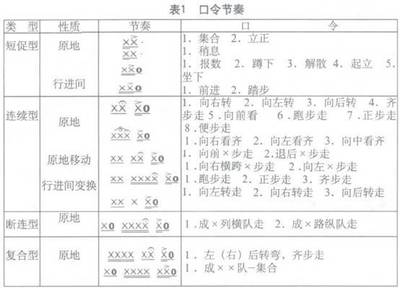一、能对三观进行深入破坏的作品,不啻革故鼎新的佳作
1980年,海政歌舞团苏小明唱了一首《军港之夜》,军队有首长说,苏小明的歌,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新华社发内参表示:“苏小明不可不唱,不可多唱,要适可而止。”海军机关有人向上面反映说,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
同在1980年,中国音协开了个音乐创作会,点名批评了李谷一的演唱风格,要求她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唱《乡恋》,李谷一拒绝。之后,李谷一收到中央乐团领导的信,警告她再这么下去就别在单位待了。1981年除夕,在人民大会堂迎春晚会上,李谷一决定在邓小平出席时演唱《乡恋》,结果邓小平没来。1983年第一届春晚,观众把剧组的电话打爆,点播《乡恋》,总导演向央视台长请示,台长不敢定夺,请示上报到广电部部长吴冷西面前,吴冷西踌躇了半天,拍板说:“上!”至此,《乡恋》正式被官方认可。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执笔的9位作者都是音乐界的名家,此书批判了受年轻人追捧的港台流行歌曲,认为那些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是资本主义的流毒。书中有60首歌曲被点名批评,包括两首英文歌曲,其中之一是猫王的LoveMe Tender。
1105年,宋崇宁四年,朝廷将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309人列为奸党,在全国刻碑立石,以警后世,是为元祐党籍碑。次年,朝野反对,皇帝下诏摧毁各地党籍碑。后来,党人的子孙反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
今天,回看30年前的中国流行乐坛,一首歌曲能被列入《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实在是对它的肯定。这就像如果一篇文章被称为“毁三观”的文章,我一定会找来拜读。在这个三观破产的年代,如果还有作品能对三观进行更深入的破坏,它就不啻革故鼎新的佳作。
一首歌“黄”,抛开时代的价值观不论,至少说明它们比别的歌曲更能感染人、打动人。“打动人心”是对艺术作品的最低要求。如果一首曲子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具备起码的艺术性。
二、能被贴上“黄色”的标签,是曲子的幸运
但是,贴上“黄色”的标签并不等于完全的赞誉,也可能只是一次侥幸的旗开得胜。
900年后,再看元祐党籍碑,除了司马光、苏轼等少数几位尚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其余名字早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你一时可以很有名气,但历史会毫不留情地淘汰你。除非你像司马光、苏轼那样,有重量级的作品镇着,才能灵魂不死。今天,知道司马光、苏轼的人远比知道元祐党籍碑的人多。许多人靠名字在刻在碑上才得以流传,而碑自身则是靠上面刻着腕儿级人物的名字才流传。
30年后,在名列《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中的58首中文曲子中,恐怕极少有年轻人听过10首以上。仍为新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只有《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凤阳花鼓》、《大阪城的姑娘》四首。所以,被时代贴上“黄色”的标签,对许多歌曲来说,不是羞辱,倒是幸运。它们得以同《何日君再来》并列于同一本书而流传——否则早被听众遗忘了。
贴标签并不是坏事。一个文艺作品被贴了标签,除开不幸,也有幸运的一面。别人会因此记住这个作品。例如,豆瓣有网友评论我的文章说:“看到如此尖酸刻薄又现实的标题还有作者姓王就知道名字必定是单名一个路字。”我很喜欢这个过誉的评价。上月有网友说某刊转了我一篇日志,却署了别人名字,我为此失落。失落的不是文章被剽窃,而是我的文章还不足以让人一眼认出来。
身为一个文艺创作者,我未尝敢不追求如下的自我修养——它和演员的自我修养相反——如果我的文章被大卸八块,从中捡出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拿到读者面前,他稍读几句,就说这文章一定是王路写的。这样的文章才算得上是我的文章,才是死后可以垫棺材底的。否则只能算是我写的文章,不能算是我的文章。
三、流传10年以上的曲子,背后几乎都是腕
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父亲辛丰年先生是古典音乐发烧友,严锋自幼受古典音乐熏陶,中学时去高干子弟家玩儿,听了港台流行音乐,当即指责别人肤浅庸俗、格调不高。回家后,严锋提及此事,满以为父亲会因此欣慰,不意父亲肃然道:《何日君再来》是好歌,我非常喜欢。后来他才知道,《何日君再来》的作曲者是刘雪庵,父亲粉刘雪庵好几十年了。
来看58首歌曲中至今听众仍有记忆的四首。《何日君再来》创作于1936年,1937年由当红歌星周璇演唱,1939年电影明星黎莉莉翻唱;1978年,邓丽君携此曲杀回华语乐坛。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榜单上58首中文歌曲的魁首。《小城故事》的作词者是庄奴,与乔羽、黄沾并称词坛“三杰”;作曲者是翁清溪,在台湾乐坛被称为“幕后金手指”、“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音乐教父”。《凤阳花鼓》是民歌,在流行前已经有较长的历史渊源了。《大阪城的姑娘》比前三首稍弱,上世纪90年代还有人唱,新世纪之后几乎无人再唱,但寿命也超过了10年。它是维吾尔族民歌,由王洛宾整理,王洛宾有“西部歌王”之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34级的学生。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流传10年以上的曲子,背后几乎都是腕儿!——无论是出自功力深湛的创作大家之手,还是已经身为民歌广为流传,都说明它们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因素,和黄不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一个平庸的创作者,哪怕是搭了时代的顺风车,什么流行就去创作什么,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只能让作品具备三五年的生命力。而真正的经典,或者引领时代潮流,或者不被时代所接纳,但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它一定是纯粹个人的东西。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正是鞭辟入里之见。
四、要裹上流行的外衣,才可能逃脱堙没的宿命
腕儿也是很脆弱的,有才的人很多,有命的人极少。许多极有才华的艺术家,要么英年早逝,要么销声匿迹。
《何日君再来》是刘雪庵的不幸,也是刘雪庵的幸运。刘雪庵创作此曲时,并没有填词,导演方沛霖未经刘雪庵同意,让编导填写了歌词,刘雪庵极为不满,但碍于交情只能作罢。《何日君再来》的歌词的确很平庸。没有哪个自我要求极高的作曲家乐意让自己的曲子为一首平庸的词作配曲。这已是不幸,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期间,因为《何日君再来》谐音“贺日军再来”,并创作于中日战争期间,被定性为“汉奸歌曲”,刘雪庵被划为右派,关进牛棚22年。
刘雪庵实在没有想到这首歌曲让他吃了那么大的苦头。但冥冥之中或许真的自有天意,正是这首让他坐了22年监牢的歌曲成全了他。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而言,最大的不幸不是死掉,不是坐牢,而是作品销声匿迹、灰飞烟灭。比这更痛苦的是,作品并没有失传,但已永远无人问津。让刘雪庵的曲子还能留在世上为人传唱的,正是这首《何日君再来》。
刘雪庵一生创作了无数歌曲,今天只剩下《何日君再来》和《长城谣》稍为人知。《长城谣》也渐渐不行了。《何日君再来》阴差阳错地因误填了一首平庸的词作得以流行,又因流行而流传。
时下流行的东西多半是平庸的,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越是平庸的事物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而高雅永远和时代有隔膜,只能从少数人中甚至异代寻求知己。由此而来的困境是,也许还没有等到和千年后另一个相似的心灵相遇,就已湮没在尘埃里了。例如清代文史大家章学诚,他的议论謦欬之间都是金声玉振,高蹈出尘。今天海内外的汉学论文专著,没有一篇不引用“章学诚”这个名字,他生前撰写了大量著作,却连一本都没有出版。若非后来被发掘,恐怕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里。
反倒是那些披着流行之皮的作品,更易躲过几番劫数,修成正果。
五、一首歌的成功是运气,一百首歌的成功是功力
同是时代的弄潮儿,《乡恋》在当时火得的程度超过《军港之夜》,而30年后,《军港之夜》依然在传唱,《乡恋》却早已显得过时。这一方面因为《军港之夜》是军旅歌曲,军队的时间纪元要比社会上缓慢得多。另一方面也表明,《军港之夜》在艺术成就上并不逊色甚至更胜于《乡恋》。虽然一时风头会被《乡恋》遮掩,但历史会给出一个相对公正的打分。
即便在一首歌上占了胜场,苏小明也不能与李谷一相提并论。苏小明的成名作只有一首《军港之夜》,而李谷一除了《乡恋》还有许多代表作,即使当年《乡恋》被彻底封杀,《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难忘今宵》、《妹妹找哥泪花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歌曲依旧能撑起李谷一的大旗,它们无论在风行程度还是在艺术水准上,都丝毫不比《乡恋》逊色。邓丽君的风行也绝不是凭借一两首歌曲造成的,单看黄色榜单上的58首中文歌曲,仅邓丽君一人就占了近三分之一的阵容,就足以推断出之后的十年必定是邓丽君的时代,邓丽君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八十年代华语乐坛霸主。
一首歌的成功是运气,一百首歌的成功是功力。杨臣刚、庞龙的走红都是运气;而陈奕迅、周杰伦的走红必然是功力。这种功力不是学院派总结出来的技巧和规定,不是咬字清晰唱腔圆润,而是与艺术影响人心的规律暗合。凭运气你可以红一首,但红十首、二十首绝对做不到。即便单从一时流行的尺度上看,慕容晓晓也无法和凤凰传奇相提并论,她只拿得出一首《爱情买卖》,凤凰传奇却能拿出几十首。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足以天才到把同时代的所有对手都打降半级,那么,通过数量取胜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前者是天分,后者只要努力就可以。
六、在艺术领域,一流和三流的界限很不明显
假如你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先去读《红楼梦》的文本,能不能读到第81回时,分辨出来它和前80回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如果你能,说明你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像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天才也许能做到,但很多红学家做不到,更不要说普通读者。一个明证是,第78、79回,有红学家认为出自曹雪芹之手,有红学家认为出自高鹗之手,聚讼不已。这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艺术领域,一流和三流的界限非常不明显。艺术创作者应为此深感恐惧,因为它侵蚀了一流作品存在的土壤。
对普通的读者、听众、观众来说,他们无法辨别一流和三流作品中微妙的高下之分。甚至连腹笥甚丰的学者都难以做到,这是天分,非关学力。红学家“二昌”(吴世昌、周汝昌)交恶,就是因为周汝昌补全了曹雪芹一首佚诗,冒充原作,吴世昌写了上万字的论文论证它的确是曹雪芹所作,后来此事揭破,相当于给吴世昌的红学鉴定水平一个大大的否定。
其实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不入流的作品冒充入流的作品很难,但入流作品之间互相冒充则不易分辨。这就像围棋初段在一盘棋中打败九段一样,并不罕见。《蜀道难》也许只有李白才能写出来,但“故人西辞黄鹤楼”和“床前明月光”无数人可以写出。即便是李白自己,也无法渴求每篇诗都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些必须在适当的年岁、适当的时机、适当的环境才能创作出。二流的作品是艺术家自己的创造,而一流的作品必然是上天和艺术家共同的创造。更何况一流的艺术家本身就是上天的作品。
七、在李志的歌里,《他们》是黄色歌曲,《梵高先生》则不是
在人人都能轻易下载到色情电影的今天,“黄色歌曲”的概念几乎被摧毁了。如果只论色情因素,恐怕唯有云南山歌这种大神级别的歌曲才有资格入选。不过,“黄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除色情因素外,也包括讽刺和反动因素。讽时讥政的歌曲也在黄色歌曲之列,例如高又泰的《根》。“黄色歌曲”的准确定义是带有资本主义毒素的歌曲。今天,第一类“黄色歌曲”几乎绝迹,不过第二类“黄色歌曲”仍然存在,代表人物是李志,代表作是《他们》。
李志往前,可以追溯到崔健、郑钧,他们的“黄色”代表作分别是《一块红布》和《赤裸裸》。但这种“黄色”仍然是第一层意义上的,而且只因词作而黄,和曲子没有关系。如果只看歌词的话,那些歌词和“下半身诗人”沈浩波的新诗比起来,实在算不上黄。因此,从第一层意义上看,“黄色歌曲”的概念已经破产。“黄色歌曲”必须完成从第一重意义到第二重意义的转身才能涅槃重生。完成这个动作的人是李志。
李志歌曲的“黄色”尺度并不比后来某些摇滚乐队和酒吧歌手更大,但李志是一个坐标。1980年代,中国大陆乐坛以民乐和流行乐为主,1989年,崔健推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从此,摇滚乐和流行、民乐鼎足三分。李志的歌曲以摇滚为基调、渐次融合了民谣和流行,至小众而大众,精准地诠释了新一代的文青和愤懑和愤青的孤独。他是当今乐坛的一个另类和反动。此外,他草根出身的身份也影响了后来的酒吧歌手和摇滚乐队。
在李志的歌曲里,《他们》是黄色歌曲,《梵高先生》则不是。但《梵高先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我的意思是,在艺术领域,讽时永远不是绝好的题材。一个艺术家必然要对抗时代,但比对抗时代更为困难的是对抗自身,更确切地说,是对抗自己内心的孤独。
晚清时期,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红极一时,它们可以算得上是第二类的“黄色”小说,但它们的艺术价值远远逊色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黄色”也许会流行,但和经典绝无关系。
讽刺题材的“黄色”作品容易流行,因为它是对大众心理的迎合。换言之,它是对时代的迎合。“黄色”的概念如同“公知”的概念一样,看似对时代的反动,实为对潮流的迎合。他像传销队伍中坐在金字塔尖的人一样,“挟庸众以令诸侯”,把持着话语权。但他只肯趁着一个时代的流弊蜂拥向前,而绝不肯也不敢对抗整个时代的流弊。
如果李志得以流传,一定是因为《梵高先生》而非《他们》。“黄色”作品搭载了时代的风帆,便于顺风行船。但如果跳出时代,从历史的大背景下着眼,“黄色”极不足观。凡是在一个时代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观念,在其后的时代必然会遭遇否定或修正。只有拨开时代风气的迷雾,直击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才有恒久的生命力。
八、耳光乐队的歌是下酒菜而不是酒,是暗讽而不是痛斥
李志往后,“黄色歌曲”有川子的《郑钱花》,万有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耳光乐队的《狼局长十八摸》、《善会长十八难》等。耳光乐队为其中的翘楚。
耳光乐队在摇滚基础上融合了地方戏和曲艺的表现手法,因此能别开生面,与古代的乐府是一类。耳光乐队的作品亮点不在作曲上,乃在作词上。它的主唱即词曲作者赵越鹏是古典文学爱好者,打小迷恋古诗词和地方戏,这也是耳光乐队的词作能超乎时流、卓然自立的原因。
但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狼局长十八摸》、《善会长十八难》并没有超越《郑钱花》和《他们》。其病首先是用典太多。作品用典的幅度究竟该如何,有文学史上的例子为证:汉赋精于用典,许多篇章是作者翻类书查草木鸟兽之名写出来的,有些甚至耗费十年之功,但很快就没人读了,因为太艰深晦涩,同时缺乏动人的感情。与汉赋同时期的乐府,至今仍被人传诵。耳光乐队的作品以时事典故入词,故容易红火,也易遭淘汰。如果不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刷微博的人,恐怕很难明白《善会长十八难》中的所有包袱和典故,对今天的听众尚且如此,更何况以后的听众。相比之下,《他们》的作词则质朴通俗得多。耳光乐队的歌是下酒菜而不是酒,是暗讽而不是痛斥,不如《郑钱花》更易激起共鸣。
用典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作者本人的气质。归根结底,作品是创作者个人风格的体现。李志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悲伤和孤独是极为个人的感受,而耳光乐队的作品则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2010年,李志在某次登台演出时,腰里还挂着一串钥匙链,这种1990年代后期就已淘汰的民工造型出现在李志身上,以至于台下粉丝惊呼“李逼屌爆了”。再看耳光乐队,主唱穿着整齐干净的马褂,把着折扇,不紧不慢地吟唱曲子,与李志的演出相比,一个是品茶,一个是痛饮,高下自见。
九、《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只是多被人看油了,当成了笑料。它和《怎样打飞机》(广州军区司令部,1965)、《怎样养好母猪》(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有本质的不同。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作者都是在音乐界浸淫了一辈子的名家。他们在道德价值的判断上固然难以摆脱时代的流俗之见,但在审美价值的判断上,有着无可否认的深湛功力。因此,把此书当中道德说教的内容刨除掉之后,还是能看出许多对艺术鉴赏相当有见地的论断。例如:“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
如果一首歌没有歌词,只有曲调,一般听众恐怕难以辨认它“黄不黄”,有多“黄”。而音乐修养和功力恰恰在这里体现出来。——这何止是音乐创作上的诀窍?如果把这段话翻译如下:“古龙小说的特点是:篇章上,大量采用动词,白描,带有速度感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与悬念相结合的写法;渲染精致的配角。文风上,大量采用短句,口白式词汇;招数的抽象处理;大量使用直笔与冷峻笔……”这简直就是极好的小说写作教案。
又如:“音乐并不是和黄色的内容表现无关的东西,而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音乐可以替换成美术、摄影、戏剧、小说;黄色可以替换成别的词汇。这实在是很中肯的文艺评论。只是,今天的读者早已不会披沙拣金的功夫了。
此外,我略感不好意思地承认,我认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里的部分评价是对的。书中说《夜雾》、《郎是春日风》这些属于黄色歌曲,我不同意。但说《疯狂的周末》属于黄色歌曲,我同意。它的低俗趣味超过了审美趣味,引诱人放纵身体的程度超过了蕴含的美感。
![[转载]从黄色歌曲谈一代文艺创作者的自我修养(文/王路) 王路 凤凰网](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15049t012ab4b0f2f335eed8.jpg)
对于《畅饮一杯》,我不认为它是黄色歌曲,但我认为它的词很粗鄙,以至于玷污了邓丽君的嗓音和名字。我可以接受“低俗”,但永远无法接受“庸俗”和“媚俗”。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不敢不无条件地反对这种庸俗,庸俗是美天然的仇敌:“哎哟/你们都说我喝醉了/其实我比你们还清醒/哎/哎/假如你怀疑/可问酒保看他会怎么说/哎哟/三瓶两瓶不在乎/我丽君是上打的真海量/哎哟/真海量”。
十、我该为此感到恐惧吗?也许是我太落伍了
最后,谈一谈“黄色”。这个话题无法多说,也不可能说明白。这是道德判断。
在这个时代,手淫早已被视为正当的宣泄,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手淫不再是罪恶、不洁和不道德的行为,理由是它是正常的生理需要。那么,单身汉为了缓解生理需要去招妓或者寻找一夜情是否正当?有恋爱或婚姻关系但长期异地分居的人如此做呢?用陌陌约一夜情或者去酒吧寻找艳遇,是不是可以接受的事情?有人说性和爱的分开是对身体和思想的解放。对于以上种种,我不予评论。在每个时代,必有这个时代可以接受的道德标准,和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此种标准和底线又因人而异。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让我看得有些沉重,难以当成轻松的笑料。当我看到他人智商上的缺陷时,我首先为自己的智商感到捉急。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一个国家如何在短短的30年里,从压抑走向放纵。从本质上看,压抑也是一种放纵,就像忏悔也是一种激情。文革中充斥的血腥和暴力,全民的狂热,正是在极端压抑下的放纵。同样,放纵也是一种压抑,今天许多人沉溺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正是这个时代下人性被扭曲和压抑最直观的反映。
我没有办法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当成因时过境迁而适于嘲讽的对象。我不敢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在思想上和身体上被解放了,更不敢为此感到优越。我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观念上巨大的局限性。并因此知道,我们如同他们一样,价值观也被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我们不能自知。
我从我早已落伍的父亲和祖父身上,看到自身的悲哀。也许五十年后,面对电子产品上的娱乐节目和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会感到难以接受。正如同今天我父亲难以接受我三观不正的文章一样。
最近看《一个》。看到诸如丁楷镔的《少儿不宜》、暖小团的《致前男友的一封信》等文受到热烈追捧,我心中有大恐惧。当年,沈浩波的诗、木子美的书问世,都丝毫没有让我感到害怕。在我看来,他们比沈浩波、木子美要“黄色”得多。因为沈浩波、木子美的黄色明目张胆,直言不讳,大家都能看得到;而他们曲折迂回、暗通款曲,让读者受到了引诱还不自知,沈浩波的“心藏大恶”只是嘴上说说,和他们相比微不足道。我同事的闺蜜是暖小团的忠实粉丝,她对我同事说想有一次未预期的滚床单,可以完全享受而不必为此负任何责任。
我很清楚《一个》这种刊物是时代的风向标,也许再过五年十年,铺天盖地的文艺媒体上的作品都是今天在《一个》上所看到的那种。时代的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地转变而人不自知。
也许,在我们即将老去之前,新一代年轻人眼里,和哥们的女朋友上床、和闺蜜的男朋友上床、和陌生人随时发生关系,如同今天参加同学聚会一样司空见惯,时人也不再因此评判一个人的道德。——我该为此感到恐惧吗?也许是我太落伍了。
我唯一知道的是,作品可以打动人,或让人飞升,或让人下坠。天堂和地狱也许都不存在吧,但是,在一个创作者的心中,它们万分真实,作品正因此才有存在的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