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外科医生,做过的手术不计其数。单是给病人切除的胃,就是俗称为“心口”的那个东西,足够装满一马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例,是一个女人。正确地讲,是那个女人的鼻子。
那时候我刚从医学院毕业,潇洒而热情。眼睛除了观察教授的操作,还关照漂亮的女护士。
“小伙子,我想从教你怎样戴工作帽开始,指导你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教授的目光象双筒显微镜,无遮拦地瞄准我工作帽边探出的那缕黑发。
我的帽子略微有点歪斜,象一个快乐的水兵。教授残酷地剥夺了我的潇洒,从此不得不经典地把帽檐压得很低,以至于使人怀疑我还有没有眉毛。
一天深夜我值班,楼道里突然响起急骤的跑步声。
医院里是不可以随便跑的,尤其是深夜。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了极危重的病人。
急诊室里坐着一对男女。女人戴着大口罩,面目表情不清,端然坐着,双手顺在夹紧的两膝之中,脚尖恭顺地并在一处。那男人千瘪瘦削,眉头紧锁,嘴角翁动,两眼通红,象条被刮掉鳞的金鱼。
我的临床经验尚不十分丰富,一时竟分辨不出谁是病人。
“你……怎么了?”我朝他俩发问。
女人石像似地不动,男人小心翼翼地去解女人的口罩,动作极轻柔。
我终于发觉了一点怪异:那口罩样式古怪,过于平坦……不……不是口罩的问题,口罩很正常,而是……
口罩终于解下来了。我于是犯了一个医生的大忌,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
啊!
口罩下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向外冒着腾腾的白气,深不可测。
我竭力镇静住自己,才想起那被黑洞霸占了的地方,原来是长鼻子的部位。
没有鼻子的人面,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平铺直叙到难以容忍。眼睛没有来由地同嘴靠得很近,两颊不可遏制地向黑洞滑去,只有失去血色的上唇,还象破败的灰墙狙击在黑洞的边缘。
它甚至不如骷髅好看,骷髅骨质洁白,简练合谐。眼眶、鼻准、口颊均为结构对称的洞穴,通畅练达,自成风格。
“这是用什么东西……搞的?”
我急切地想搞情凶器的性质。本想用“剜”或是“削”那种字眼,怕太刺激病人和她的家属,才临时调换为词意模糊的“搞”(护士在一旁紧张地登记,我已知道女人叫小茶,男人是她的丈夫老姜)。
“用刨刃,剃的。推木头的那种。”老姜用目光抚摸着创口,那里边缘清秀。想象得出凶器一定薄利如风。他回答得很清楚,用词也准确。
“是谁干的?”我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这罪行太野蛮大凶残了。
不知何时,教授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问话:“要记住我们是医生,而不是法官。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挽救生命,修补人体。至于其它的事,自有其他的人去售。”
是的。我应该首先处理病人,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是个优等学生,可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上写过:鼻子被刨刃剃掉的病人该如何处置。也许我应该去读法医系,现在只有机械地服从教授的安排。
常规冲洗消毒,就象处理一颗虫牙被拔掉后的窟窿。小茶的脸庞在冰冷的消毒液下凝然不动,波光粼粼带有樟脑气味的液体,轻柔地在凝脂般细腻的皮肤上漫过,使这张一马平川的人面,象收藏已久横遭破坏的蜡制品。
凭心而论,只要躲开脸中部那个巨大的三角形洞穴,小茶的脸还是很美丽的。眼睛象黑杏仁一样,反射出无影灯众多的光斑,如没有月亮的晴朗的星空。嘴有一个极精美的轮廓,象一颗饱满的花生米。
我不禁升起好奇:原来属于这张美妙绝伦脸庞的鼻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种时候想这种问题,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病人家属在一旁长吁短叹,我动作幅度稍大,小茶尚未反应,老姜就吸开凉气了。
“痛吗?”我问小茶。对这永远失去亲生鼻子的年青女人,颇多侧隐,生恐自己弄痛了她。
“一点也不痛。那刨刀是新磨的,很利。嗖的一下,凉凉快快,象雨后的风。”
声音是从嘴和黑洞中一齐发出的,单调、刺耳、尖锐。没有鼻腔共鸣的声音。类似秋蝉或毒蛇的嘶鸣。
我感到沁人心脾的恐惧。不单因为这怪异的声音,更因为小茶脸上那似笑作笑的表情,她好象并不感到痛苦,甚或还有几分自豪。
伤口处理已毕。只要鼻腔切割权部不感染,生命便无妨。作为外科医生的职责,已告一段落。至于以后的事,那是整容医生的范畴。
看来,可以结束了。我用眼睛请示教授,发现他正在观察老姜的手。老姜的手虎口处生着厚厚的茧子,简直象那里多长了一块骨头。只有长年握持某种工具的匠人,才会这样积重难返。
“看来,咱们俩是同行喽。”教授对老姜说,老姜正充满怜爱地看着小茶,被这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几乎是本能地点点头,又立即摇头。
“我哪能跟你比呢?您是修理人的,我是修理木头的。”
“你是个木匠,这么说,这件事就是你干的了?”教授压得很低的白帽子耸起一道粗重的棱。我知道,白布遮掩下的眉毛皱缩起来。
我想教授一定是被这张没有鼻子的女人脸唬得思维混乱。老姜一定得捶胸顿足,因为不仅不可思议,而且近乎诬。退一万步讲,即令真系他所为,也断乎不会承认。
不想,我错得一败涂地。老姜很痛快地回答:“是我。”
也许我惊愕之色过于外露,老姜受了委屈,指着小茶:“你叫她说!是不是我?”
“是哩是哩。你别看他这个样子,真是个好木匠,刨刃磨得最快。冬天若吃涮锅子,让他给刨羊肉片,薄得能透过书上的字。”小茶的声音象急刹车时轮子与水泥路面的尖啸。
这一对男女!吃他们的涮羊肉,只怕自己的鼻子也会掉进火锅。
教授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我没有兴趣。我只想问一下,用刨刃刨下的那个东西,还在吗?”他的眼内充满天真的渴望,象一个企盼压岁钱的孩子。
“在。在。”老姜忙不迭地回答,回头白了他年轻但已经不美丽的妻子一眼:“我说拿上,你说没用了。怎么样,还是我想得周到吧!”声音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骄傲。
事情愈发变得令人瞪目结舌。老姜掏出一个很干净的手绢包,窝在手心,一层层打开。于是我看见一条鼻粱骨朝下的完整的人鼻子。
教授不动声色地翻看着,象在鉴别这条鼻子的真伪。我猜他也感到好奇。没有谁在这个角度观察过人人都有的鼻子。司空见惯的东西,仅仅换一个方位。就变得令人惊诧不已。它玲珑剔透,曲线优雅,就象一件小型乐器。
我们都围过来观看小茶的鼻子,包括她本人。
“我打算把它栽上去。”教授征询地望着我。
人有时候问询别人,并不是为了得到答案,只是要坚定信念。
这是一个玄妙而充满风险的主意。如果栽上去的鼻子感染,不但得象未人活的枯树一样拔出来,而且性命难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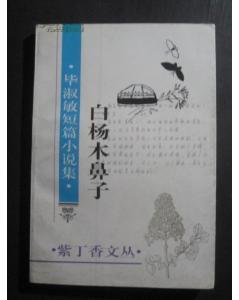
“没有鼻子,除了影响美观,妨碍并不太大。”我委婉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五官之中,除了耳廓,就数鼻子没用了。
“可人是一个整体,人应该是完美的……”教授注视着黑洞说。
“您老若是能给她把鼻子再接上去,我给您老打雕花的五斗柜……”老姜虔诚地央告,一眼瞥见我这个反对派:“给您也打一个……”
只有小茶没说话,仿佛这事与她毫无关系。
“准备器械。”教授简洁地对我下达命令,口气不容置疑。
我们通宵达旦地手术,细节我已记忆不清。我非常想看看那块使我们耗费了如此巨大精力的刨刃,究竟是怎样狞厉而刻薄。一个愚蠢木匠举手之劳,害得我们付出百倍千倍的时间与汗水。教授的技术精巧娴熟,我想任何一个伟大的雕塑家都要甘拜下风。他面对的材料是模糊的血肉,他把所有的血管神经都接洽得天衣无缝。老姜在电光石火般一瞬中的破坏,终于被教授(当然也包括我)惨淡经营地修补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了——将薄薄的表皮缝合到脸模上。我们碰到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合宜的缝合线。小茶的皮肤极细腻洁白,所有的丝线都嫌太黑太粗。
“就这样吧。鼻子能长上去就很不错了,没有人挑剔黑和白。”我的白色手术服下扭动着僵硬如铁的腰颈,长时间俯身操作,即使在无影灯下,我看所有的线条也都成为重影。助手如此,担任主刀的教授,其疲累可想而知。
“如果是这样,她的鼻翼周围会遗有一圈密集的雀斑……不!只差这最后一层,我要完美……尽量完美……”教授喃喃自语。
他摘下自己压得很低的白帽子,露出光洁如月的秃顶,四周还残存着几根银丝般的白发。教授叉开五指,梳理他的白发,平均每个指缝不到一根,他很心痛地迟疑了一下,然后猛地一用劲,把白发拔下来,泡进消毒液。
现在,教授的头颅是大一统了,光可鉴人,显露出巨大的前额和高耸的枕邻。在这两块隆起的头骨之下,是人类智慧最密集的脑叶。
泡在消毒液中的白发,婉蜒伸展,象一条条闪光的小路。
小茶的鼻子被教授的白发,固定在她自己的脸上了。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任何天然的东西,终免不了瑕疵。小茶的鼻端有一粒小痣,其状如一只小小的蚊虫。教授为她做了修正。小茶的鼻子,现在堪称人世问最杰出的鼻子了,造化之灵加鬼斧神工,精妙绝伦,无以复加。
我天天去看小茶的鼻子。它高贵优雅,象浮出海面的一段象牙,闪着晶莹的光润。经过它共鸣过的小茶的声音,柔美动听。
小茶自然很高兴,时常把手掌挡在面前,无端地微笑。只有我知道,她手心里有一片小小的镜子。有时也会把镜片胡乱扔到松软的床上,显出莫名的忧郁。
认识小茶的人,都说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老姜的态度却令人莫名其妙起来。他非但不再提起雕花的五斗柜(当然我和教授都不会接受这种馈赠,但收不收同给不给是两个范畴),而且双眼不时露出凶狠的敌意。对小茶倒是很好。因为鼻子做手术,嘴的活动大受影响,老姜就给小茶包极小的饺子,喂给她吃。饺子只有拇指盖大小,令人想到他做木匠的手艺也一定精良。
这真是一对古怪的男女,我开始打听他们的身世。如果教授知道,一定会斥责我。他是只认病不认人的。我还没有老练到他那种程度,对病和对人同样感兴趣,更不用说拥有这样一只美丽鼻子的漂亮女人了。
事情简单到今人遗憾。好汉没好妻,赖汉娶仙女。不知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原因,年轻貌美的小茶嫁给了丑陋的老姜。姜木匠夜以继日地为人打家具,为小茶添置许多衣物,小茶却不愿为老姜添一个孩子。终于有一天,当老姜手提斧锯外出而归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俊俏的小伙子,正在吻小茶鼻梁上的那颗痣,于是……
这故事远没有书本上舞台上缠绵绯侧,但因为活生生发生在眼前,我还是很关切它的结尾。
“为什么单要剃鼻子?在脸上划几刀不是也可以么?”有人问木匠。
我觉得这问话很卑鄙。小茶那张美妙绝伦的脸庞,若是被乱刀划破,纵是教授再巧夺天工,恐怕也难以完壁归赵,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嘛!
“没有鼻子的女人,比老母猪还要丑。别人不要,我不嫌。家中就太平了。”姜木匠很憨厚地答道。
教授对这一切都不知晓,每天只是很认真地观察鼻子,好象那是他檀下的一株珍稀植物。鼻子很争气,长得结实挺拔,欣欣向荣。我想把小茶的病历整理成资料,投往医学杂志发表。这是外科史上一例罕见的鼻子再植成功病例。
教授摆摆手:“不忙,再看一段时间。医学追求完美,更追求长久。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
鼻子也象家用电器,有保修期吗?我悻悻然,又不得不服从。
小茶出院了。用极清亮极柔美的声音同我们说:“再见。”想起她入院时那毒蛇般的嘶鸣,你会觉得鼻子对于音色比对于美观要重要百倍。
老姜什么也没有说,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好象怕小茶找不到回家的路。
小茶没有再来。连例行的追踪复查也没有来。有人说她的鼻子长得很好,同老姜也过得可以,只是还没有孩子。
我再次想把这病例报道出去,教授依旧不慌不忙:“要注意远期效果。我们一定要亲眼看一看病人的恢复情况,而不要匆忙下结论。”
随时留有充分的余地,也许是成熟医生和实习医生最大的区别。
看来只有哪天到小茶家去一趟了。我一定要看看刨刃,用手指试一下它的锋利程度。
这件事一直拖延着,教授很忙。
一大深夜我值班,楼道里突然响起急骤的跑步声。
医院里是不可以随便跑的,尤其是深夜。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了极危重的病人。
急诊室卫坐着一对男女。女人戴着大口罩,面目表情不清,端然坐着,双手顺在夹紧的两膝之中,脚尖恭顺地并在一处。那男人干瘪瘦削,眉头紧皱,嘴角翁动,两眼通红,象条被刮掉鳞的金鱼。
这是小茶和老姜。
老姜很熟练地解开口罩。
我已经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医生了,终于没让什么声音从嘴里发出来。
口罩下又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切的一切,都依旧。只是黑洞四周有线团样的白丝,随着呼出的气流,旗幡似的拂动。那是教授充作缝线的白发,依然晶莹雪亮,结实柔韧。
“还是用的那个东西吗?”我克制住心中的厌恶、恐惧和愤怒,不愿说出那凶器的名称,尽量平稳地问。
“是。还是上回用过的那种,我觉着挺好使。”老姜恭敬地回答我。知道医生需要了解详情,便努力周全。
小茶什么也没说,象凝固的蜡象。
我点点头,不再询问别的。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救治病人。
教授到了。我明显地看出他踉跄了一下,然后倚靠在一旁,看我情洗伤口。
小茶的脸庞在冰冷的消毒液下凝然不动,波光粼粼带有樟脑气味的液体。轻柔地在凝脂般细腻的皮肤上漫过。老姜象自身受酷刑一般长吁短叹,每当我手势略重,他便不满地重重斜视我一眼。
伤口处理完毕,后来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教授突然按住我的手,犹豫不决地对老姜说:“那个……我说的是那个……还在吗?”
我从未见过学问精深德高望重的教授这般畏葸不前。他面色苍白,目光焦的,双手微微发抖,急不可待又惊惶不安。
“带着哩。带着哩。”老姜显出先见之明的得意之色,从一块油污的纸里,模出一团东西,伸到教授面前。
于是我看见了小茶那条光洁如玉的鼻子——只是它现在类似一个柿饼。也许叫肉饼更恰如其分。血肉模糊、狼藉一片。两个鼻孔蛮不讲理地重叠在一起,象火车失事后的钢轨。唯有教授白发的残根,依旧闪亮如银。头发是最不容易被吸收的物质,人体可以腐烂,头发却依然长存。
“这是什么?”教授茫然地扫视四周,希冀什么人能给他一个回答。他真的不认识这团椭圆形污浊的物体。
“鼻子呀。小茶的鼻子。不信,您问小茶。”老姜耐心地解释,并找出证人。
“那是我的鼻子。”
声音从嘴和黑洞中一齐发出,单调、刺耳、尖锐。却没有悲伤。
“它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教授咆哮起来。全然不顾医学专家温文尔雅的风度和对面墙上斗大的“静”字。
这问题原是不必回答也不能回答的。可惜老姜是很实诚的人,原原本本答道:“是用脚踩的。我用脚后跟在地上碾着踩了一圈。”
这方法的确很地道。它使鼻子的所有微细结构消失在肉酱之中,任何高超的技艺都将望洋兴叹。
“很好!好极了!”教授的白眉毛从帽子里探针般地刺了出来,根根倒立:“那你还把这东西本来给我看什么?!你可以拿它去喂猪,当肥料,扔到坟堆里!可你偏要给我看!我不看!我不认识这东西……永远……不看……”教授的话,开始时气壮如牛,其后却迅速萎顿下去,象行将熄灭的蜡烛,尾声竟带出了呜咽。
老姜愣了片刻,嘴角象被绳扯着,慢慢裂了开来,不知是哭还是笑。
在救治小茶的同时,我不得不同时对教授实施急救。他的心脏在倾刻间衰老,微弱得几乎听不见跳动。
“看来,你的鼻子只能这样了。”面对小茶脸上那个简洁的黑洞,我爱莫能助,用残存的侧隐之心说。
“这样也好。早这样,早好了。”小茶的声音高细单调。
小茶第二次出院了,这一次没有说“再见”。她戴着上下都很平坦的大口罩,远看象是糊了一块白纸。
后来,听说她给姜木匠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听说她依旧戴着口罩,口罩布很白,天天都换洗。口罩也不再那样扁平,丰满地膨隆起来,一如其下有个周正挺拔的端正鼻子。那是老姜给小茶做的,用最白最细的白杨木。春天叶子绿了的时候,走过小茶身边的人,会闻到白杨树的清香。
“可是那白杨木的鼻子,是怎样安到脸上去的呢?”有人问木匠。
“用胶。粘柜橱拉手的那种。”姜木匠并不保守,很和气地告诉别人。
我于是想到我们用过的缝合线,觉得不很聪明。教授绝口不提这件事了。好象它从未发生过。我却始终存有淡淡的遗憾,它是一次那样成功的手术。却永远无法报告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