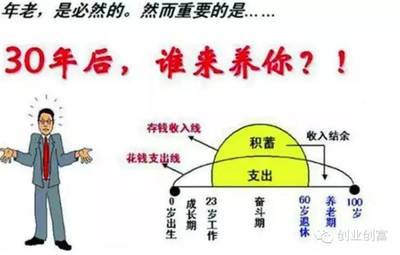图为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先生
张维华死了,终年86岁,算是好寿数。来了讣告,我也去了唁电,其中说“先生在五十年代山大历史系教师中,为具有真正水平之一员”。写着这样的电文,不禁想起了童书业。童死去已19年,终年差几个月不到60岁,真是寿夭之事不可测。1980年我到杭州,童的小女儿童教英同志对我说,“你是先父生前好友,为什么不见写一篇纪念文章呢?”当时我未作答,并非我“语为之塞”;而是要答,需要涉及很复杂的一段历程,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1984年在西安我把情况一股脑对童的老友史念海讲了,史说还是不写文章为好。但不写不写,连我本人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岂不遗闻湮没了吗?因此,还是趁20年忌辰的前夕,把它写出来吧。
童的长婿黄永年写的童传,好几年前就度过了,感到不少形式化的地方。这也不能怪黄,那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打就要打到地,好就要好上天。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运动”,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单这一条,在过去“左”的年代,能写吗?我想有朝一日教英同志读到这里,七年前的疙瘩就可以解开了。
以1955年的肃反运动为例,先是批胡风,接着从党内揪出华岗,慢慢就要深入到本单位的问题了。照例先开一个“吹风会”。记得“吹风会”的主持人是三个:杨向奎、蒋捷夫、孙思白。不久之后,我就是肃反的大对象:可是“吹风”之时,我还侥幸有资格跟若干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听“吹风”。“吹风”的大意是,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其一是张维华,他是美帝的忠实走狗,齐鲁大学的洋人离去时,给他留下埋在地下的几缸金银,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还有一张地图,标志埋缸的方位。我们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张缴出这张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二是童书业,他有血债,他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有检举材料可证。其三是韩连琪,济南解放后他化装成乞丐到青岛去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听了“吹风”内容后我回来对妻子高昭一说,童先生看见咱家杀鸡都吓得捂着脸,他怎么会一夜之间杀死一千个党员呢?
原来事出有因。童跟他父亲的关系,不甚协调。童夫人时常谈起抗日战争时,童的父亲受其妾的挑唆,将童夫妇赶出家门,逼得童夫妇从江南到江北、从江北到江南跑“单帮”生意过活。那时童的鞋底都是大洞,用一把稻草塞住。解放后,童父及其妾住在上海,写信到青岛来,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应该按月给一点赡养费。最初,准备每月给30元,不知怎么一来没有给。上海那边就写了检举信,信在肃反之前早已由市委转下来,贮藏在党委的组织部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徐州解放之前,顾祝同为了勉强点缀升平,发起要邀请一些学者到徐州去讲学。很多人拒绝前往,童书业和杨宽二人应邀前去了。当时使用军用卡车把他二人送往苏北,黑夜之间有不断的枪声,童问这是什么声音,蒋军官兵回答说,“打共产党,我们一夜可以消灭他们千把。”回到上海之后,童是“书呆气”很重的人,不懂得这话的轻重,就把这话传出来了,传来传去,话的主词从蒋军官兵讹成了童本人。童父之妾,就是按这话头写成了检举材料的。
童如何对待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在他们之前被斗,并被宣布为“披着马列外衣、猖狂向党进攻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气氛,远较他们的为盛大热烈。但我心里并不太紧张,因为对我一未抄家,二未隔离,一直让我“逍遥”着,不久,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来青岛以“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的原则,替我宣布了平反。
事情过了很久,已经是运动的“收尾子”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的事。似乎是一个星期天,家里人大部分都出门了,只剩高昭一在家合衣午睡。当时只有我三岁的小女儿赵红从外面偶然跑回家,意外的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她喊着跑着出去找人。后来高昭一也醒了,我也从街上回来,研究的结果,那个跪着的人是童书业。
事情的关键是,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我得悉之后,立刻去找了组织部长高芸昌,高派人到合江路宿舍把童找来,就在组织部组织部办公室内找来一只盆子当着童的面,把供状撕开烧成了一盆灰。童从此才释然了。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与孙思白之间,曾展开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孙认为,我去替童书业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但我不以为然。任何人,任何人的性格、品质,都是跟他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在“左”的路线下,一次次运动的架势,真是吓得死人。前文表述过,童是个“怕”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到神经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血债”,不够他发疯的吗?这是被扭曲的第二回。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童写那样的《供状》是好的、应该的。童在平时经常对我谈,一个变态心理的人制造的谎言和假相,往往是最精致的。可是他究竟还是在长达数万言的《供状》中并未遗漏下连他自己也是其中成员之一的“坦白”。存心害人的人,是光害别人,绝对不害自己。而他既害别人,也没有忘记了害自己,这是他“精神病”、“变态心理”的铁证。法律不是规定,有精神病的人,杀了人也是不判死罪的吗?根据这一点,我对童采取的是谅解的态度。
童在生前经常给我讲弗洛伊德,我腹内所存的一点有关弗洛伊德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似乎弗氏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他有时对别人是“施虐狂者”,有时对自己是“施虐狂者”,但最终点上却是个“受虐狂者”。这话高明极了,并且完全可以适用于童书业。试看长达万言的《供状》一案,到头来还不是害了自己吗。再举一例。有一年,咱们大陆方面宣传蒋记要反攻大陆,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紧张到控制不住了,他去找当时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是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比小孩还幼稚。可是不久,“受虐”的时机很快到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童书业的第一张大字报上写着“童书业有变天思想”、“童书业借反攻大陆妖艳恫吓党员干部”。想来,光这两条就够他受得了。
我和童的交谊,建筑在三件事情上:一、谈学问;二、看京戏;三、品画。
童书业最爱谈学问。谈到高兴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管听的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他一直谈下去,谈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但谈起学问来就什么都不怕了,因而造成过小事故,有时迷路,有时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厌烦地谈学问,径直撵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听他谈,所以他认我二人为终生好友,一到周末或星期天,就一定到家下去。我家的饭并不特别好吃,个别菜的烹调技术距童夫人远甚。但他恋着谈学问,就到处宣传我家的饭如何好。童在吃东西方面也有怪癖,如裸露的肉他是绝对不吃的,吃了就吐出来;但包裹起来的肉他却大口大口地吃,这不是“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倒是见其形不忍食其肉的“仁者”了。我们就顺着他,把肉用面糊、豆腐皮或茄皮、瓠片包夹起来,做给他吃。吃完就谈,吃是次,谈是主。他谈的,都是治学中新收获的萌芽,或者说,是一些论文未成形前的毛坯。并且在这里又须加一笔,童有时很傻,但有时有很精。例如,他跟一个人谈过某个他自己的“精义”,过些时候这“精义”不知不觉被摄入该人的论文中去了。从此,他就再不到这家去谈学问;我们问起来,他只把眼睛弯成娥的眉那样眯眯地笑着,不出一语。再者,他总有一种偏执,认为我夫妻二人接近革命早一步,接触马列早一步,而他晚一步,从而对我们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信赖,仿佛我们听后没有认为大谬的论点,就是可以站住脚的了。其实,这是十分靠不住的,我们自己的许多论点后来不都变成“反动透顶”了吗?
当时有四个人是京戏迷:杨向奎、卢振华、童书业和我(我妻因脚有湿气不能常去。)大家一起去,互相请客。童听戏,也有他的怪癖。第一,他不听票价高的戏,如梅兰芳2.8元、马连良1.8元、张君秋1元等,他都不听。原因之一,怕是夫人卡得紧。(有一次,他跟我一起从合江路宿舍到大学路去上课,他花5分钱买了一包尖底纸包的花生米,倒给我一半,一面吃一面唠唠叨叨地说“连剃头加吃花生米,才给我发5块钱”)他只听东镇一家小剧院门票3角的戏。第二,在一夜3块或4块的戏中,他有他的选择。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黄慢板时,我们三人都眯起眼睛听得入神的时候,童却不见了,他到吸烟室休息去了。等武打戏一上场,什么《龙潭鲍骆》,什么《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他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诉我,听了这样的戏,他的精神所得到的恢复,要比睡过一场好觉或者接受一次休克治疗要强得多,明天的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我专门去听他那一堂课。有时,联系龙潭鲍骆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宋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意气风发了。
童书业是历史学家,此外,他还兼备画家和画论家的身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他早年习过画,卖过画,还专门到北平跟胡佩衡学过。他画山水,路子是四王。他仿过王石谷,也仿过戴醇士。他自己说,仿石谷达不到乱真,仿醇士完全可以乱真。他说,旧社会有做假画的集团,谁着墨,谁上色,谁题字,谁刻图章,谁把新画来加旧,谁上裱,都有专行任务,赚了钱大家分。有时,眼看着自己参与制造的伪品,连社会上最著名的鉴赏家的眼睛都骗过,使那人连连表示珍赏的时候,他都笑不敢笑出来,只好憋着。但说来可怜,他家纸笔墨砚一概不备,只有正月初一到黄公渚家拜年时,借黄家高档的画具设备,才即兴给朋友们画一两幅。
当时解放不久,诸城一带大官僚大地主家里的字画,在扫地出门时成了贫雇农家的胜利果实,一转手二转手到了青岛来卖。此外,青岛是德日美三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许多先朝政客,如今失意了,都愿到青岛来当寓公,老一辈死后,少一辈就把所藏书画也拿到店里出卖。所以50年代前半段,在青岛市面能见到的字画比较多,价钱比后来也便宜不少。童是从来不买画的,但是我买,买来之后挂在墙上,由童来品评。他的品评,带专家气息,也带偏执气息。他往往不从画法、纸色、绢色、墨色、题款、用章、藏章诸方面的综合情况上取下判断,而是单打一,根据某年某地他见此画家有某种画法、笔法为理由,判断与此画法、笔法极类似的一幅画为真品,而判断与此画法笔法迥不类似的一幅画为赝品,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误差往往很大。所以在当时青岛的卖画、买画、品画的人们当中,他的品评不太被人重视,理由是他的观点太偏执了。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童已经支持不住了。我听说,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们拔草时,大家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准许两个人带板凳,一是冯沅君,因为她是小脚;二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后来我问杨向奎是否如此,杨说,“哪里?!板凳已坐不住了,是躺着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拔。”有一年在杭州郊外,我见到童太太,我问童先生是怎么死的。童太太说,她也不知道。她问医生,医生说“他的肺没有了”
王仲荦告诉我,当童的噩耗传来时,一位讲师的夫人在阳台上说“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现在这位夫人的丈夫也已上了教授职称,照我看这批人民币也不能亿万斯年地领取,有朝一日也会像童书业名下那笔人民币一样被节约下来的。(选自《赵俪生文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