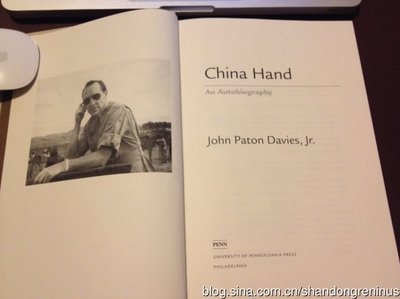1.我是一个有病的人。
舍斯托夫曾经这样评论:《地下室手记》“不仅在俄罗斯文学,而且在世界文学中,都是一部最有名的作品。”(注一)在我看来,也许应该说它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并且,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人类哲学著作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此,它才能被视为存在主义最宝贵的文献之一。罗赞诺夫说:“《地下室手记》的每一行都是重要的,几乎不能把它归结到通用的公式里;同时,任何一个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去讨论其中所发表的见解。” (注二)
1864年,《地下室手记》在俄国出版,二十三年后,尼采看到了该书的法译本,他异常兴奋地说:“一种血统本能(否则我何以名之)直接呼叫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注三)
罗赞诺夫认为,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并且最详细地批评了这样一种思想,我将其概括为理性专制主义,这种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即借助理性建立人类生活的如此完善的大厦,以便它能给人以安慰,结束历史,根除痛苦。对这个思想的批判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注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是以反思人开始的。
“我是谁?”这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首要问题。古希腊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那么,我到底是谁?《地下室手记》一开篇就问了这个大问题。
“我是谁?”答案:“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注五)
“病人。”对人的这个定义令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福音书,那上面记载了耶稣的一段话,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罪人,乃是召罪人。” (注六) “病人”与“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明白地说,但看他的整个小说,他所谓的“病人”,就是“罪人”。
《地下室手记》的开场白是“我”的大段自白,其实,整个《地下室手记》,就是“我”的自白书: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是一个不漂亮的人。我相信我的肝脏有病,但是,关于我的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我体内骚动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请教医生,绝不——尽管对于医药我有某种敬仰。再者,我极其迷信,非常迷信以致敬仰药物(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致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拒绝请教医生是出于恶意。这,或许是你不懂的。好,就让你不懂。当然,我无法解释这种恶意所伤害的究竟是谁,我十分了解,不去请教他们并不就是‘惩罚’了他们。我也十分了解,这样做除了自己之外,伤害不到任何人。但我仍旧由于恶意不去请教医生。我的肝脏很坏——好,就让它坏下去。”(第23至24页)
为什么说这个“病人”就是“罪人”?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不仅肝脏有病,心里也有病,这个病的名字叫“恶意”。“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恶意”,这就是“罪”。耶稣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注:有古卷在此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注七)在人里面的,在人心中的这些恶念或者说恶意,就是“罪”。
但正像一些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专家所看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双重视力的人,他除了那一双的“天然眼睛”之外,还有一双“超自然的眼睛”,这双“超自然的眼睛”使他能够直视人的心灵,看到人心中不为人的意识自觉到的深层的心灵活动,包括超理性的活动和下意识的活动。并且,在精神的一切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看到了正面,也同时看到了反面,不仅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更看到了“生就是死,而死就是生”。(欧里庇得斯)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断地解剖或者说述说“我”的心灵,并且是用相反的话来述说。于是,刚刚承认自己“心怀恶意”的“我”,立即又说:“我根本不是一个恶意的人”。
“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恶意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好,整个的症结,真正的毒针所在的地方,使我不断的,即使在真正发怒的时候,内在里仍然羞耻地感觉到我根本不是一个恶意的人,甚至连刻薄都够不上,我只不过是随便吓唬吓唬麻雀,并以此自娱。” (第24页)

“刚才当我说我是心怀恶意的公务员,我是在扯谎,我扯谎是由于恶意。我只是用那些请愿者和那个军官来取乐自己。事实上我无法使自己成为心怀恶意的人。每一刻我都十分清楚,在我心里有许多因素与这个互相冲突。我感到它们在我心中我心中嗡嗡作响——这些冲突的因素!我知道它们在我心中嗡嗡作响已经整整一生,它们要找一个出口,但我不让它们,我不让它们,我有意的不让它们。它们折磨我,直到我感到羞愤;它们驱使我,直到使我痉挛——折磨我,到最后,是何等折磨我!好啦,先生,现在你以为我表现某种忏悔了,以为我要要求你某种原谅啦;我可以确定你会以为如此。。。。。然而,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根本不管你以为什么。。。” (第25页)
简单地说,恶意与善意,不在彼岸,只在“我”心。它们彼此冲突,相互敌对,并且从生到死,一直争斗不息,这就是一场无声的战争,战场就在那看不见的心灵的深处,敌军与我军都是我自己,不过一个是善意的我,一个是恶意的我,这两个“我”同居一室又彼此反对,“我”反对的正是我自己。保罗这样描述这场战争:“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注八)
“我不仅不能变成心怀恶意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变成任何一种东西。。。。。不懂如何恶意,不懂如何仁慈,不懂如何成为无赖,也不懂如何做老实人;不懂如何成为英雄,又不懂如何做得个虫豸。现在,我就在这个角落里生活,以这种恶意的无用的自慰来嘲弄自己:一个聪明人决不会一本正经的把自己弄成任何性质所确定的东西,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是的,在十九世纪作一个人,必须并且非常应当非常显然的成为没有个性的生物;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性质确定的人显然是受限制的东西。这是我四十年的信条。现在我四十岁,四十岁,你知道,是整整的一生;四十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比四十岁活得更长,是颟预的,卑鄙的,不道德的。活过四十岁的是些什么人?回答我,要诚实。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蠢货和臭皮囊。我对着所有的老年人讲这个话,对着他们的脸——所有可敬的老年人,头发银白,可敬的老者!我对着全世界的脸讲这个话!我有权这样讲,因为我自己要继续活下去到六十岁!到七十岁!到八十岁。。。好,让我喘一口气。。。” (第25至2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人性固定化,确定化。人性不是一个物体,不是山川,不是河流,也不是飞禽走兽。人性不是“任何一种东西”,不是“任何性质所确定的东西”,人性,个性,这一切都在生成之中。显然,这样的思想与时代潮流相反对,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要求的恰恰是人要成为并且必须成为没有个性的生物。但是,人要成为一个自己,如祁克果所说,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人。
2.几乎每一种意识都是疾病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几乎就成了时代的旗帜。人们以为思想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而人则成了思想的动物。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并且,用精细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如何从我思中得出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我”的口,将这种时代病概括为“意识太多”。从《地下室手记》第二章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尽管我想变成一个虫豸,但为什么我不能变成一个虫豸?
“我” 说:“曾经有许多次我确实想变成一个虫豸。但连虫豸我也不配。先生,我可以发誓,太多的意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为了日常的生活,通常的意识已经足够。” (第27页)
“每个人都如此;每个人都因自己的病觉得骄傲,而我,或许比任何人更甚。这不用争论,我的论点当然是荒谬的。然而,我仍旧相信,大部分意识——几乎每一种意识——事实上都是疾病,我固执的认为如此。但是,让我们把这个话也暂时摆在一边,告诉我:为什么在我最能够感受一切精美的事——如人们所说,每种‘美与善’的事物——时,就正正在这个时候,似乎设计好的,我不但会感受到最可恶的事情,甚至会作出最可恶的事情。。。诸如,好,诸如我所做过的一切,而这些事情,似乎有意的,发生在我明明知道不可让它发生的时候,我越是意识到善,以及一切‘美与善’的事物,越是沉陷在我的泥淖,并且准备完完全全投进去中,而最糟的是这些事情之发生,对我并非偶然,而似乎是命定,似乎那是我最正常的状态,根本不是疾病或堕落。因此,到最后,当我内心对这种堕落挣扎的欲望过去了,结果我几乎相信(或许真正相信)它是我正常的状态。但起初,一开始,这种挣扎给我的苦难是何等严重!我不相信别人也是如此。我把这件事当作秘密,终生隐藏在心里。这种事情是我羞耻(即使是现在或许我还在羞耻):在某个可厌的彼得堡的深夜,返回我角落里的家中时,我感到一种秘密的,不正常的,卑鄙的快乐,强烈地意识到这一天我又做了一件可恶的事情,并且意识已经做的永远无法不做,内心里秘密的为了这件事情啃噬又啃噬自己,撕裂腐蚀自己,直到最后这种辛辣转变成一种可耻的令人咒诅的甜蜜,而最后——变成真真确确的响了!是的,变成了享乐,变成了享乐!我坚认如此。我说这个话是因为我一直想知道别人是否也感到同样的享乐。我可以解释:这种享乐,正是来自对于自己堕落之过度浓烈的意识,意识到自己已经推至极限,意识到它的可怕而又别无他途;没有道路可供你逃脱;你永远不能变成另一个人;即使有时间有信念去变成另一个人,你还是绝对不愿意去变;或者如果你愿意,你仍旧一步也不肯走;因为事实上或许没有什么好让你去改变的。” (第28至29页)
人生命中最深刻的奥秘就在这里:就在人最能够感受一切美善的事物的同时,人不但会感受到最可恶的事情,甚至会作出最可恶的事情,而且,这两种感情可以同时并存在一个心里!而且你自己的意识清楚地告诉你:你正在做的事是一件可恶的事情。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们通过不同的途径鼓吹人性本来善良,人之堕落是由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否定的正是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善与恶同存于一心之中。更有甚者,在人自以为是善的意念之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觉到的恶,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这一声叹息,正是灵魂深处最悲恸的叹息。
但令人无奈而又十分可悲的是:这种堕落对人并非偶然,而似乎是命定的,它成为人生存的最正常的状态。人根本就不把它看成是疾病或堕落,他相信那是人的正常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没有使用“原罪”这个概念,但他表达的正是人的“原罪”,换一句话说,人的存在命定是在罪中存在。问题在于,人并不把罪当成是罪,他反而以为那一切都是正常的!他甚至以此为乐。人到底有多么堕落,人之堕落有多么深,以此可见一斑。
“而最坏的是,这一切坏的根源,在于它们同锐利意识的基本常规相合,与这些规律直接而来的性格相和,而最后,一个人不仅是不能改变,甚至是绝对没事可作。于是跟着来的,成为锐利意识之后果的,是一个人并不因自己做了无赖而背负责任,似乎当他认清了自己确是一个无赖之后,他就得到了某种慰籍。” (第29至30页)
3.去了解所有的不可能性以及石头墙
《地下室手记》第三章叙述了另一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直筒子和实行家”:“这种先生只是简单的向目标冲过去,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把角俯得低低,除了一堵墙之外,是什么也阻挡不了。” (第31页)
“我”认为直筒子和实行家是真正的正常人。“这样一个直筒子我认为是真正的正常人,是他温柔的母亲——自然界——仁慈的把他生到地球上来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我嫉妒这种人直到脸色发青。他是蠢货。这个我不想争辩,但或许一个正常人必须是蠢货,你怎么能否认?事实上,这或许是极美的事。” (第32页)
直筒子和实行家与“一个有锐利意识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个有锐利意识的人,“由于他一切夸张的意识,他确确实实以为他自己只是一个耗子而不是人,他可能是一双有锐利意识的耗子,但是,他仍旧是耗子,而另一个却是人。而最糟糕的是他自己,他原原本本的自己,把自己看作一双耗子;没有别人要求他如此,这是重点所在。”
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着一段的时候是否知道或者想到进化论,但他写的的确太妙了,如果把“耗子”,换成“猴子”,或者,所谓的“类人猿”,那就成了他把自己看作一只猴子。高级一点,但终究是猴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描写这种具有锐利意识的耗子是如何采取复仇行动的:他的心中纠缠着一大堆卑下而有肮脏的欲望,除了这“基本的肮脏之外,这只不幸的耗子又围绕着它创造了许多的肮脏的问题与怀疑,把一个问题附加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因而无可避免地围绕着它搞出了一种要命的泡沫,臭不可闻的藓苔,以及由那些直筒子和实行家啐在它身上的轻蔑。。。留给它唯一可做的事是用爪子挥一挥,把一切念头驱散,然后带着一种自己也不能置信的,矫作的轻蔑微笑,屈辱地爬进他的耗子洞去。在它肮脏的,臭烂的地下室中,我们这位受了屈辱的,被欺压了的,被玩弄了的耗子,立刻陷入冷酷的,歹毒的,以及——最要紧的——永恒的恶意之中。” (第32页)
与之对应的是直筒子和实行家,“当他们遇到了无法通过的事情,却立即收卷尾巴。无法通过的意思就是石头墙!” (第32页)
作者要突破的就是这堵石头墙,这石头墙是阻绝人类心灵与上帝相通的巨大障碍。
“什么样的石头墙?当然是自然律,是自然科学的演绎,是数学。比如说,当他们向你证明了你是猴子的后代,那么,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你只能把它当作事实接受。当他们向你证明了事实上你身上的一滴油要比你的同伴的十万滴还贵重,而这个结论是一切所谓道德,责任以及诸如此类的偏见幻想等等的最终解释时,那么,你只能接受它,这是毫无办法的,因为二二得四乃是数学定律。不然你反驳试试看。
我的老天!但是当我为了某种理由而不喜欢这些事情以及二二得四的时候,我管他什么自然律或数学律。当然,如果我确实实力不够,我是不能用我的头把它撞倒的,但我并不因为它是堵石头而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把它撞倒就与它妥协。” (第35页)
对!决不妥协,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他知道得很清楚,什么自然律,客观定律,历史必然性,理性,都是被时代奉为神明的,但大家都相信它们对,他们就真的正确吗?不!它们“只是一个面具,是一个戏法,是一个牌戏的骗局,它只是一个谜团,既不知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知它是什么人。” (第36页)
因此,要拒绝妥协。要“去了解所有的不可能性以及石头墙;去认清如果与不可能性及石头墙妥协你感到厌恶,你就不要同它妥协。” (第36页)
4.用头去撞一座石头墙:二二得四。
“我”寻找行动的基石,寻找将自己的心灵奠基于其上的第一因,他说:“何处是我的基石?我从何处去得到它们?我在反省之中前思后想,结果是每一个第一因,从它自己身后又对我抽出另一个第一因,如此反复至于无穷。这正是一切意识与反省的本质。这又可能是自然律。结果怎么样呢?好,结果还是一样。”(第41页)
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它不断地超越自身,它永远也不可能在其自身依靠其自身而确立第一因。理性之所以不能成为人的精神的国王的原因也正在这里,理性可以把自身作为一个对象而不断地超越其限制。
当代人把科学,理性,自然律,历史必然性至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寻找第一因的替代品。但“留给你的只有那同一条出路——用尽全力握紧拳头去捶打你那堵石头墙。最后你挥一挥手,只好把它放弃,因为你根本找不到第一原因。或者,你可以试图让自己被情感牵着鼻子走:盲目的,不要反省,不要第一原因,至少暂时把意识压下去;恨也好,爱也好,只要你不交臂而坐。但是,至多到第二天,你就开始为你的明明自欺而蔑视自己。结果是:肥皂泡以及倦怠。” (第42页)
与理性相联系的是利益。这是一幅现代的神话:利益是人行事的根本推动力,只要满足了人的利益,就可以在人间实现天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笔下的“我”问:“请你告诉我,是谁第一个这样宣称,是谁这样第一个发布:人之所以作肮脏的事,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假如他得到启发,假如他的眼睛开向真正的利益,他就会立刻停止做肮脏时,而变为高贵善良。” (第44页)
“我”继续告诉你:“第一,这整整数千年,有没有一个时期人类仅由自己的利益而行事呢?上百万的事实,证明了人有意识的,即是说,完完全全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却把它丢在背后,急急忙忙冲向另一条路,去迎接危险与毁灭,不是被任何人任何物所逼迫,而仅仅因为他厌烦旧路。他顽固的,有意的打开另一条荒谬而困难的路,几乎是在黑暗中去追寻它,因此,我想,这种顽固与乖僻恐怕要比任何利益更使他高兴。。。利益!什么是利益?你是不是想自己扛起这个责任,用更完美确切的字眼来界定人类的利益究竟包括什么?有些时候,人的利益,不仅是可能,甚至必须包括在对他有害的事物的渴望之中,而不在对他有益的事物。设若如此,设若有这种情况,那么整个原则则就碎成灰烬。你以为如何——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笑,好,去笑你的,不过你要回答我:人的利益可否用完美的确切性来计算呢?有没有某种东西不但是从来没有被任何分类所包括,而且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分类所包括?”答案是,当然有。无论这利益是繁荣,财富,自由,和平以及其他,但仍然有人会不顾一切地违反它。(第44至45页)
“我相信人的最佳定义就是忘恩负义的两脚动物。然而这还不够,这还不是他的最坏的缺点,它的最大的缺点是它永恒性的德性偏斜。。。结果是善意的缺乏。” (第55页)
利益,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切,都是无法定义的。什么是利益?这是一个问题。好了,就算这个问题是自明的,大家都知道利益是什么?或者说,这种利益是由数学公式精确地计算好的,并且实施这个数学公式的步骤也都设计好了,预备好了,大家在理解了自己的正当利益之后也都按照会这些数学表格而行动,一切都将必然的发生,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一切都被计划好了,生活还剩下什么?生命还有什么意思,人又算做什么?人,不就不但成了机器,而且要像机器一样地运转吗?尽管推动这部机器的不是汽油或者电力,而是什么利益。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假如一切都设计好了,都列好了表格,还有什么可做呢?” (第48页)
其实,就算你能精确地算出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你如何保证人能够根据这个最大的利益去行动?没有任何保证。就算你告诉他这是一条路,唯一的正路,但是,他偏偏不走,他要走自己的路,他要自己走路,你有什么办法?你可以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说你不走这条路就把你枪毙了,于是他跟从你了。但那究竟是“利益驱动”,还是求生本能,怕死的本能在驱动,还需要说吗?
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利益,有些利益是彼此和谐的,有些是彼此对立的。对于某些利益,即使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但是,少数人为什么必须服从它,少数人可以说:这是你们的最大利益,不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不,这不是我的最大利益?如果要他顺从最大利益,以他不喜欢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他自己着一个人的最大利益,除了强迫之外,还有什么出路?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神话正与多数人的暴政直接联系在一起。它剥夺的正是人的自由,不论用的是什么名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我” 感到“最令人吃惊的乃是:为什么一切统计学家,圣人,人性的拥护者,在核算人类利益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的把其中一项遗漏?” (第46页)他自问自答:事实上,“对一切人而言似乎真正有某种东西比他最大的利益还要亲切,或者说(免得违反逻辑)有一个最有益的利益(就是我们刚才忽略的那一个),它比一切利益更为重要,更为有益,为了它,如果必要,一个人会甘愿违反一切规律;这就是说,违反理性,荣誉,和平,繁荣——事实上,为了这个比一切更亲近,更基本,更有益的利益,它可以违反一切漂亮而有益的东西。‘是了,’你说,‘毕竟他还是利益。’但是,请你原谅,我要把话说得清楚一点,这并不是我在玩弄字句。事实是,这一种利益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的一切分类,并且持续地粉碎人性的拥护者为人类的利益所建构的每种体系。事实上,它颠覆了一切。” (第46至47页)
它是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它是任性。是选择。是自由意志。
“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个人,不论他是谁,他总喜欢按照他选择的方式行动,而丝毫不愿依照理性与利益。然而,人不仅可以选择与他自己的利益完全相反的东西,有时甚至确实应当(这是我的想法)。无拘无束的选择,自己的任性(不论何等放肆),自己的幻想(不论何等疯狂)——这就是我们所忽视的‘最有益的利益’。它不能归入任何分类,但任何系统与学说碰到它都会一成不变的粉碎无余。为什么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会以为人类需要正当的,德性的选择呢?是什么事情使他们认定人必然会寻求理性上有益的选择?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独立的选择,不论这种选择需要付出何等代价,也不论这种独立会把它导向何种方向。不过,当然,什么是选择,只有鬼知道。” (第50至51页)
自由,这就是人性的基础。剥夺了人的自由,就是剥夺了人的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的正是以理性,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取消人的自由,让每一个人都听从理性的引导和指示,按照科学的方法改变人性,一切都按照依据理性,科学,历史必然性设计好了的康庄大道前进,(而理性,科学和历史必然性掌握在谁手里,谁发出指示,这些可以暂且不去管它们,尽管那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就让我们前进好了。但那样的日子,还叫日子吗?这样的人,还算是人吗?
5.人终究是人,不是钢琴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是人,是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是不能放进一个数学公式的。 “如果有一天发现了我们一切欲望与任性的公式——这就是说,它们依据什么,它们如何升起,如何发展,在某一状况它们的目标如何,另一状况又如何等等。这当然是一条真正的数学公式——那么,很可能,人会立刻停止感到欲望,实际上,他一定会如此。因为有谁会依照公式来选择呢?更且,他会立刻由人转变为一个风琴拴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因为当人不再有自由的欲望及选择,他除了是一个风琴拴还能是什么?” (第51至52页)
当人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他也就无任何自由可言了,于是,人就成了机器,或者,钢琴键,风琴拴。
人们经常说,我们的选择之所以陷入错误,通常是由于对利益的错误看法。理性可以帮助人权衡利弊得失,使人对利益形成正确的看法。这个论点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人的行动是受头脑支配的,而人是理性的动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这种简单化的理性主义说:
“先生,理性是件很妙的东西,这是不用争辩的,但理性终究只是理性,它所能满足的指示人的理性面;而意志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白,这就是说,包括理性与一切冲动的整个人类生命。我们的生命,在它的表白之中,虽然是没有价值,然而它仍是生命而非开出来的平方根。现在,比如说,很单纯的,我要活下去,这是为了满足我生命的一切官能,而不只是要满足理性,这就是说,不只是要满足我生命官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所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它所知道的仅是它所以学习到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可能永远学习不到;这很糟糕,但为什么不坦坦白白承认?)而人类的本性却是一个整体,它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与它里面的一切因素共同行动,而即使它走错了方向,还是活下去。”(第53至54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理性主义永远也无法解释的,这就是人们有时执意要做蠢事和傻事(聪明人会说),异想天开的事(在讲究实际人的心目中),毫无意义的事(在别人看来),不值得或者得不偿失的事(以计算之心来看)。“有一个状况,仅有一个状况,人们有意识的,蓄意的欲望与他有害的事物,欲望愚蠢的事物,最最愚蠢的事物——仅仅为了取得欲望愚蠢之事的权利,而不愿被拘束于仅仅欲望明智之事的束缚之中。当然,这个最最愚蠢的东西,这种我们的任性,先生,事实上很可能比世界上一切事物对我们更有益处,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特殊之点是当它很明显的对我们有害,很明显的违背我们的理智的时候,它仍然可能比一切的利益对我们更有益处,因为不论外在情况如何,它为我们保存了最珍贵最紧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个性。” (第54页)
正是如此,献身爱情,献身正义,献身科学,献身于美,献身真理,都是证明。没有自由,就没有个性,没有人格。历史正是如此说明的。
“你可以用任何字眼来形容这个世界的历史——一切能够进入你得乱七八糟的想象之中的东西都可应用,唯独不能用‘理性’来形容它。这两个字刺在你的喉咙里吐不出来。” (第56页)
“即使人真的仅仅是一支钢琴键,即使自然科学与数学一起向他作此证明,他仍然不会变得理性,却要做出一些乖张行为——仅仅因为忘恩负义,仅仅是为了贯彻他自己。设若他找不到方法,他就会制造毁坏与混乱,会发明一切样式的折磨痛苦,以便贯彻他自己!他会向全世界发动诅咒(这是他的特权,是人与其他兽类的首要区分住走),他可能因他的诅咒而达到他的目标——这就是说,他让自己相信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假如你说,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被计算出来并列成表格——纷乱,黑暗以及诅咒,以及仅须事先对它加以计算就可把它制止,理性重而可以重新肯定自己——如果你这样说,好,人可能就会蓄意的发疯,以便把理性赶出去并贯彻他自己。这是我相信的,我可以为这个话负责,因为人类整个行为似乎都包含于,且仅仅包含于此一事实:不断的,每分钟向他自己证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这可能要以他的性命为代价,可能以互相残食为手段。” (第57页)
人终究是人,不是钢琴键
“如果我们变成表格化及数学化,如果一切都成二二得四,自由意志又算什么东西呢?二乘二不用我的意志还是得四。” (第58页)
近代人又一个梦,要改变人性。无论方法是理性,科学,教育,还是革命,虽然方式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相同的:改变人性。他们如此巨大的信心依据两个前提:第一,人性是可以依靠人自己而从根本上改变的;第二,存在着某些改变人性的客观规律(数学公式)。从此出发,这些人立志“要医治人们的旧习惯,并依照科学与善意来改革他们的意志,但你怎么知道,以这种方式改革人类,不但可能而且值得?究竟什么东西使你认定人类的倾向需要改革。总之一句话,你如何知道这样一种改革会对人有益?把话说到底,你怎么会如此确信理性与科学,认为由它们作保不违背人类正当利益的行为,就真正必定有益于人类,并且是人类的一种定律呢?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你的设想。它可能是逻辑定律,但不是人性定律。” (第58页)
“我承认人很明显的是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意识清楚地为一个目标挣扎并从事工程事业——这就是说,不断的并且永恒的去开创新的道路,不论它导向何方。” (第59页)他很可能就“像玩棋子的人,只爱棋戏的进行,却不爱它的结束。而谁又知道(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人类在世间所挣扎获取的唯一目标不就是这种无休止的获取过程而非所获取之物?这种获取过程用另一种说法,即是生活本身,而获取之物乃是生活的结果,可以用公式加以表达,其确定性就如二加二得死;然而,先生,确定性却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之死亡的开端。”(第59至60页)
人是一个创造性的动物,他注定要不断地创造。没有任何自然律可以阻挡它。
“事实上,人是一种滑稽的东西,似乎在它的生命中秉具某种玩笑的成分。然而,无论如何,数学的确定性仍然令人无法忍受。二二得四对我而言似乎仅是一种骄横的东西,二二得四是一个无礼的纨侉子,两手插腰而站,挡住你的去路并吐口水。我承认二二得四是很漂亮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给每种东西应得的价值——二二得五有时也一样很有魅力。” (第60至61页)
“谈到利益,难道理性不可能是错误的吗?人除了爱安宁幸福之外,难道不可能爱其他的东西?他是否会同样爱痛苦?痛苦是否可能与安宁幸福对他一样有利?人有时出奇的,热烈的喜爱痛苦,这是一个事实。” (第61页)
何止是爱痛苦,人还可能爱邪恶!魔鬼不正是在人心之中吗?破坏性与建设性,都存在与人性之中。在人性里面,善与恶并存,生与死同在。
“我想人类永不可能放弃真正的痛苦,这即是说,不肯放弃毁坏与纷乱。为什么,因为痛苦是一切意识的根源。虽然我在一开始说过意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然而我却知道人类赞扬它,并且绝对不会用任何代价把它出卖。意识,比如说,就无限的高越二二得四。一旦你获得了数学确定性,就再没有东西让你去做或去了解。” (第61至62页)
但又能怎么样呢?理性,已经被偶像化,成了永远不能毁坏的水晶宫。人们对之充满了信心,连历史都被它涂上了进步的色彩,反对理性主义的霸权,成了大逆不道之罪。但是,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要拼死一搏,他要向它做鬼脸,或者,偷偷吐舌头。
“你对于一个永远不能毁坏的水晶宫具有信心——一个不能向它偷偷吐舌头做鬼脸的水晶宫。而这或许正是我何以惧怕它;它是水晶做的因而无法毁坏,甚至不能向它偷偷吐舌头做鬼脸。。。。然而,如果我脑子里发生一种念头,意味这不是生命中的唯一目标,我要住最好的大厦——这时又怎么办呢?这是我的选择,我的欲望。” 与理性是否符合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决不会为了自然律真正存在以及为了与自然律相符合,就接受某种妥协。(第63页)“当我还活着并且具有欲望的一天,我宁愿让我的手枯干也不肯放一块砖头在这种建筑上!你用不着告诉我:我刚才摈弃水晶宫仅仅是为了不能向它吐舌头。我并没有说我之摈弃它是因为我太喜欢吐舌头。我所愤慨的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恨我们所有的大厦竟没有一桩是不可以向它吐舌头的。相反的,假如你们的一切事物布置得使我不想对它吐舌头,我因感恩而心甘情愿让你把我的舌头割掉。然而一切事物未曾如此布置并不是我的错,人必须满足于典型公寓也不是我的错。然而为什么我被造就出如此的欲望?难道我生命如此的结构,仅仅是为了让我认识我如此的构造仅是一种骗局?难道这会是我整个生命的目的?我不能相信!” (第63至64页)
我不信!这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抗议。
“我自己知道地下室并不是更好的。更好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十分不同的东西,那个东西是我所渴求的,但我找不到它!该死的地下室!” (第65页)
那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
注释:
注一,列夫。舍斯托夫 著 董友 等译,《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1版,第30页。
注二, 注四,罗赞诺夫 著,张百泰 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北京,2001年1版,第36页;第36页。
注三,转引自 冯川 著,《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7年1版,第125至130页。
注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孟祥森 译 ,《地下室手记》,万象文库, 台北, 1993年初版,第23页。以下引自该书只注明在本书中的页码。
注六,注七,注八,《圣经》(和合本)《马太福音》第8章第12至13节;《马可福音》第5章第14至23节;《罗马书》第7章第15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