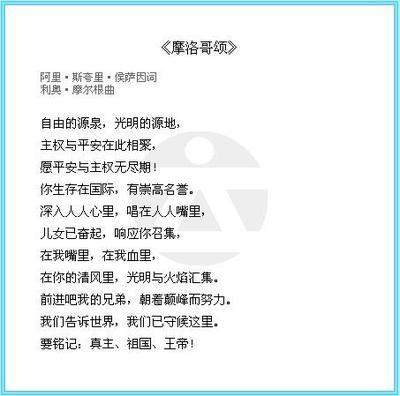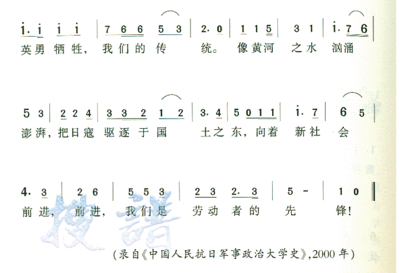李广义为他新书稿自拟的书名是《我心皎洁》,不错,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如月的李广义。
如果广义执意让我写这书的后记,我就决定用这六个字作为文章的题目了。
广义与我朋友近四十年,为诗为文豪放大气,为人为事坦荡率真。“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实学者,必不夸学。以本色做人,以本心说话,以本性处世,乃是我心‘皎洁’之所望。”他在本书的前面如是说,我懂。
广义是我一生的朋友,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也是生命意义上的。
想当年我们年轻时,他写诗大气磅礴气度非凡才华横溢,且又李姓,人多誉其为李白。我虽不才,却也与他同时舞文泼墨小有名气,俩人的名字时常在报刊上同时出现,私下里,我有时认为自己中庸内敛生不逢辰悲观现实,也许就是时下的杜甫……回头看来,其实我与他的诗文并不见得可比,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远远超过李杜。
那时,我们真年轻。
今天,时过境迁,看到《李广义主要创作年谱(1970——2010)》,才突然想到时光荏苒,不禁让我的思绪一下子跌回到了当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浑身充满斗志欲望和文学梦想的青葱岁月,一遍遍地回忆起那些李广义与张洪波、张伟、孟繁华……我们在一起那一生都值得回味的青春时光。我是从长春上山下乡来到敦化的,正如张笑天在为《雁鸣湖丛书》写的几句话:“那些年正是人生最壮美的韶华岁月,可以说我把青春留在了长白山脚下的那片黑土地。在短暂的人生之旅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的,你想忽略都不行。”其实,最不能忽略和忘记的原因还有一个:四友中的大哥,挚友李广义。
正如他写给我的一首诗中说“那段旅途的确十分泥泞\炽热的太阳更使人步履蹒跚\共和国也艰难地喘着粗气\一场蟋蟀咬斗的游戏才接近尾声\亿万张嘴那时还重复着一支歌谣\我们虽不信宗教却在祈祷中相知逢”(《人生回眸》)。我在下乡插队到敦化的时候,一次被抽调到县里办农业学大寨的展览,第一次认识了瘦瘦高高的李广义,他是写文字稿的,我是负责画展版的。一见如故,我们同是为寻诗之花粉那两只饥渴的蜜蜂。
那时,没有稿费,没人指点,也没人苛求,但是我们却嗜诗如命,写诗几乎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至今我记忆最深的两个镜头是:一次,广义的小儿子突然得了重病,刚刚在县医院里抢救完,当孩子静静地睡去时,他擦擦额头上的汗水,用膝盖顶着稿纸在并不明亮的病房里,又旁若无人地写起了诗!我当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另一次是,年轻的他和妻子从母亲家里搬家刚刚出来,借租了一间低矮潮湿的农家小屋,除了身上的衣服和简单的碗筷,那真叫家徒四壁。我们一起用四根小木杆直接钉到屋里的土地上,上面又钉上几块木板,便成了他的日后屡屡写出诗来的小书桌……当年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我们拥有全部梦想和未来的世界!“在那个相对寒冷的年代\我们还买不起太厚的棉衣\要踩热那段缀雪的残冬\谁也不能离开真诚的友谊”(《零碎的记忆》)。
当年,广义带领我和张伟、洪波创办了《寸草》诗社,在延边,在吉林,在国内的期刊上推起了一次又一次不大不小的诗界浪花。借用广义诗中的一句话“相信一个草叶的工程并不小于星星……”(《草叶上的月光》)。
后来,岁月和现实让我们四友相继分开。张洪波到华北油田报社又到了北京《诗刊》,张伟到了省报又创办了《新文化报》和《巷报》,我也放弃了延边作家协会副主席回到了长春编杂志,只有广义还留在林业局党委,留在我们四友起步的地方。
那时,为了打拼,天各一方,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追求着忙碌着,即使有时并不通信通话,但我们却时时相互牵肠挂肚。其实,那时的我们之间,早已不仅仅是诗了。
前些年,广义每每出版一个新诗文集送我的时候,都令我都兴奋不已,一次次进入了广义用文字编织的美好心灵世界中,每每都感慨他的才华和坚守,都钦佩他的真挚和执著。回忆起来那些个读后让我无法入眠的夜晚,是我庸常的日子里诗情萌动思如泉涌的日子,也是我后半程忙碌人生中最为美好和纯净的时光。
今天,见面李广义还是那么执著,为文为诗依然行云流水文思泉涌,为人为事还是那么心高气旺、白黑分明!
永远的李广义。这个句式也许最适合他。
其实,岁月是不饶人的。想来,当年舞动诗坛的“四小天鹅”(姑且就这样以讹传讹吧)经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大半已经是“裸露山岩”上的“栖息之鹰”了。
读着长长的文稿,我在不同人风格迥异的笔下和不同人时光交错的回忆中,仿佛看到广义周围我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是一些以文交心的真朋友,在赞誉和景仰的背后,都是笃深的友情。与其说朋友们在评介广义的诗品,不如说同时也是在赞誉广义的人品。
成诗者,文坛之大可谓无数,但是成挚友者,被大家如此推崇在上,如此挂在心底的却着实不多。“广结鸿儒,义拜金兰”,广义自己在诗集中也曾经这样注释自己的名字。一个义字——价值千金。
此集中大多都是大家对李广义作品的评价,我在此编后中就不多赘言了。
其实我写编后,只是出于友情,广义自己编辑好了,让我在最后也说上几句话。因为,如果这里没有我的名字出现,他遗憾,我也会遗憾。尽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真正写什么东西了。
拟本篇文字的题目着实让我难住了,如果按一般的作法应在李广义前面加一个什么词,那是什么呢?冠以:豪放大气、率真坦荡、耿直侠义、文不染尘、诗心皎洁……人如其文,一个词,还真达不了意。
我一直在你的身后——我忽然觉得这个标题可用。
多年来我的名字在广义之后,我的创作水准也在广义之后,我在这个诗友群体中排行二哥,威望自然也在广义之后。我是从一开始就步广义的后尘。起初我一个知青,独在异地为异客,孤独苦闷,一个人独自写诗,孤芳自赏,并从没有发表的念头,是广义带我出发,让我走出敦化,走出延边,走出吉林……当初,他虽然觉得我行,但我还没有发表出作品让大家熟知,他便急得什么似的,在自己的李广义名字后面带上我的名字。我呢觉得心中有愧,便没白没黑地写,终于成了。那时一度大家很习惯地连贯地就说出我们的名字:李广义、贾志坚。从此,我的名字也就经常与他同时出现在一个报刊之上——在李广义的后面。若不是广义整理作品目录,我都忘记了当年他写词,我谱曲曾经一起创作过几首歌曲呢。我习惯于在他的名字后面,更安于在他名字的身后……后来,《诗刊》《人民文学》《散文》《作家》很多期刊上我们都并肩同时发表作品,可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广义的身后。即使再后来当我作为高级职称评委,评定那些教授级别的编审时,即使当我被省政府评为新闻出版界的优秀社长总编时,即使在全国出版工作研讨会的讲台上,我也觉得在广义身后……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大,没有他的当初,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多年了我们虽然不在一座城市,心却一直牵挂一起。他像十分称职的老大哥一样想着你,不时地到长春来,带上成双成对的山野鸡,带上不可多得的黑龙江大马哈鱼、带上嫂子自家酿的红葡萄酒,带上他出席会议或者观光旅游或者出国归来的种种消息……
“一辈子扎根北方\黑土地养育太多的恋情\尽管外面的世界十分精彩\发誓与故乡不分离”(《顶冰花》),广义离不开“随手丢弃的拐杖\竟也长出一片黑森林”的故土(《播种鸟啼》),因此,当年他没有去各种文学期刊到北京或长春谋职,而选择了做一只永远盘桓在长白山上空的雄鹰。“鹰的心中\永远充溢着翱翔\……一生志在千里\至死锐气鹰扬”(《栖息之鹰》)。我深深理解他在《题老照片》一诗中说的“我只能用爱把故土固守\你们知道我追求身心的自由”。是的,尽管他官居党委书记,但他的身心是自由的,他的生命是昂扬的,他的诗情如泉是永不枯竭的。正如他说曲有源“诗意如沐浴之巾\总是拧不干”(《诗缘》)。
当永远精力过剩张洪波像一团火似的从北京再一次回到长春北方文艺出版社时,他风生水起的势头和节节攀升的成就,又一次点燃了广义心中的诗情!当时,我也陷在繁杂忙碌的工作之中,借用广义的一句诗是“我案头的稿纸已荒芜成青苔”(《诗缘》),在洪波的追逼下,我总算写了一首诗,庆幸还被刊登在了阔别多年的《诗刊》上,算是我对多年文友的一个照面。可是,广义却是行家不出手,出手就有。《四友诗选》出版之后,广义一下子就连续出了几部诗文集!如栖息之鹰,他轻轻一飞,便跨进了别人舞文弄墨拼了一生也没能涉足的中国作协。
此处,我想借用张云波文章中的话“广义心地正直善良,性情率真坦诚,心灵纯得像一泓清水,容不得半点尘埃……”他还说:《瓯北诗话》中称赞李白的诗是“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我不知道广义是否是李白的后裔,但我感觉他是像李白一样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诗人。广义的诗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也应了广义自己在开头说的“我心皎洁”。
我在最后想说,广义如月。
没错,我有这样一位朋友,一生都沐浴在友情爽洁晶莹的月光中……
广义,如太白之月的皎洁,也让结识他的所有朋友都沐浴于其中……
2011.08.08 于长春 掬月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