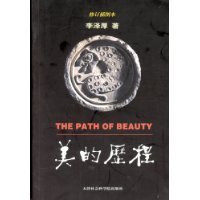梦想北京
彭富春(摘自《漫游者说—我的自白》)
我在湖边生活一年了。湖边看起来是寂静的,但它实际上是动荡不安的。不过这不意味着暴风雨中的东湖水的波浪汹涌,也不是珞珈山森林的松涛起伏,而是人们生活的变动不居。湖边似乎是一个教师人生的中转站。一批批青年教师从本校或外校带着行李和书籍单身来到了湖边,但当人们结婚生子了,就会移居到珞珈山南教师宿舍中更大的房子。还有的会因为工作变动而离开湖边,也有的会由于到外地或者到外国读书深造而远走他乡。
每当看到他人离开湖边时,我都会在内心里有一股深深的触动。他们离开了武大,去了一个我只知道名字却尚未去过的地方。我一直只呆在武汉大学,而它只是只是世界的一角。五年来我已经走遍了它的每一个角落,对它也失去了往日的新奇。而外面的世界是多么丰富和精彩。我对它们的了解不过是通过书刊,报纸,广播和电影,它们对于我只是一个想象的存在,是一个名字,是声音,图象。我从未用自己的身体去经历,去体验过。我甚至还没有乘过在原野上飞驰的列车,在江河和大海中行驶的轮船,更不用说在云层上飞行的飞机了。因此我非常渴望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漫游。
去外面的世界成为了我的梦想,但是否真正走出珞珈山对于我还是一个问题。这样在我的内心,是留在武大还是离开武大,似乎是在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留在武大,当然有许多优点。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环境,不畏惧它夏天火炉般的炎热和冬天冰雪的寒冷。我也熟悉了周围的人们,其中许多是我的同学老师和朋友。另外我生活的地方和我的家乡也非常地近,便于我去看望我的家人。但留在武大也有许多缺点。最主要的是武汉地区缺少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学校里蔓延着保守和落后以及夜郎自大的歪风。特别不能令一个独行特立的年轻人忍受的是,在本地的学界存在着一种由地头蛇和土皇帝所编制的网络。在经过了反复的比较之后,我还是决定离开武汉和武汉大学。但离开武大到哪里去呢,这个世界太大了,它几乎让人无法作出合理的选择。但我自己有很明确的目标,去北京或者去美国。不过这又存在一个问题,是通过考研究生去北京还是通过靠托福去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做着美国梦。周边人连续不断的去美国的消息,更是激发着我要早日实现美国梦。我也买了托福资料,借来了英语录音带,了解一下到美国去英语入学考试的困难度。但我从朋友那得知,去美国是需要许多钱的,而且是美元。首先考托福需要很多钱,然后申请学校也要一些钱。如果有幸被某个大学录取并获得奖学金的话,那么还需要许多路费。这些钱对于我来说几乎就是天文数字。我毫无疑问,靠我自己的工资,也许永远都无法支付这些费用。但我也无法找人借钱,因为我只有亲戚和穷朋友。在农村的家人不仅不能帮助我,反而还需要我的支持呢。我实在无法解决我考托福和出国的相关费用,因此我只好放弃了我的美国梦。这种放弃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奈和痛苦。
尽管我不再做美国梦,但是我还在做北京梦。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研究生,而且是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我从一些渠道知道,李泽厚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研究,回到了北京。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广告也标明,他将在一九八五年招收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也不时地听到,有许多人都想报考他的研究生,特别是一些在全国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亲自指导。我明白,报考李泽厚的研究生将是一场全国性的竞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公开的冒险,失败的几率是很高的,而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我参加这场竞争也意味着步入了冒险者的行列。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当然很好,如果失败的话,那么就糟糕了。我在周围人的眼中是一个佼佼者,失败将无情地抹去我头上的灵光圈。同时从上大学以来,我在学习上一直非常顺利,没有经历什么挫折,失败将折磨我骄傲的心灵。但我认为,我要寻找一位最优秀的老师,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关键问题是,我要借此对自己进行考核,自己的学习离李泽厚所要求的入学标准究竟有多远。至于是否能考上,谁也说不准。但我对自己始终怀有信心。我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样我就不顾一切地到学校报名处,填写了报名表。然后我就准备复习,但感到没有什么好复习的。
到了考试那一天的早上,我按时来到了设在桂园教学楼的研究生入学考场。走进桂园,我就有一种家园之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同时看到考场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又想起了参加两次高考的经历。在考场前,我还遇到了一些熟人,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老师。我们都是试图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一进考场,发现同考李泽厚的还有两个同学。我们作了考前的简单交谈,我感到他们远远不是我的对手。这使我对于自己的成功更充满了信心。我们一门接一门地参加考试,如同过了一道鬼门关又过一道鬼门关一样。每门课考完之后,另外两个同学都垂头丧气,说这下完了。我的感觉却非常轻松,因为对每一道的答题都得心应手。在所有的科目考完之后,我如同卸掉了一个包袱,回到了湖边宿舍,享受起那宁静的时光。
几个月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的朋友给我传来了好消息。全国报考李泽厚的考生近五十名,学校计划录取五名。我的专业考分第一名,一般都八十分以上,有的则高达九十多分。这样我自然列入了初录名单。在这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我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当然使我感到自豪。不久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就派人到武汉大学对我进行考察。他们先找了哲学系的领导座谈,了解我的政治,道德和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们还索取了一份对于我的书面鉴定,上面盖有哲学系的红印。鉴定写得非常好,说我无论哪方面都是优秀的。后来考察人员又来到了我的寝室,与我面谈,看看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走时他们说,要作好到北京长期生活的准备,因为哲学所培养的研究生一般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研究队伍。他们回到北京后,就给我发出了去京面试的通知。
复试的时间非常紧,北京的朋友跟我打听情况,并连发两封电报,要求我尽快去北京。为了保证时间,我赶快去火车站买票,但当天的坐票都售完,只剩下了站票。但晚上我还是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我当时心情有些紧张,不知道在北京面试会到遇到什么问题。火车上人很多,座位都坐满了,连走道都塞满了乘客。在车厢间的接合处也早已被人占领,几乎没有插足的地方。我在人群中的缝隙中往前挤,终于在一个车厢的接合处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车厢内声音嘈杂,火车的轰鸣声与人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人的耳鼓膜虽没有震破,但听觉变得迟钝。车厢内的空气也非常污浊,人体的气味,尤其是烟雾弥漫的烟味使呼吸变得更难受。但我无法考虑这些,心里只是想着面试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站了一夜时间之后,双腿有些酸疼,人已经支持不住了,我不得已蹲了下来,靠着车壁打盹。好不容易黑夜过去,天亮了,火车到达了北京站。
我匆匆地走向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当我来到九楼的哲学研究所办公室找到管研究生的干部之后,他们告诉我要直接找李泽厚去面试,并说明了他的家庭住址。我又急切地乘车找到了李泽厚家所住的地坛北门附近。在敲他家门时,我的心情极为紧张,我就要见到我一直所景仰的老师。我既感到激动,也似乎有些害怕。李泽厚教授很快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作了简单的交谈。他给了我一本英文书,并指明了其中的章节,要求我明天译出来,后天交到哲学所办公室。这就是我面试的任务。
我到了北京的朋友所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宿舍,在那里开始我的翻译工作。我看了一下李泽厚给我布置的任务,所要译的章节关涉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有十多页,译成汉字达一万多字。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要考我什麽东西呢?我想他无非是想知道我专业(哲学)英语的阅读与翻译的水平如何,尤其是在速度方面。我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从事这一章节的翻译工作。我首先认真地通读了一篇,并借助英汉词典将其中的生字查了出来,心里已有了把握,正确地翻译这一章节问题不大。问题只是在于时间是否来得及。我只好除了吃饭以外,全力投入翻译过程中。经过紧张的工作之后,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将译稿按时交给了哲学所办公室。然后我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了一下,乘上了回武汉的列车。我想我一定会再来北京的,而且是在今年的开学之日。
过了几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终于给我发来了入学通知书。他们将通知书寄到哲学系办公室转交给了我。系里的干部说,我现在走了,以后还是回来吧。我将我去北京读书的消息也告诉了刘纲纪教授,他说我去北京读书非常好,可以扩大眼界,提高境界,但读完了还是回来工作,不要“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说,如果他继续在武汉大学任教,那么我会考虑回来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