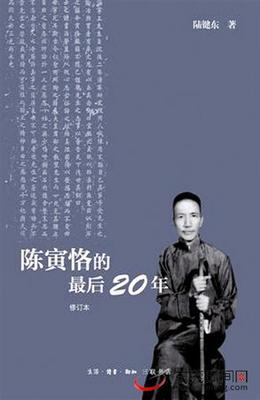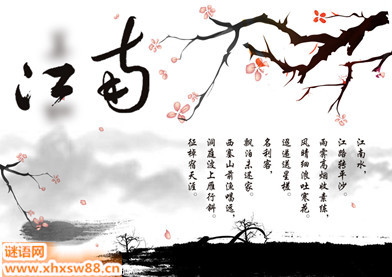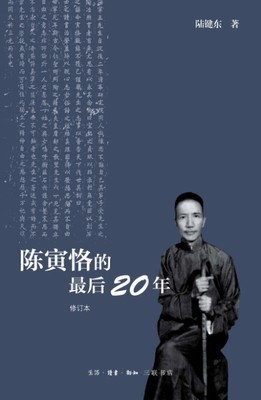作者:吴格
报告中会涉及到这么几个人,我把他们分成甲、乙、丙三个部分。

首先将陈寅恪先生做一下介绍: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话,做传统学问的人都将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叫做“知人论世”,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反过来,要了解一个时代又可通过那个时代所生活人的活动和经历来判断。我们对陈寅格先生这样一位蜚声海内外、有着大师的称誉、有着教授之教授的称誉、有着三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最渊博、最有创造性的学者这样一些美誉的大学者,我要对他的身世作一介绍。
第二,因为是谈《柳如是别传》,也就是陈先生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花了前后大约九到十年的时间,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完成了这部数十万字、对三百年前知名度不太高的、并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青楼女子的生平介绍,这样一部著作本身也引起我们这些后人的浓厚兴趣。那么柳如是究竟是何许人也,是我也是大家所感兴趣的。
第三就是柳如是生平、《柳如是别传》中还有到一位主角,就是钱谦益,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是“文学家”,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大宗伯、少宗伯。钱谦益,别号牧斋,尊重他的人称之牧翁。而钱谦益也颇为不幸,他有着少年才子、中年文士的美誉,晚年又被推为文坛领袖,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尊崇,而在他身后百年左右,就被清朝乾隆帝重新评价,用现代的术语说:“重新评价”就是被完全推翻。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距钱、柳生活的时代已有三百多年,他对钱、柳身世及明末清初的历史做如何的评价呢?我们下面将谈到。
甲、关于陈寅恪
对陈寅恪先生,我个人的看法,他是一位奇人,非常奇特的人,不仅是他的个性奇特、命运奇特,而且他所出生的家庭,他的父祖两辈及他个人所经历的,正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外侮凭人的时代,我们的国家经受了许多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战争及近五十年来种种的社会变动。当然,陈先生并没有活到二十世纪末,他是一九六八年过世的,他的身世就非常之奇特。清代后期,满清统治到了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地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维新派,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推行新政。在一八六○年以后,我们的东邻日本,一个一直以大陆文化为母文化的岛国,历代的中国人不无所谓大汉族主义,我们是有些自大的因素,他们与我们是同父同种,我们是母文化,日本是我们的子文化。他们从我们这里学了文化,学了衣冠。许多人讲,到了日本看到的招牌,看到的服饰,看到的习俗,还不是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大唐、唐宋时代的服装和语言,有些人会觉得非常光荣。日本到了近代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影响,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要开拓的市场,最初通过精神方面的传教,再有就是通过枪炮、兵舰的。它也是挨了打的,但它较早地破除了锁国的政策、打开了国门。在我们明代的后期大概相仿的十六、十七世纪以后,逐步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管理制度。尤其重大的是一八六二年的“明治维新”,举国由天皇下令进行改革,非常见成效,从一八六○年到一八八○年、一八九○年已是出成效。
对于中国来讲,清代统治阶级内部,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湘西、淮西的领袖,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后,手中握有重权,他们也在新管辖的湖广地区、京津地区、上海地区、福建地区、广东地区先后开办了洋学堂、机器制造局,造船、造枪炮,引进外资造铁路、开煤矿、铁矿,也在逐步向所谓的工业国家、工业革命发展,但因我们的改革不彻底,统治集团挨了洋枪洋炮的打,就觉得要“师夷之长技”,但许多场合还是以“国朝天威”自居。我们是中国,天下之中、要八方来朝,把西方人称为“夷人”、“鬼子”,这样一种盲目的自大,我们把东洋人、近邻的日本人从来都看得比我们低一些、弱一些。可是到了一八九四年我们有了一个教训,日本的改革显示出了国力,甲午海战中,李鸿章经营了二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大连讲北洋水师的覆没,我想关心本土历史,关心近代史的人们都会知道,山东的北洋水师的总部刘公岛失守后,我们的旅顺口也相继失守,日本人登陆进攻,军队向北京进逼,逼得李鸿章担任全权谈判大臣,在日本非常羞辱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我们落后必然挨打。
这些形势的介绍后,我们要回到陈氏祖孙身上。陈寅恪的祖父叫陈宝箴,他在清代的维新运动中,担任湖南巡抚,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长的职务。当时的两湖地区(湖北、湖南)是中国的腹地,同时也是最先开展新政的地区。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他自己和别人的回忆中都谈到他是大施新政,大启民智。具体做法就是兴办矿业局、机器局、银元局,开实务学堂,办乡学报。稍后戊戌变法中出名的两位是康、梁,其中梁启超是位口才极好的政治家,也被陈宝箴请到湖南主持实务学堂,这新学堂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成为辛亥革命及稍晚的国共两党中早期人才,这与湖南的风气先开、办报、办学堂的启蒙活动不无关系。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一八九八年发生所谓“戊戌政变”,朝廷中的激进派与在野的许多知识分子汇合成一股改革的力量,强迫慈禧交出政权,让其子光绪帝归政,希望通过维新派对年轻的有改革意图的光绪帝的影响,来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可是这个政变前后只有数十天就流产了,后果就是大批有维新倾向或参与政变的人士受到了镇压,著名的康、梁逃往海外,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弟等六位被斩首。陈宝箴在湖南主持改革,在光绪帝亲政时间他曾上过奏折,推荐了湖南本地及全国范围内三十多个改革人才,这些人大都被慈禧扭转政局后列上了驱逐的、砍头的、永不录用的名单。陈宝箴和他儿子陈三立也都在严谴之例,也就是不杀你,但立即撤去职务,回到原籍,而且永不再用。政变挫败后,陈宝箴和陈三立回到了原籍南昌。陈寅恪先生是第三代,生于一八九○年,他在四岁时正赶上祖母过世,全家扶着棺木,坐着船从湖南回到长沙。祖父回到长沙后,在效外西山的一所房子里,虽是退休了,但是在自己湖南任上做得轰轰烈烈的事业也还是有自己的看法,但因为当时政治上一片萧杀之气,只能与自己的儿子相对叹气:没有抓住时机,操之过急等等。但西太后并没就此放过他,现在也未经证实,所谓一八九○年陈宝箴的故事有一种说法就是西太后又派了太监从北京直接跑到南昌,进了陈家宅院,在内室宣读太后密诏,其内容就是要取他的性命。也就是要他体面地死,对外只说是生病死了,实际是要他自尽,而且非常残忍,据记载人自杀后要取他的喉尖,即取一块喉骨回京覆命,这事一直为陈家所忌讳。但对陈寅恪来讲,祖父与父亲都是极有才干,在当时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中极有影响的干吏、学者、才子,一下子从政治的上层落到民间,对他的幼年当然是刺激很大。他父亲陈三立也是举人进士出身,而且也有礼部主事的职务,但未到任,而是在湖南辅佐父亲推行新政,清末有“十大公子”之称,湖南就有好几位,包括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都是当时学问好、思想先进,两者兼容的人才。陈宝箴被贬并过世后,到了宣统年间,朝廷有启用陈三立之意,但他不愿出来,民国政府也曾愿重用他,但三立老人从此不踏入政坛,三立老人因以传世的是他的诗文。
十八世纪的最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传统诗歌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以后,慢慢转向衰落,但在最后阶段,我们称之回光返照,有一段很大的繁荣期,即清代的末期到民国的前期。清末同光年代,文学史上称为“同光体”的诗歌形式,“同光体”后期的领袖就是散原老人陈三立先生。他的诗歌学的是宋诗,他本身是江西人,江西诗派,大概在自己的作品中要用许多典故,对许多曲折的、不能明言的、许多有隐意的时事的感慨、身世的感慨。散原先生诗是中国十九世纪传统诗歌领域中不能轻视的一份遗产。复旦大学的一位朋友现在还在专门做陈三立先生诗歌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另外三立老人非常有气节,清末民初的北洋政府,包括一九二八年后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都想借重他的威望和影响出任一些职务,他都不愿意。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三立老人住在北平的郊区西山,日本人想拉一些有影响的老辈出来,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军阀叫吴佩孚,当时也老了,日本人也去拉他,总之一些有名气的老人,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化界,日本人都要把他们拉出来,三立老人也名在其中。老人很生气,让仆人关上大门,门外总有便衣在等着,三立老人知道就当时情况带着全家回南已是力不从心,就生病拒不服药,多少天后就去世了。
这时的陈寅恪先生作为清华的教授,因为战争爆发,正在由北方向中国西南迁移的途中。陈先生出生世家,有着这么好的传统修养,而且又不是传统的教育子弟埋头只读圣贤书,得一举人进士好做官。他出生于一个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是中国处于近代的世界环境中,具有开放意识、有改革中国传统封建统治愿望的官僚队伍中激进分子的家庭。从小在家中念私塾,十三岁由亲属带他到日本。最初他是随到日本留学的大哥见见世面,回国后在他所属的江西省考到一个官派的留学资格,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留学,三十岁左右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当时在欧洲和美洲的留学生队伍中,许许多多的年青人都知道陈寅恪其人,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胡适、俞大维、吴宓等他们在欧洲或美洲碰到时,无一不把陈寅恪推为他们这一拨人中最努力、最渊博、最优秀者。陈先生是一个世家子弟,不是不知道读书能进入官僚阶层,有较好的生活。如清代的科举制度没变,他肯定会和他的兄长一起一个个地去考试,但因他的家庭有过那样的变故,他们又会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又重视,不得不把它当成敲门砖,同时又不是真正的看重。陈先生留学若干个国家,到了多少个学校,都是要学他感兴趣的学问,找他所佩服的老师。我做学生时,我的老师说过,陈先生真了不起。有的老师听他一个学期的课就够了,有的老师听他一星期的课就够了,还有的老师听他一节的课就够了,他并不是和老师比高低,有较量的想法,他只是我要学的,就是与我的学术、理想,与我一生要完成的学术任务有关,感兴趣的东西,并不完全被学分、学制所左右。
吴宓说陈寅恪的学问是我们当中学识最渊博,但不止是渊博令人佩服,而且他的好学深思,他能对学问融汇贯通,他的见解更令同学们佩服。根据记载,当时的留学生中有许多贫寒子弟,父母供不起,但由于刻苦,得到有钱人资助,或考上官费,有了特殊的待遇,有的就是世家子弟,有的是通过各种关系,不管怎样,这些留学生在海外大多是只想文凭,只想所谓个人今后的利益。而吴宓、傅斯年、胡适,包括陈寅恪这些人笔下所写的当年世纪末的那批留学生真了不起。陈寅恪后来是一个书斋的学者,但二十年代在德国留学时每天听的是梵文、巴利文等一些很专门的学问,但周末同学们聚会时,除交流学习的情况外,谈论的是回国后中国的征兵制度、军队制度、通过征兵提高中国穷乡僻壤的百姓的水平、教育应推行德国式的,还是英国式的,谈的都是学成以后如何报效国家,如何改造遍体疮痍的国家,数千年的封建文化虽然给了我们光荣、给了我们骄傲,但近代以来,他更象一个生病的老人。这批年青人从大陆出来,日夜萦绕自己的信念就是如何拯救自己的国家,为国家寻找一条富强之路。陈先生早期在德国和美国碰到两位国际大师级的语言学专家,一个是美国的Lanman,非常了不起,另一位是德国的Lueders。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有一位外国专家叫钢和泰,他与陈先生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当时已是清华教授的陈先生每周与他见面两次,习梵文。梵文及巴利文不是现代的语言,是古代曾经存在过,后来越来越少有人知道,变成一死掉的语言,但是偏偏我们东方的包括亚洲西部、中亚、东亚古代历史中许多不同时期的文献,不都是用现代的文字,如阿拉伯语、汉语来记载的,它们多是用梵文、巴利文,突厥文等这些古代的文字记载。我国的少数民族中西藏有藏文,蒙古有蒙文,满族有满文,新疆所用的语言就属于突厥语系统。历史上这些民族有分、有合、有并,我们中国的版图在唐代曾推到中亚。清代康熙帝时我们西边疆也不是到伊梨为止,还要延伸到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东北的疆域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库叶岛地区,后来历史的演变中我们萎缩了。但历史上那些疆域、那些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民族间的交融,曾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
陈寅恪一是因为他天资聪明。二是对语言特别的敏感。过去的士大夫之家,小孩子从小读书,不是只读《三字经》《百家姓》,而是从《说文解字》开始,《说文解字》就是把中国文字的源由从头说起。陈先生先后学过的语言很多种,他一九二五年回国,三十六岁,没有任何学历,没有任何著作。胡适之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后威望很高的北大教授、文学院长,他推荐陈先生担任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导师,当时只设四个人,校长听说陈先生是胡先生介绍的,一定不差的,问哪个大学读的博士?他说不是博士。问有什么著作?没有著作。校长说,这就难了,清华研究院可不是谁要来就能来的。同时聘请的另外几位中有声名赫赫的梁启超、王国维。梁启超就说:我梁某人从清末到民初,可说是著作等身,可我也没有博士,陈先生没有博士还在其次,我告诉你,我的等身著作,在近代影响很大的那些政论文章,加起来虽有我的身体那么高,但不如陈先生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清华的校长姓曹,他一听,噢,这么大的保人,胡适之、梁启超都推荐他,那就请他来吧。陈先生到清华后,他的学问,他的人品,他的治学态度很快就博得了师生一致的尊敬。
抗日战争开始后,清华北大都迁至西南,所以有过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成西南联大的事情。联大时期,英国最大的学府牛津大学有一个专门的汉学、东方学的讲座,应邀讲座的教授都有很高的荣誉,请的都是著名的外国的汉学家,但他们认为陈先生的文学、语言、历史各方面的修养足以担任牛津大学的讲座教授,这比一般教授地位要高,当时就请陈先生去。当时陈先生还有一个私人问题就是他的眼疾,陈先生的右眼是一九四四年失明的,左眼视力也极差,抗战结束后,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左眼也失明了,本想去英国讲学并检查治疗眼疾,但由于战争原因,没有成行,留在了当时的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一九四八年从北京南下,到了当时的岭南大学,解放后岭南大学撤消,他又到了中山大学。
陈先生学问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曾湘乡就是曾国藩,张南皮是张之洞,好像湖南有一唐姓作家,连续写了《曾国藩传》、《张之洞传》,颇有影响。曾是湖南人,张是河北南皮县人。过去称呼大人物不用名和号,而是用他的籍贯称呼他。陈先生的话有很多解释,有人说很准确,也有人说是陈先生的谦词。还是让我们从字面上看一下,这样一个世家出身,留学西方十多年,对传统学问和西方文化都下过大功夫,有过长期积累的饱学之士,没有对自己自视甚高的评价。“不古不今之学”看上去贬意,实际是有讲究的,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陈先生讲上古史材料太少,三皇五帝开世,《六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加上其它的一些史料,假如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没有大量增加的话,他认为靠这些现有的资料把古代的历史描述很准确很具体是不足的,不够的,要大量依靠地下出土文物。从明清以来,大约距我们五、六百年的历史资料又太多,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无法把这些资料都看过,都研究到,就容易顾此失彼,不能有全方位的观察。所以陈先生最初给自己定囿的范围就是晋、魏晋开始,晋、南北朝、隋唐,中间的部分,就是中古这部分。因此,说他的学问是“不古不今”。“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现在有人说是指同光这一段。这期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任期内湖北、湖南兴学新政蓬勃开始,我们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发生在湖北,湖北的新军接受了新思想后,这些满清政府养的军队起来反对清朝统治。国共两党早期的军政人才都是两湖出来的。
大家知道人才的造就不是三天五天,总得一代人,要上溯至清末的维新运动。陈先生到了三十年代,他中年时的思想是服膺信奉张之洞的观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学科技、技术是用来改良我们物质生产、生活的质量,但我们的“体”,我们的内涵还应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观点一直是受批判的。记得我读书时一提到改良主义,不行的,马列主义要彻头彻尾,从里到外。现在改革开放了,倒不这样说了,提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他的一生中如果没有镇压太平天国这一段,他可以是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学得是“孔孟之道”,行得是“孔孟之事”。曾的传记、家书、日记在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仍有广泛的读者,我想我们民族的心理不是一个简单的潮流和风气就能改变的,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学校历史书上描绘的“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一个人,想起他应是很鄙视的,但读了他的书、日记、家书,就会很受启发,很有兴趣。张之洞同样也做了方面大员、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奠定了湖北的教育、工业基础,到广州办书院,造就了近代的许多人才。孙中山的黄花岗起义、民初的许多广东进步青年,都与广东的教育和开化有关。
这是陈先生对自己学术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他呢,上面讲过,过去的读书人,尤其是家学渊源的知识分子,说话都很质朴,“读书须先识字”。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与大连的朋友也有过交流,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孩子学电脑、学外语,出去留学的年龄从大学生降到中学、小学,许多父母将孩子外语的学习视为头等大事,可我们不得不看到,没有人担心孩子的中文是否过关,好像中文是母语是天经地义的。我的老师语言方面很有造诣,懂五六国语言。我们说了不起,懂那么多语言。老师说你们还是先把母语学好。小孩子学语言不仅学语音,更重要的是思维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些都是在日积月累的认字、造句、作文中完成,长到一二十岁,语言运用熟练了,思想也成熟了,而我们现在母语还不熟练就去学外语。回到陈先生这,他掌握十几种语言,除欧洲的英、法、德、意外,还懂许多古代的、死掉的语言,而研究佛教经典,就懂了梵文、巴利文、藏、满、蒙、突厥文。学生会问老师怎么懂那么多语言,他的回答很平淡,他说这些语言我一旦不用,我就不掌握了,语言只是工具。他为了攻读清廷内北海大高殿内的满文档案,就攻读满文,他的语言天赋的确是很高,每天到北海,一面读一面翻译。语言是工具,学语言并不仅是表示自己的兴趣和渊博,是为了做研究,而陈先生最了不起的是他的中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