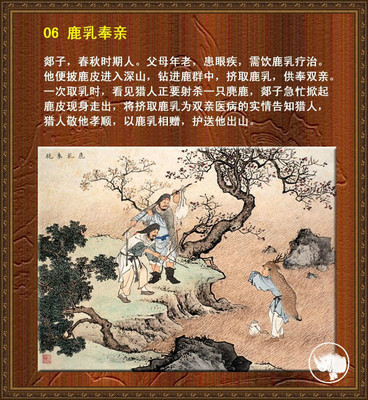论剧情片对传统纪录片手法的借用
——从《冷酷媒体》到《二十四城记》
【内容提要】 剧情片与纪录片有着明确的身份区别,但文本形式上却有着模糊的边界。本文通过对美国电影《冷酷媒体》和中国电影《二十四城记》的对比分析,说明了剧情片借用传统纪录片手法的方法、策略,部分揭示了这些策略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诉求。
【关键词】 直接电影真实电影隐喻 采访空间自我反射严肃话语去政治化
作为相对存在的两种电影类型,剧情片和纪录片都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呈现,都可以传达创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不同的是二者各自的表达机制。纪录片一般直接取材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就是作品的直接指称对象。剧情片则会营造一个虚构的世界,或许它也会采用高度纪实的风格,但从根本上说,它对现实的指涉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实现的。纪录片、剧情片的这种分别并没有隔绝彼此之间在表现手段上的相互借鉴。事实上,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纪录片《北方的那努克》(Nanookof the North,1922)就非常成功地借鉴了剧情片的叙事手法。在本世纪初,我国纪录片界曾热议一时的“纪录片故事化”也可以视作是类似的一种尝试。相应地,剧情片对传统纪录片手法的借鉴也从未停止。特别是在1960年代,西方纪录片经历了直接电影(directcinema)、真实电影(cinemaverité)运动之后,剧情片对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手法的借鉴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影片《冷酷媒体》(MediumCool,1969)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纪录片与西方的直接电影、真实电影非常接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了1990年代中期,纪实手法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成了中国新纪录片最显著的标志。一些导演,如张元、贾樟柯等,开始自觉地把纪录片的表现手段运用于剧情片创作。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贾樟柯的作品《二十四城记》(2008)。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对《冷酷媒体》和《二十四城记》这两部相距近40年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考察这两部作品运用传统纪录片手法的不同方法、策略,进而揭示这种策略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意识形态诉求。
一
回顾纪录片发展的历史,纪录片的形式、风格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不同的时期往往有不同的主导。但当我们讨论剧情片对于纪录片的借鉴的时候,更多指向的是1960年代初期出现的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事实上,尽管纪录片的形式、风格的发展变化从未停止,在直接电影、真实电影之后也有表述行为型纪录片(performativedocumentary)、自反型纪录片(reflexivedocumentary)等纪录片亚类型的出现,但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技术却被运用于几乎每一部纪录片之中,甚至成为观众指认其纪录片身份所凭借的最重要的依据。在本文中,我们考察《冷酷媒体》和《二十四城记》首先关注的也是影片对直接电影、真实电影技术的运用。
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技术基础都是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16毫米便携式摄影机、能够在自然光条件下进行拍摄的镜头和胶片、特别是可以实现同期录音的磁带录音机等。但二者对纪录片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直接电影的创作者相信客观世界里真实的存在,相信只要观察得足够细致,就可以捕捉到真实。因此他们摒弃此前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中常见的摆拍,摄影机置身事件发生的现场,充分运用运动长镜头、同步录音、连贯剪辑等技术手段,呈现出社会生活的原生态。直接电影这种对抓拍的强调使得其影像风格少了精致、多了粗糙。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直率、不事雕琢的风格却大大强化了影像的真实感。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在评论英国纪录片《住房问题》(HousingProblems,1935)时,曾经谈到:“正是由于这部影片的画面具有快照的特点,才让人感到它们是一种真实可靠的记录。”这种表达技巧在影片《冷酷媒体》中有充分的运用。
影片《冷酷媒体》拍摄于1968年的芝加哥。当时的美国越战正在进行,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阶级对立、族群冲突等问题集中爆发。影片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片中主人公约翰(John)是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他原本有些玩世不恭,认为记者只是一个记录者,并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但当他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社会底层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少数族裔、贫民区中挣扎的穷人们的真实处境,他逐渐改变了看法。当约翰偶然发现政府借助于电视台所搜集的新闻素材来监视民众的时候,他愤而辞职。在工作中,约翰结识了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寡妇艾琳(Eileen)和她的儿子哈罗德(Harold),并和艾琳产生了感情。在偶然发现了约翰和艾琳之间的亲昵行为之后,哈罗德离家出走。当天正是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大会,而来自全国的示威者与当局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艾琳穿梭于骚乱的人群,寻找失踪的儿子,此时影片达到了高潮。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两夺奥斯卡最佳摄影的哈斯凯尔·韦克斯勒(HaskellWexler)。这部影片的摄影风格比较多变,但其反复出现的纪实风格的段落最引人注目。影片第一个场景是一个车祸现场,一位女性伤者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约翰和他的搭档似乎对伤者毫无怜悯,表情冷漠进行拍摄,甚至在拍摄完成之前都没有打电话叫救护车。接下来是一个聚会的场景。一群人在热烈讨论关于新闻伦理的话题。有人主张记者就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不应介入社会事件,另外有些人则强调记者本身应该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从技术上说,这个段落包含手持摄影、长镜头、单一视点等纪实手法。
这个段落中很多镜头都有明显的技术缺陷。下面四帧画面是从同一个镜头中截取的。其中第二和第三帧画面显然已经失焦了。除了失焦,在这个段落中,摄影机始终在晃动,没有一个稳定的固定镜头。很多画面在构图上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同时,多次出现的推拉摇移等镜头内部、外部的运动也显得仓促、忙乱,不时出现摇摆、顿挫。这些都凸显了手持摄影机抓拍的特征。
长镜头是这个段落的重要表现手段。在长达3分15秒的时间里,只有十几个镜头。这个段落最后一个镜头长达45秒,其中包含了推、拉镜头,左摇、右摇镜头等。尽管也有摄影机本身的微小运动,但总的来说,几乎所有镜头都是从同样一个角度拍摄的。下面的四帧画面是从这个段落中四个不同镜头中分别截取出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致是从一个方向拍摄下来的。影片导演试图让观众感觉只有一台摄影机在现场,并且这台摄影机只在一个严格受限的位置上完成拍摄。
这个段落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其剪辑完全依赖于人们的谈话内容。尽管讨论是在一个总的话题之下,但是确切的议题每个人都不同。镜头从一个人切到另一个人,内容很少连贯。这就造成了一种效果,让人觉得这这个段落只是一系列未经任何安排的随机谈话的现场记录。
这个段落的摄影与之前车祸现场的段落完全不同。在那个段落里,创作者采取了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全知视点。但这个段落里,由于上述手段的运用,创作者强化了在银幕上展现的事件与观众之间摄影机的明确存在。这是这部影片为营造一种纪录片外观而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不止一次约翰的采访对象直视镜头,表情各异地侃侃而谈。这也是对摄影机在场的承认。在影片结尾处,一直被暗示存在的摄影机甚至被直接呈现在了银幕之上。这是影片最后的一个镜头。先是一个远景镜头,逐渐拉开,向右摇,导演韦克斯勒和他的摄影机以全景进入镜头。镜头逐渐推上,一直推向摄影机的镜头,直至边界消失、形成黑场,影片结束。显然这个镜头有着强烈的自我反射的色彩。它打破了剧情片的幻觉,让观众得以一瞥影片制作的后台。这个镜头的处理会在观众中产生一种间离的效果,使得观众从故事情节中瞬间摆脱出来,将影片本身的制作过程也视为一种历史存在。这里影片展示的已经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说的“第二层次的叙事”或前苏联电影先驱吉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所说的“次级主题”了。从观众的角度说,这种对影片的接受方式显然是属于纪录片式的。
二
如果说《冷酷媒体》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直接电影的影像风格的话,那么《二十四城记》则是系统运用真实电影中的采访来形成影片整体结构的绝佳范例。与直接电影不同,真实电影不追求绝对的、未受干预的真实。它所强调的是影片创作者介入事件后,“撞击产生的真实”。在真实电影里,创作者作为社会角色之一,主动地介入事件,展开采访或搜集信息,与其他社会角色进行互动。它采用和直接电影相类似的技术手段,如同期声、长镜头等,完整捕捉镜头前影片创作者与他人的互动过程。采访、口述是真实电影的重要标志。在比尔·尼科尔斯(BillNichols)的早期文章中,直接称其为“采访引导”或者“基于采访”的影片类型。
《二十四城记》讲述了成都一家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军工企业420厂的荣辱兴衰和工作、生活在这个厂里的几代人命运。据说贾樟柯为了这部影片,曾经历时一年多进行采访,前后接受采访的职工有三十多位。贾樟柯为此整理出了四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最后的影片中包含了九个被采访对象的访谈。这些访谈对象有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本人,有的人物是由专业演员来扮演的。虽然影片中也有一些采访之外的故事情节,但那些都只起到陪衬的作用。九个采访支撑起了影片的总体结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九个角色以外,影片中还有一个核心角色不应该被忽略,这就是贾樟柯本人。与《冷酷媒体》中的约翰类似,这里贾樟柯扮演的也是一名记者。只不过《冷酷媒体》中的约翰有着丰满的个人形象,整个影片的叙事也围绕他而展开,《二十四城记》中的贾樟柯则没有任何视觉形象,只有他采访的声音偶尔出现在声轨。比如在采访陈冲扮演的“小花”的时候,小花说到她刚到厂里的时候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标准件”,这时贾樟柯问道:“(标准件是)什么意思?”之后贾樟柯又问:“您真名叫什么?”“当时是不是好多人追你呀?”这些问话突出了贾樟柯的在场。此外,角色在讲述过程中,经常会有黑场的隔断,这和贾樟柯的插话一样,也是影片强化访谈这种形式的一种手段。
除了对于采访形式的借用以外,《二十四城记》中还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被拍摄对象直视镜头的独立段落。这也是纪录片常用的表现手段之一。早在《北方的那努克》中,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J. Flaherty)就曾在影片的开始采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主人公那努克。这种处理让人容易回想起19世纪80年代以前,用三脚架照相机进行20秒曝光的摄影术。在那种情况下,拍摄者必然要参与对拍摄现场的组织,而被拍摄者也一定要摆出合适的姿势和表情。这种摆拍和快照相比,感觉完全不同。在《二十四城记》中,多次出现身穿工装的工人静静地凝视摄影机镜头,画面中的人物有了一种雕塑感。这个时候被拍摄者的表情、衣着、姿态、所处环境、以及身边的物品摆放都有一定的设计。这种画面不同于手持摄影机抓拍的画面。这是一种明确的摆拍,是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一种共谋。观众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感受画面中的人物,体会其中可能蕴含的各种细致的含义。19世纪意大利艺术评论家乔瓦尼·莫雷利(GiovanniMorelli)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完全认识意大利的历史,那么,请仔细端详人物肖像……在他们的脸上总有那么一些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东西有待解读,只要你知道如何去解读。”《二十四城记》中对这些普通职工的这种处理,也是如此。从效果上说,既增添了影片的历史感,又传递出难以言说的情绪。这是这部影片对纪录片手段的又一次成功借用。
三
每个人都生活、行动于特定的空间之中。由于电影画面具有多重信息同步呈现的特点,电影对人物、事件的刻画与其背后的空间背景无法分离,“空间其实始终在场,始终被表现。”从概念上说,剧情片的空间和纪录片的空间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虚构的,后者则是现实中的真实空间。但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开始,就有剧情片打破摄影棚的限制,到现实世界里进行拍摄。贾樟柯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影响,从第一部作品《小山回家》(1995)开始,他就一直坚持纪实的风格,也一直坚持实景拍摄。在影片《二十四城记》中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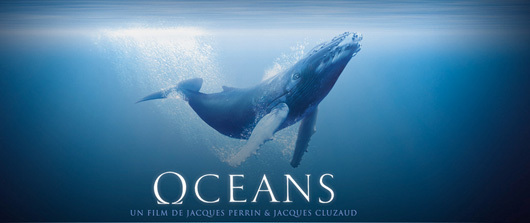
在影片开始字幕结束后,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一辆装载着从420厂拆卸下来的大型设备的卡车,行驶在街头。这时字幕告诉我们,这里是成都。除了成都市的街景,影片中出现更多的420厂镜头。片中的九个采访也大多在公共空间中完成。比如采访关凤久是在一个大礼堂。其时礼堂的舞台上两个年轻人正在打羽毛球。采访侯丽君是在一辆夜间行驶的公交车上。采访小花则是在一个居民区的小发廊里。贾樟柯曾经对自己一直遵循的实景拍摄方式做出解释。他说:“……把戏剧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发生,那个空间里的人该干嘛干嘛,但是我的戏在那里展开。”在贾樟柯看来,这个现实空间不仅仅是指静态的城镇、街道、建筑,还有其中形形色色流动中的人。比如在影片《小武》(1998)的开头,小武出场之前,镜头乡间公路旁一个等车的少年,接着镜头捕捉了一个农民家庭送女儿远行的画面。这个空间是真实的空间,这些人也都是真实的人,这些画面实际上都是纪录片性质的。在《二十四城记》中,虽然主体结构都是采访,但是类似的画面也有一些。贾樟柯电影中这种对当下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场景、人物的捕捉和表现,使得影片很大程度具备了一种接近于直接电影的精神气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评价贾樟柯的另一部影片《三峡好人》(2006)的时候就曾经指出,由于影片非常真切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三峡拆迁的大背景,因而影片就“同时具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变迁时代的重要痕迹和人们所感到的揪心的那些(内容)。”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也一语道出了贾樟柯的电影理想。
如果说包括《二十四城记》在内的贾樟柯的电影将虚构的故事巧妙地纳入到了现实的空间,那么《冷酷媒体》所做的就更前进一步,将虚构的人物、事件与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结合到了一起。在影片《冷酷媒体》中,当艾琳的儿子哈罗德发现母亲与约翰的亲昵行为后,离家出走。艾琳焦急万分地寻找。当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进行,在会场外,来自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与示威者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警察动用了装甲车、催泪瓦斯来驱散示威者。示威者用公园中的长椅搭起路障,阻挡警察的进攻。镜头捕捉了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贴身肉搏,哭喊、叫骂、厮打,场面极度混乱。有些示威者被打得血流满面,有些受伤的示威者被担架抬走。艾琳裹挟在这场骚乱之中,脸上不时闪现出恐慌和惊愕的表情。这个时候艾琳的扮演者已经很难说是在进行纯粹的表演了,她所做出的很大程度是面对残酷暴行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承受这种冲击的甚至不仅仅是艾琳的扮演者,肩扛摄影机进行拍摄的哈斯凯尔·韦克斯勒等人也是一样。当警方向示威者发动袭击的时候,一颗催泪弹就在摄影机前突然爆炸。这时影片声轨上传来一声急切的呼喊:“小心,哈斯凯尔!这个(催泪弹)是真的!”这显然是镜头后面摄制组的人情急之下的自然反应。一般来说,在剧情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影镜头前的剧情空间和摄影镜头后摄制组所在的现实空间性质不同,二者有着清晰的物理分隔。但纪录片与此不同,纪录片摄影镜头前后都属于同一个现实空间。这个段落中,镜头前的催泪弹和镜头后的呼喊提醒我们,至少在这个段落中,这个界限是不存在的。
四
相较于剧情片,纪录片往往对社会政治议题具有更直接的关注,其传播可以直接作用于外部世界,能够影响事件的发展,甚至产生具体可见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称之为“严肃话语”(discourseofsobriety)。为了准确传达有关的信息、对事实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进而实现说服观众的目的,逻辑性的推理、论证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影片的手段往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推理、论证可能直接通过影片创作者或被采访对象的语言来构成,也可能通过对不同事件的选择、安置,含蓄地传达出特定的立场和观点。这和以叙事为核心的剧情片的结构方式形成很大不同。在《冷酷媒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纪录片的结构方式。
影片中,导致主人公约翰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采访一位拾金不昧的黑人司机时所经历的事。由于很少有白人记者在没有警察陪同下来到这里,从街头到的司机住所,不断有黑人们他们进行威胁、挑衅。他们见到了黑人司机,但他却拒绝接受采访。当约翰准备撤离的时候,却又被其他一些黑人拦住了去路。约翰试图摆脱纠缠,却险些酿成冲突。在一位比较理智的黑人的劝说下,约翰真的坐下来倾听几位黑人的声音。黑人们表达了对自身处境的不满,特别是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压迫。一位黑人谈到他们之所以拿起武器、诉诸暴力是因为权力阶层对他们的处境漠不关心。另一位黑人激动地指着镜头说:“你们为什么不说出事情的真相?真要等到死了人才去关注吗?很快就会有人被弄死了。”这句话之后转场,画面是一位白人妇女面目狰狞地对着镜头开枪射击。这个场景就是一个射击场。约翰采访射击场的白人老板,他说到自从去年的骚乱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购买枪支保护自己的安全,枪支注册数量快速增长。比较这两个场景,在叙事上二者并无直接关联,时间、地点也互不相干。是共同的主题,即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族群矛盾问题,将两个段落联系到了一起。这种处理和一般的以叙事为中心的剧情片有所区别,它更多是属于纪录片式的。类似这样的处理在《冷酷媒体》其他部分还有很多。比如在开场的车祸段落中,约翰表现出了媒体的冷酷无情,接下来的场景就是一群人争论新闻媒体的伦理问题。这种结构方式对于叙事的推动微乎其微,却将影片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
与《冷酷媒体》相比,以采访形式构成的《二十四城记》虽然在形式上更像一部纪录片,但却缺乏纪录片一般应该具备的对于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19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强制性移民,它彻底改变了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但那些历史的当事人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影片中侯丽君在公交车上的访谈可能是影片最打动人心的一段了。当时她的父母告别亲人从沈阳来到成都是被迫,几十年亲人骨肉分离是被迫,今天下一辈的侯丽君们失业也是被迫。这些悲惨的个人际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二十四城记》无意回答。影片只是捕捉了这些精彩的个人故事,并将其演绎成了一段段的传奇。
英国纪录片理论家布莱恩·温斯顿(BrianWinston)在讨论约翰·格里尔逊(JohnGrierson)纪录片创作的时候曾经说道,格里尔逊和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结构纪录片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不论什么选题,不论其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需要在影片中进行分析。温斯顿指出:“这种方法的关键就在于,将影片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个人的身上。”笔者曾经撰文说明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新纪录片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策略,即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取代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并由此实现了纪录片的“去政治化”。从这个角度说,《二十四城记》在一个令人失望的方向上实践了中国新纪录片的表达模式。
虽然在概念上剧情片与纪录片之间有着明确的身份区别,但二者在表达形式上却有着模糊的边界。本文的讨论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就《二十四城记》来说,如果影片放弃了陈冲、吕丽萍、赵涛、陈建斌等明星,转而采用一批非职业演员来表演,很多人恐怕也会将其认作是一部纪录片。在《冷酷媒体》发行的前两年,美国曾经有一部严格依照真实电影风格制作的剧情片《大卫·霍尔兹曼日记》(DavidHolzman's Diary,1967)。一直到看到影片最后的演职员字幕,人们才意识到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个有剧本、有演员的剧情片。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虽然有些手法、策略更多地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他们同样也都能为剧情片所用,并非为纪录片的专属。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本文的标题没有直接使用“纪录片手法”一词,而是在前面加了“传统”二字进行限定。文中讨论的手法或源于纪录片,或在历史上更多地被用于纪录片,但他们本身无法构成“纪录片手法”这个类别。严格地说,这个类别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这些手法可以被用于剧情片,那么他们就不再是纯粹的“纪录片手法”了。这是一个悖论。其根源就在于,纪录片与剧情片从来不是在表现手法上区分彼此的。要判断一部影片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甚至任何局限于文本内部的考察都是不够的。此时我们必须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本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纳入视野。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远非本文所能胜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