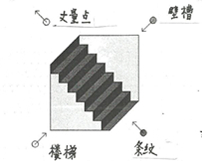——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考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谭光辉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经历了64年时间,其中小说叙事模式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必然世界叙事到可能世界叙事的转变。必然世界叙事与可能世界叙事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用来描述一种叙事态度:故事到底在讲述事物(世界)发展的必然性,还是讲述事物(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必然世界叙事重在表现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基本意图在于证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证明社会必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叙事重在表现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因为种种偶然,社会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还有种种偶然,社会还可能成为其他样子。从必然叙事向可能叙事的转变,是对世界、社会发展认知发生转变的结果。
一、可能世界与必然世界
可能世界概念的提出者是比柏拉图更早的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处于无秩序、无规律运动中的原子偶然巧合组成的,因而存在无数个可能的世界。柏拉图反对这种宇宙观,认为宇宙是被按某种理念创造的,有其本原。理念世界靠理性把握,作为理念世界的摹本的现象世界靠感官认识。柏拉图的理论中包含两个世界: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不包括可能世界。
德谟克利特的可能世界概念启发了莱布尼兹,他的理论在18世纪闻名遐尔。莱布尼兹认为,在上帝的观念中有无穷个可能的世界,上帝在许多可能的世界里选出了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所包含的可能的邪恶最少、最适宜、最完满。一旦这个世界被选出来,其中的所有事物就必然会是过去和现在的样子。必然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一,是具有本体地位的那个世界。
可能世界概念被纳入形而上学思考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发展可能世界理论。模态逻辑学家刘易斯《论可能世界的复多性》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我们的世界只是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事物本来可以按无数种方式与它们现在的样子不同”,可能世界是某种现实世界,是独立于我们语言和思想之外的实体。
至今,对可能世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观点被称为激进的实在论;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被称为非实在论,以亚当斯、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可能世界语句集论”支持了非实在论,认为可能世界并不与现实世界一样真实存在,它只处理命题及其真假关系,是一种技术手段;以克里普克的观点为代表的被称为温和实在论,有人称为“可能世界状态论”。克里普克的主要观点是:“可能世界并不是与现实世界并列的真实存在,真实存在的世界只有现实世界,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及其各种可能的状态。”[1]
上述三种观点各有道理,但是对可能世界最基本的认识却有一个共识,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清理出这样几组关系:可感世界一定可能,可能世界未必可感。可感世界一定可知,可知世界未必可感。可能世界必然可知,可知世界未必可能。这几组概念的关系在哲学理解上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清楚明了。
可能世界是逻辑可能世界,逻辑上不可能的世界是不可能世界。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提出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两个命题可以同时为真。二律背反现象表明:逻辑也是有限度的,逻辑会导致理性内部的矛盾。现代量子理论的研究发现量子的特性是多种可能同时存在。这一理论大大地丰富了可能世界理论,在现实世界之外,在我们周围同时存在无数可能世界。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同时为真,且逻辑不可能世界也可能为真。即是说,逻辑不可能在另一个领域也可变为可能。量子理论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基本态度,世界是平行、多元的,一个文本是多个世界的叠加,“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想看到什么。”“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批评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2]同理,作家观察世界并对世界加以描写,关键不在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作家用什么样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文学的作用并非复制再现一个可感(可见)世界,也非描述世界的必然趋势,也不止于描述逻辑可能世界,而是对多个可能世界的展开。
必然性指世界一定向某个方向发展的趋势。现在,必然性用来描述在一切可能世界都必然要发生的趋势。在实际思维操作过程中,必然世界指世界按因果律一定会朝某方向发展的未来世界或按因果律已经成为现实或历史的世界。必然世界的概念,必须依赖于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并且已存在的物又会成为原因而导致另一个必然的结果。可能世界理论说明正反命题在逻辑上都可以同时为真,矛盾律在其他世界不一定成立,必然性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必然性。换言之,即使对世界是必然还是可能的判断这一命题本身,都要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视角和方法。
作家以一个视角观察、想象世界,他所观察的世界相当于一个文本,是多个可能世界的叠加,他的理解受制于他的观察方式。一旦作品被写出,作品文本又构成一个文本现实,这个文本又可被批评家看作是多个可能世界的叠加,阐释结果受制于批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方式。另一方面,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理解方式不可能不受到他所看到的文本的引导。即是说,观察者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观察者的主体性之获得,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确立的。在现代批评理论中,他者被视为一种可能的世界[3],世界由无数的他者组成,也就由无数的可能组成。所以,可能世界不仅是构成世界的本体,而且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可能世界理论的烛照下,历史、现实、未来都不再被理解为必然,而是变得捉摸不定,不再可靠。用可能世界理论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会发现一条作家和批评家对世界观察方式变化的线索。
二、当代初期二十七年文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前二十七年文学在哲学观念上受制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可能世界的观点看,这个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主要按照莱布尼兹的方式理解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按照莱布尼兹的观点,上帝因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选择了它,这个选择是依据善的原则,即道德的必然性而决定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现实都是必然的结果。当代初二十七年文学的认识论基础,与这一思想暗合。
1.将现实世界理解为必然世界
这种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瞿秋白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瞿秋白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发,论述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关系。按他的说法,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之所以有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决不能因为‘不知因果’便说‘没有因果’。”[4]按这种理解,所有成为现实的都是因果的必然。但是,“不知因果”固然不能说“没有因果”,“不知因果”也不能说“一定有因果”。既然因果是未知,如何能够推导出现实世界就是必然世界呢?瞿秋白的论断在逻辑上犯了错误,其理论本原是对世界普遍因果联系的承认。“没有因果”和“一定有因果”之说都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又是可以共存的判断。康德从逻辑上论证了世界是必然的是正确的,世界是偶然的也是正确的,瞿秋白的论证直接武断地判定历史是必然的,与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理论是一致的。问题是,既然历史是必然的,那么人又如何能够获得自由?瞿氏却认为必然世界可以向自由世界飞跃,这从逻辑上说很难以理服人。
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中国当代文学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证现实世界是必然的世界。几乎在所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观的影子,用艺术的手法表现革命的必然胜利,英雄人物也都充分地相信现存世界是必然如此的。《红岩》中的英雄都抱着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坚定不移,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个推论逻辑的问题在于:如果胜利真是必然的,那么即使不要信念,胜利仍然会到来。如果需要信念才能取得胜利,那胜利就不是必然的,胜利是依赖于信念的。既然需要依赖信念胜利才会到来,那么现实世界的基础就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人的信念。即是说,推动历史的并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的意志。反过来看,人之所以能够有这个信念,又要依赖于对必然律的认同。要对必然律认同,又需要另一个信念——对必然律的信念。那么推动历史发展的到底是规律还是人的意志?终点到底在哪里?从这个逻辑谁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现象:英雄成了上帝。按照莱布尼兹的观点,在众多可能世界中,上帝选择了最完满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英雄、人民按这一准则选择了这个世界。所以,革命传奇小说是一种将“英雄”和“人民”进行神化的思维方式。
假若我们不承认这个神话,将“英雄”和“人民”还原为人本身,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种思维模式。因为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自然也是人,然而人因为存在自由意志,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不是必然的行为,而是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按存在主义观点,人永远是自由的,人的自由选择成就了人自身。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之间有一种交互影响的作用,现实世界会干扰人的自由选择。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与他者的关系是人存在之根本。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也是互动的二维之一维,另一维是他人的自由意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推动历史的基点是人的自由意志。既然如此,历史的发展也就不存在必然,历史是人的自由意志相互干扰、影响、选择的结果。把现实世界看作必然世界,把既成事实看作必然结果的思维乃是强制性的倒推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或显或隐地呈现在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之中,给人强烈的暗示效应。
《红旗谱》讲述了三代农民的革命道路。朱老巩的旧式农民革命被叙述为失败,被理解为他没找到正确的道路而必然失败。朱老忠跨越新旧两个时代,旧时代的农民式革命的失败也被理解为必然的失败。他后来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正确的革命道路导致斗争的胜利也就被理解为必然,因为有新社会这一事实作为最有力的隐含证据。这一思维模式推导出两个更加具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在正确的领导下,农民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只要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农民革命就能够取得胜利。正确的道路与领导,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即,只要有了正确的道路与领导,胜利就是必然,现实就是必然。因为现实具有不可置疑的说服力,所以上述逻辑就不可被驳倒。
同样的逻辑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小说之中。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解放与幸福,与卢嘉川的党派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林道静才可能走出个人生活的阴影,那个正确的前途才会摆在她的面前。在林道静面前,等待她的就只剩一条路,因为其它道路都在她的尝试中被逐一否定。因为现实不需要论证,事实胜于雄辩,所以,除了“现实”这个必然性之外,人的解放不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按照可能世界理论,文学虚构都是属于可能世界的范围,因为虚构毕竟不是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十七年历史小说隐含了一个认知前提:无论在哪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中,结果都是不变的——现实世界。因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必然要发生的趋势就是必然性,所以当代初十七年的经典小说大都把虚构的可能世界导向了必然世界。例如《创业史》让我们认识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趋势,《红日》向我们昭示了解放战争的历史风云和胜利的必然,《林海雪原》展示了英雄的必然胜利,等等。我们之所以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小说中有一种必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些小说中很难看到偶然性,故事情节大都有严格的因果逻辑,好人与坏人的分野是由这些人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物偶然选择造成的结果。
将现实世界理解为必然世界的观念,不仅在小说中有暗示,在对这些小说进行评介的话语中更为明显。何其芳在《林海雪原》出版后不久即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如果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要求,就不能不说这部作品虽然正确地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军事斗争的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总趋势,然而对于当时的艰苦困难还是表现得不够。”主要原因是《林海雪原》的描写“常常是自然的困难超过了敌人给与我们的困难”[5]。何其芳的意思是,描写军事题材的作品,总趋势应该是“所向无敌、无坚不摧”。何其芳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对文艺政策的理解很具有代表性,可见对于军事题材的处理,结局的胜利必须被处理为必然,失败是不允许的。另一位叫何家槐的评论者则认为《林海雪原》“对于党的领导作用是写得不够的”,“太少反映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斗争,太少反映人民的成长和人民的力量”[6],这个评论反映了战争必然胜利的原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这些原因和结果已经成为战争小说的一种必要的模式,因而战争题材小说是不能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而对《创业史》等小说的评价则反映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政策性要求。例如冯牧在1960年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文章评价《创业史》说:“正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所决定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生动地看到了农村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的鲜明图景,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了广大农村历史发展法则和走向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7]李希凡则说:“而这幅画卷,所以能获得那样丰富的艺术形象的表现,那样有说服力地展示了五亿农民必然要走向集体化的生活道路,就是由于作者并不是一般地描写这个革命群众运动的过程……”[8]如此观点的评论在对多数的文学作品的评介中均可找到,在此不用更多举例,对当代文学初期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稍微熟悉的读者都能体会到这种逻辑。
2.将可能世界处理为必然世界
文学作品均可被理解为虚构,哪怕它有写实的成份。从叙述学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可被视为虚拟叙述者的叙述,因而所有小说都可视为虚构。既然为虚构,它表现的世界就只能是可能世界。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当代二十七年的小说又几乎都在用虚拟的可能世界论证一个必然的世界。这个必然世界不仅是如上文所述的现实世界,它还可以是尚未变成现实的未来世界。
从可能世界的观点来看,未来的世界只能是可能世界,而不会是必然世界。即使像“人必然是要死的”这样的命题也未见得绝对正确。因为“人必然会死”这条规律是用归纳法得出的,而归纳法永远不能穷尽被归纳的对象。所以,凡是对未来必然如何的预言,其实都只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个真理。毕竟,谁也不敢保证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当代二十七年的小说大多数是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对未来题材涉及相当少。偶有涉及对未来的信念的小说,也一定是对未来之必然性的坚信。对未来题材的拒绝已经证明了当代初期二十七年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拒绝,而少数涉及未来展望的小说也一定暗示了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与走向。《创业史》(第一部)和《上海的早晨》都有未完成的特点,但是都预示了未来的必然道路,如孟繁华所言:这两部小说“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是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9]即是说,虽然我们尚未看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未来形态,但是我们知道它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因为我们是按照既定的目标在对它们进行改造,而胜利又是必然,所以,未来的社会形态就是必然的。这一逻辑支撑了二十七年小说中为数极少的涉及未来的小说的形态。
赵毅衡认为,中国的未来小说,除了世纪初十年和最后十年有过未来小说的集束出现之外,其他阶段几乎一片空白。现代三十年只出现过老舍的《猫城记》和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两部,当代四十年几乎绝迹。赵毅衡所说的未来小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未来小说,指叙述者的时间立足点在未来之未来,讲述在那个时间点已成往事的未来[10]。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初二十七年的小说确实找不到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未来小说,但是却有不少小说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凡是没有结局的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对未来的预期。
许多评论者都敏锐地捕捉住了小说对未来的预期,例如顾松明评《创业史》:“只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农民才有光辉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创业史、幸福史。”[11]1995至1999年间,“红色经典”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社重印,策划者和出版者称:“小说中刻画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一批栩栩如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12]“未来和希望”说得并不具体,但是读者都知道是什么未来和希望。
对未来、希望之可能视为必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社会发展道路的操作过程中将这些可能过快地变成现实。在大跃进年代直接将必然的信念提到现实层面就是这种“希望与未来”浮出水面的具体表现。
3.对其他可能世界的拒绝
建国初二十七年的文学,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最高指导纲领。《讲话》以严格的政治标准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第一原则,拒绝不为“工农兵”服务的一切文艺,因此也就拒绝了对规定的必然性以外的其他设想。《讲话》的核心,就是规定了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方式、对未来的展望的唯一性和必然性,用必然性代替事实和信念。
整个讲话一万八千多字,一共用了133个“要”,22个“必须”,13个“一定”,5个“必要”,4个“决心”,1个“必然”,1个“必定”。通过用词考察,我们发现《讲话》提的要求很多,用比较强势的话语对文艺的未来做了规定,从而对不符合设想的可能加以排斥。因此,建国初二十七年文学的世界观是一种被规定了的世界观,规定之外的可能世界叙事是不受欢迎的,这从历次文学大批判中也可得到印证。
拒绝可能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小说中首先设定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叙述者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描写“正面人物”的言行与内心活动以证明其选择的正确与合理,同时不愿花过多的笔墨去描写“反面人物”的言行与内心活动,不深入挖掘反面人物或错误路线执行者之所以作此选择的理由。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表现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张栓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形象,他倒腾牲口,失败后便想卖地。宋老定是在资本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路线之间徘徊的形象,想买张栓的地,最终在党员儿子东林的劝说下放弃了买地行为,借钱给张栓度过了难关。小说对张栓的心理活动描写很少,而对宋老定的描写很多,突出了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对土地买卖行为的可能性予以否定。
由于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需要给政治意图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都不能解释其他路线的合理性,政治干预是杜绝表现其他可能世界的最重要的原因。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表现农业合作化道路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落后分子失败,农村进行合作化改造,农村幸福生活的前景呈现在眼前。政治方向限定了作品只能描绘符合政治意图的康壮大道,文学批评也只能以此为评判标准。
综上所述,建国初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的总体倾向是拒绝对多个可能世界的展开,未来只剩一种可能,这唯一的可能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倾向。这种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停止了对未来多种可能的有益探索,从而限制了文学想象,文化因此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三、新时期以来文学叙事对可能世界的展开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从可能世界的观点看,这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在于否定世界发展的必然性,承认偶然性和可能性。批评“两个凡是”意味着思想向其他可能敞开,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鼓励对可能世界的探索。这次思想解放,把中国的未来向多种可能敞开,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
可能世界的打开在文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本就应该是对可能世界的描述,其生命力正是在可能世界中展开想象、探索可能。新时期文学起初努力做到的是对必然世界叙事模式的否定,对按必然性思维推动的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与批评。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代表了对历史进行否定的思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意义在于,它通过文学故事证明,我们曾经认为必然正确的路线与方向,事实上不利于人的健康发展,并不正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打开了一个反面的可能世界:按曾经的路线,可能导致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改革文学的思维模式有质的飞跃,因为改革文学不再致力于证明过去的正确或错误,而是提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多种可能摆在面前,做出正确的抉择反而成了这个时代人的痛苦与难题。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次重要变革,因为它开始向未来敞开。张炯的判断很有道理:“把‘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乃至‘寻根文学’等量齐观,是不恰当的。它将是一个更为恒定的文学现象。它所反映的不仅是过去十年,而且是未来数十年间中国向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进程。”[13]“改革文学”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对可能和未来的探索、疑惑、展望等主题,是新时期文学真正剧变的开始。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多部小说都贯穿了这一思想特征。《乔厂长上任记》的要点在于,乔光朴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无数的矛盾,生活极其复杂,未来不会只有一种或两种结果,而是可能有多种结果。《赤橙黄绿青蓝紫》写出了改革的丰富多彩的特征,表达了人生应有的要义:“人应该是全颜色的,单色不好。”即是说,人应该有多种生存的可能,人与人应该不同,同一个人也可以有多种生存方式。
如果说改革文学展开了现实与未来可能,那么寻根文学则展开了文化可能,先锋小说敞开了人性可能。此处不得不提及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八十年代的全面传播,具有极为深广的颠覆作用。武侠小说展开了一切可能:历史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人性可能呈现多种状态;人的武功可能极为高强;结局可能很难预料。因为武侠小说把现实世界挪移到江湖世界,于是便为现实世界开拓了无穷可能。武侠小说的纯虚构性质对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最大的挑战。因为武侠小说的受众面远远大于同时期其他类型小说,所以其中的虚构情节塑造了文学读者对可能世界的接受倾向性,以致他们不再愿意被一个必然的未来束缚住想象的翅膀。这导致一个事实上的结果:从80年代中后期至今,最具轰动效应的小说往往是那些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的、带有更多虚构性的小说。历史成了“新历史”,现实成了“新写实”,魔幻成为文学新宠。可能世界叙事在新时期的全面发展,以新历史小说和未来小说的出现为标志,以魔幻小说的全面兴盛为结束。
怀疑现实往往以怀疑历史为开端。在中国历史上,通过历史否定现实的方式常有两种:一是复古,二是否定。古人常用复古主义,今人常用批判思维。新文学以否定历史开端,以戏说历史为其高潮。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样本,以《狂人日记》否定历史始,以《故事新编》戏说历史终。新时期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否定历史始,以新历史小说的蓬勃发展终。莫言是这个转变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作为新历史小说的样本的《红高粱》[14],不再致力于宏大的历史画卷和历史必然性的描写,而是在历史中还原与人的野性相关的各种细节。莫言的所有小说,都不再被必然世界束缚,而是在可能世界中翱翔。历史被人性化、魔幻化、民间化,宏大的必然世界被细微的可能世界遮蔽,人被拉入各种可能之中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其罪恶与伟大,凡人的神性被重新塑造出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新历史小说的另一个样本,人物玩世不恭,但他却能够用锐利的眼睛观看世界,质疑历史,历史被画上花脸,供人们取乐、嘲笑、鞭挞,历史不再神圣,变成了囚徒,历史成为叙述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主体。对待历史的第三种态度是“戏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戏说历史渐成风潮,大批古装电视剧开始重述帝王将相王孙贵族,《宰相刘逻锅》、《康熙微服私访》、《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汉武大帝》、《戏说乾隆》等“戏说”历史系列电视连续剧陆续上映,反响热烈,这类作品揭去正史严肃的面纱,给历史以另外的解释,带领观众在可能世界中遨游,给历史一个轻松的喜剧色彩。
对历史的考问、嘲弄、戏说、神魔化、细节化,都是对历史的可能理解,但历史仍然停留在历史的层面。至21世纪,偶然的历史导致如今的现实也被作家思考。何大草《所有的乡愁》描写了一个情节,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荒诞性: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一个惊慌逃跑躲在屋梁上避难的木匠尿急淋熄了清军的大炮焾子,历史被一泡尿改变。无数的偶然最终发展为现实的世界,现实中的偶然终将成为令人捉摸不透的历史,还将发展为更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未来,人类历史哪有必然?历史没有必然,但是有可能。正是今天对可能世界的探索精神,才会造就未来。没有人为我们提供可能世界,世人将面临选项的匮乏,未来也就没有了可能,对可能世界的探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几篇典型的未来小说,是对未来可能的探索,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讽刺。王小波的《白银时代》(1994─1997),将叙述时间设定在2020年,讲述2010年和2015年的故事。虽说未来叙事很多时候只是玩了一个时间游戏,想说的仍然是关于现实的隐喻,但是时间毕竟设定在未来,它讲述的一定不是真实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可能的故事。《白银时代》关心的,不是未来世界将如何美好光明,而是对未来乌托邦的反动,“是在完成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描绘及批判”[15],“都是秩序混乱的反乌托邦”[16],即是说,关于未来乌托邦之必然,被王小波用既轻松又严肃的故事尽数瓦解,未来不美好的可能敲响了现实的警钟。如果说鲁迅用沉着的态度预言了未来必然不美好,那么王小波则用轻松的态度预言了未来可能不如意,如赵毅衡所言,“既然能够找出原因,走向未来之路,并非绝对不可改变。”[17]即是说,鲁迅的绝对悲观导向必然绝望的世界,而王小波的可能绝望的世界引领人们改变现实以避免进入鲁迅预言的未来。同样是对现实的悲观,两位文学家却采取了相反的叙述态度,这是对未来世界的两种认知方式在文学上的呈现。
王力雄的《黄祸》(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1)以匿名方式发表,表现未来生态灾难,中国成为世界中心,中国的解放使全世界有了未来,中国为世界提供发展模式,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遥相呼应。梁晓声的《浮城》(花城出版社,1992)虚构1999年的故事,一座中国沿海城市漂向大海,城内失控,各色人等上演谋私利丑事。浮城漂向日本,日本拒绝城中人登陆。中国军舰来救,城人拒绝回国,因为他们相信浮城正在漂向美国。《浮城》类似科幻小说,讽刺90年代出国热潮。乔良《末日之门》(1995)是一部军事外交未来小说,设想中国军队有强大的未来作战能力,所有强国在混乱中都不得不向中国求救,中国军官成为世界级的大英雄。虹影的《康乃馨俱乐部》、《来自古国的女人》、《千年之末义和团》作于1993年至1995年,写的是1999年的上海。三部小说合称“女子有行”,以“我”的视角审视中国女性在未来世界的命运。曾经的“实践的乌托邦,榨干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未来小说却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作家想象力的大爆炸,“未来小说之功用,恰恰是荒唐背后的认真,在不可能世界中构筑某种可能。”[18]
“在不可能世界中构筑某种可能”是未来小说的基本思维模式,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历史世界中构筑可能遂成为80年代以来小说叙述模式的最大变化,玄幻小说是这个叙述模式变化的产物。在玄幻小说中,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时空可以穿越,人类可以修仙,历史可以改写,现实可以改变,未来可以预知。在玄幻小说中,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一切皆有可能,其中包括逻辑不可能。玄幻小说正是“可能世界”大爆炸的产物。
对于潜心表现现实的小说,也没有被必然世界的叙述模式束缚,现实的多元取代了一元,生活突然变得无比丰富。邓晓芒评论新世纪作家的创作时说:“对使他们困惑的问题,他们可以以性命相拼,但更多地是诉之以清醒的理智和逻辑,是创造语言去建构一个超越现实之上的‘可能世界’,是坚持‘应有’而不和‘实有’相妥协。”[19]这大约就是新世纪文学家对世界最基本的认知态度。底层文学被新世纪批评家赋予了最具现实精神的称谓,但是多数底层文学作家从来没有认同一个“实有”的世界。一方面,底层文学展示了现实世界中多元化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底层文学家展开了对现实生存空间最强有力的批判态度,坚持“应有”的生存空间,以期鼓励人们探索未来生存空间的可能。
对于新世纪小说而言,时间不再是重点。小说的功用,不仅表现为批判、隐射、设想、娱乐、教育等常规功能,小说已成为解放人自身最有效的方式。
四、结论
总而言之,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最大变化,就是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都逐渐允许多种可能性的并存。这个转变可以视为对可能世界的认识论从莱布尼兹模式向刘易斯模式和量子论模式转变的结果。因为世界本来可以有很多形态,所以想象力可以被无限挖掘。又由于观察视角与方式不同也可能导致事物呈现出不同形态,所以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是“并在”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能世界叙事的兴盛,打开了国人的眼界、思维,在建构新的文化形态、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能世界叙事不仅是认识论,也是本体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必然世界叙事向可能世界叙事的转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嬗变的核心线索。
[1] 臧勇:《论模态逻辑中的“跨界同一”》,王南湜主编:《南开哲学》(第一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2] 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
[3] 王杰、仪平策:《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趋势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4] 瞿秋白:《瞿秋百文集》(文学编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7页。
[5] 何其芳:《谈“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林海雪原〉评介》,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29页。
[6] 何家槐:《略谈“林海雪原”》,同上,第37、39页。
[7] 冯牧:《初读<创业史>》,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创业史>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页。
[8] 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同上,第31页。
[9]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10] 赵毅衡:《可怕的不对称:中国的未来小说》,赵毅衡:《言不尽意: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121页。
[11] 顾松明:《中国小说漫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12]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
[13] 张炯:《张炯文存》(第3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
[14] 谭伟平:《现代中国文学教程》,第134页。该书认为,《红高粱》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在中国的发先声之作”。
[15] 韩袁红:《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16] 赵毅衡:《可怕的不对称:中国的未来小说》,赵毅衡:《言不尽意──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17] 赵毅衡:《可怕的不对称:中国的未来小说》,赵毅衡:《言不尽意──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18] 赵毅衡:《可怕的不对称:中国的未来小说》,赵毅衡:《言不尽意──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110页。
[19] 邓晓芒:《论21世纪中国文学的前景》,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