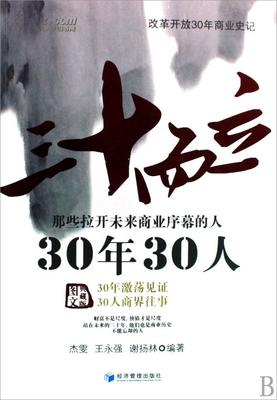饿死鬼的由来
那天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我热火朝天的正吃在兴头上,偶一抬头,只见男士们喝酒聊天,女士们拿着筷子象征性的加一点点菜放进嘴里,慢慢嚼来。唯有我一个忘情的埋头苦干,我突然感到很尴尬,马上整理一下学做淑女状,一点点的慢慢吃,但觉得很不尽兴,别扭的很。你想想,那淑女是能装出来的么?在这种场合,拿筷子的手似乎不听脑子的指挥,照样稳准狠的伸向各种美味佳肴。
为此我常常很痛苦,别人大概背后都会叫我“饿死鬼托生的”,也是,哪个女人家会有这样不雅的吃相呢?想起小时候我妈妈对我们非常严厉,吃饭时不许说话,吃面条时不许发出吸溜的响声。(这点最残酷:吃面条不吸溜还有什么劲?)有人说了,家教严还吃成这样,若不严,岂不要剁下脑袋往里灌?但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原因:因为我生在1951年,经历了难忘的自然灾害(后来我知道,人祸远远大于天灾),童年时代吃不饱饭的滋味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又有人说了,生在那个年代的人千千万万,未必人人都像你一样是饿死鬼。我只能说像我这样的“饿死鬼托生的”人,势必要比一般的人痛苦的多,因为我属于“天生有副好下水”永远吃不饱的人。
现如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但每每吃起小时憧憬着的美味时,我都会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吃不饱饭的艰难年代。
60年我刚9岁,个子不高,很瘦。因吃不饱,脑子里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我记得那时都在食堂吃饭,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为什么不在家里吃饭。家里的阿姨也不做饭,每天领着我端着大锅去食堂打饭,每人的定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是一天7两半,早上一碗很稀的汤,一个馒头,这样用去二两半,中午三两米饭,那米饭里面百分之九十是胡萝卜,少得可怜的米饭掺和在里面,每次我都狼吞虎咽的先把乏味的胡萝卜吃完,然后把攒起来的一小撮米饭就上菜,一口咽下,回味半天。晚上只剩下二两,一碗稀汤和半个馒头就用完了一天的定量。后来回忆起这段时间,我才知道那时多么幸福,虽吃不饱,但终究吃的都是粮食,蔬菜,再到后来,吃糠咽菜的时代到来了。
记不清到了哪年,每天只能吃些豆腐渣,海带根,还有树叶杂粮做成的菜团子。豆腐渣在今天上好的东西,但那时的豆腐渣却难以下咽,因为那渣子被压榨的太干了,吃到嘴里剌嗓子眼儿,得伸着脖子才能咽下去。还有海带根,非常坚硬,要使劲嚼,牙口不好的绝对吃不了。
我每天饿的够呛,美味佳肴只有在梦中出现,吃一个白面馒头成了心中的梦想。那时有一个政策是70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定比例的白面供应,我奶奶的白馒头都会留给我小妹妹吃,我只能在一边看着,后来索性不看了,实在受不了那样的痛苦和煎熬。有一天,阿姨让我去买饭,剩余了一张儿二两的饭票,我犹豫了半天,战战兢兢装在了口袋里。饭票在口袋装了好几天,没人时掏出来看了又看,揉的皱皱巴巴的也没敢用。终于有一天,晚饭后我跑进食堂,那时买饭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师傅在吃饭,我鼓足勇气掏出饭票,买了一个馒头,师傅说,“都凉了,没事吧?”
“没事!”我接过馒头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到机关院子的外面,看看没人,狼吞虎咽的吃完了那个白面大馒头。那馒头虽然凉了,但还算酥软,我几乎来不及品味就吞了下去。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中许多年不敢讲,怕大人们打我,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偷吃粮食,这是不能饶恕的罪行,至少我当时这样认为。几十年后我讲给妹妹们听,她们又讲给我妈妈,没想到我妈妈说:“怎么没听她讲起?她饿成那样,吃个馒头还能说她吗?”多年后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
后来有一天,好消息传来,我爸爸每个月可领一张券,用它可带领家人去指定的饭店吃一顿好东西。我记得头几次是我奶奶和我哥哥跟着去的,我和妹妹羡慕的看着他们,想象着满桌的美味佳肴,我们的口水咽进肚子里。终于有一天我也要去那家饭店了,一进门,久违的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我的心通通直跳,肚子叽里咕噜的响着,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的好东西如今就摆在眼前,这是在做梦吗?
那天,我吃了许多从未吃过的好吃的饭菜,印象最深的却是那白白的富强粉小花卷。平日里杂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里,看见又白又软的小花卷,我的心里很难受,又想起了偷吃馒头的那件事,若是知道有一天能有富强粉花卷吃,我就不会胆战心惊的去偷馒头了。
不知又到了什么年头,局势似乎有些好转,粮食的比例明显大于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吃不饱饭仍是常事。忽然又一天,食堂传来好消息:今天吃油条!这是何等的振奋人心!记不清多长时间没有吃过油条了,它的味道已经忘光了,当我把金灿灿的油条拿在手中时,绝望的差点哭出来——那是用羊油炸的油条!
我从小不吃羊肉,因为那个膻味儿实在受不了,不要说吃,闻着都会恶心。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虽然吃不下去,我仍旧没有放弃,决心试一试。我心中默默地念着着,这可是最最好吃的油条啊!快吃啊!咬了一大口迅速的咽下去,生理的本能反应让我吐了出来,看着手中的油条,我还是没舍得把它丢掉。下午上学的路上我还带着那根油条,因为是羊油炸的,凉了之后变得很硬,上面还泛着一层白色,膻味愈发浓重。我下最后一次决心再试一次,结果可想而知,当我无奈的要把它扔掉时,我心中的遗憾让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几年后,文革开始了。大串联时在火车上,拥挤的人群让我动弹不得,头顶的架子无数条腿耷拉着,座椅下也躺着人,那场面,能和现在春运相匹敌。我站在那,试着把双脚同时抬起也没倒下,就这样无聊的四下张望,忽然有个大人在拥挤的红卫兵小将中艰难跋涉往前冲,我忽然看到,他高高举起的手中是一只用黄色草纸包着的烧鸡!在那个革命的年代,烧鸡似乎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是哪个无产阶级不知道那是何等美味的好东西啊!火车上烧鸡的价钱是一块钱一只,现在想起来好像是白给的。但在那个每月收只有二三十块钱收入的年代,吃烧鸡无疑是奢侈的享受。望着高举烧鸡的手臂渐渐远去,我想,等将来我有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只烧鸡自己一个人把它吃掉!当时我就被自己这远大的志向感动的热泪横流。
但凡有过这样惨痛经历的人,肌饿的感受能够忘记吗?它已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要感谢那个伟大的年代,它让我多年之后仍保持着旺盛的食欲,让我成了“饿死鬼托生的”,我想,这有什么不好呢?不知有多少人艳羡不已呢!想想看,没有好胃口的人,对美好生活的体味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