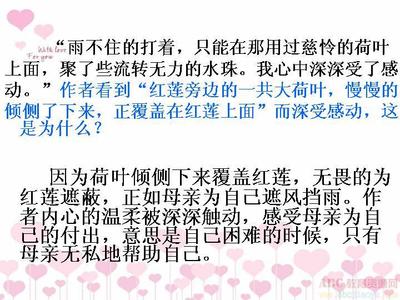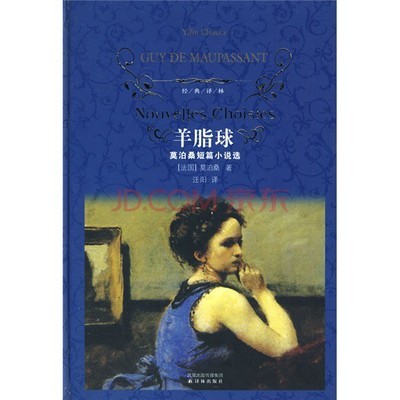他们经历了生活的困苦颠连;
能做到这种地步也就是胜利,
尽管他们输掉了赌博的本钱。
他们两个一瘸一拐地,吃力地走下河岸,有一次,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中间失
足摇晃了一下。他们又累又乏,因为长期忍受苦难,脸上都带着愁眉苦脸、咬牙苦熬的
表情。他们肩上捆着用毯子包起来的沉重包袱。总算那条勒在额头上的皮带还得力,帮
着吊住了包袱。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来复枪。他们弯着腰走路,肩膀冲向前面,而脑袋冲
得更前,眼睛总是瞅着地面。
“我们藏在地窖里的那些子弹,我们身边要有两三发就好了,”走在后面的那个人
说道。
他的声调,阴沉沉的,干巴巴的,完全没有感情。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前面的那
个只顾一瘸一拐地向流过岩石、激起一片泡沫的白茫茫的小河里走去,一句话也不回答。
后面的那个紧跟着他。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虽然河水冰冷——冷得他们脚腕
子疼痛,两脚麻木。每逢走到河水冲击着他们膝盖的地方,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
跟在后面的那个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差一点没摔倒,但是,他猛力一挣,
站稳了,同时痛苦地尖叫了一声。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一面摇晃着,一面伸出那只闲
着的手,好像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站稳之后,他再向前走去,不料又摇晃了一下,
几乎摔倒。于是,他就站着不动,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
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好像心里在说服自己一样。接着,他就叫了起
来:“喂,比尔,我扭伤脚腕子啦。”
比尔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他没有回头。
后面那个人瞅着他这样走去;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眼睛里却流露着跟一头受伤
的鹿一样的神色。
前面那个人一瘸一拐,登上对面的河岸,头也不回,只顾向前走去,河里的人眼睁
睁地瞧着。他的嘴唇有点发抖,因此,他嘴上那丛乱棕似的胡子也在明显地抖动。他甚
至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来舐舐嘴唇。
“比尔!”他大声地喊着。
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患难中求援的喊声,但比尔并没有回头。他的伙伴干瞧着他,
只见他古里古怪地一瘸一拐地走着,跌跌冲冲地前进,摇摇晃晃地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
向矮山头上不十分明亮的天际走去。他一直瞧着他跨过山头,消失了踪影。于是他掉转
眼光,慢慢扫过比尔走后留给他的那一圈世界。
靠近地平线的太阳,象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几乎被那些混混沌沌的浓雾同蒸气遮
没了,让你觉得它好像是什么密密团团,然而轮廓模糊、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个人单腿
立着休息,掏出了他的表,现在是四点钟,在这种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季节里——他说
不出一两个星期之内的确切的日期——他知道太阳大约是在西北方。他瞧了瞧南面,知
道在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就是大熊湖;同时,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北极圈的禁区界线
深入到加拿大冻土地带之内。他所站的地方,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铜矿河本身则向北
流去,通向加冕湾和北冰洋。他从来没到过那儿,但是,有一次,他在赫德森湾公司的
地图上曾经瞧见过那地方。
他把周围那一圈世界重新扫了一遍。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到处都是模糊
的天际线。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
片辽阔可怕的荒野,迅速地使他两眼露出了恐惧神色。
“比尔!”他悄悄地、一次又一次地喊道:“比尔!”
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好像这片广大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压着他,
正在残忍地摆出得意的威风来摧毁他。他象发疟子似地抖了起来,连手里的枪都哗喇一
声落到水里。这一声总算把他惊醒了。他和恐惧斗争着,尽力鼓起精神,在水里摸索,
找到了枪。他把包袱向左肩挪动了一下,以便减轻扭伤的脚腕子的负担。接着,他就慢
慢地,小心谨慎地,疼得闪闪缩缩地向河岸走去。
他一步也没有停。他象发疯似地拼着命,不顾疼痛,匆匆登上斜坡,走向他的伙伴
失去踪影的那个山头——比起那个瘸着腿,一瘸一拐的伙伴来,他的样子更显得古怪可
笑。可是到了山头,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寸草不生的浅谷。他又和恐惧斗争着,克服
了它,把包袱再往左肩挪了挪,蹒跚地走下山坡。
谷底一片潮湿,浓厚的苔藓,象海绵一样,紧贴在水面上。他走一步,水就从他脚
底下溅射出来,他每次一提起脚,就会引起一种吧咂吧咂的声音,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
吸住他的脚,不肯放松。他挑着好路,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并且顺着比尔的脚
印,走过一堆一堆的、象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
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却没有迷路。他知道,再往前去,就会走到一个小湖旁边,
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枞树,当地的人把那儿叫作“提青尼其利”——意思是
“小棍子地”。而且,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溪水不是白茫茫的。
溪上有灯心草——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但是没有树木,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
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这条溪是向
西流的,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那里,在一条翻了的独木船下面可
以找到一个小坑,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还有钓
钩、钓丝和一张小鱼网——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同时,他还会找到面粉——并不
多——此外还有一块腌猪肉同一些豆子。
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接着,他们就会在湖里
朝南方划,一直朝南,直到麦肯齐河。到了那里,他们还要朝着南方,继续朝南方走去,
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让湍流结冰吧,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他们会向南走
到一个暖和的赫德森湾公司的站头,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
了。
这个人一路向前挣扎的时候,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也同
样苦苦地绞着脑汁,他尽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
他。
他不得不这样想,不然,他就用不着这样拼命,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当那团模
糊的象圆球一样的太阳慢慢向西北方沉下去的时候,他一再盘算着在冬天追上他和比尔
之前,他们向南逃去的每一寸路。他反复地想着地窖里和赫德森湾公司站头上的吃的东
西。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至于没有吃到他想吃的东西的日子,那就更不止两天了。
他常常弯下腰,摘起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果,把它们放到口里,嚼几嚼,然后吞下去。
这种沼地浆果只有一小粒种籽,外面包着一点浆水。一进口,水就化了,种籽又辣又苦。
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份,但是他仍然抱着一种不顾道理,不顾经验教训的希望,耐
心地嚼着它们。
走到九点钟,他在一块岩石上绊了一下,因为极端疲倦和衰弱,他摇晃了一下就栽
倒了。他侧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会。接着,他从捆包袱的皮带当中脱出身子,
笨拙地挣扎起来勉强坐着。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他借着留连不散的暮色,在乱石
中间摸索着,想找到一些干枯的苔藓。后来,他收集了一堆,就升起一蓬火——一蓬不
旺的,冒着黑烟的火——并且放了一白铁罐子水在上面煮着。
他打开包袱,第一件事就是数数他的火柴。一共六十六根。为了弄清楚,他数了三
遍。他把它们分成几份,用油纸包起来,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
子的帽圈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做完以后,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慌,于是把
它们完全拿出来打开,重新数过。
仍然是六十六根。
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毡袜子有好多地方都磨穿
了,两只脚皮开肉绽,都在流血。一只脚腕子胀得血管直跳,他检查了一下。它已经肿
得和膝盖一样粗了。他一共有两条毯子,他从其中的一条撕下一长条,把脚腕子捆紧。
此外,他又撕下几条,裹在脚上,代替鹿皮鞋和袜子。接着,他喝完那罐滚烫的水,上
好表的发条,就爬进两条毯子当中。
他睡得跟死人一样。午夜前后的短暂的黑暗来而复去。
太阳从东北方升了起来——至少也得说那个方向出现了曙光,因为太阳给乌云遮住
了。
六点钟的时候,他醒了过来,静静地仰面躺着。他仰视着灰色的天空,知道肚子饿
了。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一种很大的呼噜声把他吓了一跳,他看见了一只公鹿,
它正在用机警好奇的眼光瞧着他。这个牲畜离他不过五十尺光景,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
鹿肉排在火上烤得咝咝响的情景和滋味。他无意识地抓起了那支空枪,瞄好准星,扣了
一下扳机。公鹿哼了一下,一跳就跑开了,只听见它奔过山岩时蹄子得得乱响的声音。
这个人骂了一句,扔掉那支空枪。他一面拖着身体站起来,一面大声地哼哼。这是
一件很慢、很吃力的事。他的关节都象生了锈的铰链。它们在骨臼里的动作很迟钝,阻
力很大,一屈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最后,两条腿总算站住了,但又花了一分钟左
右的工夫才挺起腰,让他能够象一个人那样站得笔直。
他慢腾腾地登上一个小丘,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小树丛,什么
都没有,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色苔藓,偶尔有点灰色的岩石,几片灰色的小湖,几条灰
色的小溪,算是一点变化点缀。天空是灰色的。没有太阳,也没有太阳的影子。他不知
道哪儿是北方,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走到这里的。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
向。
这他是知道的。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小棍子地”。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
而且不远——可能翻过下一座小山头就到了。
于是他就回到原地,打好包袱,准备动身。他摸清楚了那三包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
虽然没有停下来再数数。不过,他仍然踌躇了一下,在那儿一个劲地盘算,这次是为了
一个厚实的鹿皮口袋。袋子并不大。他可以用两只手把它完全遮没。他知道它有十五磅
重——相当于包袱里其他东西的总和——这个口袋使他发愁。最后,他把它放在一边,
开始卷包袱。可是,卷了一会,他又停下手,盯着那个鹿皮口袋。他匆忙地把它抓到手
里,用一种反抗的眼光瞧瞧周围,仿佛这片荒原要把它抢走似的;等到他站起来,摇摇
晃晃地开始这一天的路程的时候,这个口袋仍然包在他背后的包袱里。
他转向左面走着,不时停下来吃沼地上的浆果。扭伤的脚腕子已经僵了,他比以前
跛得更明显,但是,比起肚子里的痛苦,脚疼就算不了什么。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它
们一阵一阵地发作,好像在啃着他的胃,疼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到“小棍子地”必须
走的路线上。沼地上的浆果并不能减轻这种剧痛,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反而使他的舌头和
口腔热辣辣的。
他走到了一个山谷,那儿有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地里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它们
发出一种“咯儿-咯儿-咯儿”的叫声。他拿石子打它们,但是打不中。他把包袱放在地
上,象猫捉麻雀一样地偷偷走过去。锋利的岩石穿过他的裤子,划破了他的腿,直到膝
盖流出的血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迹;但是在饥饿的痛苦中,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他
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弄得衣服湿透,身上发冷;可是这些他都没有觉得,因为他想吃
东西的念头那么强烈。而那一群松鸡却总是在他面前飞起来,呼呼地转,到后来,它们
那种“咯儿-咯儿-咯儿”的叫声简直变成了对他的嘲笑,于是他就咒骂它们,随着它们
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
有一次,他爬到了一定是睡着了的一只松鸡旁边。他一直没有瞧见,直到它从岩石
的角落里冲着他的脸窜起来,他才发现。他象那只松鸡起飞一样惊慌,抓了一把,只捞
到了三根尾巴上的羽毛。当他瞅着它飞走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恨它,好像它做了什么对
不起他的事。随后他回到原地,背起包袱。
时光渐渐消逝,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或者说是沼地,这些地方的野物比较多。一
群驯鹿走了过去,大约有二十多头,都呆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来复枪的射程以内。他心里
有一种发狂似的、想追赶它们的念头,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一只黑狐
狸朝他走了过来,嘴里叼着一只松鸡。这个人喊了一声。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那只狐
狸吓跑了,可是没有丢下松鸡。
傍晚时,他顺着一条小河走去,由于含着石灰而变成乳白色的河水从稀疏的灯心草
丛里流过去。他紧紧抓注这些灯心草的根部,拔起一种好像嫩葱芽,只有木瓦上的钉子
那么大的东西。这东西很嫩,他的牙齿咬进去,会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味道
很好。但是它的纤维却不容易嚼。
它是由一丝丝的充满了水份的纤维组成的:跟浆果一样,完全没有养份。他丢开包
袱,爬到灯心草丛里,象牛似的大咬大嚼起来。他非常疲倦,总希望能歇一会——躺下
来睡个觉;可是他又不得不继续挣扎前进——不过,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
“小棍子地”,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他在小水坑里找青蛙,或者用指甲挖土找小虫,
虽然他也知道,在这么远的北方,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小虫的。
他瞧遍了每上个水坑,都没有用,最后,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一
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象鲦鱼般的小鱼。他把胳膊伸下水去,一直没到肩头,但
是它又溜开了。于是他用双手去捉,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正在紧张的关头,
他掉到了坑里,半身都浸湿了。现在,水太浑了,看不清鱼在哪儿,他只好等着,等泥
浆沉淀下去。
他又捉起来,直到水又搅浑了。可是他等不及了,便解下身上的白铁罐子,把坑里
的水舀出去;起初,他发狂一样地舀着,把水溅到自己身上,同时,固为泼出去的水距
离太近,水又流到坑里。后来,他就更小心地舀着,尽量让自己冷静一点,虽然他的心
跳得很厉害,手在发抖。这样过了半小时,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剩下来的连一杯也
不到。
可是,并没有什么鱼;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
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如果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他
一开始就会把它堵死,那条鱼也就归他所有了。他这样想着,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
上。起初,他只是轻轻地哭,过了一会,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陶大哭;
后来,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
他升起一蓬火,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
露宿。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并且上好表的发条,毯子又湿又冷,脚腕子
疼得在悸动。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在不安的睡眠里,他梦见了一桌桌酒席和一次次宴
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
醒来时,他又冷又不舒服。天上没有太阳。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愈来愈阴沉昏
暗。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初雪铺白了山顶。他周围的空气愈来愈浓,成了白茫茫
一片,这时,他已经升起火,又烧了一罐开水。天上下的一半是雨,一半是雪,雪花又
大又潮。起初,一落到地面就融化了,但后来越下越多,盖满了地面,淋熄了火,糟蹋
了他那些当作燃料的干苔藓。
这是一个警告,他得背起包袱,一瘸一拐地向前走;至于到哪儿去,他可不知道。
他既不关心小棍子地,也不关心比尔和狄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的地窖。他完
全给“吃”这个词儿管住了。他饿疯了。他根本不管他走的是什么路,只要能走出这个
谷底就成。他在湿雪里摸索着,走到湿漉漉的沼地浆果那儿,接着又一面连根拔着灯心
草,一面试探着前进。不过这东西既没有味,又不能把肚子填饱。
后来,他发现了一种带酸味的野草,就把找到的都吃了下去,可是找到的并不多,
因为它是一种蔓生植物,很容易给几寸深的雪埋没。那天晚上他既没有火,也没有热水,
他就钻在毯子里睡觉,而且常常饿醒。这时,雪已经变成了冰冷的雨。他觉得雨落在他
仰着的脸上,给淋醒了好多次。天亮了——又是灰蒙蒙的一天,没有太阳。雨已经停了。
刀绞一样的饥饿感觉也消失了。他已经丧失了想吃食物的感觉。他只觉得胃里隐隐作痛,
但并不使他过分难过。他的脑子已经比较清醒,他又一心一意地想着“小棍子地”和狄
斯河边的地窖了。
他把撕剩的那条毯子扯成一条条的,裹好那双鲜血淋淋的脚。同时把受伤的脚腕子
重新捆紧,为这一天的旅行做好准备。等到收拾包袱的时候,他对着那个厚实的鹿皮口
袋想了很久,但最后还是把它随身带着。
雪已经给雨水淋化了,只有山头还是白的。太阳出来了,他总算能够定出罗盘的方
位来了,虽然他知道现在他已经迷了路。在前两天的游荡中,他也许走得过分偏左了。
因此,他为了校正,就朝右面走,以便走上正确的路程。
现在,虽然饿的痛苦已经不再那么敏锐,他却感到了虚弱。他在摘那种沼地上的浆
果,或者拔灯心草的时候,常常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他觉得他的舌头很干燥,很大,
好像上面长满了细毛,含在嘴里发苦。他的心脏给他添了很多麻烦。他每走几分钟,心
里就会猛烈地怦怦地跳一阵,然后变成一种痛苦的一起一落的迅速猛跳,逼得他透不过
气,只觉得头昏眼花。
中午时分,他在一个大水坑里发现了两条鲦鱼。把坑里的水舀干是不可能的,但是
现在他比较镇静,就想法子用白铁罐子把它们捞起来。它们只有他的小指头那么长,但
是他现在并不觉得特别饿。胃里的隐痛已经愈来愈麻木,愈来愈不觉得了。他的胃几乎
象睡着了似的。他把鱼生吃下去,费劲地咀嚼着,因为吃东西已成了纯粹出于理智的动
作。他虽然并不想吃,但是他知道,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吃。
黄昏时候,他又捉到了三条鲦鱼,他吃掉两条,留下一条作第二天的早饭。太阳已
经晒干了零星散漫的苔藓,他能够烧点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了。这一天,他走了不到十
哩路;第二天,只要心脏许可,他就往前走,只走了五哩多地。但是胃里却没有一点不
舒服的感觉。它已经睡着了。
现在,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带,驯鹿愈来愈多,狼也多起来了。荒原里常常传出狼
嗥的声音,有一次,他还瞧见了三只狼在他前面的路上穿过。
又过了一夜;早晨,因为头脑比较清醒,他就解开系着那厚实的鹿皮口袋的皮绳,
从袋口倒出一股黄澄澄的粗金沙和金块。他把这些金子分成了大致相等的两堆,一堆包
在一块毯子里,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藏好,把另外那堆仍旧装到口袋里。同时,他又从
剩下的那条毯子上撕下几条,用来裹脚。他仍然舍不得他的枪,因为狄斯河边的地窖里
有子弹。
这是一个下雾的日子,这一天,他又有了饿的感觉。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一阵一
阵地晕得什么都看不见。现在,对他来说,一绊就摔跤已经不是稀罕事了;有一次,他
给绊了一跤,正好摔到一个松鸡窝里。那里面有四只刚孵出的小松鸡,出世才一天光景
——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只够吃一口;他狼吞虎咽,把它们活活塞到嘴里,象嚼蛋壳
似地吃起来,母松鸡大吵大叫地在他周围扑来扑去。他把枪当作棍子来打它,可是它闪
开了。他投石子打它,碰巧打伤了它的一个翅膀。松鸡拍击着受伤的翅膀逃开了,他就
在后面追赶。
那几只小鸡只引起了他的胃口。他拖着那只受伤的脚腕子,一瘸一拐,跌跌冲冲地
追下去,时而对它扔石子,时而粗声吆喝;有时候,他只是一瘸一拐,不声不响地追着,
摔倒了就咬着牙、耐心地爬起来,或者在头晕得支持不住的时候用手揉揉眼睛。
这么一追,竟然穿过了谷底的沼地,发现了潮湿苔癣上的一些脚印。这不是他自己
的脚印,他看得出来。一定是比尔的。不过他不能停下,因为母松鸡正在向前跑。他得
先把它捉住,然后回来察看。
母松鸡给追得精疲力尽;可是他自己也累坏了。它歪着身子倒在地上喘个不停,他
也歪着倒在地上喘个不停,只隔着十来尺,然而没有力气爬过去。等到他恢复过来,它
也恢复过来了,他的饿手才伸过去,它就扑着翅膀,逃到了他抓不到的地方。这场追赶
就这样继续下去。天黑了,它终于逃掉了。由于浑身软弱无力绊了一跤,头重脚轻地栽
下去,划破了脸,包袱压在背上。他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久,后来才翻过身,侧着躺在地
上,上好表,在那儿一直躺到早晨。
又是一个下雾的日子。他剩下的那条毯子已经有一半做了包脚布。他没有找到比尔
的踪迹。可是没有关系。饿逼得他太厉害了——不过——不过他又想,是不是比尔也迷
了路。走到中午的时候,累赘的包袱压得他受不了。于是他重新把金子分开,但这一次
只把其中的一半倒在地上。到了下午,他把剩下来的那一点也扔掉了,现在,他只有半
条毯子、那个白铁罐子和那支枪。
一种幻觉开始折磨他。他觉得有十足的把握,他还剩下一粒子弹。它就在枪膛里,
而他一直没有想起。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始终明自,枪膛里是空的。但这种幻觉总是萦
回不散。他斗争了几个钟头,想摆脱这种幻觉,后来他就打开枪,结果面对着空枪膛。
这样的失望非常痛苦,仿佛他真的希望会找到那粒子弹似的。
经过半个钟头的跋涉之后,这种幻觉又出现了。他于是又跟它斗争,而它又缠住他
不放,直到为了摆脱它,他又打开枪膛打消自己的念头。有时候,他越想越远,只好一
面凭本能自动向前跋涉,一面让种种奇怪的念头和狂想,象蛀虫一样地啃他的脑髓。但
是这类脱离现实的逻思大都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饥饿的痛苦总会把他刺醒。有一次,正
在这样瞎想的时候,他忽然猛地惊醒过来,看到一个几乎叫他昏倒的东西。他象酒醉一
样地晃荡着,好让自己不致跌倒。在他面前站着一匹马。一匹马!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
的眼睛。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霎时间金星乱迸。他狠狠地揉着眼睛,让自己瞧瞧清楚,
原来它并不是马,而是一头大棕熊。这个畜生正在用一种好战的好奇眼光仔细察看着他。
这个人举枪上肩,把枪举起一半,就记起来。他放下枪,从屁般后面的镶珠刀鞘里
拔出猎刀。他面前是肉和生命。他用大拇指试试刀刃。刀刃很锋利。刀尖也很锋利。
他本来会扑到熊身上,把它杀了的。可是他的心却开始了那种警告性的猛跳。接着
又向上猛顶,迅速跳动,头象给铁箍箍紧了似的,脑子里渐渐感到一阵昏迷。
他的不顾一切的勇气已经给一阵汹涌起伏的恐惧驱散了。处在这样衰弱的境况中,
如果那个畜生攻击他,怎么办?
他只好尽力摆出极其威风的样子,握紧猎刀,狠命地盯着那头熊。它笨拙地向前挪
了两步,站直了,发出试探性的咆哮。
如果这个人逃跑,它就追上去;不过这个人并没有逃跑。现在,由于恐惧而产生的
勇气已经使他振奋起来。同样地,他也在咆哮,而且声音非常凶野,非常可怕,发出那
种生死攸关、紧紧地缠着生命的根基的恐惧。
那头熊慢慢向旁边挪动了一下,发出威胁的咆哮,连它自己也给这个站得笔直、毫
不害怕的神秘动物吓住了。可是这个人仍旧不动。他象石像一样地站着,直到危险过去,
他才猛然哆嗦了一阵,倒在潮湿的苔藓里。
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进,心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这不是害怕他会束手无
策地死于断粮的恐惧,而是害怕饥饿还没有耗尽他的最后一点求生力,他已经给凶残地
摧毁了。这地方的狼很多。狼嗥的声音在荒原上飘来飘去,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危险的罗
网,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吓得他不由举起双手,把它向后推去,仿佛它是给风刮紧了
的帐篷。
那些狼,时常三三两两地从他前面走过。但是都避着他。一则因为它们为数不多,
此外,它们要找的是不会搏斗的驯鹿,而这个直立走路的奇怪动物却可能既会抓又会咬。
傍晚时他碰到了许多零乱的骨头,说明狼在这儿咬死过一头野兽。这些残骨在一个
钟头以前还是一头小驯鹿,一面尖叫,一面飞奔,非常活跃。他端详着这些骨头,它们
已经给啃得精光发亮,其中只有一部份还没有死去的细胞泛着粉红色。难道在天黑之前,
他也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吗?生命就是这样吗,呃?真是一种空虚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只有活着才感到痛苦。死并没有什么难过。死就等于睡觉。它意味着结束,休息。那么,
为什么他不甘心死呢?
但是,他对这些大道理想得并不长久。他蹲在苔藓地上,嘴里衔着一根骨头,吮吸
着仍然使骨头微微泛红的残余生命。甜蜜蜜的肉味,跟回忆一样隐隐约约,不可捉摸,
却引得他要发疯。他咬紧骨头,使劲地嚼。有时他咬碎了一点骨头,有时却咬碎了自己
的牙,于是他就用岩石来砸骨头,把它捣成了酱,然后吞到肚里。匆忙之中,有时也砸
到自己的指头,使他一时感到惊奇的是,石头砸了他的指头他并不觉得很痛。
接着下了几天可怕的雨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露宿,什么时候收拾行李。他白天黑
夜都在赶路。他摔倒在哪里就在哪里休息,一到垂危的生命火花闪烁起来,微微燃烧的
时候,就慢慢向前走。他已经不再象人那样挣扎了。逼着他向前走的,是他的生命,因
为它不愿意死。他也不再痛苦了。他的神经已经变得迟钝麻木,他的脑子里则充满了怪
异的幻象和美妙的梦境。
不过,他老是吮吸着,咀嚼着那只小驯鹿的碎骨头,这是他收集起来随身带着的一
点残屑。他不再翻山越岭了,只是自动地顺着一条流过一片宽阔的浅谷的溪水走去。可
是他既没有看见溪流,也没有看到山谷。他只看到幻象。他的灵魂和肉体虽然在并排向
前走,向前爬,但它们是分开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
有一天,他醒过来,神智清楚地仰卧在一块岩石上。太阳明朗暖和。他听到远处有
一群小驯鹿尖叫的声音。他只隐隐约约地记得下过雨,刮过风,落过雪,至于他究竟被
暴风雨吹打了两天或者两个星期,那他就不知道了。
他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温和的太阳照在他身上,使他那受苦受难的身体充满了
暖意。这是一个晴天,他想道。
也许,他可以想办法确定自己的方位。他痛苦地使劲偏过身子;下面是一条流得很
慢的很宽的河。他觉得这条河很陌生,真使他奇怪。他慢慢地顺着河望去,宽广的河湾
婉蜒在许多光秃秃的小荒山之间,比他往日碰到的任何小山都显得更光秃,更荒凉,更
低矮。他于是慢慢地,从容地,毫不激动地,或者至多也是抱着一种极偶然的兴致,顺
着这条奇怪的河流的方向,向天际望去,只看到它注入一片明亮光辉的大海。他仍然不
激动。太奇怪了,他想道,这是幻象吧,也许是海市蜃楼吧——多半是幻象,是他的错
乱的神经搞出来的把戏。后来,他又看到光亮的大海上停泊着一只大船,就更加相信这
是幻象。他眼睛闭了一会再睁开。奇怪,这种幻象竟会这样地经久不散!然而并不奇怪,
他知道,在荒原中心绝不会有什么大海,大船,正象他知道他的空枪里没有子弹一样。
他听到背后有一种吸鼻子的声音——仿佛喘不出气或者咳嗽的声音。由于身体极端
虚弱和僵硬,他极慢极慢地翻一个身。他看不出附近有什么东西,但是他耐心地等着。
又听到了吸鼻子和咳嗽的声音,离他不到二十尺远的两块岩石之间,他隐约看到一
只灰狼的头。那双尖耳朵并不象别的狼那样竖得笔挺;它的眼睛昏暗无光,布满血丝;
脑袋好像无力地、苦恼地耷拉着。这个畜生不断地在太阳光里霎眼。它好像有玻正当他
瞧着它的时候,它又发出了吸鼻子和咳嗽的声音。
至少,这总是真的,他一面想,一面又翻过身,以便瞧见先前给幻象遮住的现实世
界。可是,远处仍旧是一片光辉的大海,那条船仍然清晰可见。难道这是真的吗?他闭
着眼睛,想了好一会,毕竟想出来了。他一直在向北偏东走,他已经离开狄斯分水岭,
走到了铜矿谷。这条流得很慢的宽广的河就是铜矿河。那片光辉的大海是北冰洋。那条
船是一艘捕鲸船,本来应该驶往麦肯齐河口,可是偏了东,太偏东了,目前停泊在加冕
湾里。他记起了很久以前他看到的那张赫德森湾公司的地图,现在,对他来说,这完全
是清清楚楚,入情入理的。
他坐起来,想着切身的事情。裹在脚上的毯子已经磨穿了,他的脚破得没有一处好
肉。最后一条毯子已经用完了。枪和猎刀也不见了。帽子不知在什么地方丢了,帽圈里
那小包火柴也一块丢了,不过,贴胸放在烟草袋里的那包用油纸包着的火柴还在,而且
是干的。他瞧了一下表。时针指着十一点,表仍然在走。很清楚,他一直没有忘了上表。
他很冷静,很沉着。虽然身体衰弱已极,但是并没有痛苦的感觉。他一点也不饿。
甚至想到食物也不会产生快感。
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只凭理智。他齐膝盖撕下了两截裤腿,用来裹脚。他总算
还保住了那个白铁罐子。他打算先喝点热水,然后再开始向船走去,他已经料到这是一
段可怕的路程。
他的动作很慢。他好像半身不遂地哆嗦着。等到他预备去收集干苔的时候,他才发
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他试了又试,后来只好死了这条心,他用手和膝盖支着爬来爬
去。有一次,他爬到了那只病狼附近。那个畜生,一面很不情愿地避开他,一面用那条
好像连弯一下的力气都没有的舌头舐着自己的牙床。这个人注意到它的舌头并不是通常
那种健康的红色,而是一种暗黄色,好像蒙着一层粗糙的、半干的粘膜。
这个人喝下热水之后,觉得自己可以站起来了,甚至还可以象想象中一个快死的人
那样走路了。他每走一两分钟,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他的步子软弱无力,很不稳,
就象跟在他后面的那只狼一样又软又不稳;这天晚上,等到黑夜笼罩了光辉的大海的时
候,他知道他和大海之间的距离只缩短了不到四哩。
这一夜,他总是听到那只病狼咳嗽的声音,有时候,他又听到了一群小驯鹿的叫声。
他周围全是生命,不过那是强壮的生命,非常活跃而健康的生命,同时他也知道,那只
病狼所以要紧跟着他这个病人,是希望他先死。早晨,他一挣开眼睛就看到这个畜生正
用一种如饥似渴的眼光瞪着他。它夹着尾巴蹲在那儿,好像一条可怜的倒楣的狗。早晨
的寒风吹得它直哆嗦,每逢这个人对它勉强发出一种低声咕噜似的吆喝,它就无精打采
地呲着牙。
太阳亮堂堂地升了起来,这一早晨,他一直在绊绊跌跌地,朝着光辉的海洋上的那
条船走。天气好极了。这是高纬度地方的那种短暂的晚秋。它可能连续一个星期。也许
明后天就会结束。
下午,这个人发现了一些痕迹,那是另外一个人留下的,他不是走,而是爬的。他
认为可能是比尔,不过他只是漠不关心地想想罢了。他并没有什么好奇心。事实上,他
早已失去了兴致和热情。他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的胃和神经都睡着了。但是内在的
生命却逼着他前进。他非常疲倦,然而他的生命却不愿死去。正因为生命不愿死,他才
仍然要吃沼地上的浆果和鲦鱼,喝热水,一直提防着那只病狼。
他跟着那个挣扎前进的人的痕迹向前走去,不久就走到了尽头——潮湿的苔藓上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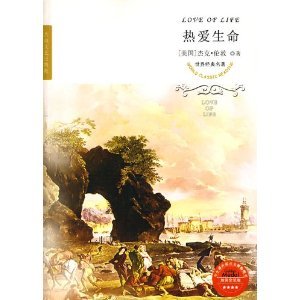
着几根才啃光的骨头,附近还有许多狼的脚樱他发现了一个跟他自己的那个一模一样的
厚实的鹿皮口袋,但已经给尖利的牙齿咬破了。他那无力的手已经拿不动这样沉重的袋
子了,可是他到底把它提起来了。比尔至死都带着它。哈哈!他可以嘲笑比尔了。
他可以活下去,把它带到光辉的海洋里那条船上。他的笑声粗厉可怕,跟乌鸦的怪
叫一样,而那条病狼也随着他,一阵阵地惨嗥。突然间,他不笑了。如果这真是比尔的
骸骨,他怎么能嘲笑比尔呢;如果这些有红有白,啃得精光的骨头,真是比尔的话?
他转身走开了。不错,比尔抛弃了他;但是他不愿意拿走那袋金子,也不愿意吮吸
比尔的骨头。不过,如果事情掉个头的话,比尔也许会做得出来的,他一面摇摇晃晃地
前进,一面暗暗想着这些情形。
他走到了一个水坑旁边。就在他弯下腰找鲦鱼的时候,他猛然仰起头,好像给戳了
一下。他瞧见了自己反映在水里的险。脸色之可怕,竟然使他一时恢复了知觉,感到震
惊了。这个坑里有三条鲦鱼,可是坑太大,不好舀;他用白铁罐子去捉,试了几次都不
成,后来他就不再试了。他怕自己会由于极度虚弱,跌进去淹死。而且,也正是因为这
一层,他才没有跨上沿着沙洲并排漂去的木头,让河水带着他走。
这一天,他和那条船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三英里;第二天,又缩短了两英里——因为现在
他是跟比尔先前一样地在爬;到了第五天末尾,他发现那条船离开他仍然有七英里,而他
每天连一哩也爬不到了。幸亏天气仍然继续放晴,他于是继续爬行,继续晕倒,辗转不
停地爬;而那头狼也始终跟在他后面,不断地咳嗽和哮喘。他的膝盖已经和他的脚一样
鲜血淋漓,尽管他撕下了身上的衬衫来垫膝盖,他背后的苔藓和岩石上仍然留下了一路
血渍。有一次,他回头看见病狼正饿得发慌地舐着他的血渍、他不由得清清楚楚地看出
了自己可能遭到的结局——除非——除非他干掉这只狼。于是,—幕从来没有演出过的
残酷的求生悲剧就开始了——病人一路爬着,病狼一路跛行着,两个生灵就这样在荒原
里拖着垂死的躯壳,相互猎取着对方的生命。
如果这是一条健康的狼,那末,他觉得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一想到自己要喂
这么一只令人作呕、只剩下一口气的狼,他就觉得非常厌恶。他就是这样吹毛求疵。现
在,他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又给幻象弄得迷迷糊糊,而神智清楚的时候也愈来愈少,
愈来愈短。
有一次,他从昏迷中给一种贴着他耳朵喘息的声音惊醒了。那只狼一跛一跛地跳回
去,它因为身体虚弱,一失足摔了一跤。样子可笑极了,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有趣。他
甚至也不害怕。他已经到了这一步,根本谈不到那些。不过,这一会,他的头脑却很清
醒,于是他躺在那儿,仔细地考虑。
那条船离他不过四哩路,他把眼睛擦净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同时,他还看
出了一条在光辉的大海里破浪前进的小船的白帆。可是,无论如何他也爬不完这四英里路。
这一点,他是知道的,而且知道以后,他还非常镇静。他知道他连半英里路也爬不了。不
过,他仍然要活下去。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他居然会死掉,那未免太不合理了。命
运对他实在太苛刻了,然而,尽管奄奄一息,他还是不情愿死。也许,这种想法完全是
发疯,不过,就是到了死神的铁掌里,他仍然要反抗它,不肯死。
他闭上眼睛,极其小心地让自己镇静下去。疲倦象涨潮一样,从他身体的各处涌上
来,但是他刚强地打起精神,绝不让这种令人窒息的疲倦把他淹没。这种要命的疲倦,
很象一片大海,一涨再涨,一点一点地淹没他的意识。有时候,他几乎完全给淹没了,
他只能用无力的双手划着,漂游过那黑茫茫的一片;可是,有时候,他又会凭着一种奇
怪的心灵作用,另外找到一丝毅力,更坚强地划着。
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现在,他能够听到病狼一呼一吸地喘着气,慢慢地向他逼
近。它愈来愈近,总是在向他逼近,好像经过了无穷的时间,但是他始终不动。它已经
到了他耳边。那条粗糙的干舌头正象砂纸一样地摩擦着他的两腮。他那两只手一下子伸
了出来——或者,至少也是他凭着毅力要它们伸出来的。他的指头弯得象鹰爪一样,可
是抓了个空。敏捷和准确是需要力气的,他没有这种力气。
那只狼的耐心真是可怕。这个人的耐心也一样可怕。
这一天,有一半时间他一直躺着不动,尽力和昏迷斗争,等着那个要把他吃掉、而
他也希望能吃掉的东西。有时候,疲倦的浪潮涌上来,淹没了他,他会做起很长的梦;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不论醒着或是做梦,他都在等着那种喘息和那条粗糙的舌头来舐他。
他并没有听到这种喘息,他只是从梦里慢慢苏醒过来,觉得有条舌头在顺着他的一
只手舐去。他静静地等着。狼牙轻轻地扣在他手上了;扣紧了;狼正在尽最后一点力量
把牙齿咬进它等了很久的东西里面。可是这个人也等了很久,那只给咬破了的手也抓住
了狼的牙床。于是,慢慢地,就在狼无力地挣扎着,他的手无力地掐着的时候,他的另
一只手已经慢慢摸过来,一下把狼抓住五分钟之后,这个人已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狼
的身上。他的手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把狼掐死,可是他的脸已经紧紧地压住了狼的咽喉,
嘴里已经满是狼毛。半小时后,这个人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馒流进他的喉咙。这东
西并不好吃,就象硬灌到他胃里的铅液,而且是纯粹凭着意志硬灌下去的。后来,这个
人翻了一个身,仰面睡着了。
捕鲸船“白德福号”上,有几个科学考察队的人员。他们从甲板上望见岸上有一个
奇怪的东西。它正在向沙滩下面的水面挪动。他们没法分清它是哪一类动物,但是,因
为他们都是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就乘了船旁边的一条捕鲸艇,到岸上去察看。接着,他
们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动物,可是很难把它称作人。它已经瞎了,失去了知觉。它就象一
条大虫子在地上蠕动着前进。它用的力气大半都不起作用,但是它老不停,它一面摇晃,
一面向前扭动,照它这样,一点钟大概可以爬上二十尺。
三星期以后,这个人躺在捕鲸船“白德福号”的一个铺位上,眼泪顺着他的削瘦的
面颊往下淌,他说出他是谁和他经过的一切。同时,他又含含糊糊地、不连贯地谈到了
他的母亲,谈到了阳光灿烂的南加利福尼亚,以及桔树和花丛中的他的家园。
没过几天,他就跟那些科学家和船员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饭了,他馋得不得了地望
着面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焦急地瞧着它溜进别人口里。每逢别人咽下一口的时候,他
眼睛里就会流露出一种深深惋惜的表情。他的神志非常清醒,可是,每逢吃饭的时候,
他免不了要恨这些人。他给恐惧缠住了,他老怕粮食维持不了多久。他向厨子,船舱里
的服务员和船长打听食物的贮藏量。他们对他保证了无数次,但是他仍然不相信,仍然
会狡猾地溜到贮藏室附近亲自窥探。
看起来,这个人正在发胖。他每天都会胖一点。那批研究科学的人都摇着头,提出
他们的理论。他们限制了这个人的饭量,可是他的腰围仍然在加大,身体胖得惊人。
水手们都咧着嘴笑。他们心里有数。等到这批科学家派人来监视他的时候,他们也
知道了。他们看到他在早饭以后萎靡不振地走着,而且会象叫化子似地,向一个水手伸
出手。那个水手笑了笑,递给他一块硬面包,他贪婪地把它拿住,象守财奴瞅着金子般
地瞅着它,然后把它塞到衬衫里面。别的咧着嘴笑的水手也送给他同样的礼品。
这些研究科学的人很谨慎。他们随他去。但是他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
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
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就是这么回事。研究科学
的人说,他会恢复常态的;事实也是如此,“白德福号”的铁锚还没有在旧金山湾里隆
隆地抛下去,他就正常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