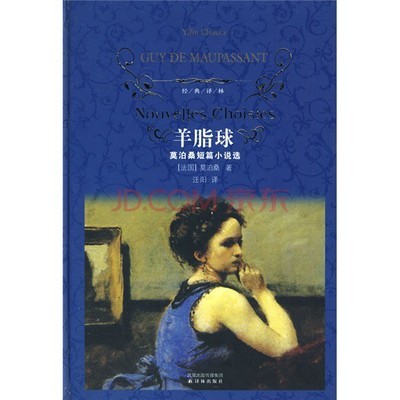刚刚在听一首琴曲《秋风词》,其词源自李白的《三五七言》: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只是琴曲中又添了几句: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何如当初莫相识”...倒让我想起了容若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然而人生中又哪来这般多的“如、若”呢...
李白的另几首《三五七言》,贴在这里,想来谱成曲子也会好听的心碎。
木叶黄,花渐褪。
流水与山静,黛影随心碎。
车与江水相低昂,寂寂虫吟人不寐。
灯影残,珠帘垂。
弱水自向东,相思渐成灰。
五粮酒好醉难欢,依稀梦影还相随。
风一缕,愁一缕。
树静栖野鹭,水冷隐河鱼。
未有江枫映渔火,但闻村笛断肠曲。
小苑静,漏断催。
月残树影乱,岸远水声微。
秋风吹尽花溅泪,且待冬心听雪醉。
天欲晓,思未了。
秋风瘦花影,流水乱岸草。
相逢未肯轻言笑,却叹青丝与花少。
一时间又对“三五七言诗”有了兴趣,于是找到了一篇文章:
试论李白《三五七言》的创作机制与体式特征
吉文斌
李白诗集中有一首为人称道的小诗,题为《三五七言》,其诗曰: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许多人认为它的体式很像一首小词,具有明显的音乐特性。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云:“三五七言诗起于李太白:‘秋风清,秋月明。……’此其滥觞也。刘长卿《送陆澧》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寇莱公《江南春》诗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林芳草远,斜日沓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①指出了它和“江南春”词牌的渊源关系。南宋邓深曾依此调式填写词作,名为“秋风清”。清人还把李白这首诗当作是一首创调词而收入《钦定词谱》,云:“本三五七言诗,后人采入词中。”②下面我们就从音乐文体的角度,对这首诗的创作机制、体式特征等进行一番新的探究。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本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诗体”一章就说道:“有三五七言。”自注云:“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世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郭绍虞先生校释曰:“沧浪所谓郑世翼有三五七言,不知何据。案《诗人玉屑》无‘秋风清’以下各句,以从《玉屑》为是。‘秋风清’云云,见《李太白集》,当是李作。”③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人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义净诗曰:
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诚难遇,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
关于义净这首诗的格式与性质,王昆吾先生《唐代酒令艺术》第四章“唱和”中予以论证,他认为《一三五七九言》应是义净和五行两人的“唱和之作”,而且它的形式也“反映了佛教偈赞对于唐代俳谐诗题的影响”④。这一推测是有根据的,义净之后的大历间出现的鲍防、严维、周政、张叔政等人的《入五云溪寄诸公联句从一字至九字》《登法华寺最高顶忆院中诸公从一字至九字》也采用联句形式,而白居易等人的“一字至七字诗”,则唱和多达十首。⑤因而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推论:李白这首与上述诗歌体式相似的《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像以上所举鲍防、严维等人的联句诗题就包括了内容和体裁两方面的要素,还如权德舆的《杂言赋得风送崔秀才归白田限三五六七言(暄字)》也是如此。就是义净诗的诗题,在他本人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提到时,也是正文作“一三五七九言”,小字注为“在西国怀王舍城旧之作”⑥。可能“一三五七九言”就为初题。再有《唐诗纪事》卷三九韦式条载:“乐天分司东洛,朝贤悉会兴化亭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云:……李绅赋《月》诗云……令狐楚赋《山》诗云……元稹赋《茶》诗云……魏扶赋《愁》诗云……韦式郎中赋《竹》诗云……张籍司业赋《花》诗云……范尧佐道士赋《书》字云……居易赋《诗》字诗云……”⑦同样是先确定诗歌格式再自命诗题。只不过李白的诗题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罢了。
“唱和诗”的主要表现为当场的相互酬答,那势必要求一个接一个地即兴把自己的诗作吟诵出来,这就涉及到某一种口头表达方式。同时,唱和活动又经常发生在文人集会和筵席间,这些场合正是歌辞类作品的主要出产地之一。而且,王昆吾先生曾认为:“唱和诗的艺术手法的演进,与唐著辞的艺术手法的演进大致同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唱和诗的格律来源的追溯,来认识唐著辞格律的一部分渊源”⑧。如果李白的诗确实为席间酬和之作,那就为它能作为歌词的可能性创设了更多的条件。
除此以外,有的学者还找到了“三五七言”辞式的另一渊源,如刘念兹先生就认为“唐代诗歌中除五、七绝律诗体之外,此种三五七言诗体应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诗体,在唐短歌中尤为突出。……其实汉魏乐府中‘望江南’即是此诗体之滥觞,唐人敦煌写本中亦累见”⑨。实际上,正如刘念兹先生所说,这类体式在李白之前以及同代作家的诗作中屡有出现。这当中有“单片式”的,如《读曲歌八十九首》中的一首曰:“坐起叹,汝好愿他甘,丛香倾筐入怀抱。”王勃的《江南弄》开头三句为:“江南弄,巫山连楚梦,行雨行云几相送。”顾况的《行路难?其三》曰:“君不见,古人烧水银,变作北邙山上尘。”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中也有这种格式:“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还有“部分叠加式”的,如晋代刘妙容的《宛转歌》曰:“月既明,西轩琴复清。寸心斗酒争芳夜,千秋万岁同一情。”王勃的《采莲归》里有:“相思苦,佳期不可驻。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唐代出现的词牌《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梦江南》等)的格律也为:“三五七七五”。这个词牌本来是唐教坊曲名,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⑩刘禹锡就有一篇作品,题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由此可以看到,这类辞格与唐代流行乐曲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杜甫诗集中还出现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格式:“三五+三五七七”,如《君不见简苏》开头:“君不见,道边废弃池。君不见,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中有:“君不见,西汉杜陵老。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归。”这种格式已经和李白的《三五七言》十分接近了,可算是一种变体。
但总的来说,在李白之前很少有像《三五七言》这样“双片叠加式”的情况。这种格式只有在李白的歌词类作品中才能找到,如:
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当安之。(《梁甫吟》)
帝不去,留镐京。安能为轩辕,独往入杳冥。
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春日竹》)
食不噎,性安驯。首农政,鸣阳春。天子刻玉杖,镂行赐耆人。
白鹭之白非纯真,外洁其色心匪仁。(《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
从内容和歌辞体制分析,它们都可以说是能够独立自足的曲段单位,是整体歌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第二例都用在歌辞末尾,节奏由急转徐,起伏摇曳。前四句特别是两个三字句的使用,为全曲将终时又掀起一处高潮,之后的两个七字句又把旋律线延长,这就为平稳毕曲铺设了一个圆弧形的轨道。拿《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来说,由于整个《白鸠辞》曲式由三个部分即三解构成,这个“三三三三五五七七”格式就是当中的第二解。从第一解的辞式“三三三三七七七”来看,第三解中多出的两个三字句是为了与第一解的双头格式相呼应而特意加上的,可看作“三五七言”体的一种附加体。并且,第二解的辞式与第一解保持了总体上的一致性,但也有所改变,那就是把第一解中的第一个七字句拆成了两个五字句,使乐曲主体部分的节奏更加鲜明多变,同时也符合了音乐旋律“寓变化于整体之中”的艺术美感。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能最终确立“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11}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吉文斌,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讲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