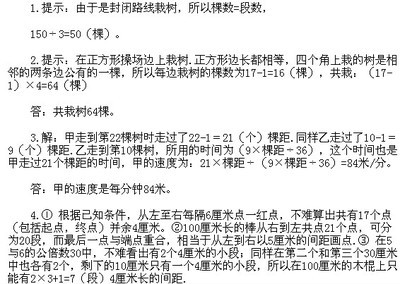【中庸胜唱】(中)
第二编正说分
第一章 统说《中庸》
第一节 总 论
【原文】
"梁太子昭明者,开《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为三十二分,识者悲之,谓妄割先圣伟范宏言,身陷地狱,名讥大雅。今先生割裂经义,开此十章,明知故犯邪?抑别有绍承而启未来邪?胡不远咎,自毁如此?"
先生曰:"余早晚入地狱也。"问者大惑。曰:“会么?”进云:"不会。"
【译文】
“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开《金刚经》为三十二分,有识之士对此感到伤心,说他妄自将先贤宏篇妙语割裂,死后将身陷地狱,受人讥笑。现如今先生分《中庸》为十章,难道是明知故犯吗?或者是先生另有传承而启发后人?为什么不远离是非之地而这样糟踏自己的名声?”
先生说:“我早晚要下地狱。”问话的人感到很迷惑,先生问道:“明白吗?”那人答道:“不明白。”
【原文】
先生曰:"昔赵州念云:‘我不入地狱,阿谁教化汝?'比来与若说玄说妙,说短说长,义已违乎胜谛,形固囚于情牢。昭明死入地狱,余今生困愁城。非仅余也,先圣后圣,无不共萦此苦。盖至高、至妙、难行、难信之法,初欲演之,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继欲缄口而众生长劫沉沦,爱河莫度,大径不游。故仲尼兴‘余无言'之叹。至若释迦掩室摩竭,净名缄口毗耶,《楞严》曰‘真非真恐泥,我常不开演',皆此义也。然则终不说乎?此固不可。于焉开方便,示权宜,横说竖说,以说说,以不说说。右之左之,前这之后之,上下之,总以奖策,或诱掖行人履乎中庸而已。既履也,是法可,非法亦可,开此经为十章、三十三章可,千章或一字一章、不立一章均无不可。不然,饶汝鞭笞三藏,驰骋五车,痴狂外边走也。何有于当人邪?今以十章说《中庸》,此而曰统,义固尚乎斯也。"
【译文】
先生说:“从前赵州从谂禅师说过‘我不下地狱,谁来教化你’,近来向你们谈玄讲妙,说短道长,已经违背了胜谛,本来就已经陷于情牢。昭明太子死后下地狱,我则是活生生给困在愁城中。不光是我,前贤来哲,没有不身受这种苦的。因为极高明、极精妙、极难实行、极难信服的法门,你想宣扬它,但它却不是语言能够说清楚、意识能够了知通的。你想沉默不言,但众生却眼看着身陷沉沦,在欲海沉浮而不能脱离,走不上解脱之道。所以孔子才会感叹道:‘我想沉默不语’,还有释迦在摩竭陀国沉默无语,在毗耶离维摩诘不答一语,《楞严经》讲‘真理一旦僵化就不是真理,所以我常常不讲解’,都是这个意思。那最终就不能说了吗?这当然不行。于是就有各种方便,指示各种权宜之法,横说竖说,以说为说,以不说为说,左讲右讲,前讲后讲,上讲下讲,总之是为了劝导或吸引实践之人能行中庸之道而已。既已走上中庸之道,肯定这个法行,否定这个法也行。把《中庸》分为十章分为三十三章行,或者分为千章、一字一章、不立一章都无不可。不然的话,就算你通晓三藏、学富五车,也只是疯癫癫在外乱闯不得其门而入,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现在分十章讲解《中庸》,第一章为统说,与内容相符。”
第二节经文
【原文】
[朱注][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
(朱熹原注)[第一章]上天赋予人的就叫性,遵循着性行事就叫做道,修饬道行就称为教。道是不能片时片刻脱离的,如果可以脱离的那就不能叫作道。所以君子对于没有人看见的场合也应小心谨慎,在人们不知道的场合也应心怀敬畏。没有比阴暗之处更容易呈现的,没有比细微事物更明显的,所以君子独处时应非常谨慎。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以前称为“中”,表现出来而又合乎规矩就叫作“和”。中是天下的基本原则,和是天下应共同遵行的规律。达到了中、和,则天地正位,万物化育。
【原文】
一、释字
天《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他前切。"朱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今注曰"轫始而上之谓天。"
命《说文》“使也。从口从令。眉病切。"朱注曰"命犹令也"。今注曰"不能违越之谓命。”
之《说文》"出也。象过,枝茎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止而切。"朱注无释。今注曰"出荡十方而无碍之谓之。"
谓《说文》"报也。从言胃声。于贵切。"朱注无正释。今注曰"尚其所指而语人之谓谓。"
性《说文》"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息正切。"朱注曰"性即理也。"今注曰"空有无之谓性。"
显《说文》"头明饰也。从页显声,呼典切。"朱注曰"明,显也。"今注曰"无处不见曰显。"
微《说文》"隐行也。从彳(微右部)声。无非切。"朱注曰"微,细事也。"今注曰"无处能见曰微。"
慎《说文》"谨也。从心,真声。时刃切。”朱注曰"戒惧而谨也。"今注曰"勿忽而不苟曰慎。"
独《说文》"犬相得而斗也。从犬蜀声。羊为群,犬为独也。徒谷切。"注曰"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今注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曰独。"
致《说文》"送诣也。从攵从至。陟利切。"朱注曰"致,推而极之也。"今注曰"至也,言至乎此而证入中庸也。"
【译文】
一、释字
“天”。《说文》解释道:“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他前切。”朱注说:“天用阴阳五行变化生育万物,气生成万物的形体时,也赋予理。”我这里解释为“创世之先称为天。”
“命”。《说文》上说:“使也。从口从令。眉病切。”朱注说:“命即令”。我解释为“不能违背称为命。”
“之”。《说文》上讲:“出也。象形表示草已长高长大过了小草阶段,枝和茎越来越大,有不断发展的势头。一表示地。止而切。”朱注没有解释。我解释为“纵横捭阖没有阻碍称为之。”
“谓”。《说文》释为:“报也。从言胃声。于贵切”。朱注中没有确解。我解释为“把自己推崇的东西告诉给人称做谓”。
“性”。《说文》解释道:“人的阳气,就是人性善的‘性’。从心生声。息正切。”朱注说“性就是理”。我解释为“超越有无称性。”
“显”。《说文》里讲“头上装饰物。从页,显声。呼典切。”朱注说:“明是显之意。”我解释为“无处不见称为显。”
“微”。《说文》释为“隐行。从彳(微右部)声。无非切。”朱注说“微,指小事物”。我解释为“无法看见称为微。”
“慎”。《说文》解释为“谨也。从心,真声。时刃切。”朱注说“因警惕敬畏而小心。”我解释为“一丝不苟称做慎。”
“独”。《说文》解释为“两犬互相争斗。从犬,蜀声。羊喜成群结队,犬性好斗故常独来独往。徒谷切。”朱注解说为“独是指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我解释为“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称为独。”
“致”。《说文》解释为“送达。从攵从至。陟利切。”朱注说“致指推而广之直到顶点”。我解释为“到达。意思是说至此可以悟入中庸。”
【原文】
二、通义
"天",轫始而上之谓天。释氏缘生之说曰:"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缘生。"此说统万有,偕诸义。取以释此甚偕。何也?盖有此缘而轫始,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中者人也。权此土而立之假名也。"而"者,谓此土立名,并同化、非同化、人物也。不然,色界、诸天、天人谓上,无色界为天,己色界、下欲界不名曰天,岂通义乎?故曰轫始而上之谓天。故此"而"字为不可忽。"命",不能违越之谓命。如轫始为晴,无论自他,不得名阴。轫始而阴,无论自他,不得名晴。故曰"不能违"。又不得谓晴后即阴,阴后即晴。且正晴时无阴,正阴时无晴也。故曰:"不能越"。有轫始而上曰天。天,上也,颠也。此上此颠,即现示此晴此阴最初一现者。此一现也,在无知之现示者,不能违越,非晴非阴,亦犹领受彼现示者,不能违越非晴非阴也。故曰不能违越。成此不违不越,权称曰命。
【译文】
二、通义
天,天地开辟以前称为“天”。佛教有“缘生”的说法:“诸法不自己生成,不是外物生成,不共生,都是由因缘而生。”这个说法可涵盖一切事物,调和各种道理。用它来解释天也很恰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因缘才会有创始,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人,这些都是此土权立的假名。“而”指这些概念都是创始而上的那个东西演化出来的,不仅仅限于演化出人和物。要不然,色界、诸天、天人称上,无色界称天,己色界、下欲界不叫做天,那“天”岂是涵盖一切的概念?所以说“创始而上之谓天”,这个“而”字轻视不得。
命,不能违背超越称为命。如果创始是晴,无论自他,不能称阴。创始是阴,无论自他,都不能叫晴。所以说“不能违。”也不能说晴后就是阴,阴后就是晴。而且正晴时没有阴,正阴时也没有晴。所以说“不能越”。创始之上称为天。天,上也,颠也。这个上这个颠就体现着那个晴和阴最初的出现。这个出现,是不知不觉中出现的,不能违背超越,即使出现的非晴非阴,同样受制于它。那个导致最初出现的东西,不能违背超越。因为它非晴非阴。所以说“不能违越”。导致这个不能违背超越的就叫做命。
【原文】
"之"出荡十方而无碍曰之。谓轫始而上而命则此之也。出荡十方而无碍,入则纤毫而不留。使无此之,则彼晴彼阴从何而命而显邪?临济玄曰:"东涌则西没,南涌则北没,中涌则边没,边涌则中没。"故曰出荡十方而无碍曰之。
"谓",尚其所指之谓谓。盖自尚其所欲言而及他也。
"性",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今曰空有无之谓性,盖方便而言也。《说文》"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朱注"性即理也",两义皆悖。必曰人之阳气性善,然则人之阴气性恶,非性欤?必曰性即理,然则非理非性欤?是此性狭而不遍也,讵知阴阳相乘而化育成,善恶相乘而社会成?故无一事理而不备善恶,即无一事理而不该阴阳。合阴阳善恶,则无所谓事理也。执一事理而曰全,众盲摸象,讵达者之言乎?然则合阴阳善恶,曰理曰事即性乎?曰非。舍阴阳善恶曰事,曰理即性乎?曰:非。然则必如何而曰性?古哲于斯各封己说,必欲诠真,宁逾亲证?若然,亲证当依何陟?
【译文】
之。纵横无碍称为之。意指创始之上再到命接着就是之了。出则纵横无碍,入则丝毫痕迹不留。假使没有这个“之”,那么晴和阴怎么受命而显示它呢?临济义玄禅师讲:“西边没而东边出,北边没而南边出,四边没而从中间出,中间没而从四边出。”所以称纵横无碍为之。
谓。推崇自己所说的称做谓。因为推崇自己要说的东西所以才告诉他人。
性。很难用语言来解释、用意识来认知它。这里定义为“超越有无”,也只是方便的解释。《说文》解释为“人的阳气,性善的”,朱熹注解说“性就是理”。这两种解释都不通。如果硬说性是“人的阳气、性是善的。”那人的阴气性恶就不是性了吗?如果说“性就是理”,那非理就不是性了吗?那这个性也太狭隘而不能包容万物了。哪里知道阴阳相互作用才有万物的生长,善恶交互作用才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所以没有一事一理不具备善恶的,没有一事一理不体现着阴阳。没有阴阳、善恶,就没有什么事与理。以偏概全,如同盲人摸象,岂是智者之言?那包含了阴阳、善恶就可称为理、称为事,也就是性了吗?回答是:“不能”。那么抛开阴阳、善恶就可称为事、称为理,也就是性了吗?回答是“不能”。那到底怎样才叫性呢?先贤对这个问题,都避而不谈。现在一定要知道真正答案,除非自己亲自领悟,别无他法。那么,自己亲自求证应如何下手?
【原文】
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告子,孟子之徒也,反其师说曰"性无善无不善"。等斯说也,皆远宗乎孔子者也。考《论语》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夫子贡者,亲炙于圣门,且不可得而闻,余也孰得而闻?又,既不可得而闻,然则此不可得而闻者,为已闻?为未闻?若曰已闻,云胡不闻?若曰未闻,知此不可得而闻者为已闻为未闻亦可怀也。又,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检《论语》之记问孝、问政、问礼、问为邦,皆有问乃答。今则不叩而鸣,自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何邪?讵知希有之法不说不可,欲说无从。虽颜、曾之徒尚不能兴一问,况游、夏乎?今兹去圣已遥,行人内失自修之勤,外无师友之勖,困妙义于字里行间,昧胜行于人欲天理,曰得中庸的旨,孔孟薪传,真缘木求鱼,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矣!讵不惑哉!讵不惑哉!
【译文】
孟子称人性善,荀子称人性恶。告子是孟子的学生,却与老师的说法相反:“人性没什么善,也没什么恶。”这些说法都是从孔子那儿继承来的。考察《论语》里面子贡说过“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话,都无法听到。”要知子贡是亲受孔子教育的,尚且不能听到,其他人谁又能听到呢?既然听不到,那这个听不到的,是已经听到还是没有听到?如果说是已经听了,那为什么要说没有听到?如果说是没有听到,知道这个“不能听到的”东西,是听说了还是没听说,也是让人怀疑的。另外孔子还讲过“人的性情本来是互相接近的,由于习俗的不同才渐渐地相差很远了。”翻一翻《论语》里的问孝、问政、问礼、问为邦等问题时,都是学生先提出问题,然后老师予以回答。现在却不问自讲,自己说“人在性情本来是互相接近的,由于习俗的不同才渐渐地相差很远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知道无上妙法不说不行,欲说不能吗?即使是颜渊、曾子那样的高徒,尚且不能有此一问,更何况子游、子夏呢?现如今离圣人已很远,实践者自己已经不能精勤修行,又没有师友互相勉励,困在文字里搜寻妙理而不能拔身,被天理、人欲搞得迷失胜行。还自称是得了中庸的真谛、得到孔孟的真传,实可说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啊!怎能不迷惑呢?怎能不迷惑呢?
【原文】
昔余以此义叩一老宿。宿曰:"此理至明。人性与人性相近,与狗性相远。狗性与狗性相近,与人性相远。近者,亲也﹔远者,疏也。"余曰:"止!止!且不问习,人与人性相近也,商臣弒父,五公子争立,乃至夫妇、朋友互相攻贼者,何邪?与狗性相远也,人见狗必致狗死,狗见人必致人死。斯世界者,不尽人必尽狗。云何狗有饲养于人,人不必尽杀其狗者,何邪?"宿大窘。曰:"若言伊何?"余曰:"此理至明,实无当人摹拟处。若穿凿太玄,傅会过异,则去道愈远,滞而难通矣。夫远近乃相对而立,无近不表远,无远不立近也。相乃连介之说,片面不言相。性者,习之体﹔习者,性之用。无体不表习,无习不见体也。性当体即是,对习而言,故曰近﹔习对境乃有,于性而言,故曰远。"宿闻语未卒,色然而喜,起而语曰:"旨哉!旨哉!希有之论也。得自何书?传自何人?"余曰:"非因师得,不以书通。每日但虔参一个话头,敬念千声佛号而已。"宿闻语已,凝神久之。乃怫然曰:"我已投孔子,不再佞释迦"。余曰:"若不尔者,许先生穷劫不识孔子。何也?不会性相近、习相远矣。"
【译文】
当年我曾将这个疑问去向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请教。老先生说:“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人性与人性相近,与狗性差别很大;狗性与狗性相近,与人性相差很大。近指亲近,远指疏远。”我说:“停!停!先不讨论‘习’。人与人性接近,那楚公子商臣贼杀生父、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在桓公死后争位,甚至于夫妇、朋友之间互相残害,这又是为什么呢?人性如果与狗性差别很大,那人见了狗必置之死地,狗见人必置之死地,这个世界要么就全剩下人,要么就全剩下狗,为什么还有人养狗、人为什么都不杀死他的狗呢?”老先生十分狼狈,说道:“那你怎么说?”我说:“这个道理很清楚,实在无法摹拟。如果穿凿太过、牵强附会,反而离道越来越远而讲不通。本来远和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近就无法说明远,没有远的话近就不能成立。‘相’是连接二者的中介,如果片面用不着说‘相’。性,是习的本体。习,是性的功用。没有体,习就无法显出来;没有习,也就显不出体。性当体即是,相对于习而言所以说近;习是因境而有,相对于性来讲所以称远。”我的话还没听完,老先生脸呈喜色,站起来说道:“精辟!精辟!真是难以听到的高论呀!你从什么书上看到的?是谁教你的?”我说:“不是从老师那里得的,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每天只不过恭敬诚心地参一个话头,恭敬地念千声佛号而已。”老先生听完我说的话,神情庄重地看着我,不高兴地开口道:“我已经是孔子信徒.不会再讨好佛祖。”我说:“不信佛,我保证先生永远不懂孔子。为什么呢?因为不懂‘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
【原文】
清之季,华阳谢先生者,以傅大士偈闻余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牯牛。人走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杜顺大士偈曰"益州牛吃草,嘉州马腹胀。天下觅医人,灸猪左膊上",余闻大诧,立斥其僻,且咎具愚,引孔子"攻乎异端","不语怪力乱神"等说折之。谢故笑而不言。三台张先生梦余者,闻之让曰:"闻忠言而逆。岂开士之行乎?"乃授余以《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余三十服官,四十反政。既反政己,暮究朝参。民二十七年夏,张先生梦余弃世,固已二十年也。忽于成都春熙路遇谢先生,谢神形清逸,怡然自伟。余喜而握其手曰:"比来如何?"谢曰:"潜心净宗。"余曰:"若然念佛,进程现为如何?"谢曰:"余正念时无念,无念时却念。"余曰:"果尔,得念佛三昧也。"谢曰:"不敢。"
【译文】
清末华阳谢先生曾将傅大士的法身偈“空手把锄头,步行骑牯牛。人走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杜顺大士的法身偈“益州牛吃草,嘉州马腹胀。天下觅医人,炙猪右膊上”告诉我。我听后深感诧异,当下斥责那些说法僻陋,并深讥其愚蠢,而且引用孔子“把气力心思用在歪门邪道上,祸害不小”的话和《论语》上讲“孔子从来不谈怪力乱神这四样事情”等说法驳斥他。谢先生只是笑而不语。三台张梦余先生听说这件事后,批评我说:“忠言逆耳岂是智者所为?”于是他就送给我一部《金刚经》。我三十从政,四十弃官。弃官后闲居,朝参暮究。民国二十七年夏天,张梦余先生逝世,算来已二十年了。一天忽然在成都春熙路碰见谢先生。谢先生神形清逸,表情和悦,怡然自得。我大喜之下紧握先生的手问道:“最近怎样?”谢说:“心思全用在净土宗上。”我说:“是这样。念佛的境界如何?”谢先生说:“我已达到念佛时其实没有念,没有念佛时却是在念。”我说:“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是得了念佛三昧。”谢先生说:“哪里!”
【原文】
又二年,复遇于成都之春熙路,相邀品茗。余固知其未至也,复申问如前,谢答亦如前。余曰:"若然,还往生否?"谢曰:"当然往生。"余怫然而怒,且诘曰:"无念已得法身,而念法身已起用。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法身即起用,起用即法身。当人当下,即显净土。且能接引众生来生汝土也。今曰往,往何处?又曰生,生何土?曩者足下曾以傅大士、杜顺大士法身颂示余,今云无念而念,是已得法身。既得法身,此颂当明。即请足下为余通说彼二颂者意果何在?"谢大沮。
【译文】
过了两年,再次相遇于成都春熙路,相邀去喝茶。我心里清楚谢先生参佛功夫尚不到家,再次象上一次那样问他,谢先生回答也跟上次相同。我说:“如果那样的话,还想不想往生极乐净土?”谢先生回道:“当然往生。”我变色作怒,并质问道:“无念就可以得法身,而念法身即起用。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法身即起用,起用即法身,斯人斯境,即现净士,而且能普度众生来此净土。现在却说想往,往哪里?又说生,生生到哪个土?以前先生曾拿傅大士、杜顺大士的法身偈给我看,现在说什么无念而念,就是说先生已得到法身。既然已得到法身,那这偈子应该懂得。就请先生现在为我讲一讲那两个偈子意思到底在哪里?”谢先生极为丧气。
【原文】
余曰:"若此不会,今为足下寻个注脚。唐之中叶,有尊宿者曾于此偈注云:‘太行山上云蒸饭,佛殿阶前狗矢天。剎竿颠上煎锤子,三个胡孙夜簸钱',其义云何?"谢闻已,窘如前。余又曰:"若此不会,再与足下寻一注脚。曹山寂读此颂已,曰:‘我意不欲如是道',门弟子请别作之。其词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无我即死,我无渠即余。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即驴。不食空王俸,何假雁传书。我说横身唱,君看背上毛。乍如谣白雪,犹恐是巴歌'。其义复为如何?"谢又窘如前。余曰:"不但足下会他不得,纵饶把这一切玄言妙语会得透顶透底,还是法身边事,犹未透得法身向上事。"谢曰:"然则法身向上事为何?"余曰:"余言轻,不足信汝。今再以古德言章开若之惑。北宋之末,有一尊宿曰张无尽者,见皓布裈举大士此颂。皓亦曰:‘斯颂也,只颂得法身边事,而法身向上事则颂不得也。'无尽曰:‘请师颂。"皓遂应声而颂曰:‘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人力,拄的拄,撑的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当人果于上之一切葛藤了得清清澈澈,而不作了与不了想,庶几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不然,自欺欺人也。"
【译文】
我说:“这个若不会,我给先生找个说法。唐朝中期,有一前辈曾对那两个偈子说过这佯的话‘太行山上云蒸饭,佛殿阶前狗矢天。刹竿颠上煎锤子,三个胡孙夜簸钱’。这是什么意思?”谢听完我的话后,和先前一样的狼狈。我又说:“这个不会的话,我再为先生找一说法。曹山本寂禅师读了那两个偈子后,说:‘要我说我不会这样讲的。’弟子请他另作偈子。曹山的偈子是‘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无我即死,我无渠即余。渠如我是佛,我知渠即驴。不食空王俸,何假雁传书。我说横身唱,君看背上毛。乍如谣自雪,犹恐是巴歌’。这又是什么意思?”谢先生还是象前面一样窘困。我说:“不光是先生不能证会它,就算有人把所有这些奇谈妙论领悟透了,也还是法身边的事,还没有证得法身上的事。”谢先生问道:“那么透过法身向上的事是什么?”我说:“我人微言轻,说了你可能不信服。我还是再引前辈贤人的话为你解惑。北宋末年,有一个前辈,名叫张无尽,遇见皓布裈拿那两个偈子给他看。皓布裈也说:‘这个偈子,也只讲法身边的事,关于法身上的事则是无法颂的。’张无尽说:‘请大师。’皓布裈随口说出一个偈子:‘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人力。拄的拄,撑的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当人如果能将上面所讲的葛藤一一弄得清清楚楚,而又不作了与不了想,差不多可以说到了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不然的话,就是自欺欺人了。”
【原文】
谢闻语已,窘不自胜,愤不自胜,而喜亦不自胜。即时礼而诘曰:"然则必如何而可?"余曰:"毋躁!毋躁!足下既念佛也,仍然把一句佛号,朝斯夕斯、行时坐时直下念去,一朝念到无可念处,取不得,舍不得,忽然转身摸着自己鼻孔,或此方报尽生彼方净土,花开见佛,悟无生已。然后洞彻今说,滴滴转珠字,字字吐玉,与三世诸佛一口同音。一切圣贤无二无别,实又一句也用不着,而一字也未说也。"谢闻说已,欢喜踊跃,色然赞曰:"希有哉!此论也,开我未闻。"
【译文】
谢先生听完我的话,又窘、又恼、又喜,立即向我施礼而质问道:“那到底怎样才行?”我说:“不要急!不要急!先生既然在念佛,不妨仍把那一句佛号早念晚念,走时念坐时念,一直念到等到有一天念得你不能再念,念也不是不念也不是时,忽然转身摸摸自己鼻孔,或者你报尽往生净土,花开见佛,领悟不生不灭的真谛。然后你就会彻底明白现在我讲得句句圆转,字字珠玉,与三世诸佛同一个声音,与所有圣贤所讲没有丝毫不同,其实是一句也用不着,一也没说。”谢先生听完后,欢喜踊跃,欣然称赞道:“真是少有啊!这一番话,我以前从未曾听到过。”
【原文】
法身者,性也。某老宿不信而难入,谢先生信而入也。未至斯二先生者,皆今人也。至于古人,二祖断臂,云门损脚,佛灯封衾,性之难注如此!今曰空有无之谓性,义安在?义安在?权语也。
一切有情、无情、曰事、曰理,未轫始前固不可状、不可名、不可评也。不可状、不可名、不可评,不得言有。如上晴阴喻,未轫始前不可言晴、或新晴、久晴、晴善、晴不善等。阴喻同。故曰非有。有情、无情、曰事、曰理,既轫始后实可状、实可名、实可评也。实可状、实可名、实可评,不得言无。如上晴阴喻,轫始后不可言现晴、现阴、无晴、无阴。立名与评例同上说,故曰非无。正有时非实有。若实有,有即不坏。晴则总晴,阴则总阴。今不尔者,故曰正有时非实有,因无故有。古德所谓"言有时纤毫不立"也。正无时非实无。若实无者,无即不有。若有则不名无。若然,无则总无,而世无若晴若阴之状,况名与评邪?故曰正无时非实无,因有故无。先哲所谓"言无时遍界不藏"也。
【译文】
法身就是性。那位老先生因不信而不能悟入,谢先生因信而悟得,还不如这两位先生的,就是今人啊!至于古人,二祖慧可大师为求道而自断其臂,云门文偃禅师向睦州求法而伤一足,佛灯封衾,性这个字就是如此难以下注!现解释说空去有无称为性,意思在何处?意思在何处?这只不过是权且拿来用用的名称罢了。
一切有情、无情、称事、称理,没有被创始前本来是不可形容、不可称谓、不可评说。不可形容、不可称谓、不可评说,所以不能称为有。拿前面用来作比喻的的晴和阴来说,未创始前不可以说晴或者新晴、久晴、晴善、晴不善等等。用阴作比也一样。所以称为“非有”。有情、无情,称事、称理,创始之后,那就确实可以形容、可以称谓,可以评说了。确实可以形容、可以称谓、可以评说,那就不能说是无。比如前面用来作比喻的晴和阴,创始后就不能说现在晴、现在阴、没有晴、没有阴。称谓和评说的比喻与前面相同。所以称为“非无”。有的时候不是真有。如果是真有,那个“有”就不会坏,晴的话就一直是晴,阴的话就总是阴,现在则不然.所以说有时不是真有,因为有了无所以才可说有。前辈所谓“说有时其实是半点也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的时候不是真的没有。如果真的无,无就是没有,如果有就不能称无。那样的话,无就永远是无,世上也就没有若晴若阴的情形,更不用提称呼和评说了!所以说无时并非真无,相对于有才说无。先辈所谓“说无时遍界不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总上之说,法尔如幻。安立权名曰空,有无之谓性。行人如实了知,如实证知,释曰见性,老曰自然、耶曰识主,回曰真宰,孔曰中庸矣。证实相,了生死,得大涅槃,上趣乎三藐三菩提也。此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异语者。行人苟不自疑,当下即入,不依他得,不从师授,不因己灵,一切圆成也。曰修性,曰修命,曰坎离,龙虎,三还九转,犀然而妖异自见矣。不然,斯脱网而无日,泛归舟以何年?昔永嘉觉虑行人不能决择,丝路无从也,乃大声疾呼曰"证实相,无人法,剎那消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愿遭拔舌尘沙劫",千载下犹耳提面命也。吾人倘不甘暴弃,必自思自反,自怒自谴而涕满襟,而泣滂沱矣。曰亲证者,必依此而陟,讵他异哉?次以五释统说全章经文。
【译文】
综上所讲,法是如此虚幻不实,安立一个假名为超越有无称做性,学人如实了知,如实证知,那么就达到了佛教说的见性,老子说的自然、基督教说的主、回教说的真宰,孔子说的中庸了,这样便可证得实相,悟生死,得大涅槃进而得三藐三菩提。这些是实悟、如语、不妄语、异语,实践之人如果不自生疑心,那么立地即可证道,不借外力而得,不需要老师传授,不靠自己的智慧,一切都是圆满现成。什么修性、修命、坎离、龙虎、三还、九转,自然会灵光突现,看穿其妖异。要不然的话,就好象鱼无脱网之日,舟行迷路要回来谁知等到哪一年?当年永嘉玄觉禅师担心实践者不能抉择,迷失歧路,于是大声疾呼道:“证实相,无人法,刹那消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愿遭拔舌尘沙劫。”千载之下,仍发人深省如亲受教诲。我辈如不甘自暴自弃,就一定要扪心自问,迷途知返,自责自怨,泪流满面而痛悔前非。所谓亲自证道,必须如此去做,岂有他法!接下来以“五释”通讲全章内容。
【原文】
(一)释天命之谓性至谓教
广言天即性,命即性,之即性,谓即性,一切世间、非世间、遍空有、穷三际,何一而非性?必曰天命之谓性,此一性字而曰性,不可矣。若此一性字乃曰性,余不得曰性,性碍也,狭也,岂中庸博厚、高远、攸久、生物不测之义乎?以约言,不但此一性字也无,而无亦无。不然,下文曰隐、曰微,义当何释?有一滴可睹,一粒可数者,其得谓之隐与微乎?夫广与约,固非性,然亦非离广与约而别有也。盖有非是有,因无而有。无非是无,因有而无。故曰空有无之谓性。性即道,非离性而别有道也。率字与上文之字义合。又循也,谓循此性而出即道也。整理此道以示人,令其择乎中庸。孔曰入德,释曰见性,修道之谓教也。圣人立言,明显如此,宁有盲者说常、说异、说坎、说离,如是妄计邪?
【译文】
(一)解释“天命之谓性……谓教”这一节。
笼统地讲,天就是性,命就是性,之就是性,谓就是性,一切世间、非世间、遍空有、穷三际,有哪一个不是性?一定要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才算性,这是不对的。如果这个“性”字才算性,其他不能称为性,那“性”也太狭隘了,又岂能表示“中庸”广大深厚、高明阔远、经久不衰、生养万物神不可测的含意?简单来讲,不但这个“性”无,连那个“无”也没有。不然的话,下文里讲“隐”讲“微”,意思又该如何解释?有一滴可以看见,有一粒可以数的话,那能称为隐和微吗?虽然笼统讲和简单讲都不是性,但也不能说离开这两种讲法而另外有什么性存在。因为有不是真有,因为有无才说有;无不是真无,因有有才可说无。所以要说“超越有无称为性”。性就是道,不是说离开性而另外有什么道存在。“率”字与上文所讲的意思相同。“循”字(注:指朱熹注中“率,循也”之“循”)指遵循这个性而使合乎道,解释这个道使人知闻而选择中庸,孔子称之为“入德”,佛教名之曰“见性”。修习大道称为教。圣人说的这样明白清楚,怎么还会有一班睁眼瞎子在那儿说不变说变,讲什么坎离而如此乱猜呢?
【原文】
(二)释道也者至不闻
虑行人向外驰求,舍心别觅,计外有也。开其说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以救之。既不驰求向外,或执无言、无说、无声、无臭,而潜念无为计内无也。乃申其义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启之。行人如无如是等过,圣人之言从何而立?中庸之名宁居此世?果于此一觑觑破也,所谓入德、所谓见性、所谓允执厥中、所谓曾子之唯、子路之拱,一时瓦解冰消。昧者执何者为胜法劣法,何者为道,何者为教邪?
【译文】
(二)解释“道也行……不闻”一节。
担心修行之人一味往外边去追寻,抛开自心另找他物,以为道在身外。所以开门见山地说道:“道,不可片刻舍弃,可以舍弃那就不是道了。”以此来补救其蔽。既然不能向外寻求,有人也许会抓住无言、无说、无声、无臭,私下里认为这些“无”是内无。在此孔子进一步用“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场合小心谨慎,在人们不知道的场合害怕敬畏”这话来启发大家。修行之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过失,圣人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中庸这个名称又怎会存在于世?如果真能一眼看穿,也就是所谓“入德”、“见性”、“允执厥中”,如曾子闻听夫子自称“一以贯之”后而大悟、如子路见丈人而拱手敬立,片刻间万念俱失如瓦飞冰消,愚人认为什么是胜法劣法、什么是道、什么是教呢?
【原文】
(三)释莫见乎隐至独也
不住内外,而虑其任运闲闲,执一切不计为自然为解脱,为乐天也。乃指的途,示彼显径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无处不见曰显,无处能见曰微。若然,显微现隐,一派圆成。何事而非事?何事而是事?任运固闲闲,不任运讵不闲闲邪?君子慎独,独也者,非屋漏自勖、暗室自律,凝神静坐、百需仰人如三家村中土地也。果尔,福必折尽,自救不了,矧曰以道自教教人邪?独者何?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矣。若曰笃恭暗室,无惭屋漏,此小知细行未脱拘系,安知大象所游,大智所诣,有超然于言相之外者邪?该中庸之大义,续诸圣之心灯,必俟君子。
【译文】
(三)解释“莫见乎隐……独也”一节。
既不执着于内也不执着于外,又担心修行的人放任自流,无所顾忌,把一切不认为是自然、是解脱、是乐天,于是就指示一条正确道路,即“没有比隐藏的更明显,没有比细微的更清楚”,没有地方看不见的就叫“显”,没有地方可以看见的就叫“微”。如此一来,显、微、现、隐,一派圆成,什么事不是事,什么事算是事?听天由命自应该说是从容自得,不听天由命难道就不是从容自得了吗?“君子对独处很谨慎”,“独”,不是说一个人呆在漏雨的房子里仍自我激励,一个人呆在黑乎乎的房子里仍自我约束,整日凝神静坐,凡事都要仰仗别人,就好象三家村里供的土地神一样。如果真那样的话,你肯定消折福报,想自救也没办法,更何况以道来自教教人呢?那独指什么呢?那就是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如果说在黑屋子诚实恭敬,呆在漏雨的屋子里问心无愧,这都是细枝末节,仍没有脱离束缚,岂知大象所游、大智慧所到之处,不是语言、形迹所能限制的呢?总括中庸大义,重燃诸圣智慧之灯,那就得等君子了。
【原文】
(四)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至达道也
行者沦空有、囿显微、泥内外、执一而不得乎中,或居中而忘于一也,当下专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何等亲切!何等现成!又虑执喜怒未发为中,发为不中、中节为和、不中节为不和而失圆也,复以体用明之,令行者无时、无事、无地皆能证乎中庸。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本者,中也、体也﹔和者,庸也、用也、达道也。体用之义如上释。
【译文】
(四)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达道也”一节。
修行之人沉溺于空有,局限于显微,拘泥于内外,抓住一边而不得其中,或者居中而忘记还有边,所以接下来马上讲“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称为中,表现出来而能够不越规矩合乎分寸称为和”,说得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又担心只认为喜怒没表现出来是中、表现出来就是不中,只认为表现出来而合乎规矩是和、不合规矩是不和,因此而导致不圆融,所以又用“体”“用”来阐明它,让修行之人不论何时、何事、何地都能自证中庸。所以说“中,是天下的基本原则。和,是天下都可遵循的道路。”本,即中,就是体;和,即庸,就是用,就是都可遵循的道路。“体”“用”的解释如上。
【原文】
(五)释致中至育焉
天地位,万物育,中之至亦和之至也。耀全章之统旨,立万世之极规,行人即此乃证中庸,宗门下客曰"大事了毕"矣。不然,统谓不至。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万物育,乃法尔圆成,非他与,非师授,非求得,非江湖下士所谓取坎填离、乾坤大转、阴阳大交、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及修性、修命之一切光影、一切空有、一切玄妙等境界也。此法尔圆成者,中亦育,和亦育、不中不和亦无不育﹔中亦位,和亦位,不中不和亦无不位。臻此,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也,华严之"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者也。然此一路,不趋已入,非假方便,亦无渐顿,不因师授,不以己求,宁有趋而不入者乎?苟不臻此,葛藤极多。古德云"枯木岩前歧路多,非上上根人不至。"何也?彼上上根者,不尝一脔而自足,不护己短而轻人,诚求师友,虔修胜行,不底于成势必不已。上上根者,亦非别有他长也。
【译文】
(五)解释“致中和……育焉”一节。
“天地秩序井然,万物生长繁育”,达到了中的极致,也达到了和的极致。这两句是全章的精髓,为万世建立了最根本的原则。行人到此方证中庸,禅宗学人称为“大事了毕”。不然的话,都叫做不到家。所以说是“达到了中和,天地井然,万物生育。”天地井然,万物生育,是妙法自成,不是别人强加的,不是老师传授的,不是乞求所得,不是江湖术士所讲的通过坎离、乾坤大转、阴阳大交、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及修性、修命等一切声色光影、一切空有、一切玄妙等境界。这个法圆融无碍,中也养育,和也养育,不中不和也养育;中也井然,和也井然,不中不和也无不井然。达到这个境界,也即孔子所讲的他七十岁时可随心所欲而不越法度,《华严经》所讲的“理无碍、事无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但这种境界,并不需刻意努力已经达到,不是靠什么方便,也没有什么渐悟、顿悟,不靠师傅传授,不是自己追求的,如能这样又怎么会寻而不得呢?若不能至此,会遇到很多歧路,前辈所讲“枯木岩前歧路多,非上上根人不至。”。为什么呢?因为上上根人不尝一脔而自足,不回护自己的短处而轻视别人,诚心诚意向师友请教,恭敬地修胜行,不到成功,绝不罢休。上上根人并非另外也有什么长处啊!
第三节拈提
【原文】
宋侍郎张九成者,号无垢居士。未第时,慕杨文公、吕微仲之学。谒宝印明,叩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舍,久久纯熟,时节到来,自然证入。"复举柏树子话令时时提撕。一夕如厕(先生曰:"古人用功何等精进!如厕犹勤,余可知也。")正提柏树子话,闻蛙声,释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声蛙,惊破乾坤共一家。正恁么时谁会得,岭头脚痛有玄沙。"旋谒大慧杲于径山,与冯济川辈议及格物。大慧杲曰:"公只知格物,不知物格。"(先生曰:"晴天霹雳,见缝插针。")张茫然。大慧杲大笑。张曰:"师能开谕否?"杲曰:"小说载唐人有与安禄山谋叛者,其人先为阆守,有画像在焉。明皇幸蜀见之,怒令侍臣以剑掣其首。时阆守在陕西,首忽落。"张闻举,顿领微旨。题其轩曰:"子韶格物,昙晦物格。欲识一贯,两个五百。"(先生曰:"若要识真学孔者么?只这是。你看他出格人物何等气慨!不拘一墟,不瞒己,不瞒人,必要澈头澈尾,打穿后壁。")
【译文】
宋代张九成侍郎,号无垢居士。没中进士前很敬慕杨亿、吕大防的学识。他拜见宝印楚明禅师,请教入道法门。宝印便说:“这件事只有时时想着不要抛开,时间长了自然纯熟。时机到来时,自然就入道。”又举出赵州庭前柏树子的公案,让他时时参究。有一天傍晚张居士去上厕所(先生讲道:“古人修行是何等地勤苦不懈!上厕所都这样,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正参究柏树子的公案时,忽然听到蛙声传来,当下大悟,作了一个偈子道:“春天月夜一声蛙,惊破乾坤共一家。正恁么时谁会得,岭头脚痛有玄沙。”不久他又去径山拜见大慧宗杲禅师。与冯给事济川等人讨论格物,大慧宗杲禅师就说道:“居士只知道有格物,却不知还有物格。”(先生说:这话说得直似晴天霹雳出入意外,又如见缝插针机缘极巧。)张九成听了这话茫然不解。大慧宗杲禅师哈哈大笑。张九成说道:“大师可否开导一下?”宗杲说:“小说里记载唐朝时有一个人与安禄山同谋反叛,那个人原先曾任阆中太守。阆中有他的画像。唐玄宗往四川逃时看见画像大怒,命侍臣用剑砍画像之头。那个阆中太守此时身在陕西,脑袋忽然就掉了。”张九成闻言顿悟,在他住处墙壁写道:“子韶格物(子韶是张九成的字),昙晦物格。(按《五灯会元》卷二十记此事“昙晦”作“妙喜”,妙喜是宗杲的庵名)要知一贯,两个五百”。(先生说:要学佛学孔,就得这样!你看他超凡脱俗的人是何等气概!不抱残守缺,不自欺,不欺人,一定要搞得有头有尾,打通后壁了无滞碍”。)
【原文】
又以临济四料拣叩曰:"此甚议论?"大慧杲曰:"公之见解,只要入佛,不可入魔,安得不从料拣中去邪?"遂举克符问临济至人、境两俱夺,不觉欣然。杲曰:"余则不然。"张曰:"师意如何?"师曰:"打破蔡州城,杀却吴元济。"张于言下得大自在,尝曰:"某了末后大事实在径山老人处。"(先生曰"这回不是梦,真个到庐山。"又曰:"是谁说的?")其甥于宪者侍张次,张令拜径山杲。宪曰:"素不拜僧。"张令扣以法要。宪遂举《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问。杲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神下落处,又要牵好人入火坑。如何圣贤于打头一著不凿破?"宪曰:"吾师能凿否?"大慧杲曰:"天命之谓性,便是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便是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便是千百亿化身。"言已,张顾宪曰:"子拜何辞?"
【译文】
又拿临济义玄禅师所讲四料简请教说:“这是什么意思?”宗杲说:“居士的见解,只能悟佛,不能悟魔,又怎能不经过选择而有所淘汰呢?”于是就举克符向临济义玄禅师请教,听到义玄解释什么是人、境两俱夺时不觉大喜。宗杲说道:“要我就不那样。”张九成问道:“大师意下如何?”宗杲说:“打破蔡州城,杀却吴元济。”张九成闻言得大自在。张氏曾说:“我是在径山老人处了毕生死大事的。”(先生说:“这回不是做梦去庐山,是真的去了。”又说“这话是谁说的?”今按:先生后句话,并非真问“这回不是梦,真个到庐山”这话是谁人所言。真去庐山喻悟道,悟道之后又担心难以保任,有我之心顿起,先生为杜绝此失,故有后一问。泯灭人我,使人不存主宾之念,悟非我悟,说亦谁说?)张九成的外甥于宪侍陪他时,张九成就让他去拜见宗杲。于宪说:“我从来不拜僧人。”张九成让他向宗杲请教法要,于宪就向宗杲请教《中庸》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几句话。宗杲说道:“凡人既不知道本命、元神下落处,又要把好人也拉进火炕。为什么圣贤不把这关键之处点透呢?”于宪说:“大师能点透吗?”宗杲说:“天命之谓性,即指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即是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即指千百亿化身。”听完此话。张九成回头看着于宪说:“你怎么谢大师?”
【原文】
先生曰:"三身具,释氏之学,天地之道尽也。孔、老、耶、回、百家之学亦尽矣。瞎汉!瞎汉!孔子何曾要汝取坎填离、作一切大背圣道、惊奇欺俗等说,曰修性、曰修命、阴阳大转、神存黄庭、气还虚府邪?大慧杲亦何曾教汝取坎填离、修性命为得法化报邪?此不明,害必巨,所谓因地不真,果遭迂曲。今皓首穷研毕生不至者,囿乎此也。可叹!可叹!张无垢,儒老也,潜心内籍,必臻于至,此之谓善学儒。大慧杲,释者也。于儒家者言,精透如彼,此之谓善学释。岂陋者画地自封、同舟较胡越、一室论长短邪?故曰‘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智不拘于小节'。"
【译文】
先生说:“如能三身具备,那佛教要讲的道理以及天地之大道都在这里了。孔、老、基督教、回教、诸子百家之学也都在这里。瞎子!瞎子!孔子何曾让你取坎填离、作一些违背圣道、惊世骇俗的学说,而称为修性、修命、阴阳大转、神存黄庭、气还虚府呢?宗杲禅师又哪里教你取坎填离、修性、修命而由此得到法报化三身呢?这点不弄清楚,其害不小,正所谓‘因地不真,果遭迂曲。’现如今那钻研得头发花白、一辈子到头仍不能到那个境界的人,都因为是受此局限啊!可叹!可叹!张无垢居士,是个儒生,专心佛典,一定要求得正道,这就叫善学儒。宗杲是佛门之人,对于儒家学说,又是那样精深了解!这就叫善学佛,岂如那些浅陋之人画地为牢、同在一船而分什么彼此、同在一室而论什么短长呢?所以说“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智不拘于小节。”
第二章赞美中庸
第一节 总 论
【原文】
朱子谓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终此章[天命章]之意,义失偕,何也?十章外余章者,非引孔子之言欤?子曰"无忧",子曰"舜其大孝"等,何邪?必曰非释此章之意,然此余章者,何不列于他经如《论语》等,而必归此篇,又何邪?此固例也。至"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等,义虽近是,然亦为初机者说也。若曰升乎堂寝,益滋其病。何也?外诱之私,与本然之善相对为二,非本经"其为物不二"义也。
【译文】
朱子说下面十章是子思引孔子的话来结束本章的意义(即“天命之谓性”一章)。这是讲不通的,为什么呢?十章之外其他章节所引难道就不是孔子的话吗?孔子说“没有忧虑”,孔子说“舜真是大孝子”等等又是什么?非要说这些话不是解释这一章的意思,那其他章节为什么不列在别的经书如《论语》等里面去却一定要放到《中庸》里来,又是为什么呢?这当然是体例上的问题。至于朱子所讲“接下来讲保持反省的关键,最后讲大道的神奇效用,这是为了学者能于此返求于自身而自己悟解,以便学者能舍去外物的诱惑而扩充原本存于心中的善”等等道理,虽然勉强可说不错,但这也只是说给刚入门者听。如果是已经登堂入室的人,那些话只能更增加他们的过失。为什么呢?受外物诱惑的私心与心中原本就有的善成了相对的两个东西,不符合《中庸》所讲“那个东西表现出来是一不是二”的原意。
【原文】
又去外诱之私是增,充内有之善是减。不增何去?不减何充?有增有减,岂本经"不动而信,不言而成"之义乎?况曰反求诸身而自得,即有自得,必非无得。既非无得,必是有得。若是有得,岂无为义乎?故余是其说为接导初机之是,非是其所是也。初机者不是此德胡入?已入者苟是此业何至?朱子一代硕儒,语失圆透,义远精工若此,盖其所治,乃言前荐得,句下精通,非彻证乎中庸者欤!风穴曰:"设使言前荐得,犹为滞壳迷封。纵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故余不惜口业而揭如上说。甚矣,立言之难,不亦甚乎?此诸圣在未说前而欲缄口也。余以十章说是经,首立统说,次言赞美,盖因立此之统,故有继统之赞,讵得已乎?黄叶枯桐,原无实义。然则赞何赞?美何美?久之,先生以手示一圆相曰:"古德云:‘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无涯岸。大千沙界海中沤,六道四生如梦幻。'"
【译文】
另外,舍去受不住外物诱惑的私心是增,扩充心中原本就有的善是减,因为如果不增怎么来舍去?不减的话怎么扩充?有增有减,这岂是本书里所讲的“不动而达到目的,不言语即可有所成就”的意思呢?况且还讲到返求于自身而自己悟解,既然自己可以悟解,那一定就不是无所得,既然不是无所得,那就一定是有得,如果是有得,岂是无为的意思?所以我不反对那是适合初饥的说法,但却不认为朱子讲的道理究竟。对初饥之人来讲,不从此下手怎么能入门?对于已入门的人说,如果从此着手怎会有成?朱子是一代大儒,话说得不圆融透彻,意思讲得如此不准确,因为他是从语言中悟得、句子下精通的,并没有彻底证会中庸的意旨!风穴延沼禅师说:“假使言前悟得,仍滞壳迷封,如果句下精通,仍不免触途狂见。”因此,我不惜造下口业而作如上之说,立言实在是太难了呵!这正是诸圣在讲道之前想缄口不言的缘故所在。我用十章来解说此经,首先是“统说”,接下来讲“赞美”。只因为立了那么一个纲,所以有继纲之后的赞,岂能停下来?黄叶枯桐,本来没有什么真实意义,那赞又是赞什么?美又是美什么?过了一会,先生才用手势表示一圆相说:“古德说: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无涯岸。大千沙界海中沤,六道四生如梦幻。”
第二节经文
【原文】
[朱注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朱注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译文】
[朱注第二章]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能随时行之,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
[朱注第三章]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美德了!人们失去它已很长时间了!”
【原文】
一、释字
反《说文》:"覆也。从又厂。反形。府远切。"今注曰"逆对方之事理曰反。"
时《说文》:"四时也。从日寺声。市之切。"今注曰"表过、未、现之假程曰时。"
忌《说文》:"憎恶也。从心己声。渠记切。"今注曰"外愧于行曰忌。"
惮《说文》:"忌难也。从心单声。一曰难也。徒案切。"今注曰"内愧于心曰惮。"
至《说文》:"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脂利切。"今注曰"极十方而无往曰至。"
【译文】
一、释字
“反”。《说文》:“覆也。从又厂,反形。府远切。”我解释为“与对方的事理相反称为反。”
“时”。《说文》:“四时也。从日,寺声。市之切。”我解释为:表示过去、未来、现在流程的假名就叫时。”
“忌”。《说文》:“憎恶也。从心,己声。渠记切。”我解释为“外愧于自己的行为就称忌”。
“惮”。《说文》:“忌难也。从心,单声。另一种解释为难。徒案切。”我解释为:“内愧于心就叫惮”。
“至”。《说文》:“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就象地,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脂利切。”我解释为“无处不到称为至。”
【原文】
二、通义
仲尼子曰者,子,孔子,仲尼其字。曰子思重其说而证其人以信示乎他也。无征则不信,不信则民弗从。民也者,用于政,人民也趣乎中庸,行人也。人民不信,政必失;行人不信,述此中庸者无的而放矢,岂子思之意乎?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孔子至人也,犹曰"宪章文武"。释曰世尊,皆重其说而定于一尊,以信示来兹矣。不然,于自为不重,于人为轻法,皆过也。后释同后,故不释。
有君子中庸,有小人中庸。君子必反小人中庸,小人必反君子中庸。故曰逆对方之谓反。无论事理,法尔然也。此君子者,非曰在位如诗"彼君子兮"等,谓彻证乎中庸者,君子也。既彻证也,虽无位,亦君子。反之,在位亦小人。
【译文】
二、通义
“仲尼曰”,孔子的字叫仲尼。称字是因为子思敬重孔子的学说而证明真有孔子其人以使他人确信。没有证明则人不相信,人不相信则百姓不会跟随。人民,是当政者对百姓的称谓。实践中庸的人称为行人。人民不相信,为政一定会有过失,行人不相信,那讲这个中庸就成了无的放矢,岂是子思的本意?所以孟子说人性善,开口必称尧和舜。孔子是圣人,还说“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佛称世尊,这是为了让人相信都看重自己的学说,而自立为尊,以取信于后世。不然的话,对自己求讲是不尊重圣贤,对他人来说则是轻视真理,这两者都是过错。”
有君子中庸,有小人中庸。君子一定反对小人中庸,小人一定反对君子中庸。所以说是“与对方相反称为反”,无论是事还是理,本来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君子,不是说身在朝廷象《诗经》里所称的“彼君子兮”等的“君子”,是指完全证会中庸的人,方可称为君子。既然已经证会,没有官职也是君子。反过来说,身居高位者仍是小人。
【原文】
春仁、夏荣、秋杀、冬藏,四时之代谢,君子中庸也。故曰"圣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天地合其仁。"曰仁、曰荣,而曰中庸﹔曰杀、曰藏则反是。曰杀、曰藏而曰中庸,曰仁、曰荣又反是,岂君子行四时之化,履中庸之道哉?君子内无所蕴,外无所诱,当仁而仁,当杀而杀,宜荣则荣,宜藏则藏,而此宜此当,丝忽不居,故曰"时中",又曰"无中"。盖就其用言曰时,即其体说曰无。无即时,时即无。有时用无即实时,有时用时即无,有时时无两用,有时无两不用。此君子之胜行,中庸之至德矣。
【译文】
春天仁和,夏天万物欣欣向荣,秋日肃杀,冬日藏获,四季的更迭,是君子中庸。所以说:圣人指的就是能不违天时、仁心同于天地。说“仁”“荣”是中庸,“杀”与“藏”不是中庸;或者说“杀”“藏”是中庸,“仁”“荣”又不是中庸,这岂是君子行不违天时、实践中庸的大道呢?君子内心没有什么蕴藏,外面也没什么能诱惑的,应当仁时就仁,当杀时就杀,适合荣时就荣,适合藏时就藏。而这些“应当”“适合”,丝毫不滞留于心,所以说“时中”,又说“无中”。因为从用的方面讲可称为“时”,从体的方面讲可称为“无”。无就是时,时就是无。有时用无就是时,有时用时就是无,有时候时无两个都用,有时候时,无两不用。这就是君子的胜行、中庸的至德。
【原文】
小人反是。曰仁、曰荣放而逸,检于心、鉴于行,罔知忌惮,其至宋襄公、陈仲子之俦也。曰杀、曰藏肆而恣,天变不畏、人言不恤。其弊商臣、盗跖之流也。故曰"无忌惮"。无忌惮者,谓行人未彻证乎中庸也。若曰已证,忌惮中庸,不忌惮亦中庸,忌惮不忌惮无一而非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惟其至,行人望而难即,习不能趋。故曰"民鲜能久",讵知是法无闲,无闲者,久之至德也。此"鲜能",非君子能能,小人不能。盖君于无能可能,故曰:"鲜"。小人有能不能,故曰"鲜"。"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义固尚乎斯。若曰中庸之至德,而人而民鲜能者,抑亦久也。岂通义哉!陋甚矣!
【译文】
小人恰恰相反。讲仁讲荣,便放逸而不知自省其心、检查自己的行为,不知忌惮,以至有象宋襄公、陈仲子之流出现;讲杀讲藏,则任意胡作非为,不怕天变,不担心众人的议论,这方面的过失就会产生如盗跖、商臣之辈,所以称为“无忌惮”。无忌惮,指践行之人还没有证得中庸。如果说已经证得中庸,那忌惮是中庸,不忌惮也是中庸,忌惮不忌惮无一不是中庸。所以说:“中庸是最高的德行”,正因为它是最高的,行人可望而不可即,修行而难以抵达,所以说“人们缺乏它已很久了”。岂知这个法门并没有间断,没有间断是久的最高德行。这里讲的“很少能”,不是说君子能行中庸,小人不能。因为君子无能可能,所以说“很少”。小人有能不能,所以称“很少”。“中庸真是最高的德行,民众缺乏它已经很久了。”应作如此解释才对。如果解释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很少有人能实行它,已很久了”,岂是中庸的通义?真是太浅陋了!
第三节拈提
【原文】
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忠国师验之。师曰:"汝得他心通邪?"对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良久再问,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良久,复问曰:"汝道老僧只今在什么处?"藏罔测。(先生曰:"实见实见,即见即见,真见真见。")师叱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藏无对。举已。(先生曰:"只如大耳三藏,是不会无对,会了无对?若在此下得一语,许你亲说《中庸》,亲听《中庸》。")又僧问赵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未审国师在什么处?"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后问玄沙云:"既在鼻孔上,为什么不见?"沙云:"只为太近。"又白云端云:"国师若在三藏鼻头上,有甚难见?殊不知国师在三藏眼睛上。"(先生曰:"当人倘于这几则话言上下得一转语,亲亲切切,不蔓不枝,许你亲说《中庸》,亲听《中庸》。")众复无对。(先生曰:"今天说的呀")
【译文】
大耳三藏到京城里去,自称已修成“他心通”。唐肃宗让南阳慧忠国师去检验他。慧忠就说:“你已练成他心通了?”大耳三藏回答说:“不敢。”慧忠问:“你说老僧现如今在何处?”大耳三藏答道:“和尚是一国之师,为什么却跑到西川去看赛舟?”过了很久,慧忠再问,大耳三藏回答道:“和尚是一国之师,为什么又跑到天津桥上看人耍猴子?”又过了很久,慧忠又问他:“你说我现在在何处?”大耳三藏无法测得。(先生说:“实见实见!即见即见!真见真见!”)慧忠斥道:“你这野狐精.你的他心通跑哪儿去了?”大耳三藏无言以对(先生说道:“象这大耳三藏此时,是不会才答不上来?是会了仍答不上来?谁能在此有个说头,方有资格亲自讲解《中庸》、方有资格听《中庸》)。另外,有僧人问赵州从谂禅师:“大耳三藏第三次测不得国师,不知国师在什么地方?”赵州回答道:“在大耳三藏鼻孔上。”后来又有僧人问玄沙师备禅师:“既然在鼻孔上,为什么看不见?”玄沙回答道:“只因为离得太近。”另外,白云守端禅师说:“国师如果在大耳三藏鼻孔上,有什么难以看见的?殊不知国师其实在大耳三藏眼睛上。”(先生说:“当人若能从这几则话语下一个转语,亲切恰当,不罗罗嗦嗦,方有资格来讲《中庸》。方有资格听《中庸》。)众人仍无人应声。(先生说道:“今天讲的呀”)
【原文】
又昔者僧问嵩山峻曰:"如何是修善行人?"峻曰:"担枷带锁。"曰:"如何是作恶行人?"峻曰:"修禅入定。"曰:"某甲浅机,请师直指。"峻曰:“汝问我恶,恶不从善;汝问我善,善不从恶。”僧良久,峻曰:"会么?"曰:"不会",峻曰:"恶人无善念,善人无恶心。所以道善恶如浮云,俱无起灭处。"其僧大悟于言下。后破灶堕闻举,赞曰:"此子会尽诸法无生。"
先生曰:"试问诸法无生,从何处会?且不说尽。既无处会,赞来,赞来,若云赞他不得,大法无灵;如云赞得,龟毛千尺。然则毕竟如何?"
先生以目顾视大众,良久乃曰:"流水不会怀昨日,桃花依旧到春时。"下座。
【译文】
另外,有僧人问嵩山峻极禅师:“怎样才是行善的人?”回答说:“身带枷锁。”僧人又问:“怎样才是作恶之人?”答道:“修禅入定。”僧人说道:“我根机浅陋,请大师明说。”峻极说:“你问我什么是恶,恶不是善;你问我什么是善,善不是恶。”那僧人沉默良久。峻极问道:“证会了吗?”僧人答道:“不证会。”峻极说道:“恶人没有善念,善人没有恶念,所以才说善恶如浮云,都是无生无灭。”僧人闻言大悟。后来破灶堕和尚听说这件事后,赞叹道:“此人悟透诸法无生。”
先生说道:“试问诸法无生从哪方面去理解?这儿暂不点透。既然无处领会,你们来赞美它呵!如果说无法赞它,须知佛法不灵;如果说赞得,佛法又如龟毛兔角有名无实,那到底该怎么办?”
先生环视众人,很久之后才说:“流水不会怀昨日.桃花依旧到春时。”然后离开。
第三章难行中庸
第一节 总 论
【原文】
千里基于步始,万行肇自机先。上之二章,由统而赞。行人虽未税驾,然扬鞭之概固已潜于念初也。师友激之,环境袭之,于焉决择,乃裹糇粮,而古道绝行人,芳草斜阳,马蹄每乱素丝,歧路达者犹迷。在未启行前,放荡西东,回车不辔,固忽而易之也。乃者进不可,退不可,不进不退、上下左右均不可。望前途之茫茫,眇己躬之孑孑。徘徊去取,遂生四难。:
一、发心之难,
二、尚友之难,
三、依师之难,
四、不自瞒难。
【译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事都开始于心动。上面两章由大纲而讲到赞美,修行之人虽然还没停车歇息,但扬鞭止驾的念头却暗中早已从一开始就有了。老师朋友激励他,环境逼迫他,于是这才下定决心,带上干粮,然而古道绝行人,芳草斜阳,马蹄每乱素丝,岐路达者犹迷。在没出发前,东西乱撞,停步不前,还真的忽略了它。等到了现在这个情形前进不行,后退不行,不进不退,上下左右都不行。往前看长路漫漫,看看自己孤身无伴,徘徊而思量进退。于是就产生了四个困难:
(一)发心难;(二)交友难;(三)投师难;(四)不自欺难。
【原文】
一、发心之难,厥有三支:始难、识难、一难也。
(一)始难
行人无始驰求向外,背本逐末,熟径难忘,欲回车别觅新途,改趋如揽逆舟,不苟安而闲闲、心纷而悬悬者,百不一睹也。今日策其心于坦道,轨其行于中庸,即此回心而为极难。何也?望渺渺而惊远,神怆怆以慑危。故曰始难。
【译文】
一、发心难,此难又分三种:开始难、认识难、守一不变难
(一)开始难。
行人无始以来向外寻求,背本逐末,熟路难忘,想回车另找新路,如牵揽逆舟般困难。不苟安而闲闲、心纷而悬悬的人,百里难挑一啊!现在要鞭策他回心走上坦途,使他改辙走中庸之道,于此回心转意极为困难。为什么呢?前路茫茫,望而心寒,顾影自怜,所以说开始难。
【原文】
(二)识难
既回心已,宁有千里无波之逝水?亦无一行不阻之坦途。前境稍违,自心不牧。不希奇异,便困平常,希奇异则阴阳、丹道,越理悖行,万流竞射,一德无归。极其弊,黄巾、白莲、蛊祓、巫觋也。困平常,则囿心一隅,所谓"坐在黑山鬼窖"者也。既罹斯咎,百药难辛。此之二过,乃行人忽而失照,遂尔百异千奇。古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乱飞。"故曰识难。
【译文】
(二)认识难。
即已回心转意,哪里有无风无浪的千里流水,也没有无阻碍的平坦大道,往前走稍不如意,就管不住自家的心念,不是企盼奇异,就是困于平常。盼着奇异之事就会被阴阳、丹道所吸引,则违理乱行,肆无忌惮,心无所归,祸害发展至极端就是黄巾、白莲、蛊祓、巫觋。困于平常,就会坐井观天,所谓“坐在黑山鬼窖”即指此。一旦得了这些病,百药难医。这两种过失,是因为修行之人一时迷失,于是就导致种种怪异。前辈说:“一翳在目,空花乱飞。”所以说认识难。
【原文】
(三)一难
无上二支之过,一行斯尚,万派不羁,此为至难。《书》曰"咸有一德",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赵州问台山路,婆子曰:"蓦直去",一行之楷则也。故世无不笃行之君子,亦无不二三其德之小人。笃行者,一行也。故曰一难。
有上三支如是之难,曰发心之难。
【译文】
(三)守一难。
没有上面两种过失,守一不变,百折不回,这是最难的。《尚书》说:“都有纯一之德。”孔子说:“我没见谁喜欢德行如同好色那样。”赵州从谂禅师问一个婆子去五台山的路,那婆子回答说:“一直走。”这真是守一不变的楷模。所以世上没有不坚持不懈的君子,也没有不三心二意的小人;坚持不懈就是守一不变的德行。所以说守一难。
有以上三种困难.所以说发心难。
【原文】
二、尚友之难,亦有三支:知难、交难,笃难也。
(一)知难
无友则我行斯独,有过无攻也。子夏之贤,犹咎独居﹔夏禹大圣,尚拜昌言。倘使雪峰而不取证于岩头,慧南而不切激于文悦,宁有最后一段风流韵事乎?友于当人,重于丘岳矣。然人海茫茫,谁标达哲?纵欲友直,吾其谁从?故曰知难也。
(二)交难
既知也,人不我与,或与也而交道不终。遗金割席,见弃高明。交难也。
【译文】
二、交友难
也有三种情形:寻找知音难、相交难、积德彰文难。
(一)寻找知音难。没有朋友则自己独个儿行事,有过失无人指责。子夏那样的贤人,尚且自责独处无友。夏禹是大圣人,尚且恭敬地接受正确意见。雪峰义存禅师如果不是向岩头禅师求证,黄龙慧南禅师不深受云峰文悦惮师的激励,又怎么会有后来的一段风流韵事呢?朋友对自己重于山岳。但人海茫茫,谁是贤哲?自己即使有心交正直的朋友,但是去找准呢?所以说寻找知音难。
(二)相交难。既已了解了对方,但人家不愿和自己交往,或者虽然交往了却中途分手。遗金割席。贤者主动与自己断交,都说明了相交很难。
【原文】
(三)笃难
仲尼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者,彰内心之德也。有此内心之德,乃沛外有之文。既有外有之文,斯感辅仁之友。不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囿我于邪行,安我于乱德矣。唐之黄檗者,行乞洛京。有一妪出荆扉,间顾而语曰:"太无厌生。"檗曰:"汝犹未施,责我无厌,何邪?"妪笑而掩扉。檗大异,进而与语,多所发药。临去,妪复语之曰:"可速往南昌,见马大师去。"又,丹霞天然者,初业儒,将入长安应举。有禅者曰:"仁者何往?"丹霞曰:"长安选官去。"禅者曰:"选官何如选佛?"丹霞曰:"选佛当往何所?"禅者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速往。"黄檗、丹霞,果于是行了彻大事。之二者,以文会友之显例也。倘黄檗、丹霞无内蕴之德,失外彰之文,彼一妇人、彼一禅者,非有杯酒之接,一日之雅也,宁有如是之激勉邪?不然,天下人皆激而之南昌也。岂理事哉?经曰"笃躬而天下平",笃躬者,笃内蕴之德彰外有之文也。若然,天下犹平,况交友乎?讵知行人日鸩习染,昧而不觉,移山犹易,笃躬至难。故曰笃难。
有上三支如是之难,曰交友之难。
【译文】
(三)积德彰文难。
孔子说:“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借着朋友的帮助来培养仁德。”文章学问是来表现内心之品德的。内心有这样的德行,才会扩充至外而表现为文章学问。有了表现于外在的文章学问,这才能吸引帮助自己培养仁德的朋友。不然的话,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合道理,则会使自己被邪行包围,悖礼乱德而无动于衷。唐朝的黄檗希运禅师行乞于洛阳,有一个老婆婆打开柴门看了他一眼说道:“贪心不足。”黄檗说:“你还没向我布施,就怪我贪心不足,这是什么道理?”老婆婆笑着关上门。黄檗非常惊异,就走进去和她说话,很受启发。黄檗临别,老婆婆又说道:“你可速去南昌参拜马祖禅师。”另外,丹霞天然禅师开始修习儒业,准备去长安应考。途遇一个禅僧问他:“仁者要去哪儿?”丹霞答道:“去长安考试做官。”禅僧说“做官何如做佛?”丹霞说:“要成佛该到哪儿去?”禅僧说:“现如今江西马祖大师出世,他那儿是选佛场,仁者可火速前往。”黄檗、丹霞果然从此了彻大事。这两人是以文会友的典型例证。假如黄檗、丹霞内无德行,便不会有外彰之文,那个老婆婆、那个禅僧,与他二人没有杯酒之欢,没有一天的交情,怎么会那样用心去激励他们呢?不然的话,天下之人都应该被劝到南昌去了,这能讲通吗?《中庸》上讲“笃躬而天下平”,笃躬指的就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德行、显示于外面的学问。那样去做,天下尚且可以平定,更何况去交友呢?岂知行人整日沉溺于恶习和污染中而不觉察。所以说移山容易,积德彰文难。
以上三种情形如此困难,所以说交友难。
【原文】
三、依师之难,亦有三:一值明师难,二启自信难,三会合时难。
(一)值明师难
我眼本正,因师故邪。今古同慨也。学人本无欣异趋奇,纯然一幅净纸,而师家无实证,一一相似而言,糅杂而谈。问东则对东,问西则对西,为据实之谈;问东则以西对,问西则以东对,为超方之说。狐媚学人,亲瞒自己。末法时代,亲证者少,和会者多。一犬吠虚,千猱哇实。所谓"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天下翕然从风,众盲藐焉归化,虽有独立特行之圣哲,悯众生愚痴,以张慧魔外,恣逞而然犀,亦不可能。何也?君不见乎达摩仰毒、师子断头乎?故曰值明师难。择师具眼,古哲多途。今略以左之二事决择之。
1.品行高洁、戒律精严者;
2.不以法缚人、理陷人、无得无授者。
【译文】
三、依师难,这里面也有三种情形:遇明师难、使自己相信难、机缘相会难。
(一)遇明师难。
自眼本明,因师而盲,这是古往今来一种相同的感慨。求学之人本来并不喜欢猎奇,完全就象一张白纸,老师并没有实修实证,只讲一些似是而非、夹杂不清的道理。问东答东,问西答西,以此为据实之谈。要么就是问东答西,问西答东,以此为超方之说,取悦求学之人,欺骗自己。末法时代亲自证的人少,附和的人多。随便有一个人说些什么,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起哄。所谓“竹子生出青宁,青宁生出程”,(此《列子》中语)天下翕然从风,一般无见识的人都去归化。虽然有些特立独行的贤人怜悯众生愚昧,用尽方法想救醒众人,也已经无法挽救。为什么呢?诸位难道不知达摩祖师被毒而死、狮子断头的事吗?所以说遇明师难。择师要有眼力,先辈各有途径,现如今简单说出下面两条择行标准。一是品行高洁、戒律精严之人;二是不用定法来束缚人、不以理害人、无得无授的人。
【原文】
(二)启自信难
既值明师,昧于决择,疑而不信,或信而不专。圆悟勤犹舍五祖演而之金山,黄龙南因石霜圆乃登南岳。故密乘事师,示有仪轨,盖启自信而信人,信人即所以自信也。
(三)会合时难
知明师也,地分南北,事互穷通,趋庭不易,负笈维艰,所以牛头切思四祖,黄檗谒错马师。故曰会合时难。统此三支,曰依师之难。
【译文】
(二)使自己相信难。
已遇见明师,迷惑而不知决择,怀疑而不相信,或者虽然相信但不专一。圆悟勤尚且舍五祖演而另去投金山,黄龙慧南禅师也是为了另投石霜圆楚为师才去衡山的。密教在拜师时很注重仪式,就是先自信进而信人。只有自信了才能相信别人。
(三)机缘相会难。
知道了明师,但南北相隔,或人事困扰,不能投奔。所以牛头山法融禅师起初也只能思念四祖道信,黄檗也错过拜马祖为师的机缘。所以说机缘相会难。
以上三个方面说的是投师难。
【原文】
四、不自瞒难,亦有三:一被己瞒;二被他瞒;三总不被一切瞒瞒。
(一)被己瞒者
行人自曰一切法尽空有,穷三际,总不外此一心。此心者,我也。若无此心,则一切种种从何而立?既有此立,非我何立?我立有我,我当不坏。今不尔者,修命之说灼焉而炽,则滥觞乎阴阳、丹道、解幻、蛊巫,故曰被己瞒。
(二)被他瞒者
知心非有,心非有者,然实有有。今既有有,有实因他而有。于是乎炼神还虚之说炽也。故曰被他瞒。
(三)总不被一切瞒瞒者
己无上之如是等过,认空有一切皆空,执以为是,曰不受一切瞒。于是放荡形外,莫驭环中,置国家于不顾,弃父兄而如遗。身陷险过浪不知非,故曰总不被一切瞒瞒。
总以上三支为不自瞒难。
行人果于上之数者,穷研而精讨,则立此难行中庸为有意、为无意、为何意,不剖而析也。
【译文】
四、不自欺难,这里面也有三种情况:一是自欺、二是被外物欺骗、三总不上当。
(一)自欺。行人自己思量道:“一切法尽空有,穷三际,总不过是这一个心。这个心就是我,如果没有这心,世上一切种种从何而立?既已有了这种种一切,不是因我怎么能立?我立有我,这个我应当不坏。”但现在则不这样,修身养性的学问炽然兴起,于是产生了阴阳、丹道、解幻、蛊巫。所以称之为被自己欺骗。
(二)被他欺骗。知道心并不是实有,心虽不有但却确实有,既然有有,于是炼神还虚等邪学因此大盛。所以称为被他欺。
(三)总不上当。自己没有了上述种种过失,认识到空、有一切皆空,执以为是,自称不受任何东西欺骗。于是就放荡不羁,不遵法度,置国家于不顾,抛弃父兄如丢弃东西,身陷危境,却一点不以为非。所以称为总不上当。
综上述所述三种情形,统称为不自欺难。
行人如果真能将上面讲的好好研究琢磨,那我讲的这一节“难行中庸”是有意,是无意,是什么意,这一些都不用讲而其意自明了。
第二节经文
【原文】
[朱注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朱注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译文】
[朱注第四章]孔子说:“大道何以不流行,我已知道是为什么了。聪明者过了头,愚蠢者达不到它。大道何以不显明,我已知道是为什么了。贤德者过了头.不肖者达不到。人都是要吃饭的,但很少有人品尝出滋味。”
[朱注第五章]孔子说:“大道恐怕难以实行了啊!”
【原文】
一、释字
行 《说文》: "人之步趋也,从ㄔ从亍。户庚切。"今注曰"反止曰行"。
明《说文》:"照也。从月从["四"字内加"ㄇ"]。武兵切。"["四"字内加"ㄇ"]者,窗牖丽楼闿。明,象形,古文明从日。"今注曰"破暗曰明"。
【译文】
一、释字
“行”。《说文》:“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户庚切。”我解释为“不停下来称为行。”
“明”。《说文》:“照也。从日从["四"字内加"ㄇ"]。武兵切。古文”明”从‘日’。”我解释为“打破黑暗谓明。”
【原文】
二、通义
道,中庸之至道。当人一切事理、非一切事理明而适,行而适,无过不及也。不行则天地闭、贤明隐;不明则天地晦、贤明遁。贤明者,所以开明天地、式范万流也。反止曰行。今曰不行,则反行即止。破暗曰明。今曰不明,则破明即暗。若然,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夫妇妇、上上下下,咸失其适。讵中庸之道邪?记曰"天下昏昏,黯然失钧",责固肩乎贤明也。而智、而愚、而贤、不肖,不曰过,即曰不及。愚者固愚而不及,非知﹔贤者又越而过之,亦愚,不肖者,固不及而非贤,彼贤而过之者,亦不肖也。一十五双,宁有轩轾?夫过、不及而失驭乎中庸,无过、不及即趣乎中庸也。至简至易,宁逾于斯?曰行、曰难,无乃冤乎?既趣入也,过亦中庸,不及亦中庸,不过不及、亦过亦及皆中庸。贤亦中庸,愚亦中庸,不肖与智无不中庸。以之京于国则大,齐于家则治,用于民则亲,律于己则逸,柔远人、怀诸候、来百工,无一事而不宜,无一行而不迈。所谓繁兴大用,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下文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如是已举、未举,一切必得等,不假他求,一时具足,而当人昧不肯趋,习不欲趋,奋不能趋,以至易而形至难搁如是胜行,而不知趋,枉陷沉沦,虚荣生死,真自饮自食而不知其味也。故曰难行。
【译文】
二、通义
道,指中庸这一最高明的道理。人某对一切事理、非一切事理,理解得恰当,做的恰当,那就不会有过头和达不到这两种问题。至道不行,那就会天地闭塞,贤人隐退。至道不明,那就会天昏地暗,贤人隐退。贤人是用来照耀天地、为万世做楷模的。不停下来称为行。现在说“不行”,也就是停了下来的意思。打破黑暗称为“明”,现在说“不明”,即谓光明消失带来黑暗。那样的话,就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丈夫妻子,上上下下,全都乱了套。岂是中庸之道?儒家经书上讲“天下昏昏沉沉,失去了标准”,这个重任自然要落在贤人肩上。但智者、愚人、贤人、不肖之徒,不是做得过了头,就是做得还不够。愚人固然愚蠢而不能到达,所以不明智。贤人又过了头,实际也是愚人,不肖之徒,做得不够,当然是不贤人,但贤人做得过了头,其实也是不肖之徒。一十二五,难道有什么高下之分?过头、做得不够都不合于中庸,没有过头或做得不够可能趋向中庸,这最简单不过,岂有比这更简单的?说什么行说什么难,难道不有点冤枉吗?既已悟入中庸之道,那就过头是中庸,做得不够也是中庸,不过不及、亦过亦及都是中庸。贤是中庸,愚也是中庸,不肖与智没有不是中庸的。以此来治国,国家必强大,治家,家必秩序井然,用于百姓则百姓归心,用来约束自己则安逸而中规中矩,怀柔边远之人,安抚渚侯,招揽百工,无事不宜,没有不顺利的,所渭“妙用无穷”。孔子七十岁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违法度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下文里讲到“必享高位,必享厚禄,必享盛名,必享长寿”等等说了的没说的种种享受,不需要另外去寻求,一时都已具有。而修行之人愚昧不知趋向、尘习拖着他不能趋向、清狂而不能趋向,以如此难以名状而其实却最简单的妙理,却没有人知道去努力而趋向它,白白地陷入沉沦境地,空受生死大苦恼的纠缠,真是亲口饮食而不知其滋味啊!所以说难行。
【原文】
人固无不饮且食者,既饮且食也,叩以味,非不知,然其所以为味者,则昏昏而罔言也。一时不中则失和,一时不和则非中。不中不和,乖戾斯激。人固无一日不履乎中庸也,既履也,叩其道,非不知。然其所以为道者,则昧昧而忘言也。此至简至易,而行者蹀躞难趣。故子思引孔子之言曰"道其不行矣乎",启难行之永叹,兴末学之跻齐。故曰难行。必曰游乎通径,义固在乎当仁。
【译文】
人当然没有既不喝也不吃的。既喝又吃,问他什么味,不是不知道。但问他为什么是那样的味道时,他就昏昏沉沉哑口无言了。一时不中即失和,一时不和即非中。不中不和,乖僻偏激。人本来没有一天不是行着中庸的,既行中庸,如果问他中庸之道,并非不知道,但问他何以那样做才合乎道时,他就茫然而不知如何回答了。这道理本来最简单不过,行人却缩手缩脚难以趣近。所以子思才引孔子的话说道:“大道恐怕难以实行了啊!”感慨大道之难行,引发后生向前贤看齐的豪情。所以说难行。如果一定要走上大道,那就得当仁不让才行。
第三节拈提
【原文】
问曰:"此中庸者,千圣之心灯,不思而得,无为而成,当体即是,不假修治,无乃过易欤?"
先生曰:"唯,唯,过易!过易!"或诘曰:"古德千里趋诚,殊方决择。有周克殷,《洪范》犹借传于箕子;永嘉入道,妙谛尚趣证乎卢公。况十五志学,七十从心,警枕封衾,铭心断臂者,更无论也。无乃过难欤?"
先生曰:"唯,唯,过难!过难!"诘者又曰:"曾子之唯,了在一贯;子路之拱,闻于时哉。一唯即得,一拱斯通。此亦何得?既无所得,斯亦何难?又武王受命,经称曰:‘末';宝掌闻玄,年已逾耋。彼二至人,尤难如此!实已非易。故曰有缘者得,无心者通。无乃非难非易欤?"
【译文】
学生们问道:“中庸,是千千万万圣人的不灭心法,不用思索即可获得,不用作为即可修成,当体即是,不需修炼,不也太容易了吗?”
先生说道:“是这样,是这样。也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有人反问道:“古时贤人为求道奔波千里,多方决择。周人灭商,尚且从箕子那儿学得《洪范》篇,永嘉玄觉禅师能够入道,还多亏了六祖慧能印证。况且十五开始学习,至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胁不至席,铭心断臂,这些都不用讲了。又是否显得太难了?”
先生答道:“是这样,是这样。也太难了!也太难了!”质问的人又说:“曾子回答孔子时称‘唯’,是他明白了孔子之道用什么来一以贯之。子路拱立路旁,是因他听明白孔子说的道理。曾子应声确有心得,子路拱立心已想通。他们得到了什么?既无所得,这又有何难?另外,武王受命,《中庸》里称其时已经年老;宝掌和尚领悟佛法时,已年迈苍苍。这两个贤人得道如此困难,实在不能说是容易。所以说有缘人可以得到、无心者可以领悟。难道既不是难也不是易吗?”
【原文】
先生曰:"唯,唯,非难非易。"如是数问数答,总如前式。海众罔知所寄,默然无语。先生亦肃然在座。久之,乃朗吟曰:"鹧鸪啼了又鸣鹒,先到黄鹂四五声。毕竟惜春情未已,强扶筇杖为他行。"吟已,问曰:"会么?"众云:"不会。"先生曰:"从古及今,不知谁人能会?"复曰:"此章权名难行,盖由统而赞,既赞思行,因行知难,行人当然过程。然师家亦感诲人之匪易也。曰君子、曰小人、曰贤智、曰愚不肖,一切病一切非病,彻底剖陈,通体揭出,而病源贼薮要不外过、不及也。若曰过量人,一闻便悟,一举斯通。借摇扇于江外,假活语于楼中。抑亦钝根阿师,况取语口头,闻玄纸上邪?唐之中叶,有庞公蕴者,庵中独坐。蓦地云:‘难,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庞婆接声云:‘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其女灵照复曰:‘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彼一家者唱和如此。迄宋,有妙喜老人者,圆悟勤入室之骄子也,而于此三则话言,下了一个注脚云:‘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识博量卜度,非独不见三人落着处,十二时中亦自昧却本地风光,不见本来面目,未免被难易不难易牵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将此三人道的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带水下注脚也。'云云,汝等诸人若云将此三人道的作一句看,或作道理会,或作无义路解,不但孤负三人,并且埋没妙喜,又自把己置向镬汤烈火中也。然则毕竟如何?"久之,顾视大众曰:"千圣不知何处去,倚天长剑逼人寒。"下座。
【译文】
先生说道:“是这样,是这样。既不难也不易!”如此数问数答,先生总是像前几次一样回答。众人不知其意,默然无语。先生也庄重地坐在那儿。很久之后才朗声吟道:“鹧鸪啼了又鸣鹒.先到黄鹂四五声。毕竟惜春情未已,强扶筇杖为他行。”吟诵完毕先生问道:“会了吗?”众人说:“不会。”先生说:“自古到今,不知道谁能证会?”又说道:“这一章权且叫做‘难行’,是因为从大纲讲到赞美,既已赞美便想着去实践,因实践才知道困难,修行之人自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但师傅也深感教诲他人不是那么容易啊!称君子、小人、贤智、愚、不肖,一切病一切非病,彻底剖开展示,全部揭示出来,病根不外乎过头和做得不够两种。如果过量人,一听就悟,一举就通。借扇江外,假语楼中,也是钝根浅机,更别说哪些闻道于口头、纸上的人了。唐朝中期,有位居士名叫庞蕴,在庵中独坐,忽然开口说道:‘难!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他夫人续道:‘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庞蕴的女儿灵照又说:‘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这一家人如此唱和。到了宋朝有位妙喜老人,是圆悟勤禅师的高足,又把那三句话做了一番解释:‘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如果用尽心思去猜测,不但不知那三人落着处,十二时中昧却自家本地风光。既昧却自家本地风光,不免让难易、不难不易这些话头给纠缠住,不得解脱。想要解脱而得大自在。应把那三人说的当一句看,其实我的注释也是拖泥带水了’等等。你们诸位如果把那三人讲的当一句看,或者作道理理解,或者作无义路理解,都不但辜负了那三人,并且埋没妙喜老人,还把自家推进火坑。那么究竟怎么说?”先生停顿良久,然后环顾众人说道:“千圣不知何处去,倚天长剑逼人寒。”先生说完离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