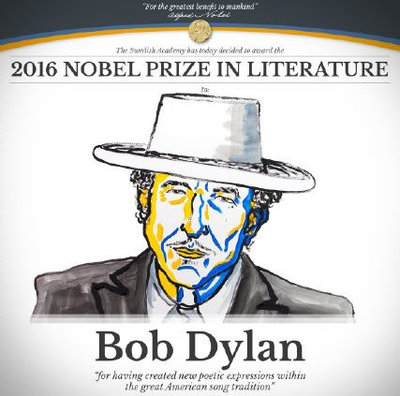(图1:鲍勃·迪伦和琼·贝兹堪称民谣界的“帝与后”,他们曾经的恋情也为民谣歌迷所津津乐道)
鲍勃·迪伦是当代流行音乐独一无二的现象,从他成为一个民歌手至今,他用难以置信的勇气,最大限度做到了对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规则的顽强挑战,他不屈从,他始终遵循他的大脑,而不是身外的任何商业规则。在此之前,也只有作家塞林格有过类似的做法。这让习惯商业规则的人们对迪伦这个人无所适从,激增了媒体和公众对这个怪人的兴趣,他的歌词、音乐、外表,甚至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人们猜测、分析的话题。但是,迪伦从来不正面解答人们对他的疑问。这反倒让人们的好奇心变本加厉,无数解读、分析迪伦的文章、书籍面世,但人们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反,这个蹩脚的诗人、反商业的歌手,在他写过的上千首歌中,没有几首成为热门歌曲,他的歌词也没有多少人能看明白,换一个人,人们早就会把他忘记,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迪伦。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用反商业方式获得成功的人,他为自己创造的商业价值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他好奇的人们因为他而创造的商业价值无法计算。鲍勃·迪伦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只刚刚从水里爬出来的猫,本能地用最快的频率抖掉身上的水一样,把人们贴在他身上的东西抖得一干二净。如果说贯穿了过去整个50年人们喜欢谈论鲍勃·迪伦作为一个美国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还不如说迪伦是一个抗议后工业社会规则的歌手。
主笔◎王小峰
“我不能告诉你”
斯科特·科恩在1985年采访迪伦时曾经这样描述他:
鲍勃·迪伦,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上十字架、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他携一把吉他,一只口琴,一顶灯芯绒帽子,一个伍迪·格思里和小理查德的混合体,在1961年像一阵风一样开始了他的传奇。他是第一个朋克民歌手。他把抗议歌曲引入了摇滚乐。他使歌词变得比旋律和节奏更重要。他的沙哑的歌喉和浓重的鼻音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创作超现实主义的歌曲,却具有自己的逻辑——就像詹姆斯·罗森奎特的画作和兰波的散文诗一样,简单,直指内心,带有民歌特有的轻松。他可以调用夜晚的黑暗,将白昼涂黑。
如果他可以自己选择,他可能会成为猫王之后最成功的性感偶像。
当他1965年在新港民歌音乐节上,登台演出插电摇滚乐而引起了骚动,纯正的民歌派别认为他出卖了自己。之后在爱与和平运动的顶峰,人人追随东方宗教的时候,迪伦头戴圆顶小帽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哭墙。10年之后他成为一个获得新生的基督徒,发行福音专辑。人们发现,迪伦真的和他之前不太一样了。
并不是迪伦忽然间变得不太政治化,而更追求灵性了。《圣经》里面的诗句一直都是他在歌曲里面经常引用的。人们多年来一直称他为预言家。谁知道呢,也许一场神性的转变即将到来,而摇滚乐则为新生世界拉开了序幕。还有谁能成为比鲍勃·迪伦更好的先知呢?
有时候,当远距离观看一件庞然大物时,往往近观会发现并非如此。迪伦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一样。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住在加州海边他的隐蔽居所里。尽管他近来常常曝光,参加格莱美,录制音乐录像带,甚至接受访谈,但这些丝毫不能减少他的神秘。
事实上,迪伦在今天重新定义了“艺术家”这个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流行歌手通常被称为唱片艺人,他们提供给大众的是一种娱乐消遣行为,很少有人把这些艺人跟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往往指的是画家、作曲家、作家。但迪伦的出现,重写了这个概念,他做的事情与任何一个艺人做的无异——录制唱片,像底层流浪艺人那样到处演出,但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一生充满叛逆和不妥协的艺术家。
迪伦从来不跟媒体和公众互动,不管在他成名之前还是之后,明星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被默认为是——你作为明星有责任回答人们的好奇和疑问,因为这可能会给你带来直接商业利益,并且是互利行为。一直以来,商业媒体、明星、公众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以互动的方式存在,从没有改变过,直到迪伦出现。
1962年,刚刚出道只有21岁的迪伦,在媒体面前就显示出他冷漠刻薄的一面,在一次广播节目采访中,主持人问:“为什么要到纽约?”迪伦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会牵扯到其他人。”在剩下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回避了主持人提出的任何问题,导致这个节目不得不中止。1963年,他在另一次广播节目中,主持人问他:“《暴雨将至》这首歌中的‘暴雨’是不是‘核雨’的意思?”迪伦说:“仅仅是暴雨。”当有人问他:“你是唱自己的歌还是别人的歌?”迪伦的回答简明扼要:“现在都是我的。”迪伦在接受访谈时的冷漠、嘲讽和机智,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自己,让他在媒体和公共视野中逐渐变成了一个谜团。
1969年,迪伦接受《滚石》杂志主编詹·温纳采访时说:“如果你接受了一家杂志的采访,很快,你就会被采访所包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接受采访的原因。”但很快有好事者对迪伦接受采访次数做了统计,从他出道至今,平均每个月接受一次媒体采访。不过从这些采访中会发现,迪伦熟练地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着整个采访,他用冷漠、尖锐的思路主导着谈话内容。在采访中他通常不会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更喜欢把媒体当成一个笑料来对待。媒体不顾一切想尝试界定他,试图使他钻进设定好的圈套,但是迪伦谜一样的态度让媒体无功而返。由于人们无法搞懂迪伦,无能的记者喜欢用平庸无聊的问题来对待迪伦。曾经采访过几次迪伦的乐评人罗伯特·希尔本说:“在他心里,就根本没把媒体当回事,人们总试图为他贴标签或者归类,所以他对整个采访和报道过程感到怀疑。”
迪伦的脑子里永远有无数和采访者希望知道的结果截然相反的答案,或者他的回答让人抓狂又难以捉摸。包括他的歌词,读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却勾起人们破解密码一样的兴趣。他经常在歌词中引用很多人物或者发表无数观点,但是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代表他的。
1966年迪伦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采访者是纳特·亨托夫,亨托夫在当时也算个挺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个爵士乐手,小说家,乡村歌手兼乐评人。看看迪伦当时是怎么耍弄亨托夫的,他说:“看,我没那么深刻,事情也没那么复杂。我的动机不管是什么它都不是商业性的,不是为了钱。但我挣钱了,我就顺其自然了,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去做这个事情。我的老歌,可以这么说,它什么意义都没有,新歌也一样没什么意义。唯一不同的是,新歌在一个更大的观念下写的,可能也是无意义……我知道我的歌是什么。”亨托夫好奇地问:“是什么?”迪伦说:“有些歌大约4分钟长,有些5分钟长。有一些不管你信不信,大约有11分钟或12分钟长。”
这种滑稽可笑的回应才是真正的鲍勃·迪伦。他一直很清醒地试图让人对他自己和他的作品感到迷惑不解。在看似严肃正经的回答背后,是迪伦为了保护自己私人世界不受到任何干扰。他说:“我唯一想对他撒两次谎的,一个是自己,一个是上帝,媒体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次在电视直播现场,他被问到:“你是怎么解释你的吸引力的?”他回答:“对什么的吸引力?”当他被问到是喜欢表演还是录唱片的时候,他严肃地说:“演出确实比以前有意思多了,但是唱片更重要,它确实可以容易听到歌词和其他东西。”
1986年迪伦在接受《滚石》杂志科特·洛德的采访时说:“当我回望过去,我很惊讶写出了那么多歌,现在回想起来,我写歌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你知道吗?写《荒芜之街》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某一个夜晚,歌词也没什么逻辑,它就从我脑子里出来了。”在另一个访谈里他的回答也大同小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反正那些早期的歌曲很神奇地写出来了。”
于是人们喜欢分析迪伦的歌词,试图寻找答案。迪伦意识到了一点,他厌烦人们的这种喜欢在歌词中搜寻隐含的意思和透露的信息的做法。所以人们评论迪伦的创作是“创造性完全是神秘甚至充满魔力的过程”。大概过于关注自我和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无拘无束的创造性。人们对迪伦的期望就是失望的过程。包括他自己。
2005年,迪伦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归家无向》中回忆他早年与媒体打交道时说:“他们认为表演者会提供所有社会问题的答案,这太荒谬了。”他还说:“谁还指望什么?我是说任何人从我这里期待得到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界线的问题。但凡现实一点的人都不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已经给他们足够多了,他们还想从我这要什么?你不能总是指着一个人给你所有的东西。”
迪伦是少有的保持一个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大隐隐于市的人。他50年来形成的深不可测的完美化形象可以随处可见。然而,今天却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看起来很难做到,但是他却实现了。
(图2:1966年5月,鲍勃·迪伦在巴黎乔治五世酒店接受媒体采访)
“我不属于任何运动和团体”
谈论迪伦,一直都无法避免“抗议歌手”这个话题,这个头衔是迪伦最风光、社会背景最混乱的上世纪60年代扣在他头上的。与其他标签不同的是,“抗议歌手”不是贴在他脸上的,而是刺在他脸上的,让他一生都洗不掉。
迪伦最为著名的抗议歌曲是在60年代初期的20个月内集中创作完成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迪伦就背弃了它们。恰恰这20个月创作的歌曲,成为迪伦后来最有影响作品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迪伦当初写出《时代变了》或者《答案在风中飘》这样的歌曲只是就事论事——因为谁都能看明白他写的是什么。后来迪伦抛弃对政治的兴趣,离开左翼激进主义,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激进。同时他的性格不可能像约翰·列侬那样成为一个街头演说家——尽管两个人同样具备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
《时代变了》确实是一种挑战,那时迪伦可能相信社会变革在所难免,民权运动,反对“越战”、“冷战”、核威慑……对于一个从小地方来到纽约大都市混迹于艺术圈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冲动最终把他推向时代代言人的位置在所难免。民权运动的成功改变了美国政治的版图,同样也给迪伦带来了机会。在他创作的反战歌曲里面,不管他是否承认,它包含的内容有核军备竞赛、贫困、激进主义、监狱、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恐惧。当然也包含一些爱情歌曲。
《时代变了》给迪伦带来真正的成功,他变成了社会运动领袖。换一个人,此时会勇往直前,这样的机会可以为自己赚得很多实际的东西,但是迪伦没有,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不是他需要的,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背叛这一切。作为一个叛逆者,他背叛了自己。一个被称为新时代的伍迪·格思里的人就这样抛弃了他的一片大好河山。他在1964年对亨托夫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去做什么代言人。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写我内心的东西,我不属于任何运动和团体。”
从此,人看到了一个不断背叛自己的鲍勃·迪伦。但他的忠实歌迷并没有这样饶过他,他们希望迪伦继续抗议下去,继续为他们代言。在一次演出中,观众们喊着让他唱抗议歌曲,迪伦冷冰冰地说:“听吧,这都是抗议歌曲。”
迪伦从心里认为这是观众和媒体对他的无理纠缠,妨碍了他遵从内心的意愿,于是他做了更为极端的事情。1965年在新港音乐节上,他像恶作剧一样给传统民歌通上了电。这在纯粹的民歌听众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迪伦听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多的嘘声。但恰恰是这一举动,让迪伦打开了自己的世界。文化评论者迈克·马克西说:“迪伦的态度却逆向而行。对他而言,远离政治就是远离陈旧的概念,以及人云亦云的所谓态度。这种远离的态度是将假装无所不知重新定义为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图3:鲍勃·迪伦与乐队成员合影(摄于1984年))
(节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