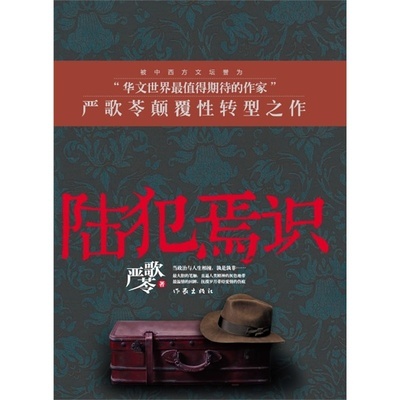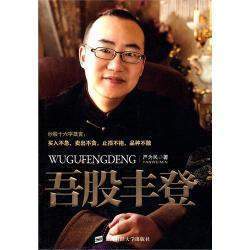壹读iRead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yiduiread

壹读iRead记者 苏更生
即便在中国文坛上活跃的作家里,严歌苓也算得上高产。继去年的《陆犯焉识》获得了中国小说协会长篇小说的首奖之后,她又推出了新作《补玉山居》。她另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编剧,与影坛数位知名导演合作过,从《少女小渔》、《天浴》,到《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坐稳华语第一女编剧的宝座。但她却想要回归到她的起点,也是终点—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
天生编剧难自弃
严歌苓全家都是作家,父亲萧马、前夫李克威、公公李准都是作家。严歌苓一出生就对写作耳濡目染,成为作家似乎是必然的。
父亲萧马不仅是作家,也是编剧,写过《淝水之战》、《青春似水》等电影。严歌苓第一次改写的剧本就是父亲的小说《无词的歌》。当时严歌苓已改写大半部分,递给父亲过目。萧马看完说:“我重写一遍。”严歌苓拿着父亲改写的剧本一看,觉得惭愧不已,萧马说:“你看看,写剧本应该是这个感觉。”
父亲让严歌苓明白了好剧本是什么样,但她却不想写剧本。在严歌苓心中,小说才能激发创作欲望,剧本只是卖钱的东西。但她的小说还未出版,即有影视公司来买版权。
从张艾嘉拍摄的《少女小渔》,到陈冲的《天浴》,后至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这些由严歌苓亲手改编于自己小说的电影无论电影好坏,都让严歌苓在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受到极大的关注,这种由影视所带来的人气让诸多作家羡慕不已。但严歌苓不愿意做编剧。曾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作编剧怎么样?她硬生生地回一句—不怎么样。
严歌苓将自己定位于严肃文学作家,认为自己最擅长小说语言,而非电影语言。“要写电影,首先要懂戏剧。有时候把戏突出了,就通俗了,不够严肃了。跟我的原则是相悖的。我喜欢电影,但从来不看电视。文字之外的东西,可以通过电影语言表达。但是这些东西在电视里,全部没有了。电视剧一集集要让人上瘾,必须煽情。煽情是我最讨厌的东西。”
但在严歌苓的小说中,随意拎出一段对话,都可以直接放上银幕成为台词。这是严歌苓小说的特点之一。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编剧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压缩,情节删减,但鲜少改动对白。小说中,妓女以南京方言嬉笑怒骂,将脏话、性事糅进笑话里,这些泼辣的对话直接成了电影中的台词。
严歌苓在小说中让人物所说的对话,接着一股鲜活的地气。《第九个寡妇》里有河南方言,《小姨多鹤》里有东北方言,在以南京话为主调的《金陵十三钗》中,妓女辛辣的荤话配以糯软的语调,将秦淮妓女的粗俗且鲜活的形象复苏在纸上,而后又被张艺谋搬上银幕。
这只是严歌苓的小说适于被拍成电影原因之一。张艺谋曾称赞过《金陵十三钗》是他这20年间见过的最好的剧本。严歌苓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编剧,都能将故事讲得圆满。从铺埋伏笔、推动情节、侧线叙事,她都能将细节和故事串联成为完美的故事。
新作《补玉山居》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龙门客栈’”的故事。北京附近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村里,漂亮能干的姑娘曾补玉看准了京城各色人等来山村休养生息的好市场,因势利导开起了小客栈—补玉山居。小客栈成了大舞台,来往的顾客则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的好戏。被重述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又被影视圈瞄中,这一回严歌苓再次亲自操刀剧本。“耳根子软了”,她解释道。
自杀就要死透
严歌苓出生于1957年。童年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孩子,她所见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自杀。
她生活在作协的大院里,每听见外头大喊有人跳楼啦,就兴奋地冲出门去看。有一次,有一对老夫妇从楼上手牵手跳了下来,尸体被拖走后,泥巴地上留着两个被砸出的大坑。一阵风吹过,楼上飘散下许多五颜六色的糖纸。当时买糖要凭票,每月一人能买二两糖果。严歌苓猜想,是两位老人在决定死之前,把积攒下来所有的糖果都先吃掉。
她幻想老人跳楼之前的情景,两人一颗一颗拨开糖纸,吃掉糖果,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慢慢地站起来,拉着手跳楼。自此以后,每有风吹起,楼上都会飘落糖纸。这些五彩斑斓从天而降的糖纸是严歌苓对人性最初的印象。
另有一位与父亲交情颇深的女作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吞服安眠药自杀。人们把她送到医院,把她衣服脱光了插上各种管子,但医院又不愿意接收畏罪自杀的人,就干脆把她放在走廊上。
赤身的女作家身上盖了一块床单,过往的人偶尔不坏好意地掀起来窥探她的裸体。在旁的严歌苓十分愤怒,对这些人怒目而视。有一个电工走过,故意将烟头掉在床单上,假意去捡,将床单抖起来,偷看女作家的裸体,严歌苓狠狠地瞪他,并在女作家的身旁守了一整夜。后来这位女作家被救活了。
成年之后,严歌苓对这位女作家说:“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你都不知道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极端时刻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复杂与丑恶让严歌苓记忆深刻,但她并不明白这是些什么。
她通常是将这些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故事储藏起来,等着哪一天能够发掘背后的意义,再写下来。严歌苓说自己有一双好耳朵,善于听到各种故事,放在心里。有些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不值得写,有些发酵出来的故事有更深的内涵,她就把它们写下来。
这种倾听和发酵远远不够,严歌苓每次写作之前,都要做好实地调查。写《第九个寡妇》时,她在河南农村住了两次,找农妇聊天,习惯河南方言;写《小姨多鹤》之前,多次带着翻译赴日本采访调查。每次写作,可能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前期的准备之上。有时候一个故事从构思到写完,中间可能有20年的时间。
除了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她还有很多鞋,能够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象各种人的心理。在厘清历史背景、查实人物严歌苓对于书中女性主人公的生命体验有生动描写,也有一套自己的女性哲学。之后,她还要凭借想象构建一个完整的人。严歌苓说:“一个作家,要能站在任
何人的鞋子里,去感受、去发现。”只有这种,才能进入人物,将其复活。严歌苓对
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极高的。她写完之后,狠命删,删除多余的情节、抒情段落,删掉10万字也不眨眼。
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
不止是写作,她生活里也透着一股子狠劲。
她15岁初恋受挫,留下了失眠的毛病。最长的时候失眠30多天,脑子浑浑噩噩,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见到人感觉是“嗖”的一声冲在面前。眼睛不能见光,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别人一问是不是睡不着,她就张口大哭,“心里觉得委屈,就像全天下人都抛弃了我。”
严歌苓12岁参军做舞蹈演员,到各地演出,但她觉得自己跳不好,不愿意跳。20岁时,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开始,为了逃避跳舞,她主动要求当战地记者,退伍后成了专职军旅作家。30岁时想出国,一句英语不会,抱着《新概念》背单词。出国后没钱,GRE成绩还不达标,听说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
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
终于上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但钱不够。她利用暑期在餐馆打工,兼做保姆。打完一天工,晚上跑到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天,回家吃了安眠药倒头就睡,几个小时后醒来开始做作业,老师要求写3页,她就写6页。然后亢奋地又开始一天的打工生活。
刚开始在美国生活,每天都遇到新鲜事物,生活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她进入一个洗手间,一大排水龙头在那儿,严歌苓就站在那儿看别人怎么打开。当时国内只有一种拧法,美国的水龙头有很多种拧法,她就怕自己半天拧不开水龙头,显得很笨拙、很傻。
她在异国生活之中感受到的不是苦闷,每日都有新鲜事物,每次都能激发她的灵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处于敏感的边缘,她用自己所有的感官来感应,面对应接不暇的变化。此时灵感迸发,她写下了诸多短篇和中篇小说。
严歌苓本人打扮入时,妆容精致,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柔弱不堪。她此番对外表的苛求讲究,好像也透着一股遵守纪律的狠劲。现在严歌苓每日在家写作,一到下午三点,她会停下来,开始化妆,换上漂亮衣服,拾掇房间,静等丈夫归来。每日如此,绝无例外。
好友陈冲取笑她:“你们当作家的,猫三日狗三日得了,天天如此约束自己,何苦。”严歌苓反驳:“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这种严格带着一种努力,避免自己写不好,做不好,以致被可怕的生活吞噬。这种狠劲也被她写到小说里,严歌苓书里的女人,为儿女操劳一生倒在锅台上,见到毛线就能织衣服。吵架舍得脸,打架舍得命。玩起来,敢扒男人裤子,
闹起来,敢脱了自己裤子上门吵架。
这种土得掉渣的狠女人,只有严歌苓才能写得鲜活。
版权归《壹读iRead》杂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引用、如需转载请联系:yidu@ireadweekly.com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