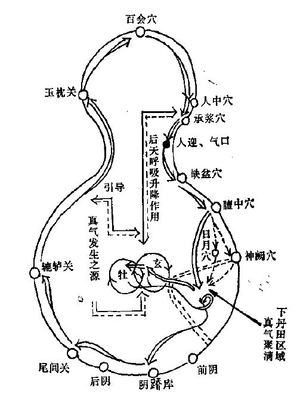“夜深了,四周不再喧嚣,心也跟着沉寂下来。这时候,一些想法浮上心头,一些话语想要诉说,来,谈谈心吧,辽远之中,夜渡心河……”
这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曾统治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长沙夜空,给无数孤独的灵魂照亮过回家的路。
但是尚能,你自己找到回家的路了吗?
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得知李尚能的消息,是十几年前无意看到一篇纪念著名散文家、诗人徐迟的文章——《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好像是《人民日报》副刊)。文中提到同样选择以自杀方式谢世的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尚勇。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大学同班同学李尚能。
尚勇就是尚能!
一代主持奇才李尚能(图片来源:necor网)
被誉为一代主持奇才的李尚能,在主持湖南经济广播电台《夜渡心河》栏目的四年时间里“用睿智、敏感、博学和细腻,抚慰了无数颗孤独、寂寞、迷茫和无助的心。许许多多徘徊在湘江畔边的惶恐、迷惑和痛苦的不眠者找到了方向和途径……”。湖南电视尚未火爆的九十年代,李尚能创造了广播界收听率奇迹,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谈话类节目难以逾越的“尚能时代”。
对李尚能的成功,我毫不惊讶。早在大学时代,担任校广播站站长的他,过人才智已显露无遗。在人们以不同的声音揣测他的死因时,我似乎在“尚能”和“尚勇”的一字之差里,悟出了些什么。
虽说逝者为尊,可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对大学时代的尚能印象并不佳。尚能的心气很高。大一时,他和从体育系转到中文系来的Y交往甚密。Y原来是排球运动员,高挑匀称的身材,姣好白皙的面容,称得上中文系的系花。尚能虽说只有一米六几的身高,和Y倒才子佳人地登对着。
一天傍晚,尚能到宿舍来找Y,一听说Y和文学社社长、大四的学长田君到江边散步去了,便满脸怒气地往外冲。我和Y的关系不错,担心会起冲突,跟在了他的身后。在江边,我们遇到了独自回返的田君。尚能二话没说,甩手就给了比他高出半个头的学长一记耳光后扭头就走,扔下儒雅的田君呆在原地发愣。
Y终究还是和尚能分手了,找了体育系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教师。传闻男教师同时和英语系一个面容更加姣好的女生关系暧昧。伤心的Y毕业后远嫁香港,不知现在是怎样的情景。
尚能家在长沙,因从小在北京生活,操一口纯正的京腔,这使他在多是农村出来的同学中感到优越。午休时,他时常召集几个长沙的朋友在宿舍打牌,闹得舍友没法休息,却又敢怒不敢言。这让同学们对尚能颇有微词。
大学时代的李尚能(左一)
学生时代的尚能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记得大一时学校搞语音观摩排话剧。当时我们年级编排的是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演的是贪婪、凶悍的渔夫妻子,扮演渔夫的是我的男友。节目最后只拿了优胜奖。可能是角色安排没能让尚能遂意,评选结果出来后,他特意走到我面前,奚落道:不过一个安慰奖而已!
在所有人的眼里,尚能是强势的,而且,似乎有足够的资格强势。但我却感到了他强硬的外表掩饰下的内心是怯弱的。这在他给我的毕业留言里得到了证实。他这样写道:
“个性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你用自己的毅力和聪慧赢得了你该得到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在这方面我常常在内心深处感到惭愧,外表的刚强与内心的怯弱构成了我。可惜再没机会向你学习了。”
李尚能给我的毕业留言
年少时的轻狂是因为心的躁动。随着岁月的沉淀,我们学会了用各种痛苦和磨难历练内心。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无论饰以多么精美的装备,在现实面前仍是不堪一击的。你说是吗,尚能?所以,你用“勇”来勉励自己、鞭策自己,甚至麻木、掩饰自己。他们说你不愿承认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平民背景;说你跌宕于成功如斯,但三十多岁居然还为一套房子奔波的强烈落差;说你接受不了当你摆出名头要求商场老板打折时被奚落的事实;说你时常纠结于毕业于北大、才色俱佳的高个女友(身材矮小的你还是那样喜欢高个女孩)对你的若即若离……
尚能,你不应该去做谈话节目,虽说你的能力绰绰有余。或许,你更适合做一名大学老师。我们很多同学不都是大学教授了吗?我相信,如果愿意,你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是收纳他人心理垃圾的。你自己也说,“我如果不用遗忘去处理听众扔给我的信息,我不久就会疯掉。”
尚能,你离自己的心灵家园越来越远,却没有任何人相信一个能从容地帮别人进行心理治疗的人,需要倾吐哪怕是些许的委屈和烦闷,以致到了生命后期,你不得不找一位精神病医院的医生来当自己的助手,注射镇静剂来暂时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
不幸的尚能!
你的时代过去了!当年疯狂追捧你的人们已把你和他们的过去一起湮灭。其中,也许还包括你曾为之冲冠一怒的Y,包括那个带着黑色墨镜、把一束玫瑰放在你的碑上又悄然离去的神秘女人。奇怪的是我会时常想起你,想起你时会去NECOR你的纪念网站替你燃一炷香。你走了,班上年龄最小的薛裕嫔也走了。没有了你们,湖南师大八三级中文系二班也永远不再完整。
远在深圳的伍颖说你走的前一天给他去过电话,因传达室的大爷没找到他,没能和你通上话。他一直在内疚。因为他固执地以为,如果那天通了电话,你或许就不会那样走了。所以,得知你的离去,当时月薪才一千多的他花了几千元在家里装了部电话。虽然他知道,这电话你是永远不会再拨响了……
你走了,每天的太阳仍照样升起。还记得教现代汉语课的伍云姬老师吗?就是后来去了澳大利亚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那次上课,她让我俩分饰陈白露和方达生演绎《日出》里的最后一幕:
陈白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方达生:外面是阳光,是春天……太阳就在外面……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方达生”注视我的那双清澈、坚定的眼睛。
陈白露永远睡了,尚能永远走了,但生活还得继续。诚如《日出》落幕时砸夯工人的《轴歌》——日出东来,满天大红。想要得吃饭,就得做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