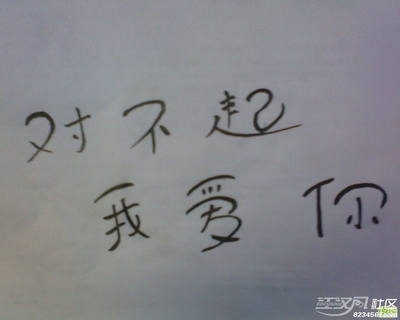其教义主要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和黑暗,即善与恶;三际则是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见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因此这是一个持二元论之宗教。有学者认为西藏苯教与纳西族东巴教之二元论教义与之有关,我所见就有四川大学孙林(《论藏族、纳西族宗教中的二元论及与摩尼教的关系》)和西藏社科院仲布·次仁多杰(《恰苯与摩尼教关系初探》)。摩尼教光明王国的统治者波斯语称“察宛”,意为永恒,汉译作明父或大明尊。察宛与光明、威力、智慧并为四位一体,许地山认为就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尾所谓的“四寂法身”,林悟殊认为草庵之“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十六字就是用来表达这一概念的。黑暗王国则充满了烟火、闷气、飓风、污泥、毒水,居住着五类魔。初际时光明与黑暗互不侵犯,到了末期黑暗开始入侵,进入中际时期;明尊虽然制止了入侵,但恶魔吞噬了五明子,我们这个宇宙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困住黑暗王国,把被吞掉的光明分子提取出来,直到世界被大火毁灭,此后进入后际;在后际,恢复到初际时的样子,光明黑暗分开,黑暗再也没有机会入侵。

摩尼教信徒分两种:正式僧侣称电那忽,在西方叫选民;普通信徒叫听者。选民只能住在寺内,穿白衣白冠,不得结婚,不得拥有财产,不从事农耕,不杀生,不能伤害植物。选民分为四等:慕阇、拂多诞(《佛祖统计》卷三九:“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一般被认为是摩尼教入华之始。另外还有唐以前和唐高宗朝的说法。曩多以拂多诞为人名,后方知是一种等级)、默奚悉德,阿罗缓。(听者为第五等,称耨沙喭。)听者可以结婚,可以种植,可以拥有财产,但须侍候、供养选民。
摩尼教经典现存很少,我倒是通过照片阅读过《摩尼教残经一》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还有一部《下部赞》,手上虽然有照片,但过于模糊,无法辨认,原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无缘得见。高昌遗址出土的摩尼教抄本残片如《沙卜拉干》等,都是用粟特文、帕提亚文等死语言写成的,则限于学力,难以研究。(这一点我倒也不怎么汗颜,当年王国维也不懂这些,还是请教的罗君楚和陈寅恪。)而在中国古籍中,志磐《佛祖统纪》、《册府元龟》、《唐会要》、李肇《国史补》、新旧《唐书》、杜佑《通典》、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王明清《挥尘前录》、黄震《黄氏日钞》、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徐铉《稽神录》、廖刚《高峰文集》等都曾对摩尼教有所记载。唐代道家还曾依托摩尼教,作《老子化胡经》,云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将道、佛、摩尼三教混齐,因此摩尼教经曾被编入《道藏》(见《佛祖统纪》引洪迈《夷坚志》逸文)。
世界上研究摩尼教最早的,应该是沙畹、伯希和,他们合著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伯希和还有《福建摩尼教遗迹》),1927年由冯承钧先生译出。这本书我有,不过一直没腾出时间看。而为我国摩尼教研究奠定基础的,是大史家陈垣1923年发表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对此文作了摘录注释,可参看。后来唐长儒、蔡鸿生、岑仲勉、方庆瑛、牟润孙、饶宗颐、向达等著名学者都曾对其进行研究,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资料。(陈垣之前,王国维、罗振玉、蒋斧也曾对此有所关注,但成就不大。)改革开放之后在这方面用力最深的,当属蔡鸿生先生的弟子林悟殊;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马小鹤,原本是复旦的,后来似乎去了哈佛燕京社。台湾有一位王见川先生,以其研究专集为基础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摩尼教通史《从摩尼教到明教》,提出了不少创见。原书我未读过,仅从韩秉芳和《敦煌研究》编辑杨富学分别对本书所作述评中了解其大概。早期研究摩尼教,大多是关注其入华及始建寺之年代,消亡时间,传播途径,摩尼本人生卒年代等等问题,这主要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今天我发现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其哲学层面上的许多细节了,这是很可喜的。当然今天也并非就无人再关注其历史发展,比如我们厦大廖大珂先生的《摩尼教在福建的传播与演变》、新疆社科院李树辉《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上海社科院芮传明《唐代摩尼教传播过程辨析》《东方摩尼教的实践及其演变》《佛耶,魔耶?——略说摩尼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两种角色》、北大王媛媛(后去中山)《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等。我所说我们开始注意其哲学内涵,解读摩尼教经典中的一些符号(这批学者应该主要是受了卡西尔的影响,我校哲学系系主任詹石窗先生作有《符号学在宗教研究中的应用初探》一文)的含义,主要指的就是刚才提到这位芮传明。我读过他的文章就有《摩尼教“佛性”探讨》、《摩尼教文献所见“船”与“船主”考释》、《“摩尼光佛”与“摩尼”考辨》、《摩尼教Hylè、āz、贪魔考》、《摩尼教“平等王”与“轮回”考》、《摩尼教神“净风”、“惠明”异同考》、《摩尼教“树”符号在东方的演变》、《摩尼教“五大”考》、《摩尼教“五妙身”考》、《摩尼教性观念源流考》。另外这方面还有马小鹤的《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国社科院元文琪的《人类自身明暗二性论——读<摩尼教残经一>》等论文,都很有学术价值。研究者们还开始将摩尼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比,也作出了一些成果,除了我上面所说的用苯教和东巴教与之对比,这方面的论文还包括芮传明《弥勒信仰与摩尼教关系考辨》、马小鹤《“肉佛、骨佛、血佛”与“夷数肉血”考——基督教圣餐与摩尼教的关系》、暨南大学范立舟《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瑞士)孟格斯《论中亚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之关系——评<丝绸之路上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之碰撞>》、元文琪《琐罗亚斯德与摩尼教之比较研究》、山东荣城二中吕仲海《唐代的袄教和摩尼教》。陈垣先生曾认为宋儒理欲二元之说与摩尼教旨有关,后来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我读过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的《朱熹与摩尼教新探》。2005年,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澳洲悉尼大学、新英格兰大学的专家到晋江进行实地考察,发表了《二十世纪现存的摩尼教信仰》一文,有一定影响。相信以此趋势继续下去,对摩尼教之研究定会更加深入发展。
摩尼教是西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之宗教,其教杂糅拜火教(Zoroastrianiam,又称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教主我国古称苏鲁支,即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人公)、诺斯替教(Gnosticism)、基督教、佛教(说佛教主要指华化之摩尼教,非原始摩尼教)而成,在华又称明教、末尼教、明尊教,中世纪曾流行从大西洋西岸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被回鹘尊为国教,有汉文《九姓回鹘可汗碑》纪其事。唐会昌初回鹘败于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之先民),摩尼教徒遂大受打击。开元二十年,明诏禁断摩尼。到南宋中国摩尼教徒自行组织教会,重新兴盛起来。可惜今已不存。
其教义主要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和黑暗,即善与恶;三际则是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见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因此这是一个持二元论之宗教。有学者认为西藏苯教与纳西族东巴教之二元论教义与之有关,我所见就有四川大学孙林(《论藏族、纳西族宗教中的二元论及与摩尼教的关系》)和西藏社科院仲布·次仁多杰(《恰苯与摩尼教关系初探》)。摩尼教光明王国的统治者波斯语称“察宛”,意为永恒,汉译作明父或大明尊。察宛与光明、威力、智慧并为四位一体,许地山认为就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尾所谓的“四寂法身”,林悟殊认为草庵之“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十六字就是用来表达这一概念的。黑暗王国则充满了烟火、闷气、飓风、污泥、毒水,居住着五类魔。初际时光明与黑暗互不侵犯,到了末期黑暗开始入侵,进入中际时期;明尊虽然制止了入侵,但恶魔吞噬了五明子,我们这个宇宙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困住黑暗王国,把被吞掉的光明分子提取出来,直到世界被大火毁灭,此后进入后际;在后际,恢复到初际时的样子,光明黑暗分开,黑暗再也没有机会入侵。
摩尼教信徒分两种:正式僧侣称电那忽,在西方叫选民;普通信徒叫听者。选民只能住在寺内,穿白衣白冠,不得结婚,不得拥有财产,不从事农耕,不杀生,不能伤害植物。选民分为四等:慕阇、拂多诞(《佛祖统计》卷三九:“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一般被认为是摩尼教入华之始。另外还有唐以前和唐高宗朝的说法。曩多以拂多诞为人名,后方知是一种等级)、默奚悉德,阿罗缓。(听者为第五等,称耨沙喭。)听者可以结婚,可以种植,可以拥有财产,但须侍候、供养选民。
摩尼教经典现存很少,我倒是通过照片阅读过《摩尼教残经一》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还有一部《下部赞》,手上虽然有照片,但过于模糊,无法辨认,原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无缘得见。高昌遗址出土的摩尼教抄本残片如《沙卜拉干》等,都是用粟特文、帕提亚文等死语言写成的,则限于学力,难以研究。(这一点我倒也不怎么汗颜,当年王国维也不懂这些,还是请教的罗君楚和陈寅恪。)而在中国古籍中,志磐《佛祖统纪》、《册府元龟》、《唐会要》、李肇《国史补》、新旧《唐书》、杜佑《通典》、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王明清《挥尘前录》、黄震《黄氏日钞》、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徐铉《稽神录》、廖刚《高峰文集》等都曾对摩尼教有所记载。唐代道家还曾依托摩尼教,作《老子化胡经》,云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将道、佛、摩尼三教混齐,因此摩尼教经曾被编入《道藏》(见《佛祖统纪》引洪迈《夷坚志》逸文)。
世界上研究摩尼教最早的,应该是沙畹、伯希和,他们合著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伯希和还有《福建摩尼教遗迹》),1927年由冯承钧先生译出。这本书我有,不过一直没腾出时间看。而为我国摩尼教研究奠定基础的,是大史家陈垣1923年发表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对此文作了摘录注释,可参看。后来唐长儒、蔡鸿生、岑仲勉、方庆瑛、牟润孙、饶宗颐、向达等著名学者都曾对其进行研究,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资料。(陈垣之前,王国维、罗振玉、蒋斧也曾对此有所关注,但成就不大。)改革开放之后在这方面用力最深的,当属蔡鸿生先生的弟子林悟殊;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马小鹤,原本是复旦的,后来似乎去了哈佛燕京社。台湾有一位王见川先生,以其研究专集为基础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摩尼教通史《从摩尼教到明教》,提出了不少创见。原书我未读过,仅从韩秉芳和《敦煌研究》编辑杨富学分别对本书所作述评中了解其大概。早期研究摩尼教,大多是关注其入华及始建寺之年代,消亡时间,传播途径,摩尼本人生卒年代等等问题,这主要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今天我发现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其哲学层面上的许多细节了,这是很可喜的。当然今天也并非就无人再关注其历史发展,比如我们厦大廖大珂先生的《摩尼教在福建的传播与演变》、新疆社科院李树辉《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上海社科院芮传明《唐代摩尼教传播过程辨析》《东方摩尼教的实践及其演变》《佛耶,魔耶?——略说摩尼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两种角色》、北大王媛媛(后去中山)《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等。我所说我们开始注意其哲学内涵,解读摩尼教经典中的一些符号(这批学者应该主要是受了卡西尔的影响,我校哲学系系主任詹石窗先生作有《符号学在宗教研究中的应用初探》一文)的含义,主要指的就是刚才提到这位芮传明。我读过他的文章就有《摩尼教“佛性”探讨》、《摩尼教文献所见“船”与“船主”考释》、《“摩尼光佛”与“摩尼”考辨》、《摩尼教Hylè、āz、贪魔考》、《摩尼教“平等王”与“轮回”考》、《摩尼教神“净风”、“惠明”异同考》、《摩尼教“树”符号在东方的演变》、《摩尼教“五大”考》、《摩尼教“五妙身”考》、《摩尼教性观念源流考》。另外这方面还有马小鹤的《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国社科院元文琪的《人类自身明暗二性论——读<摩尼教残经一>》等论文,都很有学术价值。研究者们还开始将摩尼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比,也作出了一些成果,除了我上面所说的用苯教和东巴教与之对比,这方面的论文还包括芮传明《弥勒信仰与摩尼教关系考辨》、马小鹤《“肉佛、骨佛、血佛”与“夷数肉血”考——基督教圣餐与摩尼教的关系》、暨南大学范立舟《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瑞士)孟格斯《论中亚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之关系——评<丝绸之路上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之碰撞>》、元文琪《琐罗亚斯德与摩尼教之比较研究》、山东荣城二中吕仲海《唐代的袄教和摩尼教》。陈垣先生曾认为宋儒理欲二元之说与摩尼教旨有关,后来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我读过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的《朱熹与摩尼教新探》。2005年,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澳洲悉尼大学、新英格兰大学的专家到晋江进行实地考察,发表了《二十世纪现存的摩尼教信仰》一文,有一定影响。相信以此趋势继续下去,对摩尼教之研究定会更加深入发展。
最后我想谈一下摩尼教与古代几次起义之关系。
一、五代。《佛祖统纪》卷四二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上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法有若此。”(并见卷五十四)陈垣先生据赞宁《僧史略》认为毋乙是摩尼教徒。
二、宋。方勺《泊宅编》之《青溪寇轨》言方腊事甚详,但仅言其吃菜事魔,未指明其为摩尼。《佛祖统纪》所引洪迈《夷坚志》文为今本所无,当是逸文,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袗,妇人黑冠白服(案:关于摩尼教尚白,有学者以为是效法回鹘,见郑州大学刘铭恕《有关摩尼教的两个问题》),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取《金刚经》‘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经》(即前引文,此处从略),以自表证。……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时作礼,盖黄巾之遗习也”。这里以“吃菜事魔”与明教为一。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载其读王居正之疏云“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案:陈垣先生以为千与万当有一衍字,我以为千万当为并举,非指百万之十倍)人矣。……臣闻事魔者,每乡或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之人姓氏名字,相与诅盟,为事魔之党。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以此可见吃菜事魔教之淳朴,因此民众争相归附也就很容易解释了)。竹汀又据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确指方腊为摩尼。《条对状》云:“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乌衣白帽,所在成社。……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陈垣先生认为“二襘子”就是二宗,四果却是白云宗非摩尼教。陈垣先生未言明方腊究竟是否为摩尼教徒,但从其叙述中似乎是持肯定态度多的。庄季裕《鸡肋编》卷上云:“事魔食菜,法禁至严。而近时事者亦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案:佛教所谓荤,非指今人理解的肉食,而是姜蒜之类,不知食菜事魔之荤指何物),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南宋时一些道教徒已不甚分得清“吃菜事魔”与明教之关系。白玉蟾的弟子就曾问他,“乡间多有吃菜持斋以事明教,谓之灭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遗教,然耶?否耶?”白玉蟾告诉其弟子一些明教的教义,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并未分辨“吃菜事魔”与明教的异同。(《海琼白真人语录》)林悟殊在《古代摩尼教》中说方腊起义时只是一些自称摩尼教徒的农民奋起响应。后来说明教与“食菜事魔”不能划等号,素食是许多民间教派都有的戒律,而事魔是对所有邪教的称呼,因此被指为“食菜事魔”的可能是明教徒也可能是其他教派的信徒,而方腊与明教实为风马牛不相及。(《明教:扎根中国的摩尼教》)方庆瑛统计两宋时借摩尼教举行的反叛活动起码有四次(《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其中方腊是被认为与摩尼教有关的。芮传明认为“吃菜事魔”融合了摩尼教因素,却非纯粹摩尼教信仰。(《佛耶,魔耶?》)
三、元末。元末农民起义军信奉白莲教,林悟殊认为其中有不少摩尼教成分,比如起义军领袖韩山童称“明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朱元璋诛韩林儿,称国号为“明”,有很多学者认为都与明教有关。白莲宗是南宋绍兴初年茅子元创立的,《释门正统·斥伪志》将摩尼、白莲、白云等并论,目为邪教(吴晗据此以为三派混合已久)。虽不能证明白莲教与明教二者混合,但至少有共同点,马小鹤就认为白莲宗《庐山莲宗宝鉴》中所谓“佛身之血”有受摩尼教影响的可能性(见《“肉佛、骨佛、血佛”与“夷数肉血”考》)。杨讷和美国的欧大年对白莲教都有深入研究,普遍认为这是佛教净土宗与天台宗结合的产物(见杨讷《白莲教》、《元代的白莲教》)。吴晗认为“明教与白莲社之混合或早在北宋已开其端。”(《明教与大明帝国》)戴玄之认为白莲教起源于摩尼教派。(《白莲教的源流》)范立舟根据摩尼教曾依附佛道的史实认为白莲教受到过摩尼教的影响,比如二者皆白衣,但并非混合已久。(《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明代以后白莲教成为主要民间信仰,明清多次动乱都与之有关,后来因此产生天地会一类团体,直到今天的黑社会。廖大珂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明教已不复独立存在,它已和白莲教各教派尤其是罗教汇为一体。(《摩尼教在福建的传播与演变》)。
王见川在其《从摩尼教到明教》中提出来很多新见解,他认为毋乙起义为“外国成份浓厚的佛教异端团体”;方腊起义则为弥勒会的变种;“吃菜事魔”与摩尼教无干,只是一些具反佛教性格的秘密团体如金刚禅、二会子、白佛、道民之类或其他民间信仰;元末明教与弥勒会、白莲教尚未合流,“大明”国号当采自金刚禅等佛教异端团体所习的《大小明王出世经》。这些看法都可备一说,但我认为理由还不够充分。在我们找出确凿证据证明毋乙、方腊、朱元璋与明教无关之前,我认为最好还是慎重一点,暂以传统观点为准,因为这几个团体之间本来就是很难区分的。对摩尼教不了解的人,就算是大学者,一般都直接视“食菜事魔”与明教为一。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就曾记载西方学者数人坚持魔教即吃菜事魔教,亦即摩尼教云云。
摩尼教还有许多很精美的艺术作品流传下来,可见(德国)克林凯特所著《古代摩尼教艺术》(林悟殊译),兹不赘述。
补记:撰此文时我精力主要是在阅读狄德罗《百科全书》(梁思成林徽因哲嗣梁从诫的选译本)和王静安《观堂集林》,抽出一些时间完成是篇,因此前后风格显得十分怪异,不过是有什么想法就说,尽可能地多引一些资料。将各种学者意见列在上面非为炫学,不过是希望能令读者对中国古时如此一教派能有所了解,庶几可告慰圣人摩尼之灵。
对于附记所谓在无新观点之前当以传统观点为准的说法,我后来也认为不太妥当,固执旧说怎么可以呢?但这里似乎还牵涉到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究竟怎样我还表达不清楚。这颇能令我想到像西方一些法律采用“无罪推定原则”而我们不是一样,孰好孰坏,我不敢断言。
我们厦大张星烺先生当年去泉州考察,由于草庵附近土匪颇多,未能成行。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巨著,非我能通读也。此行或可聊表对先生之敬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