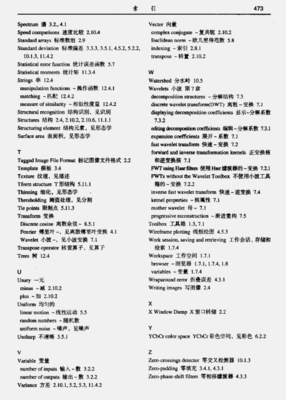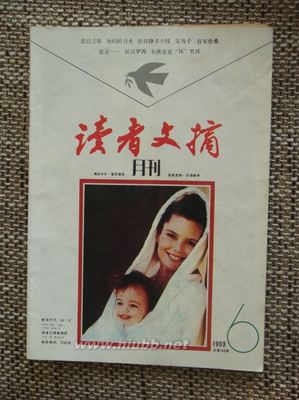我来到外面,登上小轮车,当我正准备闪人的时候,一只大手重重的拍在我的肩膀上。尽管我否认了所有的事情,可是还是被人家戳穿了,他们带我到商店楼上的房间,他们就在那里从一个单面儿玻璃里看见了我整个儿偷东西的过程,还拍了录像。他们打电话叫我妈来,我把顺来的磁带从衣服裤子里掏出来,他们摆了一桌子,准备等我妈来的时候给她看,因为我是小孩儿,所以我逃避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对我来说更糟糕的是,进店行窃这件事,让我爸妈在很多年里都处于敌视的状态,在我家里引起的影响比在法律条文上厉害多了。我永远忘不了欧拉进来时候脸上的表情,当她看着我坐在一堆我偷来的磁带的旁边。她没说太多的话,也没那个必要,因为一切都很清楚了,我做了错事。
最后,Tower商店没对我进行起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找回来了,他们让我走的条件是永远不许我进入她们的商店了,估计得到这个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商店的一些经理认出了我妈,她是那商店的老主顾。
六年以后我被那家店的视频部雇佣了,在头六个月里,我不断从商店顺东西,有人认出我并且记起我曾经在这里偷东西被抓住,然后我被开除了。我承认,那时候有些人指出我在填写的履历表里作假,而且让雇用我的人相信了。不过在我被认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已经从店里弄了比我几个月薪水还多的东西出来了。
通常我们会有大麻,
那东西能带来成堆的快乐
在之后的八年间,我生活中的变化都在自己悄然进行着,只有一次,我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稳定的像家那样的关系。
在我爸妈分开后留下的真空里,我创造着自己的世界。我非常的幸运,不考虑年龄,我在那段边缘时期交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就算我们身处世界不同的角落,也不会感到相距遥远,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个知己,算起来有三十年了,真他妈叫一个长啊。
他的名字叫做马科-坎特(Marc Canter),他家在北菲尔发克斯(NorthFairfax)拥有一家非常知名的餐饮机构“Canter'sDeli”。坎特一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新泽西搬过来,开了一家餐馆,那是一家为娱乐业服务的餐饮中心,从开张到现在就没变过,因为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张营业,提供饭菜。那家店离日落大道(SunsetStrip)只有半英里,在六十年代的时候,那里成为了音乐人们的天堂,直到今天。在八十年代,很多乐队,比如枪花都会在夜里经常光顾那家店吃东西。他们的酒吧叫做“TheKibbitzRoom”,就挨着餐馆,那里是现场音乐表演的聚集地,无数伟大的夜晚创造了无数值得记忆的现场。坎特一家对我很好,他们雇佣了我,给了我可以居住的庇护所,我无法表达完对他们的谢意。
我和马科在三小(Third Street ElementarySchool)认识的,不过知道我几乎偷他的一辆迷你自行车得手之前,我们都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非常的牢固。我们经常去汉考克公园闲逛,那里就挨着他家。我们还常常下到泛太平洋剧院的废墟里,那里现在是一个叫“Grove”的商业中心。泛太平洋剧院是一个迷人的遗迹,在四十年代的时候,那里是一个电影宫殿,有着拱形的屋顶和巨大的屏幕,那里会放映最新的影片,而且造就了整整一代人对于电影文化的价值观。在我的年代,它依旧很美:绿色的“ArtDeco”风格的穹顶还完好的保存着,其他地方则变成了瓦砾。剧院遗迹旁边是一个公共图书馆,还有一个带篮球场和游泳池的公园。像劳雷尔小学(LaurelElementary)一样,那里也是一个从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小孩儿的聚会地点,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他们找到各自的理由在夜里出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看上去都是特年轻那种类型的,在我们这种人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类型的人,比如有势利小人(走狗型儿的),还有辍学的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住在剧院废墟里,废墟边上有农民开的商店,他们就靠每周两次去商店里偷东西吃过活。我和马科被那儿那种气氛迷住了,而且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因为经常,我们会有大麻,那东西能带来成堆的快乐。和马科的相遇触发了我的一个改变,他是我第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当我觉得每人能理解我的时候,他恰恰是个例外。我们两个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都是不正常的那一种,但是我对我们俩的关系感到骄傲,那正是我对家庭的定义。一个朋友,即便好几年不见面,他仍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就如同你们形影不离的时候一样。一个真正的朋友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出现的那个,而不是在假期周末之类的围绕在你旁边的那些。
几年后我发现我没有了直接的经济来源。当我几乎没钱吃饭的时候,那倒没什么可在乎的,只要能让我继续维持枪花乐队就行,当我没钱印宣传单甚至没钱给我的吉他买弦的时候,马科-坎特就会出现,他为我应付钱的事情,无论我需要做什么,他都会帮我弄好。当枪花儿终于签约的时候,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回报给马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坎特当我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为我做的一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