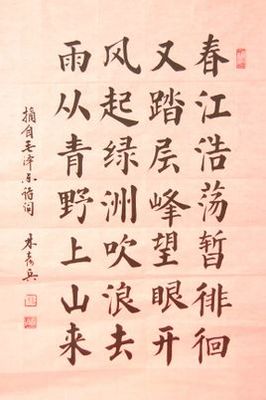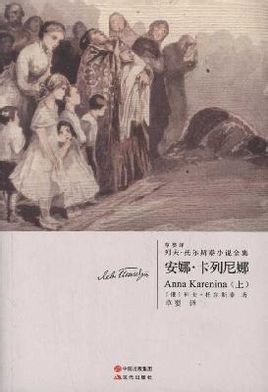(一)胜芳王氏本的面貌
碑学研究往往会因着时代变迁、旧本湮灭而处于停滞或倒退之状态,欧阳四碑中前述之虞恭公、皇甫诞皆属此种情况,然也有不同者,如化度寺随着百年来敦煌本等的惊天出世而改天换地,九成就更极端些,存世的四本北宋拓均为新中国入馆后方始得以知名于海内,几乎彻底颠覆了既有的宋拓本体系,反为时代推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二百年来对九成宋拓的各种著述放于当今其参考价值已很有限,大量新材料的涌现,印本之发展又远超过研究的步伐。因此,尽管各方面前述已颇备,仍愿多此一事,重新整理下新中国后的宋拓印本,以助后来学人再上高阶。
唐碑中最热门的一者集王圣教,二者九成,不独当世如此,自古即然。在这个公藏时代,哪家藏馆如果没有一本像样的九成宋拓镇库,怕是都不好意思上台面。九成历代所载号称宋拓极多,由于记载不周全而重复误解者无数,于是很多传说无处着落,很多藏本又失之细鉴。
笼统说来,九成存世本能与“宋拓”沾上边的可归为四个级别:第一李祺本,第二“重”字本,第三“栉”字本,第四未剜本。时代之定位或早移或晚置:有说第一级为晚唐拓,至第四级为宋末拓;也有说第一级为北宋早拓,至第四级为明拓。我个人认为定唐拓并无依据,因此倾向采用后种定位法。今回整理以既出印本者与馆藏本为主,剔除所有非官方之记载,宁缺勿滥,凡有确证者,辄可后补。
问题一:胜芳王氏本的面貌
早年各家所记北宋拓(4或5本)均有胜芳王氏本在列,此本威名素著,又称毛文达本,在光绪宣统年间是北方第一。这么有名的一本却在现代研究者的视野中逐渐消失踪迹,都是著录方法闹的祸。其实此本即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善本》见载之“北宋拓本(三)”,亦在禁中。作为相当长时间内北宋拓的标准本,李祺本、内府本(重新)入库时均是以它做为标杆进行的考比。相对李祺本一马当先却又疑云重重、内府本擦拓不精、吕伯威本虫痕纸损累累,胜芳王氏本之全貌一直吊着我们的胃口。
新中国后各北宋本均得以多次印出,为世人所了解,而故宫偏偏不印胜芳王氏本。前有王家秘藏不予示人,后有故宫怀璧不展,令此本之悠久传说几于中断,冤哉。
(二)关于翻刻本的鉴定与几个常见翻刻体系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九成诸疑中最重要的一个。
九成据载自宋时已有翻本,其下各朝屡屡见新,其品种怕是不下于兰亭等帖。翻本有摹本有临本,有仿原碑制者,亦有分石、横石等不同版本。大多拙劣翻本明眼人一眼即可断,全不用校碑(后代很多号称神奇的什么“唐拓”多在此类,捧伪者往往以校碑之通论比较存字,殊不知校字是要在一定基础之上的高阶判断法,连基础都不存的翻本根本遑论校碑)。
说九成的翻本,凭据很关键。让我们来看看传说中的一些凭据:八行“圣上爱一夫之力”之“爱”字上石晕、十四行“匪唯乾象之精”之“乾”字日部中未将石泐误作竖笔、二十一行“随感变质”之“变”字中石擦痕、末行“奉敕书”之“奉”字中竖笔右侧的微缺。如以有效性来说,我的排序是“变”>“爱”>“奉”>“乾”。
“乾”字非常有名,很多翻刻本都拿它来说事儿。中间日部原拓是有一条相当似竖笔划的石泐痕,泐痕中非光滑,然而在不同拓本中的体现与实际观感各不相同,很难找出标准件,翻刻所造此笔除了上不触顶、边缘光滑外也没有什么大不同。所以想用这个断明事情,一不小心反而容易走入迷途,非极熟悉各种拓本特征者建议勿用。
“奉”字的这个微缺同样极依赖于拓工,各宋真本基本均有描墨,更令事实难以捕捉,作伪也容易。有效性很低,同样不推荐。
“爱”字上的石晕可以隔离掉一批翻本,这些翻本大多将石晕处与下连成一整片泐痕。但是,用这个法子不能鉴定最难的案子:秦刻本。秦刻石晕仿造自然,全无痕迹可捉。
最后说“变”字。原石本字中的石擦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可做鉴证之标准,我选取了李鸿裔本中的图片来作例:
注意擦痕与笔划之间的位置关系。擦痕共四条(长短不一),呈平行状排列,方向均为左上至右下,倾斜角大约是20%左右。擦痕比笔划粗,质地亦粗糙,非尖利之物所刻。擦痕上下粗度相仿,呈直线无弯曲,没有明显“鼠尾”的现象。由于拓工、湮墨、描失等原因,有的本子中擦痕只能清晰看到两或三条(左数第二条最易湮没),但特征一致,位置统一。即使精翻如秦刻本,在此处亦露了马脚,擦痕只得两条(左数第二、四两条,估计秦刻祖本可见的亦只此两条)且明显为刻出,刀痕可见,略弯曲向上且带“鼠尾”。
鉴定凭据谈完了,再说说几个常见的翻刻体系及实例印本
第一个是肯定不能错过的秦刻本。标准的摹刻,这个本子刻工之精、参考意义之大几可媲美原石。其祖本几乎是南宋拓中所见最早的,翻后早拓从书法参习价值来说肯定大于原石明中期后已剜的拓本。民国时艺苑真赏社有印,新中国后上海书店有翻,秦刻本的很多特征可在其中捕捉。另有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自学丛贴”首印黑白本(具体辨析见后之问题三)、《中国碑拓鉴别图鉴》中九成条目图三一至三三、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中嵇永仁藏本和梁章钜题跋本。
第二种也是较精的摹本,我称之为半“醴”字本。因其首行“九成宫醴泉铭”之“醴”字左酉部下半尚存(实此处宋之前已损尽),而右半则如其他宋拓一样只存底三笔。四川美术出版社《宋拓法帖五种》印四川博物馆本即是。另有《中国碑拓鉴别图鉴》中九成条目图三六。
第三个即所谓历史最早之宋翻本,有姚鼐跋,字多移补与填改,曾有图录披露数开:
第四个已属临本,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翁藏宋拓九成”。此本后人所添笔意甚多,尤其是柳的味道。天津市古籍书店、中国书店、上海画报出版社“中国历代碑帖”黑白本皆翻印自民国有正印本。
第五个就是屡博争议的麟游本,恐亦为临本。此刻原石尚存,然为分刻二石,风格一味求瘦,笔划呆滞,刻工不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杨柳青画社、新华出版社《蟠逸斋藏帖》黑白本所印即是。另有《中国碑拓鉴别图鉴》中九成条目图三四。
(三)大名成氏本之谜
现藏上博的大名成氏本(又名长垣王文荪本)是《崇善楼笔记》中的一个神话,极得溢美之词,几列南宋本之冠。然而,它也是《书法自学丛贴.正书》中的一个谜:为何要在半路将编者如此欣赏的本子换下?
我们仔细看这个本子,就会发现它不大对头:字口非常锋利如新拓(存世南宋拓字口均有轻微漫漶迹象,盖积年棰拓所致),与现存一众南宋拓本逐字比较存在明显的细节差异。这是印本质量造成的干扰么?应该不是。一印之《书法自学丛贴.正书》(下册)墨分浓淡,成氏本又显见为原拓摄影制版,效果在当时已绝对可称精善。
这个本子究竟是何来由?
通过全碑的细校,我在十五件宋拓和相关拓本中找到了它的最近邻居——秦刻本。成氏本的石花与秦刻本几乎完全相类而与任一其他宋拓不同,包括首行“钜鹿郡公”之“鹿”字上损纹形状;二行“贞观”之“观”字末钩笔分尾(成氏本显见描去一半);前文说过的“乾”字,显然为刻笔而非泐痕,且刻法与秦刻本全同;“变”字擦痕,亦为两条鼠尾刻痕;末二行“持满戒溢”之“满”字上人为横刻线;末行“永保贞吉”之“吉”字左下同有粟米状石花一颗(这一向被认为是秦刻本最具代表性特征),等等等等。至此,事实变成明摆着的:成氏本实际就是秦刻本。
以成氏本与上图所藏秦刻本对校,几乎完全吻合,而与艺苑所印之秦刻本对校,却有些细小差别,差别最大的是末行“奉敕书”之“敕”字,不仅字形看来不类且末笔明显不同。原来秦刻这一笔下钩部本是粗丑(盖母本此处拓工未精所致),艺苑本画蛇添足,描了这一笔,描得又不佳,造成末笔像半路折断了一般。以石花看,成氏本各处均略小于艺苑本,字脚也更好,可见棰拓在其前,而艺苑本又多描墨,其所谓秦刻初拓大家姑且一听吧(艺苑社所印之本描墨一向极夥,不独此例)。
成氏本显名首先是有翁方纲的万言题跋,然后是王壮弘先生以端方本对校后的结论。两大高手为何在此本上均有失明鉴?
覃溪的万言跋其实基本都是水分,也就是他拿这册当成笔记本了,其中所记众多皆与此拓完全无关,真正谈到成氏本的1/N内容又全是虚笔赞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比较说明。猜当初友朋留此本予观,后又赠之,情感更多支配了逻辑,春秋笔法就多起来。为什么以秦刻本对校竟未发现端倪?秦刻有肥有瘦,覃溪手边或许正是瘦本,查得面貌不同之余更以为肥者在前。为什么手边四本宋拓对校仍不能看清?跋中一句透了底:“'变’字擦痕,秋史本、秦敦夫本皆不见,无锡秦本有之”,可见那几本不是描走了形就是翻本,这样的对校能找到北才怪。
王先生的失误也是源于参照系,他对校之时所用为商务印端方本,如以原拓或今二玄社“中国法书选”所印新本来校,相信其结论必将彻底不同(我一一核过,那些所录的端方本“缺点”在新印本中实际都不存在,全为旧印本低质之误导)。《书法自学丛贴.正书》成书不久(大概在二印以后),此事即水落石出,再印乃以端方本替代,正显示了编者负责任的态度。大名成氏本也自此逐渐远离公众视野。
同情前人之余,想我辈能坐观如此众多之良拓精印,实该感谢时代。
顺道说一下,翁跋中提到陆恭亦曾集得大欧四碑宋拓,仲威先生在讲座中所言吴湖帆是史上集齐四欧之第一人亦是过赞了。
(四)“栉”字与南宋拓本
但凡了解一点九成拓本断代的都说得出“栉”字与“重”字,可是有时候我们离真理越近其实就越看不清它的样子。
好了,九成南宋拓本常被称为“栉”字本,解释呢往往是:“栉”字完好为南宋拓。有的书中会再添一句“栉”字半损什么什么的话…………
我来问一句:“栉”字是何时开始损的?
答案即吓人又简单:宋前就已开始了。
清前之人基本都是抱着南宋拓在说“栉”字,所以刚上眼以当时所见状态为“不损”(其实已损),之后增损为“已损”,并以此为南宋断据。近百年来,北宋拓纷纷出世,今人如还沿袭同样的老套说法,实如历史倒流。
是不是“栉”字还在就算南宋,不在了就定明?
当然不是。
在实际的断代中,这常常是个复合检定问题。
忘记那些“完好”、“不损”、“已损”、“半损”模棱两可的形容词吧,让我们准确地还原一下“栉”字的状态。所有北宋拓的共性揭示,“栉”字在宋前就已有损,损处为:艮部勾笔上损一块;另外,几处附损随拓本的纸墨与填描状况不同略有表现差异:木部横笔左端下略损、竖笔下段中略损,卩部竖尾处当石痕有微泐。此特征一直到南宋中早期都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四欧堂本此处干扰较少,上图以做参考(其他均同):
所谓南宋本并非铁板一块,所以纯以“栉”字本称南宋是有失全面的。南宋早拓“栉”字即如上述,而晚拓增损后已难辨认,所以现存的南宋晚拓与宋元间拓本基本都将此字剪去以充早本,常与此一同剪去的还有八行“何必改作”的“作”字等。
没有了“栉”字其实没关系,因为以复合检定法一样可断清时代。我这里以首行“书”和“魏”字为例,大家还可以试引其他例证。南宋早期拓本“书”字下日部中横损而未失,右端尖如匕首;至宋末中横损失。“魏”字早期鬼部下小撇完整无损;至宋末小撇已与右勾笔石花泐连。这两字一般填描者要么忽略了,要么全凭臆想填出(书艺文化院本“书”字、岳雪楼本“魏”字),所以在南宋拓分期时相当可靠。
有记取就得有忘却。我认为考据点少有对与错,但多有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差别。几个传统的南宋拓考据听起来不错,实用起来却几乎等于无效。最显著的是十五行“光武”之“光”字,所谓扛枷不扛枷,其实现世所传宋拓基本全不见枷,而且由于著名,描得极精细,无迹可寻。同样的还有二行“长廊四起”之“廊”字(末笔底不连石泐)、三行“穷泰极侈”之“侈”字(未损)、二二行“庆与泉流”之“泉”字(未损)以及碑下部的裂纹,该描的都描了,即使以极精印本亦难断事。
(五)端方本是如何成“精”的
端方本,大名如雷贯耳,被称为“海内第一本”,传说曾于金、元、明内府递藏(这个大家也就姑且一听)。从清末到建国后的百年间,这个本子是事实上的九成标准本,兼拜192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之珂罗本所赐,似乎每件名拓都要与他较个高下方能得证金身。
端方本为南宋早期拓,过去曾被定为唐拓,然后是北宋拓,一阶阶降下来,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九成宫拓本研究的发展。它的特点不是绝早,而是拓工精卓。现在对于这个本子的断代已几无争议,令人好奇的反倒是它如何成“精”的过程。正好,二玄社的“中国法书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审视契机。
此本目视是浓墨拓(我那年在上海看过原拓),赞誉之人多言其精光四溢、清劲瘦健、锐气逼人,之前之后有不少国内的、日本的印本采用一手材料,展现的面貌也多是墨浓沉厚。所以初看到“中国法书选”我是吃了一惊,墨怎么变成这么淡?反复研看后从疑惑慢慢变成惊喜,让我来试图解开其中奥妙:
首先二玄社此次的摄影肯定采用了滤光,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多揭示拓本中的细节。具体技术环节不得而知,但从效果来看,由于人为后期加工,墨分了浓淡,一些被隐藏的细节才终于浮出水面。
我的结论是:端方本为三次施墨所成。
第一次为淡墨扑拓打底,用墨水分较厚,拓手非常细腻
第二次为浓墨横擦,墨焦,拓制取大形大块
第三次为精描,亦浓墨,然水分加厚,多采勾描(甚至双勾)填法
“精”就是这样炼成的 …………此种浓淡墨相间的拓法也偶见于南宋一些拓帖中,正与端方本时代相合。
仔细观察,锐气的字脚主要由一、三两个过程形成,大多是淡墨围出,亦有不少(尤其当断处及石花处)是出自描笔,而本子整体的精神气儿则是过程二所营造的。
端方本中的填描是大规模的,但手艺相当DI高。其目的倒不是为了断代欺人,主要是为保全字脚,基本不改笔划之形态(与其他南宋早拓相校可知)。所以多则多矣,无伤大雅,仍然算得存世至精本之一。个别夸张的双钩处看这里:
(左撇笔两侧的勾线)
(走之的勾线)
如今可见的四本九成最精早本——李祺本、李鸿裔本、端方本、四欧堂本均全本细墨精描过,但像端方本一般施墨三回却未见有第二例。
至此揭秘完毕,但我不得不再添两句。从字帖角度来说,这样的印本不知对于修习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用剥丝抽茧的人工后期处理扩大了层次差异,揭示了背后的真相,却同时丢掉了眼睛应该看到的本来面目。其意义比较像研究者所用的“副本”,而不是修习者该用的“正本”。如果大家以这本的样子当做原本的样子,才真的是误导了,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法书选”所印包括集王圣教等众多本子中。我个人钦佩二玄社所做之努力,但同时我仍主张字帖的印刷应以还原目视原貌为标准。
(六)玉山草堂本的独特价值
前文厘清了南宋早拓与晚拓的分别,现在玉山草堂本是南宋晚拓甚至宋元间拓本已显而易见,我们不必再执着于当初与商务印端方本的比较,还是同样的参照系问题。
这不是今天我要谈的事情,玉山草堂本断代的后移并不影响它传世名拓的地位,反而成为其发力之所在。
九成校碑第一个关键点是翻本的分辨,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宋明断代。历来称宋拓者众,然实多为明拓,或辅以过誉之赞词,或以填描充假。南宋150年,元仅不到百年,所以南宋早晚拓之间的差距甚至大于宋明间的差距。确立南宋晚拓或宋元间拓本标准件才是实现断代的必要条件。
南宋这百多年间碑下部的裂纹进一步加宽,之间各行增损不同,我统计了一下最下一道裂纹的情况。其中南宋早晚期增损明显的有二行“高”字、四行“能”字、七行“庶”字、八行“循”字、九行“丽”字、十六行“怀”字、十七行“在”字、十九行“怀”字和末二行“持”字。玉山草堂本此9处增损全见(一处略填底),而书艺文化院本4处保留原貌增损、5处填描,岳雪楼本只1处保留原貌增损、8处填描,几成墨猪。玉山草堂本的标准件价值由此显现。
玉山草堂本的特点是最少填描,但同样遗憾得是每行末剪失字多,尤其是“栉”字,现在所有存世本仍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此字在南宋末的确切样貌。
(七)宋元间拓本的真相拼图
这一帖的最初用意是检验一下明初拓的校据以区分宋明,结果发现这就是一个前人挖下的坑,怎么填也填不上。所有既有校据均不可靠,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寂寞。
普遍一致的意见是碑于明中期时剜凿,但对明早期的记述比较含糊,其中尚可称得上校据的是五行“王”字与六行“物”字明拓已损半。粗看上去这是个办法,比如至少有三本“南宋晚拓”此二字看上去未损,如一一仔细检视,可发现玉山草堂本“物”字为他处移补,书艺文化院本描走形,岳雪楼本笔划形虽未失,但填墨痕迹极明显。“王”字凡完好者更是无一本清明,涂描的嫌疑非常大(我意根本不适合用作校据)。说明此二字不止在明,而至少早在南宋晚期已半损了。
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是:所谓的明早拓凭空蒸发了。以相近时期的九件拓本逐字对校,其实损泐状况并无大分别,由于玉山草堂本有元人藏印,姑且将这一批均称为宋元间拓本,亦可称未剜本。
这个时期拓本到底哪些地方与南宋早本发生了大变化?一个显著之处是全碑字进一步漫漶且变化为整体性,笔划变粗变细均有,字形逐渐开始溃散。由此可见,九成宫南宋早拓基本为保持字形匀称的底限。除去上部断纹与下部裂纹的逐渐增宽,最大的考据变化就是每行行尾的损失,直至近世行尾已只字无存,碑由每行五十字变为四十九字了。
宋元间拓本行尾之字多剪失,为勘定带来了巨大难度,我只得以九件拓本交互比较,采个别存字者,记录如下:
二行
“长廊四起”
“四”
刘健之本、黄自元本尚存半,其他本剪去
三行
“以人从欲”
“以”
刘健之本字已泐尽,其他本剪去
五行
“重译来王”
“王”
左下半损,但大多填描
“西暨轮台”
“西”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
六行
“遗身利物”
“物”
右下半损,个别填描,玉山草堂本移补
“栉风沐雨”
“栉”
全剪失
七行
“庶可怡神养性”
“养”
黄国瑾本下部填描,其他本剪失,书艺本移补
八行
“何必改作”
“作”
黄国瑾本上横损一道,左下角损,其他本全剪失
九行
“可作鉴于既往”
“于”
黄国瑾本、黄自元本字形尚存,其他本全剪失
十行
“本乏水源”
“源”
黄国瑾本中下部损,其他本剪失
十一行
“踌躇高阁之下”
“踌”
全部剪失
十二行
“东流度于双阁”
“流”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书艺本移补
十三行
“将玄泽以常流”
“以”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
十四行
“上及太清”
“及”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
十五行
“醴泉出京师”
“出”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除中竖头略可见外已基本全损)
十六行
“推而弗有”
“推”
莫本只余扌部上竖一截,其他本剪失
十七行
“属兹书事”
“属”
全剪失
十九行
“书契未纪”
“书”
全剪失
二十行
“上天之载”
“之”
玉山草堂本、书艺本捺笔右半损,其他本剪失
二一行
“鸟呈三趾”
“鸟”
玉山草堂本、黄自元本下部漫漶而笔划实未损,黄国瑾本描,其他本剪失
二二行
“庆与泉流”
“泉”
笔划仅略漫漶,略描,个别本剪失,龚景张本移补
二三行
“持满戒溢”
“溢”
黄自元本、书艺本右半笔划尚清晰,其他本剪失
列表毕竟不够直观,除去南宋早期即已全损的几字,尚有四字九本皆剪,只能从南宋早本揣测他们的大致面貌(好在结论具有连续性),期待有一天新的宋元间拓本面世,能从中找到确切的信息。
下面是真章了。将上述选字拼起来,宋元间拓本行末的真实图像是这样的(黑色方块为本无字的,白色方块为字全损的,问号为九本全剪的):
(右半)
(左半)
我们用红色来标示损线(其下均损失),真相就在眼前了:
顺道说一句,从列表中可看出,岳雪楼本对真相的贡献度几乎等于零,满纸填描充假,我列它为宋元间拓本最劣者。
(八)靖康之际与吕伯威本的冤案
我们知道九成宫未剜本与明剜本有很大区别,通过前文也知道了南宋早本与宋元间本有很大区别,这些都是基本可以确证的。而北宋拓与南宋拓的区别除去人人皆知的“重”字外竟没留下只字叙述,靖康前后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唐碑的南北宋拓本往往呈现较明显差异,九成宫的变化基本是体现在碑的总体均匀蚀损上,字口更漫漶一些,笔划损泐变化反为其次。但如以可见的拓本来比,反倒会感觉南宋早拓字口更好。其中原因是两方面的:
一者,我们现在传世的北宋晚拓——内库本、胜芳王氏本、吕伯威本均为擦拓且工较粗疏,纸墨疲敝明显,有的细节在当初即湮墨或未拓出,随重装过程兼保存不善又加纸损;而现传世的南宋早拓本本都是扑拓且极精善,包括李鸿裔本、四欧堂本、端方本,以及从秦刻本看它的母本样貌。
二者………………不得不说的,这几本南宋早拓的锐利字口都来源于大量的细致填墨,无一例外。李鸿裔本相对少些,端方本最甚(见前文),郭廷翕本与毕沅本我曾在展览中寓目,亦是以浓墨填底并描。
一边是早而不精,一边是晚而精(加后期加工),字帖如何抉择大家可以自己看着办,校碑却是个苦差事。北宋几本现在的印本都不够理想,比对起来很考验眼睛的分辨力,南宋本又要跟填墨做斗争,好在每个本子的填墨、湮墨、纸损均有模式可以捕捉,一旦掌握了这些信息,只需将看到的图像“去模式化”即可大致还原真貌。
从首字直至末字,可资扑捉的差别还真是比想象中少得多。除“重”字外,即使填墨也没能掩盖的不过是:
- “绝壑为池”“为”字中北宋晚拓比南宋早拓少损
- “长廊四起”“四”字北宋晚拓左石花未泐连字
- “饮之令人寿”“之”字捺笔北宋晚拓比南宋早拓少损
- “斯乃上帝玄符”“帝”字右勾笔北宋晚拓完好,而南宋早拓已损(此据最易捕捉,书艺文化院本从他处移补)
北宋末(内库本)
南宋初(李鸿裔本)
另有一疑:“庆与泉流”“流”字三点水第二点与第三点是否连笔尚无法判定。从内库本与吕伯威本来看,此二点均呈行书一般的连笔,而南宋以后拓本均呈清楚的笔划分立,究竟是拓墨造成的误差还是北宋此时石面真如此(李琪本也显示笔划分立,但有填墨的可能)?
这里还要说说吕伯威本。
这个“冤案”其实是未得张扬的。吕本一直被视为北宋拓本,由于“重”字未损,此本断代未曾有过什么公开质疑。但我翻阅《中国碑拓鉴别图典》时发现其中宋末拓本的两幅图(“栉”字与“作”字)竟是选自吕本的,也就是说书中是将其视为宋末拓标准件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是著述方法惹的祸:一直以来均有所谓“半栉字本”的说法,定其为南宋晚拓,但这个半损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一本说得清。于是当吕伯威本出版后(见上图),模糊的“栉”字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旁证,这应该也是《中国碑拓鉴别图典》收入此图的原因。
这真的是个误会。
如果吕本是南宋末本,那“作”字应与前文(参见问题七)所述一样上损,而吕本“作”字上没有任何损痕,不符。
如果吕本是南宋末本,那“栉”字上的“物”字应已半损,而吕本“物”字完好且无明显涂描迹象,不符。
如果从头细读吕本,会发现擦拓时常出现大面积擦失的粗疏现象,碑中部较好,四边(尤其右边与下边)严重,很多字甚至整个拓失。所以“作”字尽管未损(可见的笔划轮廓非常清晰,尚强过南宋早拓)但下部已拓失,“栉”字的模糊正是同样原因,而且全碑最后一行均是如此。“栉”字尽管模糊,但上至草头,下至末竖笔其实都存在,可见完全是拓工问题,实并未损。
跟下比过,我们再来跟上比比。逐字对校吕本与作为北宋末标准件的内库本,两者石花、损泐几乎完全相同(这其间要排除大量内库本的填描、纸损与湮墨,以及吕本的虫噬、纸损与擦失),在所有的九成宋拓本中,此二本是最相合的。再以前述北宋本的“为”、“四”、“之”、“帝”来看,亦合,所以吕本的冤案至此可以初步昭雪了。
一个案子了结,另一个却正要开启。从《名碑善本》印出的几开看,胜芳王氏本倒是让人生了些问号:“栉”字上部有损一道,是同样拓工造成的偶然?还是有其它内幕?观其“重”字,在几个北宋本中最不让人信服,中间似有填描。要破这个案子,恐有待来日了。
(九)新中国宋拓印本综述
(一)北宋早本:
李祺本,每面四行,每行六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最佳印本兹推荐以下四种——文物出版社珂罗黑白线装本、“历代碑帖法书选”新版黑白印、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原色经折装册页本、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十品》原色印。此四本各有上下,以《名碑十品》综合略胜,外它印极多(台湾翻印竟有伪称赵子昂藏本的),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二玄社另出原色放大印“精选扩大法帖”,虽仅取前456字,但微距摄影极精细,信息量丰富。
(二)北宋晚本:
内库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说起来此本与前文述现藏日本东博的库装本皇甫君本为清宫逊出之“难兄难弟”。印本有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碑刻全集》原色印、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珍藏历代碑帖墨迹选”黑白印,均略缩小,效果不佳。
吕伯威本,每面五行,每行九字,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印本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原色印、“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名师指导”黑白印,均缩小,质量平平。
胜芳王氏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善本》所载之“北宋拓本(三)”即是,仅见缩印数开。
(三)南宋早本:
李鸿裔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印本有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原色经折装册页本,极精,有翻印。
四欧堂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印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特辑《四欧宝笈》原色蝴蝶装仿真册页本,极精。
端方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最佳印本有日本二玄社“中国法书选”黑白印,极精;上海博物馆《法书至尊.碑帖卷》原色印,尚可;它各版本日中印出极多。
徐荫田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大岛孝信氏处。印本有日本同朋舍“书迹名品集成”套色凹版线装本,效果平平。
毕沅本,每面五行,每行八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曾见展。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善本》所载之“南宋拓本(四)”,仅此原色缩印数开。
党崇雅本(龚心钊藏甲本),每面五行,每行八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
郭廷翕本(亦龚心钊旧藏),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可能为个人藏。嘉德2010春拍300余万拍出,曾寓目,仅《中国书画》杂志原色选印数开。
(四)宋元间拓本:
朱钧残本,每面三行,每行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此本为各宋元间本中最早者,惜只存二百余字。
书艺文化院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书艺文化院。印本有日本东京书籍“中国碑法帖精华”黑白线装本,较精。
玉山草堂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可能为个人藏。印本有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原色印,精。
黄自元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印本有书道博物馆自印黑白散页套装本,精。
黄国瑾本(亦龚心钊旧藏),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本有日本柳原书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黑白印,精。
刘健之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可能为个人藏。佳士得香港2008秋拍港币20余万拍出,仅见图录与照片原色选页数开。
费念慈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
龚景张残本,每面三行,每行六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此本缺一百七十余字,由王澍临补。
郑午昌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为个人藏。西泠2013秋拍40余万拍出,曾寓目,图录仅原色选印数开。此本内多补秦氏翻本与印本诸字,然底本出自原石无疑。
翁方纲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北京市文物局藏,《中国书法名品展》所载,仅黑白缩印首二开。
新中国后未再版的宋元间拓本尚有:
- 莫云卿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艺苑真赏社印
- 孔广陶(岳雪楼)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重”字描充北宋拓,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印
以上共录确凿之宋拓本二十三种。其他据官方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日本三井听冰阁、台北故宫均藏有未曾公开之九成宫宋拓本,期望能早日得见真颜。
兹以九段小文(八篇辨析加印本综述),向挚爱逾三十年的欧阳率更与九成宫醴泉铭致敬。
(十)原石故事自由“新”证
欧阳四碑中争议最多又最难以校考的唯化度是也。孰为原刻?孰为最早?人人均可有一套个人化认知,谓之自由心证。化度的情形很像虞世南孔庙碑,关键证据多为孤证,由于不存在近似的参照系,几乎是无法考辨,从而众说纷纭。
所以写起来这个帖子反倒最省力,仅代表个人观点即可。
现世存拓本屈指可数,出版率倒是相当高(基本全经出版过)。先述新中国后的印本:
(一)王偁(孟扬)本:又称荣郡王(南埙斋)本、潘祖荫(攀古楼)本、吴县吴湖帆(四欧堂)本等,现藏上海图书馆,每面六行,行八字。此本王壮弘述“精光四射不可逼视”、“黝黑中透紫光”,会令人误解拓墨浓亮如乌金,王先生所言者乃其古气,实则宋拓本无那般浓墨(后来的一些图录与印本人工调校过甚,同样给人错误印象),原本纸黄墨陈且历经多次重装,目视极旧。印本前后经两次原件摄影,跨度近九十年,面貌大为不同:
最新摄影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特辑《四欧宝笈》原色蝴蝶装仿真册页本,强荐!拓墨还原力超出任何化度印本,未作人为处理,最大化保存了原拓面貌。
前次摄影出版为民国时期黑白版,印有中华书局珂罗版,由于使用滤光片拍摄,对比度显得较高,佳景传承黑白册页翻印最佳。其它翻印者众,较常见者有成都古籍书店、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经典”、“欧阳询法帖品珍”、上海书店“历代法书自习范本”、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中国法书选”、台湾华正书局等,除佳景版、成都古籍版与台湾华正版外,大多将拓芯周边题识裁去,或剪其前后题跋附件,无复全貌。
除摄影的差别外,前后的原本面貌也经翻天覆地之变化,小的补跋、增减印章不计其数,光大变化计有:
- 前增一开叶恭绰跋(亦可能之前为空白开未印)
- 拓本首字“化”经涂描为撇笔不穿(痕迹在新印本中非常清楚)
- 后减去两开吴湖帆手钩失字与褚德彝跋
- 后敦煌本照片和罗振玉跋由原两开(无手书跋文)改装为七面,吴湖帆补书大量跋文
- 后增共九面新跋文,包括罗振玉、伯希和、吴湖帆、沈尹默等
注:此本亦曾为成亲王藏,有成亲王跋并逐行校缺字,需与它本相区别
(二)敦煌本:现分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残册,每面四行,行五字,残字或剪或涂,仅余二百三十六字(文献屡有错记为二百二十六字)。因幅面单薄,单行印本极少,唯见日本书学院出版部所印的黑白册页本,其他大多收于各种合集中,如广东人民出版社《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中央公论社《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二玄社《敦煌书法丛刊》、“中国法书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敦煌宝藏》,还包括各种四欧堂本印本后附的照片等等。然论图版之细节力,尚无一可与网络上流传的原色高清电子文件相比。
(三)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本:
(1)李东阳本:又称顾从义(玉泓馆)本、南海吴荣光(筠清馆)本、成亲王(诒晋斋)本等,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每面五行,行十二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时间最早者,拓本内有破损,填描却极少,同样古气莹然。最佳印本为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之原色经折装册页本,极精。
(2)大兴翁方纲(苏斋)本:现藏于日本大谷大学,每面四行,行十字,曾被刻入《墨池堂法帖》。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跋文多者,几乎就是覃溪的一部化度校碑随笔,拓本涂描较重。最佳印本为日本大谷大学《宋拓墨宝二种》套色珂罗版(委便利堂印制),精。
(3)王世贞真本第二本:又称吴县陆恭(松下清斋)本、张学良本,近日于匡时春拍拍出,可能现个人藏,每面四行,行八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拓工最精者,字数也最少,残泐字已剪。印本见嘉德2011春拍《少帅墨缘》专场原色图录,略缩小,精。注:此本亦曾为李宗翰藏,列“临川十宝”之一,需与它本相区别
(4)丰坊(道生)本:又称东吴王闻远本、繁昌鲍东方本、南海伍崇曜(粤雅堂)本、长白端方(匋斋)本,现藏北京故宫,每面五行,行十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时间最晚者,而因残字余纸未剪,存字却最多,跋文亦夥。新中国后仅见图录披露原色数开(民国时曾有全本印本),期待早日全本原色付印,对研究翁定宋拓体系有重大意义。
(5)马日璐(小玲珑山馆)本:又称朱筠(竹君)本、顾莼(南雅)本、杨氏(海源阁)本,现藏日本宁乐美术馆,每面四行,行十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较早者,曾以之配元人十三跋。日本同朋舍“书学大系”黑白印。
(四)文物本:此本来历存疑,每面五行,行九字,存字颇多,考据近于四欧堂本而不全同,或为李祺本之翻刻。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黑白印,翻印自约民国时一石印本,跋文全为从其他化度印本拼贴而来,不可信。
(五)直石本:后人临翻本,“李百药”误作“李伯药”,字体已与原石甚远。天津古籍书店“历代碑帖集萃”黑白印,每面五行,行十一字(日本民国时曾有另一直石本拓本出版)
其他下落不明且新中国后未再印之本:王世贞真本第一本(又称蒋春皋本、临川李宗翰静娱室本,属翁定宋拓本体系)、陈栩本(与文物本同一体系)、内府本、日本传本(可能有多本出于同一石),民国时皆有印本,这里暂不赘述。
其他传说原石之本,均未见印本:
- 李祺本(又名十三家跋本):现只跋尾藏辽宁省博物馆,传拓本至“永谢重昏”止,考据与四欧堂本近而不全同,与文物本关系待考。
- 缪曰藻本(又名晋王敬德堂本),曾被刻入《海山仙馆帖》,传与李祺本近,待考。
直石本不论,以拓本来看,我个人感觉几个体系的书艺水平排序为四欧堂本、文物本、翁定本、敦煌本,刻制水平排序为四欧堂本、翁定本、文物本、敦煌本。当然,由于敦煌本拓制时间最近其刻制时间,最无法藏拙,更易暴露自身的弱点,再加上本内有填描,早年印本主要依据民国时照片,细节欠缺,可能造成大家批评较多。
历史上的聚讼主要围绕四欧堂本、敦煌本和翁定宋拓本,我也来加一瓢水,凑凑热闹。
根据记载,可了解的是:
- 原石在宋庆历前已断
- 宋庆历时增断
- 南宋初年原石毁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的一些事实是:
- 通过吴湖帆之复原,证明四欧堂本为拓自四石,且的确是断石(非断石之翻刻)
- 通过翁闿运之复原,证明翁定宋拓本体系为拓自一未断石(然下部大片石花剥损)
- 通过施安昌之研究,证明敦煌本也为断本,且断处多与四欧堂本相似
难以确定的是:
- 哪本拓自原石?(或者有没有原石拓?)
- 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是否出自同一石?
- 原石最早何时断裂?
以下为自由心证,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
- 四欧堂本最接近原石拓,石花与断痕最自然
- 四欧堂与敦煌本非出一石(可参阅仲威之对校考)
- 原石早在唐(或五代)已断裂
继续演绎:
- 从刻制水平与宋拓时石皮剥损程度猜,翁定宋拓本体系可能为唐人临翻,非宋翻
- 敦煌本可能为残唐五代至宋初间翻,翻后不久所拓
最后这个最有意思,接近YY性质的心证:翁先生论由三石变为四石是靖康时所为全出猜想,造成与敦煌本时代之矛盾一直无法解决。而原石的传说皆本自解缙《春雨集》引范氏跋文,其中有“公求得之为三断矣”一说。“为三断矣”大家都理解成“是三截(石)了”,我却觉得更靠谱的翻译应是“被截断三道了”。范公南山佛寺初见者可能就是三石(两平行斜断为改作砌石时所裁,否则何苦作此规整之断?),后寺僧破最大的中石寻宝,变为四石。
这样就一通百通了:原石早断,翁藏宋拓本唐时翻自未断石,敦煌本后翻自断石(可能是三石),范公访得四石归,四欧堂本很可能为原石归赐书楼后所拓,拓制时间上限为北宋庆历年,下限为南宋初年(入井前后无可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