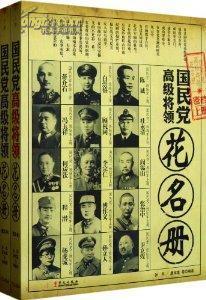吕恩(1920—),江苏省常熟人,中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本名俞晨,青年时代热爱演艺事业,中学时期遇于伶老师要她演戏,可父母坚决反对,认为“戏子”低人一等。为追求光明与自由,吕恩随动荡的时代大潮到了重庆,毅然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但她是孝女,为不“辱”俞氏门第,易名为吕恩,从外祖母姓吕,并示戴德感恩之意。1941年毕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从事话剧、电影演艺事业,建国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与电影作品,创造的蘩漪(话剧《雷雨》)、马聂法(话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白口袋(电影《骆驼祥子》)等形象,为其表代表作。由于“文革”中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得了“红斑狼疮”,治愈后便告别了舞台。(注释:这个资料依据“百度百科”。吕恩年龄另有版本,以其自述“1939年我十七岁”而论,当是1922年生;搜索其晚年活动的许多报道,包括2009年“87岁的吕恩”称谓都持此说)。
吴祖光(1917—2003),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2003年4月9日,因冠心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李:认识您快十年了,一直想听您讲讲您和吴祖光先生的故事。现在大家一般只知道吴祖光和新凤霞是夫妇,对吴先生在此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清楚,他本人和您基本上都是避而不提。我想,你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六七年,后来又是友好地分手,其实完全不必回避。对于研究吴祖光创作和传记的专家来说,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挺重要的。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聊聊你们的这段爱情婚姻生活。
吕: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生活美满,我就淡出了。我跟他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我想了半天我们的结合,他对我不错,我对他也不错的。我想,我和吴祖光的感情是朋友的感情。我怎么就没有转换成夫妻的感情呢?跟他,人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好,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呢,就不怎么样了,就又没有那么如胶似漆。我们分开了很好,写信很好,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完美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感情上、生活方式上不一样。我们就走开了。走开以后呢,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李: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吕:我是在1938年就认识了他,是在重庆。1938年夏季,我从沦陷了的老家江苏常熟逃亡到重庆,考取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一年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教务主任,吴祖光在那里当余上沅校长的秘书。他也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国语,后来又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是南方人,跟他学国语。所以,我开始一直叫他“吴先生”,后来关系转变之后,也从来没有叫过“祖光”,有时就连名带姓叫“吴祖光”。到现在为止,提到他还是叫吴祖光。
李:在学校有个人接触吗?
吕:我一到学校不久,就受到邀请,参加了他的一次请客。他就是爱请客,有这个特点。你们不是说他爱请客吗?不是现在爱请客,从小就爱请。1939年,我17岁,他大概21岁,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李:我最近在整理他的日记,是1954年到1957年的,几乎见天就是记着请人吃饭,从夏衍、潘汉年,到黄苗子、郁风、丁聪,还有梅兰芳、齐白石。好像整天就是聚会。
吕:在重庆时他就是这样,有了钱就一天到晚请客吃饭,他感到开心。
李:真正开始来往,或者说你们成了朋友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
吕:那是到离开学校以后了。1943年,我从学校出来到了中央青年剧社,当职业演员。他后来也从学校来了,好像是当编导委员,反正位置比我高。这时,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是同事关系了。从那时开始,他对我不错。他开始写《牛郎织女》,在重庆写的,完了之后,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是张骏祥当导演。《牛郎织女》赚了钱,我们都参加平均分配。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就胡花,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每天去逛街吃包子。后来,小丁、我、吴祖光三人就说到青城山去玩。青城天下幽嘛。我们三人就去了。
李:这次青城山之行,您对吴祖光有什么印象?
吕:这一段,我们大约玩了十六天。吴祖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像郁风那样,一堆人总是能看到郁风,吴祖光不太出头的。
李:从青城山下来,你们就成为朋友了?
吕:在青城山不算,回来后这时开始通信,就算做了朋友吧。
李:看来你们的爱情与四川的名山大川关系密切。
吕:也是机缘吧。1944年八九月间我回到重庆,吴祖光没有回去,还留在峨眉山写剧本。是宋之的把我送到“二流堂”去。那时,高汾还没有去,我和郁风的妹妹一起住。唐瑜的房子叫碧庐,那里的故事可多了。
李:我写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还编过一本关于“二流堂”的书,书名就叫《依稀碧庐》。我觉得“二流堂”里的你们这批人很有文人特点,值得研究。要是能拍一部“二流堂”的纪录片,其实也很有意思。吴祖光什么时候来和您在“二流堂”会合?
吕:吴祖光到冬天才回来。回来他也住了进来。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我很奇怪我的感情,很有意思。他对别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我就是不嫉妒。一堆人一起玩玩挺不错就是。走开了也想。他比我大四五岁,给我很多帮助。他中文底子深,语言也很好。我是江苏常熟人,学表演,他就纠正我的语音,像卷舌音我就发不好,教我念儿字化的绕口令,如“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他还教我写字,大字小字都写。我很听他的话。他还鼓励我记日记。挺好的。但就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两人后来就不干了。就这么一种关系,很多人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孩子。他没有提出来正式结婚,我也没提,也不想结婚。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李:就是说在1944年冬天,你们在“二流堂”开始一起生活。
吕:是的。半年多之后,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我和秦怡坐汽车回上海。我们先动身,他后到。吴祖光是坐飞机到上海,结果他比我还早一个月到上海。
李:听丁聪说过,你们是在上海举办的婚礼。
吕:开始还没有准备结婚。但又为什么正式结婚呢?到上海后,我回常熟家乡去,这时发生了一个重要插曲,促成了我们的正式结婚,而且是三天之内决定的。
我有一个同乡表兄,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学气象的,抗战八年期间当空军,他到印度一个基地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很荒凉的地方。他是个孝子,有兄弟两个,都出来了。抗战期间母亲在家乡病了,找了一个女孩子照顾她,母亲病好了后和这个女孩子相依为命。这个女孩子不错,他妈很喜欢,就写信给儿子说是替他定亲了。表兄非常孝顺,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回信还是同意了。过了几个月,他母亲要把女孩子送到重庆,但走到半路没走成,又回到了常熟。表兄给我写信说到这件事,说战争无望,他让他母亲还是把那个姑娘当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样他就了了一桩心事。这个表兄告诉我这个事,他其实对我也有意思,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过去后,他一直和我通信。吴祖光也知道这件事。我回到常熟,上午到家,下午表兄的母亲就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些事,问我他儿子的情况,我说他没有别的女朋友,要通信只是和我在通信,他呆的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她们走了之后,我母亲就说我:“你这个傻瓜,她就是来探你的”,因为外面有传言,说我和那个表兄已经生了孩子。我说:“去他妈的!”我说,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人,只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寂寞的,与我通信,我就回信而已。母亲说:“你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嫁出去。当时不愿嫁出去,还自杀过一次。”母亲警告我:“你可不能跟他好,不然要出人命!”正在这时,吴祖光到我家来了。
李:你知道吴祖光要来常熟吗?事先约定的?
吕:事先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的。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母亲对他很满意,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这个人不错,跟我谈得不错,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说,怎么一下子就说要结婚呢?母亲说:“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不然,你表兄回来又要追你,事情就闹大了。”我想怎么办呢?后来想通了,结吧,反正我们已经好几年了,感情虽然不是那么深的,但还是有感情的。我是个女孩子,不结婚挺麻烦的,老是被人追来追去的,也不好。结了婚以后,我可以专心搞事业。就这样,我决定结婚,回到了上海。就这么结的婚,当时很理智的。
李:对你们结婚,上海的朋友们好像都很高兴,前几年冯亦代也曾同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婚礼准确时间是哪天?在哪儿举行的?
吕:1946年3月,在上海梅龙镇饭店举办的婚礼。证婚人是叶圣陶、夏衍,是冯亦代、丁聪他们几个人张罗筹办的。重庆的那批朋友都来了,还有话剧界、文学界的朋友。1946年我25岁,在重庆时我和吴祖光是同居,现在是正式结婚了。那个时代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李:你和吴祖光在一起一共生活了多久?
吕:如果从1944年在“二流堂”住在一起算起,到1950年分手,应该是6年。在这之前,只是朋友交往。我回想一下,1943年开始和他来往密切,到1946年这4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他的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他写了《少年游》、《牛郎织女》、《捉鬼传》、《嫦娥奔月》,好像还改编了《红楼梦》。这四个戏都演出了的。
李:你出演过他的多少戏?
吕:我总共演过他的三个话剧《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三部电影《山河泪》、《春风秋雨》、《红旗歌》。最后一个就是1950年解放以后新中国的电影《红旗歌》。
李:你们在香港和潘汉年、夏衍他们来往多吗?
吕:我和潘汉年认识,但不像吴祖光和他那样熟。我和夏衍很熟,叫他“干爸爸”。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秘密的事情还要我做。1948年中秋前后,拍张骏祥导演的《火葬》,要到北京拍外景。那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我要走的头一天晚上,夏衍来找我。过去他每次来都是找吴祖光,谈他们的事,他一来,我就走到一边去。所以这次,我一看他来了就又要走开。夏衍马上说:“吕恩,今天你别走,这次我找你有事。”那时从香港到北京,要先坐霸王号到上海,停一晚上,然后再去北京。他说:你在上海住一晚上,替我办四件事。一,先去找于伶,把他约出来,要他转告阳翰笙,赶紧离开上海,到香港来;二,告诉陈白尘,要他隐蔽起来,这个你可以去通知;三,叫刘厚生等四个人,赶紧到苏北解放区,找什么人联系;四,带一封信给王苹,这封信是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宋之的写给妻子王苹的,先带到了夏衍手里。我们剧组到北京拍外景只有四个人,我、白杨、陶金,还有美工秦威。一个多月后,我回到香港,夏衍拍拍我说:“吕恩,干得不错!”我说:“干爸,奇怪,你怎么要我干?怎么不要白杨干,她比我细心。”夏衍说:“你糊涂,胆大。”他真教我怎么做。去上海前,他说带那些东西,不要让海关的人查,宁愿多送钱。
李:你和吴祖光分开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
吕:我们分手,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同。我这个人脾气挺怪的,他后来越来越红,名声越来越大。和现在的演员不同,我那个时候不想靠着导演上去。我要上去,要靠我自己的演技、靠自己本事上去,不能靠丈夫的关系上去。他越是红,我就越不习惯叫我“吴太太”,我不知道是叫我,香港那个地方喜欢这样称呼,而我喜欢人家叫我“吕恩”。
吴祖光这个人有一个好处,人缘很好,随和。他不像张骏祥,张骏祥脾气大。吴祖光是什么人都能交,各种人物都能交。吴祖光的朋友真多!他女朋友也不少,当然和凤霞结婚之后不一样了。在我之前,他有一个女朋友,和新凤霞样子不一样。她大大个子,是打篮球的,是他在北京孔德中学的同学。在重庆他们也是挺好的,我们也经常来往。
我们是在拍《虾球传》时决定分手的。后来,我还参加拍摄他的《红旗歌》。我们是很友好地分手。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没有吵。我们两人分开,夏衍和那些朋友他们都理解。夏衍说:他们性格不一样。
李:你怎么看待他后来和新凤霞的婚姻?
吕:我觉得他最后找到新凤霞,是找对了路子。为什么呢?吴祖光他喜欢北京的生活气氛,那种调子。我比较海派一点儿,他和丁聪都喜欢京剧,在上海时,他们带我去听京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看麒麟童的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他就说:对牛弹琴!我就说:“下次别带我去看了,带我跳舞去。”这样,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行。
李:你们分手后就离开香港了?
吕:我跟他分开是在1950年演完《红旗歌》之后,他是1949年七八月份回到国内,我是1950年初回来的。我先从香港到长春,后来到北京就分开了。在香港,我们其实就分开了。开始他不愿意分,说国内的事情还是回到国内去解决。回国后,我又参加了他导演的电影《红旗歌》。拍完之后,我就到了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上了一年学。后来,他从东北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他比我先结的婚,1950年。他结婚时我们也是礼尚往来,我送了礼,但我没有去。
李:离婚后还有来往吗?
吕:他还来看过我。我在西苑革大学习的时候。那时我抽烟,他送我一条烟。他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不知道。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都忘了。我们一起到颐和园去,当时我就提出来,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以后你不要单独来看我。他说:“为什么呀?朋友还是可以的。”我说:“我不要。你现在的婚姻很美满,我知道。新凤霞很爱你,爱情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我就不要做那粒沙子。我们以后在大众的场合见面是可以的,就不要单独见了。我拒绝了他,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单独见过。除了吴祖光以外,我和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很好,吴祖康、吴祖强、吴祖昌我们都来往,叫我“吕姐”。他的姐妹在昆明的、福建的,到北京来总是要找我。我们成了好朋友,整个吴家,FAMILY都是我的朋友。很有意思。
李:有一次你说过,你们之间有过一个疙瘩。
吕:是这么回事。1949年我们分手,他从香港回来时,经济上非常不行。那时导演接戏按整部戏的标准领取费用,演员则是按月拿薪水。一部戏拍的时间长了,导演的钱反倒没有我们当演员的多。比如说一个戏导演拿一万元,一个月是这么多,半年也是这么多。当时张骏祥和白杨在一起,他就说:“我穷得要死,白杨富得要命。”吴祖光和我也是这种情况,虽然我没有白杨拿得多,但旱涝保收。他的钱已经用光了,要回去。我们把房子抵掉了,有几千块吧,我都给他了。还是不够,我就买了一个莱卡相机送给他,很贵的。我说:“吴祖光你走了,我送你一个照相机。为什么要送呢?你是当导演的,回去后拿来拍戏采景用。”除了相机,还有一套辅助设备。他也挺感动的。后来,他和新凤霞结婚,人家告诉我,要在欧美同学会那里举办婚礼,两个人没有多少钱,把我送他的相机卖了用来请客。我心里挺不舒服的。心想我是为你工作送你的,结婚干吗卖了,多可惜呀!我不痛快,后来我告诉郁风,她批评我心眼太小。她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的就怎么的?”我想想也是,我送给他了怎么能限制他呢?所以现在也觉得没什么。
李:和他分手后,你自己的生活怎么样?
吕:我后来结婚的先生不是文艺界的,他是胡蝶的堂弟,叫胡业祥,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打过二战,打过日本人。后来参加起义,改行了,不用第一技术,让他用第二技术———英语,到体育总局当英文翻译。前两年去世了。我们有一个儿子。
李:我见过你先生。大概1994年,那次在夏衍家“二流堂”老人们聚会,我也参加了,你和你先生一起来的,吴祖光也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有没有因为他的事情遇到麻烦?
吕:分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除了老朋友,他的新朋友我后来就淡出了。他在电影界,我在话剧界,隔行如隔山。北影属于中央部门,人艺属于北京市,一些活动也不在一起。偶尔有文艺界联欢活动,会碰到吴祖光和新凤霞,但都是寒暄。我这个人是淡出的人。“反右”时我正坐月子,过后才知道吴祖光在文联礼堂挨斗了。“鸣放”时一次活动也没参加,一次会也没有参加。我的许多朋友都成了“右派”,我要是参加了活动,恐怕也跑不掉。“人艺”的领导来问过我,批判吴祖光你有什么事情要揭发的?我说,我没有什么。
李:许多年过去了,你能再说说你对他的印象吗?
吕:吴祖光是个天才,才思敏捷。我跟他说,你怎么不用功,他说用不着用功。他说:“我奶奶是有学问的人,我小时候,她坐在炕上,盘着腿,拿一大堆铜钱,要我背古诗,背一首拿走一个,把这一堆拿完就可以出去玩。”他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童子功好。这个人有意思。说他神童不假,我看他写东西不痛苦的,玩着玩着就写出一个剧本。人家写东西都得构思呀,他不,脑子确实好用。后来变成一个痴呆,真是可惜可怜。
吴祖光还有一个特点,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同情弱者。我记得在剧校时,有一个工友,叫老黄,大大的个子,农村来的,我们女孩子们调皮,都叫他“奥赛罗”。学校在江安,我们后来到了“二流堂”。那时重庆经常抓壮丁,他来找吴祖光,说家里回不去了,回去要抓他的壮丁。吴祖光就把他留在“二流堂”当男佣,替我们挑水,做饭。还有一件事,他们家在江安时,他家里的一个佣人,是个男孩子,被抓壮丁,他去抢回来,把保长他们痛骂一顿。打抱不平。
李:晚年他和超市打官司的事情,你知道吗?
吕:我知道这件事,花费了他不少精力。他就是这个特点。
李:你保留有和他一起的照片吗?有结婚照吗?
吕:我们没有结婚合影照,可见不重视。真是没有。我翻出这一张,在水里的相片。1948年,拍《山河泪》时,热得要命,拍完我就跳到水里,他给我拍的。他很喜欢这张,以后放在了他的床头。真是没有合影。他那里有没有我不知道。这是我演他的《嫦娥奔月》中的主角,1946年,在上海兰心剧院,服装还是小丁设计的。
李:他给你的信还保留着吗?
吕:一封也没了。他写给我不少信,当时也给秦怡写了不少,给我一封,给她一封。我问秦怡,吴祖光的信还有没有,她说也没有了。他的信写得真漂亮,很美,很有感情,看他的信,是一种享受。
李:你的日记还有吗?
吕:“文化大革命”时抄光了。那些都是吴祖光鼓励我写的,我还养成了写的习惯。我想,吴祖光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认识他,那不知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走另外一条道路。是不是?我想想,还是很感激他。我想了半天,吴祖光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新凤霞去世之后,他已不再能说话了,是唐瑜米寿,高汾的女儿召集的聚会,在“夜上海”。吃饭之后,唐瑜的夫人叫我,说:“吴祖光要和你照张相。”我当时愣了一下。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当时不怎么说话,只吃饭。就这样,他拉着我的手,和他照了一张相。
李:那天我在场,是1999年。这可能是吴先生病逝前最后一次参加“二流堂”的聚会。很有历史意义。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吕:在他去世前一年,2002年吧。我和吴老二吴祖康很好的,我常去他家看他。一次,我在他家,正好吴祖光的儿子吴欢来电话,他听说我在,就说:“要吕阿姨别走了,我请她吃饭。”他就来了,我们一起在旁边的饭馆吃饭。我问他,他爸爸最近怎么样,他说有两个保姆在照顾。他说,过两天我们要一起聚聚。他说要请我和他爸爸到他的新居王府花园去玩。过了几天,他来车先接我,然后到东大桥接吴祖光。那时吴祖光已经完全痴呆了,是被背下楼、背上车的。虽然痴呆,他还认得我。他看见我就这样呆着。他弟弟祖康指着我问他:“你认识她吗?”他点点头。他还认识,他不说话了。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轮廓变形了。我很难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