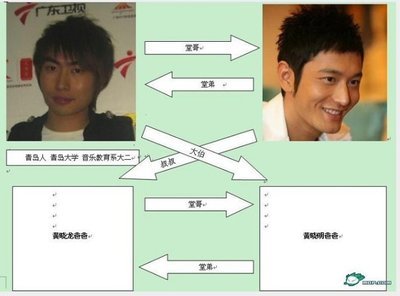7月中旬聚会,老孙介绍艾晓明女士,50多岁,穿戴朴实,神态平静;我说久闻大名,风凰卫视上见过,05年,采访河南爱滋病人,外套摄影服,肩扛摄相机,变化真大。艾晓明问,有那些变化?我赶紧说,你电视中的形象很专业,现在比较随和。我想,千万不能说年龄和穿戴。
席间,众人回忆旧人旧事,讲时政、经济等,艾晓明很少发言,只是静静的听。我想起鲁氏在《仰天长啸》中,对她有描述,武汉图书馆,阳光中的阅览室,青春的少女情怀,交织着英雄主义崇拜,默默守望的眼光,火红年代的温暖记忆。
艾晓明不喝酒,带来一瓶茅台酒,请大家。她说不知酒好酒坏,要大家尽兴。我们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情意之间。
干小雄说,文革中有不少人告密,同辈相残,置人死地,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不能全部推脱给某某人。艾晓明说,我不同意这样说,不少人是身陷囹圄,情势危难,不能自己,被迫招供,情况比较普遍,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英雄主义的观念,求全责备。
艾现在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室的主任,博导,教授。网上的称谓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人权教育工作者。
她说,我在国安局挂了号,电子邮箱常遭蔽屏,但心理上可以承受,国安局的人对我解释,监控主要是防止群体事件,稳定是压到一切的。
吾辈是过来人,平心说,知识分子现在的话语权是扩大了,原因是改革开放和自我争取。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扩大有三个阶段,80年代的话语空间是课堂,90年代话语扩大为新闻、报刊和著作方面;2000年以来,充分利用电视和网络,扩大人文影响,电视学术明星有于丹、易中天等,但有底线,一语中的话,是万万不行的,打插边球也要有分寸。
艾晓明是公共知识分子,有良心、良知,有社会责任,关心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关心爱滋病人(中原纪事),关心四川地振灾区的失学儿童。
有人问艾晓明,去年12月中旬的签名信有没有下文,艾说此事复杂,以后找时间细说。我未听明白,问其究里?柳教授解释,去年12月18日,知识界联名上书党中央,条陈政治体制改革,有1800多人签名,艾老师是其中者,我方才会意。
艾晓明的博客量比较大,说明她做人做事严谨、勤奋。博客的内容三部分:
一为通信。有指导学生如何开展学术研究,要充分收集资料。弄清“是什么”“为什么”,自己想清楚观念,不要在网上搬弄别人的观点。提出要概念,不要概念化《套用理论不可靠研究需要找史料》。与各类事件的当事人的通信,充满了人文关怀。如《北川生死书》——代一位父亲书写。
二为学术论文。如《叙事的奇观》(上、下)─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等。随笔:《中国人为什么好吃?》(上、下)。
三为访谈。剖析自我,探索自我定位,重点介绍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记录片工作。
2008年7月,台湾《天下》杂志采访艾晓明。
艾晓明说,文革对我的影响一言难尽。当时我在武汉,小学刚毕业那一年,十三岁。我父亲当时是英文老师,挨了批斗,再加上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的将领(唐生智,抗战时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因此家庭一定受到冲击。对当时的小孩(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被歧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对我的正面影响就是个性比较叛逆。其实现在也还不能说完全告别了文革,在很多地方我看到暴力、专制、践踏法律。
我比较关注公民权益的问题,人们怎么争取或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与这相关的问题我都会特别感兴趣。这些事情往往蕴含了尖锐的冲突,人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特别大
………每个问题都很具体,例如太石村涉及村民选举权、土地资源流向;天堂花园涉及针对妇女的暴力;但这些都只是一些概念,我们或许可以把纪录片归结为概念,但纪录片更重要的是捕捉、纪录与传达经历者的状态,我觉得这是纪录片的一个特殊功能。
你可以透过许多文字资料、新闻报导去了解事件成因,但重要的还有看见,看见村民的形象、他们的情感状态。直接面对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情感受到激发,这促使我们去理解这些事情背后人们的内心、动机,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我喜欢看纪录片,从中获得许多启发。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深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容易被其它概念所取代,不会特别珍惜一些价值。
记者问:你的纪录片主题政治性,社会性比较强,为什么?这是自觉的吗?
艾晓明:冲突性比较强,可以说是自觉的,但也不是我作为作者有意去激化矛盾。有些激烈场景并不是我希望看见的,更不是我的导演。我没有选择回避只是因为,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应该被公众看见、了解和寻求解决之道………但在中国大陆,存在一个状况,很多问题被权力集团变成“禁区”,因此一些学人很自觉地不去触碰。他不是出于理性,认为这些东西不值得研究,而是出于恐惧,担心研究这些问题会失去自己的安定,陷入危险,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记者:面对中国大陆上这么多不该沉默的事件,许多人都保持沉默,也没有站出来,你怎么看?
艾晓明:我想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恐惧,这不完全是一个人个性或内心强或弱的问题,它反映了制度性、结构的问题,这个制度采取了许多方式限制公民自由,并且有许多规训和惩戒的措施。这些惩戒措施使你很具体地失去亲人、朋友,毁坏你的家庭,身体遭受摧残、人格受到污辱。这种时候人们就可能会回避道德责任,选择保全安宁,不去挑战禁忌。我觉得这样的个人选择也不能说有多大的错,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人们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保有个人见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基本人权,我们不需要从态度上去评价别人做了或没做什么,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制度使人可以如何行使权力,而不是使人被迫顺从。
记者: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有什么转变吗?
艾晓明:当然在思想言论上的尺度还是比以前大了很多,此外,物质生活变化非常大。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什么看法?
艾晓明:我没有预言的能力,我驾驭不了这些问题。不管中国社会怎么变,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现在做的这些事,还是会努力去记录一些社会事件。其实再努力你也记录不了多少,你努力又能记多少?国家的变化、制度的改善常常超过一代人的生命,一代人的时间只嫌太短。但自己可以做什么,大体还是可以计画的。像我现在这样,能再工作多少年也不可测。因此只是做一步算一步,如果健康允许,可以把一部作品做好,而且做得从容、不粗糙,我觉得就很好了。我经常想的是这些具体的小事,而不是国家走向这种大事。

后排左三为艾晓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