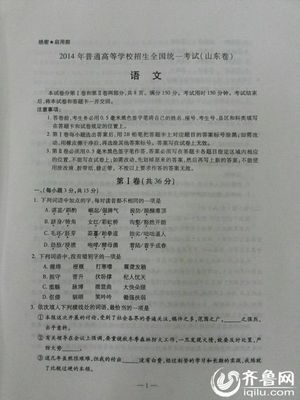昆仑“通天之旅”之二——皇天厚土
陕北黄土高原——皇天厚土上的老家
皇天厚土
我们的越野车队素质很高,车好,人好,路书好。所有的车都配备了卫星导航设备和电台。藏羚羊的车还备有警笛,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忽悠一下,超车抢路,很爽。疾驶在通往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有一种久违了的痛快淋漓的感觉,终于如愿以尝了。不由得我心弛神往…
我这个人有点奇怪,从小就非常爱玩儿。虽说是个女孩,比男孩还要淘气。因为实在不堪忍受,我刚满六岁,妈妈就改了户口,硬是把我撵出家门,送到了学校。在学校,又因为经常逃学去玩儿,挨老师打。至今老师那大灰狼的样子,还叫我心有余悸。记得有一次,玩打仗游戏,我的石头就好象长了眼睛,一下子就命中了一个小男孩的脑袋。流血了,吓得我马上带他到医院包扎好送回了家。没想到,刚一到我家,就看到了他们家的保姆气势汹汹地等着呢,爸爸没办法,只好把我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直到那保姆满意地走了,才把我拉起来。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挨爸爸的打,也是最后一次。
后来我改变策略了,在学校玩。我画画最好,是班里的墙报委员,唱歌最好,是班里的文艺委员。还被选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童声合唱团,做了小演员。因为最小,在“小鲤鱼跳龙门”中还当小鲤鱼,喊了回妈妈。孙敬修老爷爷可喜欢我呢,他用那把神奇的自动伞,逗得我团团转,多快乐呀!可惜好景不长,老师又借口学习有退步,不让我去了。没办法,精力过剩,总要宣泄,我又想出了好玩儿的。
我的二姐马改娃画我捏泥人的速写
9岁我就自编自画小人书“百合姑娘”。12岁,我又开始捏泥人,一口气就捏了三个:一个中国仙女;一个法国公主;一个非洲美女。黄、白、黑三色,可以代表全世界的女人了。据说很有水平,其中黑人还被我上工艺美院的大姐收藏了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牺牲。近些年,悟道昆仑,我才开始思考: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或许是女娲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否则我怎么会无师自通地捏泥人呢?玩儿,是孩子的天性。
玩字中暗藏天机。其秘意是:象孩子,又象王一样与天地沟通的元生自然状态。这才是幼儿学习的最好方式。玩是快乐的,大脑与心灵是开放的,最容易接受信息。所以,古人云:“寓教于乐”。况且,智慧绝不是死记硬背可以得到的,而玩的快乐的状态,倒最容易开启智慧。所以,比起别的孩子我是快乐的,幸运的。
我十六岁时,就提出了:人的“大脑”的神奇性,说它是世间最高级的结晶。它能把人类从必然王国引向自由王国。将来,女娲造人,嫦娥奔月,人造星球的奇迹都会实现。那时的人们将会随心所欲…同年,学化学时,我意外地发现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序数与原子量的规律,掌握了通过元素的序数,就可以马上计算出原子量的口算方法。当时老师很高兴。叫我上讲台给全班同学传授。
春游时,登香山。在“鬼见愁”峰顶,同学的赛诗会上,我还喊出了平生第一首诗,便一举夺魁。诗中写道:
登云踏雾九重天,
英姿飒爽彩霞边,
雷霆万钧豪气壮,
日月星辰听我言。
十七岁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可算自由了。大串联时,我最早出发,兜里揣了20块钱。第一个跟头翻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第二个跟头就翻到新疆的乌鲁木齐。一出去两个半月,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回到家,还带回了好多特产。老爸乐得直夸我:“咱家就数毛毛最聪明。”
记得当时,到西安时没钱了。我想起了三舅在西安,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马杰,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其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居然很快就找到了他。他不认识我,我只好从他的照片中找到了我的照片。讨到了20块钱,连饭都没吃就跑掉了。日后,他到北京,见了面没骂我,反而夸我,我倒真有些不好意思了。一转眼,41年过去了,太快了。如果到西安不太晚,我想去看看他们。
“哎,马姐,你的边防证办了吗?”野牦牛的话把我从神游中拉了回来。“哪儿来得及呀,只有一天半的准备时间,还赶上个星期天。”我回答说。“没有可不行,西安能不能找人想想办法,如果办不了边防证,我们就只好把你放在拉萨了。”我一听牦牛这话,心立刻凉了下来。想想法子吧。我想起了二姨的小儿子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立刻给二姨挂了电话。谁知,她一口回绝了,我说去看看她吧,她也回绝了。搞得我在车友面前丢尽了面子。不过,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况且亲戚平日往来的少,没什么感情。虽说,我妈妈是她大姐,从前没少接济过她们。她的大儿子倒是现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可是,我再也不想碰钉子了。
说起来也真有意思,1985年,我第二次去巴黎参加“国际服饰博览会”。有一天傍晚,在看音乐喷泉时,发现有一群穿着同样风衣的中国人。其中一个人很象王兆国,因为以前谈过话,我就走了过去。没想到,是我表弟。还是他先认出了我。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们好象只见过一面,我在北京外贸工作,他当时是陕西汉中一个飞机制造厂的厂长,第一次到巴黎,怎么就碰上我了呢?1995年,我拍专题片来到西安,他那时是渭南市市长,接到我的电话,立刻开车赶到西安,因为忙,他的奥迪车跟了半天,也没说上几句话。现在可不行了,不过,我也懒得理他了。反正到时候会有办法的。我放宽了心,又望着西行的路,想高兴的事去了…
陕北是我的故乡。那里有四宝,我就占了两样。民谣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我妈妈是米脂的婆姨,我爸爸是绥德的汉。妈妈有没有貂禅美,我不知道,但她出生进士门第,是盖了那一片儿的有名的漂亮媳妇。爸爸武功肯定比不了吕布,可也出生大户人家,是绥德师范、延安“抗大”毕业的北京最高军事指挥学院的教官,相貌英俊。以至于那些到陕北寻找绥德汉的影视圈朋友,在我老家的窑洞里看到了他的照片,才没有绝望。
我可以算是优良品种了,只是不够漂亮。但是很庆幸,我的根生在了——那块拯救了毛泽东与中国命运的皇天厚土之中。
我的乡亲们至今依然过着原始的穴居生活,可是健康、恬静、快乐。在这块厚土的怀抱中,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了,依然如故。几乎没有对环境有任何破坏,几乎没有制造过任何垃圾。
我记得:12岁时,第一次回老家。上厕所,找不到纸,原来他们还是在用黄土疙瘩。当时,我不理解,认为脏。现在想起来,才明白:我的乡亲们最干净。他们是老子所说的“道”上的人,是对大自然无为的人,是可以和大自然世世代代和谐共生的人。所谓现代的文明是什么?对大自然有太多的作为了,离经叛道。为了自己所谓豪华舒适的生活方式,不知灭绝了多少动物,不知破坏了多少生态,不知制造了多少垃圾,连人都快成垃圾,整个地球都要变成垃圾场了。始作俑者,自己如何呢,环境是污染的;食品是污染的;空气是污染的;连遗传基因都是污染的,你还能是干净的吗?你还能健康快乐地生存下去吗?

我的三叔,是个非常淳朴的典型的陕北农民,为了他的三个参加革命的兄弟没有后顾之忧,他一个人留守在我爷爷身边,替他们尽孝道,看守家园。解放后,兄弟们都在大城市当官享福了,可是他还是依然如故。送走了我的爷爷,又送走了我的父母,可他还好好地活着。每次回老家,看到的总是他那劳作忙碌的背影。偶尔打个照面,才能看到他那黑红的脸膛上,憨憨的笑容。他很少言语,可是那双慈祥的亮亮的眼睛,总能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的乡亲们,就是这样,默默奉献着。
不过,现在看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得天独厚”呢。他们住的是窑洞,冬暖夏凉。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自家菜,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终日劳作,清心寡欲。生活简朴而健康快乐。就象这高原上的一棵棵树,一块块石头一样,普通而自在。在那块空灵之地,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可以永远地和谐共生…
陕北人民自红军走后,又恢复了更加艰难而平静的生活。解放后,几十年来,无怨无悔。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境界,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崇敬与深思吗?
陕北还有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叫郭洪涛,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他是我妈妈的舅舅,我的舅爷。1927年,十八岁时,他被叛徒出卖,蹲了国民党的监狱,一下子就是六年。在狱中,受尽了酷刑折磨,但是坚贞不屈。当时,朋友送给他一对小白鼠,成了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后来小白鼠死了,他却难过了很长时间不得释怀。
我父母家的好多人都是他带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他非常聪明能干,外号孙悟空。1949年,他担任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曾亲自迎接毛主席、党中央进北京,就如同他当年在陕北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一样。解放以后,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他一直被打压,蒙冤几十年而不得志,后来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好多年。
他精力异常旺盛,1988年还主持了国务院能源办公室的工作。95岁还上班,一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住院了,才没有去。也算是鞠躬尽瘁了。1992年,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红宇时装艺术展”时,他不顾83岁的高龄和陈幕华副委员长一起为我的开幕式剪彩,这叫我很感动。每次清明节,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我的先生和父母时,我都会去看望他老人家,一个把他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和几乎整个家族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人。
10号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画家朋友樊洲隐居的终南山就在西安的附近。他和管先生昨天晚上连夜赶回了西安,我们在西安重逢了。
古代昆仑山也叫南山,终南山就是昆仑山的终点,也是起点。难怪,自古终南山就是修行圣地,它连着昆仑文明之太极呢;难怪西安(长安)能够成为十三朝古都,成为驰名世界的大都市。它与古昆仑“帝之下都”黄帝轩辕国一脉相承。
(未完待续,下一集:三星高照)
2009年6月25日马红宇于昆仑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