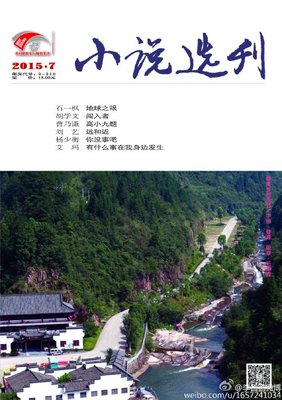他仍保持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却选择性地接收和过滤当下的信息。久负盛名的先锋作家,在《兄弟》之后,新作再次招致恶评。
文 | 苏更生
新作《第七天》上市的前一天晚上,余华只不过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预告,此外什么也没说。那是6月13日的事情;截至记者发稿,除了一个声明、一个研讨会,余华没有对这部13万字的大作遭遇的评论发表任何回应。
此后的时间,是猫在家里看NBA决赛。他转发了热火和马刺的第六场对战视频,称那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比赛”,到了6月21日早上7点47分,又发微博说睡了三个小时就醒来,因为今天是马刺和热火“抢七”的日子,脑子里便全是第六战的情景画面。到了上午11点52分,对决胜负已分,余华写道:“……我的假期结束了。”
网络上关于《第七天》的恶评正铺天盖地地袭来,有人说那是“新闻串串烧”;也有人说“就像天涯论坛加李承鹏的笔法”;还有人认为那是“余华最烂的小说,根本就是一个文摘”。
余华似乎早已有准备。在《第七天》出版之前,他就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说:“等着大家来骂吧”。对他而言,现有的声音甚至是堪称安慰的:“有人说《第七天》是我最烂的小说,这个很客气了。七年前《兄弟》出版时,有人说是中国所有小说里最烂的。”
出版方新经典的相关营销人员说,目前余华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他想再等一段时间”。而余华则通过出版方回应,NBA的总决赛已经看完,现在他等着看温网了。
余华的不高兴
《第七天》付梓前,与出版社商定了封面设计之后,余华去了一趟法国。他与作家苏童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谈论当地的房租、法餐、红酒、咖啡以及化妆品的价格,并困惑为何人们如此热衷女星走红地毯这个话题,“我说二十多年前家里铺着化纤红地毯,那时候我天天走红地毯。”他写道。
戛纳与《第七天》是世界的两个极端:前者是明媚的阳光、美女和大海,而后者则截然相反: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在《第七天》的开篇里,余华如此写道。那是一个属于死亡者的世界,亡灵在大地上游荡,目睹世间的种种惨状:被强制拆迁逼死、因卖肾感染死亡、因为男友送了山寨iPhone负气跳楼自杀、因为屈打成招最后怒杀警察……
在不少论者看起来,这种取材的方式是余华一贯的写作策略,看看他的微博就知道了:朱令案、雷政富、夏俊峰、PM2.5……有时候他也会重新转一次自己的旧帖,比如“某地用绳子牵着性工作者游街,某地遭受水灾洒水车还在工作,某地儿童医院十多年以工业氧代替医用氧,某地矿业污水渗漏后瞒报声称是维稳,某地毒奶粉再现,某地输油管爆炸,某地矿难,某地群体性事件……”他写道,“我批评自己:为何看新闻记住的全是这些。”
“它们每天都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无法躲开。”作为一个有着“社会新闻收集癖”的人,余华在他上一部引发巨大争议的小说《兄弟》的下部,就随处粘贴了社会新闻的影子:选美、处女膜修复、婚外情……他关注那些事件,而到了《第七天》,他甚至觉得这一次是自己“离现实最近的写作”。
7月3日,在批评喧嚣了20天之后,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和复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为余华联合开了一个《第七天》研讨会。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到场的学者、教授集体为余华辩护”,如北大教授黄燎宇认为余华的《第七天》“把中国人的悲哀和善良都写绝了”;复旦教授张新颖则认为余华并不仅仅在做新闻剪报,而在写我们已经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
至于余华自己,在会上谈起创作《第七天》的初衷时说:“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他对新作的看重,可以用最后的评价来形容:“这是最能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品一直到现在作品里面的因素,统统包含进去了。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的小说,如果没有文学价值,我想我不会动手!”
余华的沉默
众声喧哗而余华不语,原因可能是余华在发表上一部作品《兄弟》后遭遇的争议。按批评者所言,《兄弟》是余华写作生涯中的转折点,但也是他“狼狈地华丽转身”,是“拙劣的十年磨剑”,而余华也被认为从先锋沦为伪先锋。
在那之前,余华的写作之路可谓顺风顺水。这个生于1960年的浙江海盐县人、曾经的牙医,自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1987年因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成名,与同时代的莫言、苏童、叶兆言、孙甘露、格非和陈源斌等人被称为先锋派。此后余华一路狂飙,先后写出十多个长短篇小说,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堪称经典。经过30年的笔耕,今日的余华已经是最为欧美文化界所知的中国作家之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盛况,部分有赖于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之功。余华的《活着》被张艺谋搬上大银幕,电影《红高粱》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背后则站着莫言和苏童。但对于余华而言,这种辉煌在《兄弟》出版后戛然而止——与小说大卖(按余华的说法,一共印了86万册)相悖的是,文学评论界几乎持一面倒的批评态度。
批评者中包括曾对余华赞赏有加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和谢有顺。谢有顺说:“余华是我的朋友,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我很难过。”并称《兄弟》不值一提。当时余华仍沉浸在对惯常的赞许的期待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批评,他回应道:“再伟大的作品也有缺陷。”
谢有顺批评《兄弟》情节失真,语言粗糙,余华回击:“如果他能找出一千个这样的(失真)例子,那我就服气地说,我的小说不行。一两个构不成问题。”谢有顺再评:“许多情节和语言不符合时代现实……这样的例子我随手就可以举出几十个……要找出一千个例子来,那还有谁看他的小说。”最后,余华以“《兄弟》仍然是我最出色的小说,目前我很满意”的姿态结束了2006年的那场争论。
至于《第七天》发稿,谢有顺表示还没有看过这部新小说,因此无法评论;李敬泽虽已看过小说,但也拒绝发表评论。“南谢北李”这两个中生代文学评论家都没有发声,对于其他铺天盖地的批评,余华一反为《兄弟》急切辩护的态度——这次,他选择沉默。
“《兄弟》之后,我越来越厌倦采访,不是厌倦媒体,是厌倦自己同样的话重复说来说去。我曾经对一位作家朋友说,我们总觉得官员说套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在说套话。”他在微博上写道。
中年作家的集体焦虑
另一位知名作家苏童的新作《黄雀记》几乎在同时面世。余华夸了《黄雀记》书名起得好,除此之外,别无他言。如今,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凑在一块聊天时,已放弃文学话题,苏童说:“这些似乎在青年时期都谈光了。”
谈论文学忽然变成一种尴尬,对于余华他们而言,接受批评也变得越来越难。在《第七天》出版后三天,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新世纪文学理论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和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王安忆说:“今天的文学批评使我感到恐惧,对所有的批评我都是不看的。”书评人思郁在评论《第七天》时指出,“中国文学界已经沦为圈子文学的产物,尤其是八十年代开始成名的作家,迄今大都已经功成名就,被学院收编的收编,被市场圈养的圈养,体制与作协是那批风发意气的作家最好的生存之地……六十年代的作家,现在他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新作。”
余华今年五十有三,比莫言年轻,但比苏童略长,毫无疑问,他们都已算得上是成功者。回想20年前,33岁的余华和妻子还生活在京城一间平房里,每月只能从《收获》杂志领取400元稿费。当时张艺谋将《活着》的改编费2万元预先支付给余华,他甚至会担心张艺谋要赖掉剩下的那5000元。媒体描述过余华夫妇当年的窘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发愁了”。但时隔多年,莫言已成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而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之后,在杭州接待张伟平的余华“恭喜他和张艺谋分道扬镳,以后不用再为烂片说烂话了”,并在某一场演讲中回忆《活着》被改编成电影的情况:“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共产党,对他十分钦佩……可是张艺谋拍摄完成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共产党了。”
余华怀疑过自己江郎才尽。在2005年《兄弟》面世之前,他有十年没有出版长篇小说。这十年里,他写过随笔,却找不到写小说的感觉。《兄弟》之后,他同时写着五六本小说,但最后成型的只有《第七天》。余华也为时间逐逝而焦虑,总是有事情打断他的写作,“比如明年和后年,《第七天》的国外出版高峰就会来到,我又将不断出国去”;但他深知自己的缺点是很不勤奋,兴趣太多,总是被别的什么吸引过去。“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点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在《第七天》出版后仅有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其实他自己有过更为清晰的自白。5月8日,余华在微博上写道:“我的白日梦是做一名助理。去NBA做一个赛季的助理教练,可以在场边看球;去英超、德甲、西甲和法甲各做一个赛季的助理教练,继续在场边看球;去澳网、法网、温网和美网做裁判助理,还在场边看球;去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各做一年指挥助理,混在乐队里听音乐……最后给自己弄个墓志铭:白日梦安息在此。”
7月3日,当壹读iRead记者拨打余华电话时,他的手机保持开机状态,但他一直没有接听电话——他仍保持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却选择性地过滤和接收当下的信息。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第24期《壹读iRead》杂志。
关注壹读官方微博获得新鲜事@壹读http://weibo.com/yiduiread
*版权归《壹读iRead》杂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引用、如需转载请联系:yidu@ireadweekly.com
添加壹读官方微信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