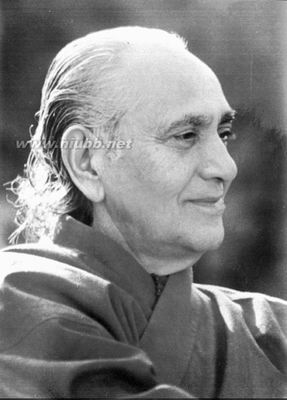麦子熟了
麦子熟了,又到了收割季节。
我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我的“根”在农村。虽然户口可以迁移,身份证地址可以变更,但是在那儿出生的就拥有了那里的一切,那里的永远,那里的唯一。那是根本抹不去的。虽然穿上军装入伍之后,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先是钻山沟在军营里摸爬滚打,后是上军校在城里安家,可以说是伴随军号声,布鞋换成了胶鞋,胶鞋换成了皮鞋,工作越干越顺,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坦,但是每到麦子快熟的时候,麦穗的裟裟声,总在我耳边回荡着。那绿绿的、整齐划一的麦田,随风轻轻摇曳,就象潺潺流淌着的一曲曲绿色音符,牵着我一肚子的思念。
麦子从播种到收割,需要在田地里生长九个月。麦收是一年中最忙最累的季节,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方能领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俗语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华北平原的气候适合一年两收,也就是说,一茬小麦,一茬玉米。每年秋收把玉米棒子掰回家,把玉米秸杆放倒,或拉到村头垛起来,或堆放在田埂上,把地腾空施肥耕地耙平。等到秋分,土壤水分合适后就开始种麦了。早了晚了都不行。农谚说,麦无二旺嘛。种早了天气还热,小麦会疯长蹿梗,浪费水肥是次要的,主要是蹿梗后小麦不分蘖,第二年的收成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颗粒无收。种晚了天气太冷了,小麦刚刚露头就入冬了,也不分蘖,影响第二年的产量。正常情况下,一粒麦种发芽后,会分蘖出四到八个枝杈,最后能分蘖出十多个枝杈,而每一个枝杈第二年春天都是一株麦穗,而且,分蘖越多,根系直发达,麦子越不容易倒伏。
我当兵离开家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大部分土地还在集体手里,每人只有两分自留地,我们家六口人,一亩二分地。集体的土地打不了多少粮食,交交公粮,所剩无己。全家人生活乃到生命全部靠这点自留地,所以,父亲把这片地看的比命还金贵。
种麦首先要耕地。在我的意识里,只有牛或者拖位机拉着犁才叫耕地。没有牛,没有拖拉机,就用最原始的一种叫铁锹的工具翻地,把表皮土翻到下面,把上面撒的农家肥翻到下面,需要一锹一锹地把整块农田翻暄腾。种地需要赶节季,掰了玉米马上就要翻地种麦。用铁锹翻地,一锹下去就几工分宽,几工分长,效率极其低下。况且,我们村的农田是胶泥地,暗红色,湿的时候像胶一样,铁锹插进去力气小的人拔不出来。干的时候像晒干了窝窝头一样,死硬死硬的,根本弄不动。
无奈,这个时候,父亲就采用人海战术,发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说人海战术,就是父亲、母亲、哥哥还有我,每人一米宽左右,一字排开,退着前进。父亲讲,挖三尺就少三尺。父亲的话让我真的想起来老愚公来。我年小无力,翻前几锹还凑合,一会儿就被拉下,每到这个时候,挨着我的哥哥就会不吭声地替我翻一些。白天干了一天,晚上接着干。种麦子的时间,多数在中秋节之后,挂在天空中的月亮,成了庄稼人的一盏不用掏钱的明灯。阴天的时候,挑灯夜战。挂马灯的木杆子牢牢地插在刚刚翻过土地里,我们边翻边退,大约退三四米就把马灯往前挪一挪。随着马灯的前进,一块一块土地被一家人真正的“掀翻在地”。有时候,父亲看着一家人实在太累了,就借生产队的牛耕地,把家里不多的玉米渣当料喂给牛,还幽默地说给牛加点油。这下好了,不用再翻地了,父亲一手拿鞭,一手扶犁,在希望的田野上,任黄灿灿带着新鲜腥味的泥土在趾缝间吱吱钻来钻去。这时,父亲会不经意间哼起小曲,那苍老浑长的嗓音总让我觉得,在生活的舞台上,只有父亲,只有像父亲一样的农民才是真正的歌手,也只有这样的歌才蕴藏着生活的艰辛和对命运的挣扎。我站在田头,放眼望去,父亲的背影和耕牛低头拉犁的姿势,立刻地永久的镶刻在心中。
地翻了,地也耙平了,该开始播种了。麦要选用优质良种。播种有两种方法,一是用耧耩,耩麦的时候,有两三个人在前面拉耧,当中一人驾辕,一人在后摇耧。耧在前进的同时,一边开沟,一边播种,一边回埋。同时,摇耧的人边走边左右摇动手中的耧把,伴着耧的左右摇动,用于调整小麦下流出口的铃铛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那小麦种便顺着耧眼滑下,三行三行的在肥沃的土地里均匀安家。四五天左右,麦苗开始露出淡黄嫩牙,随后长叶,到了五六叶片时,冬天便来了,天开始冷了,麦子停止了生长,进入冬眠。
雪花漫舞时节,小麦总是欢喜地接过上苍给自己的厚厚毯子,寒风中的冬小麦不再瑟瑟发抖,静卧在这洁白的毛毯下安稳地睡着。
冬去春来,小麦苗开始复苏、生长,并很快的窜高、分蘖,这时,应该除草、施肥、浇水。
布谷鸟叫了。田野麦浪起伏,新麦的焦香开始在乡村的上空弥漫。
端午前后,麦子很快就成熟了,麦子似熟非熟的时候,麦粒是软软的,但麦仁里并不是汁液而是已经渐趋饱满的,这时候采一把来,把麦穗放在火上烤,边烤边转,待到麦香四溢的时候,放在手心里来回地搓上几把,再吹一口气,麦皮飞扬之后,手心里就剩下喷香的麦粒了。一把填到口里,那真是回味无穷。那种香味,城里的人永远不会感觉到的。
初夏的太阳从云层中露了一下脸,使即将成熟的小麦一天就由青黄吹成了金黄。那么多的成熟的坚硬麦芒像短促的金针,闪烁闪烁一望无际地闪烁。那一地的金黄就是农民的黄金,农民的孩子,农民的生命,望着那层层的翻滚的麦浪,农民咧着嘴,哈哈的,连额头上的沟沟壑壑也在笑,连同岁月一起笑个不停。
割麦子的头天晚上,就把镰刀磨得雪亮飞快,一把把锃明瓦亮,在明亮的月光下泛着蓝幽幽的光芒,使人看了不寒而栗。“七成收,八成丢”这句农谚,是说这个时间的气候变化无常,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很可能在旦夕间毁灭。所以麦收季节是农民最为辛苦,
“龙口夺食”说的就是麦收季节,要趁芒种前后这几天天气爆热,赶紧把地里的麦子割完,因为麦收的天气,就象小孩的脸,变化无常,说变就变,晒日炎炎,刹那涌上乌云,电闪雷鸣,漂泼一场,接着晴了天,还不算坏事,倘若遇到雨天甚至连阴天,麦子就"捂"了,麦子还长在地里,麦穗上的麦粒就会发芽,一年的劳累都将毁于一旦。俗话说:“蚕老一食,麦熟一晌”。因此,割麦子求得就是一个快字,是个紧手活。
早晨的田野空气格外清晰,远出的天边渐渐地吐白,满地的金黄色麦子被风一吹,后浪推前浪象无边的大海,一派丰收的景象使人兴奋不已。草叶上还挂着露珠儿,带着湿漉漉的水气,熟透了麦穗,散发出清香。
麦地里都是割麦子的人,割麦子的人弯下腰,熟练的挥舞着镰刀,你追我赶的向前挪动着。先放“要子”,就是用棉花桔杆的皮搓成的绳子。然后,左手拢麦,右手挥镰,唰唰唰,割上一阵子。一会儿又起身,将割够一捆的麦子,捆成捆,接着再放“要子”,就是这样来回地循环着。我虽然生在农村,但大部分时间在上学,农活儿干得不多。
这年的割麦同翻地一样,父亲、母亲、哥哥、我,像翻地一样,一字排开。一会儿,抬头向前望去,父母亲和哥哥都割到了我的前面,若大的一块麦地,在我的两边已经是空荡荡的,站着的麦已经倒下成了捆。再回头望后瞅瞅,没有一个人了,好象我就是坐镇压台的人。父亲是个割麦子能手,脖子缠一条毛巾,弯着腰熟练地一手薅过麦子,一手挥起镰刀,从右往左划道弧线,一把,一把,又一把地向前挪,飘忽的镰刀,进进出出麦棵间,荡漾的麦穗,一丛丛,在他的面前倒下。母亲也不示弱,低着头一直望前割,汗水从母亲的脸上流下,顺手用缠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擦,头也不抬的往前赶。父母亲没有说过一句累的话,把我撇得老远老远。太阳越爬越高,我隐约地感到从地缝里开始往外冒热气,汗一出来就被烤干,脸上身上都黏糊糊的。我的腰也越来越疼,渐渐地好像快支撑不了我的身体了,我吃力地用镰刀杵着地,减轻一下腰的负担,好缓解缓解腰的剧痛。开镰没多久,毒辣的日头一会儿就敛起了所有的表情,麦子和人都有点蔫。干燥的天气、沉闷的气氛、枯燥的劳动。割麦真不是个好活儿,这是我割麦子的切身感受。即使什么不干,光在日头下晒着也很难消受,何况还要又蒸又晒挥汗如雨地忙着。歇歇儿时也找不到一点阴凉地儿,没有一棵树借以躲避刺目灼烤的阳光。
中午,火红的太阳,悬挂在蔚蓝的天空,浮动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站在田野里放眼眺望,只有那一片金黄的麦子正随着银镰飞舞,成排地倒下。随着无次数的弯腰,带来的酸痛已荡漾无存了,接下来的更是举步维艰,夏日的天气,空气闷热,特别是麦田里吹出来的风,更是热得难挡。割麦还得再继续,远望迷茫的麦棵子,越看越觉得看不到尽头,有些发愁。割一把麦子,站起来向前方看上一眼,望着黄了梢的麦子,一浪一浪翻滚汹涌,看上去晕晕的。此时的烈日象个火球,烧在脸上,虽然头上戴个草帽,也遮不得滚烫滚烫的热浪侵袭,我紧握镰刀的手磨出了血泡,麦茬扎破了脚趾,麦芒在脸上划出了一道道红印,裸露的胳膊,晒得发紫。我饱尝了割麦子的苦累和艰辛,真想仍下镰刀一走了知,可我看看前边的父母亲和哥哥,还有满地众多的割麦人,无一人不是在这同等条件下默默无闻地支撑着,而且没有听见任何一句怨言。想到这,我继续地挥舞着镰刀使出全身解数向前追赶着。不一会,父亲割的三耩子麦到头了,我抬起头向前一望,父亲正从对面,迎头按着我割的麦耩割来,我顿觉自己内疚,一股滚烫的暖流涌进了我的胸膛。此时,我不在顾及热和累了,拼着命的弯着腰不停的往前割,尽可能的多割些,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割的这三耩子麦也终于完成了。
正午的干热风,愈加猛烈。麦浪显得花花搭搭,麦子割倒之后,露出了空阔的麦茬地,地里露出了细小野草、纤弱野花,没有了麦子的遮挡,见了风,见了阳光,招招摇摇,自由自在,在麦茬的衬托下,更加显得生机勃勃。麦地是喧嚣的,收获的喜悦,若大的一块地里的麦子经过人们的艰苦奋战,麦子一捆捆地躺在地上,等待着人们把它运走,犹如太阳的光芒,覆盖了大地的一切,掩藏着割麦人的苦累。

割的差不多时,就开始往打麦场里运麦子了。拉运麦子也是一桩累人的农活。那时没有拖拉机,只有用排子车拉。一个人站着扶着,其余的人用叉子把割放好的一捆捆麦个子挑到排子车上。摆在地里的麦捆,一个个躺在地里,要连轴转地拉回打麦场,几十斤重的麦捆,举起扔到车上,不出几分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衣服从上到下全部湿透。碰上有的捆得不结实,挑散了架,还要重新打捆,无疑增加了劳动强度和时间。在排子车码垛是技术活,打好底子,一层比一层宽,要压好,为了多拉,还要上去一个人摆好再踩踩,然后前后左右用绳子系牢,防止中途翻车。就是从那年麦收起,我知道我是个大人了。
拉到场上的麦子均匀摊平开,晒干,用一头或两头牲口拉着大石磙子,在平整坚硬的麦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来回前进。当麦子压得很平很薄时,停下,用叉子把麦子翻过来再均匀摊平开,再一圈一圈的辗压。最后,把麦秸挑起堆好,把麦粒堆好。
这时的麦堆是混合物,里面有麦子、土、麦秸、秕子、杂草之类的东西,需要把杂东西扬出来。扬场需要风。扬场也是技术活,需要有一定技巧的。拿一把木锨一锨一锨把它们扬向空中,让自然风把它们分离开去。麦粒落在一堆,麦糠杂草等就随风飞飘远了。另外一人拿着竹扫帚“打落”,“打落”就是将风没有吹走落在麦粒堆上的细麦秸、麦糠、杂草等等轻拂扫掉。没有风,有多大的本事也没办法把麦子与麦糠杂草分离出来。风来的时候扬场的人必须“抢风”,拿出全身力气排着命干,没风时就坐着休息聊天。那时,乡亲很淳朴,互相帮着扬场打落。扬干净的麦子,再在场上晒,麦粒在太阳底下还要晒上一天,还要不时翻场,就是赤脚走进去一圈圈地拖,拖出曲曲弯弯的沟谷,增加受光表面积,提高晒的效率。晒麦子时需要看场,看到贪嘴的麻雀和母鸡,就扔一块土坷垃吓唬吓唬。
麦子棵粒归仓,全家人放心了。
“唉,总算把麦季忙过去啦!”这句话母亲说了几十年,一年总是要唠叨一遍。我这个永远不忘耕种收割的乡村孩子,也仿佛只有听到这一句土味十足如释重负的叹息,才感觉着终于把救火一样的麦季圆满地伺候过去了。
随着时代的步伐,大块大块麦田收割都实现了机器化,人工割麦子的活,恐怕也将很快的成为历史,割麦子时的苦和累也只能在回忆中慢慢的品味。
自从走进军营,踏上柏油路,再也回家割过麦子,但我心头始终不会忘记那时的收麦子境况,那情那景,一次次浮现在眼前,每每,都要难受一番,说不出是激动还是痛苦。麦收将近的时候,即使是在远离故乡麦田的城镇的夜晚,我的耳畔也总是响彻着镰刀割麦的声音。那是多么美妙悦耳的声音啊,金灿灿的麦子一片片舒服地躺下去,集合起来,成一捆、垒一垛、装满车。丰收的喜悦、繁忙的身影、滚落的汗珠伴着那幽远深沉的麦香,都在镰刀的响声中出现了。
现在,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也老了,再也割不动麦子了。每到麦收的季节,我都打电话回家,告诉母亲和哥哥,用联合收割机收麦子吧。哥哥说,现在麦场都没有了,你想体验体验割麦子也没有机会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