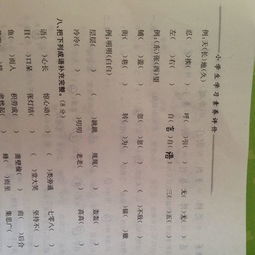“艺术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
文/程致中
1933年,上海文坛发生过一场关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争论,鲁迅发表意见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以缀合,抒写者,无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却也正如所写。(《书信·331220致徐恐庸》)
鲁迅透辟地分析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生活真实)的关系,正确地指出艺术的特殊性及艺术和生活的一致性。在他看来,生活真实是生活中实有的人事,是文艺创作的原料和基础,然而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艺术有自己的特殊形式,可以选择,加工,虚构,想象,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的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52页)鲁迅所要求的,正是具有艺术典型形式的真实。艺术并不要求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物作精确描绘,成功的艺术家不在于复制生活原型或摹写生命的自然形态,他总是通过缀合,抒写,即艺术的典型化,将生命的灵魂和精神灌注到所描写的对象里面去。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谈到艺术典型化的经验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例如,用人血馒头治病本是前清时代一种常贝的迷信活动,鲁迅在《药》中将这事放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上加以描写,表现出一般民众用革命党人的鲜血治病是多么荒唐愚昧,从而深刻地揭示出改变国民精神是迫在眉睫的“第一要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既非凭空臆造,又非历史上实有其事,而是取其一端,加以改造生发,这样的作品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具有艺术典型形式真实的艺术佳构。
鲁迅强调指出:在艺术典型化过程中,“所据以缀合,抒写者,无一非社会上的存在”。现实主义作品固然要以客观事实作依据进行“逼真”的描绘,而非现实主义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艺术形象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和精神底蕴,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所谓“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纵使写的是妖怪,在人类中也会有人和他们精神上相像。像《西游记》那样的神魔之作,尽管充满了奇特的幻想浪漫的夸张,它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本质归根到底还是和“社会上的存在”相通。
既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又重视艺术与生活的一致性,鲁迅的艺术真实论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文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鲁迅坚决反对两种不正确的真实观,即:艺术上的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
自然主义者提出“妙肖自然”的口号,采用照相师的手法,复制生活原型或罗列日常生活现象。他们宁可牺牲抒写自由,标榜“忠实于客观”,其实他们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是违背生活规律的。艺术真实当然不排斥自然形态的描写,现实主义作品还要有细节的真实;但艺术真实还要求对自然形态进行加工改造,从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中揭出事物之间相互的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艺术真实要求把自然形态的描写和典型形态的描写和谐地结合起来。
歌德说: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它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它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它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137页)
艺术家既要“用人世间的材料”写出生活真实,又要使这些材料服从他的“较高意旨”(创作目的),才能达到本质的真实。
鲁迅深谙艺术创作规律,他对忠实记事或罗列生活现象的自然主义描写提出批评:“新闻的记事”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种机械地记录事实的作品正是“不应该这样写”的“标本”。(《不应该那么写》)过去有一种观点,以为文艺作品都是写真人真事的,论者常以有无事实根据作为评判作品真伪优劣的标准。清代文学家纪晓岚批评《聊斋志异》失去真实,其理由是:“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妮之词,蝶押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信,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姑妄听之》)两个人说的悄悄话,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者何以会晓得这样精细呢?纪晓岚以为文艺作品全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作品中的描写一与事实不合,他就产生了幻灭之感。鲁迅指出,这种看法的偏颇就在于不懂得“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三闲集·怎么写》)文艺作品毕竟不是真人真事的新闻纪事,它在虚构的或根据生活原型改造的人物、事件中显出社会生活的真谛来。那些表面上全是事实,好像没有破绽的作品,牺牲了抒写自由,反而丧失了艺术真实。所谓“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实在是鲁迅对艺术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十分精彩的概括。
有一种流行的创作倾向,以为暴露社会黑暗的文艺作品可以自然主义地罗列丑恶,把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写得无论怎样脏、乱、丑、怪皆无不可。表面上追求逼真,客观上等于展览丑恶,破坏了艺术的美感和严肃性。在鲁迅看来,并非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写进文艺作品里面去:
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面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级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癫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自然主义地描写恶德丑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结果是越写得逼真,越是毁坏了艺术真实,其社会效果绝对不会好的。
暴露黑暗的文艺作品怎样描写黑暗势力和丑恶现象呢?鲁迅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塑造反面形象总是联系着广大的社会背景,一刻也不放松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尤其深恶痛绝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所宣扬的旧礼教。他总是倾注全力去解剖反面人物的灵魂,从他们的言行相悖,表里不一,透视其凶残、虚伪、卑怯的本性,他不是自然主义地搜罗黑幕秽闻,陈列堕落行为。小说中有时会出现反派人物的形象系列,构成对不幸者施加压迫的黑暗环境,从而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鲁迅笔下的群丑,无论鲁四老爷、赵太爷、四铭、高老夫子那样的地主阶级统治者,还是康大叔、陈老五、蓝皮阿五、半瓶雪花膏那样的旧势力的帮凶,都写得神情毕肖,个性鲜明。这些精心刻画的黑暗势力代表人物,经过艺术折光,也具有审美价值。它把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反复,真实生动地描绘出来,从而帮助人们反思历史、审视现实,激发人们参与社会改革,以坚韧的斗争从黑暗势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艺术上的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虚假、矫情的描写。这类作品不是从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和幻想出发;不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虚构,而是随心所欲、自欺欺人地制造谎言。鲁迅指斥这类作品是“瞒和骗”的文艺。
旧文艺中公式化的团圆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瞒和骗”文艺,其要害在于“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坟·论睁了眼看》)团圆主义用谎言掩盖真相,粉饰太平,对读者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麻痹作用,它严重地妨害人们看清社会生活中的缺陷和问题,阻遏社会改革的进程。
“瞒和骗”的文艺都有一种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的特点。旧的连环画本《二十四孝图》中,老莱子“戏彩娱亲”那徉的“艺术品”,就是虚伪说谎文艺的极致。七十岁的老莱子身著五色斑斓之衣,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戏于父母之侧。鲁迅说:“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朝华夕拾·后记》)孩子对父母撒娇,出于天性和真情,确有一种自然真率之美;老莱子“戏舞学娇痴”,装洋作假,既侮辱了孩子,又欺骗了读者,实在是将肉麻当有趣。“有真意,去粉饰”,乃创作要旨,倘若以矫饰的伪情和虚假的作态来编造作品,注定会丧失艺术的真实性。
在鲁迅看来,“瞒和骗”的文艺有多种表现形态。粉饰太平、吟弄风月之作只是一种,而盲目地赞颂铁和血的作品也值得注意。他说: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风花雪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坟·论睁了眼看》)
此类赞颂“铁和血”的文艺不敢正视革命斗争中的残酷和艰苦,或抱有对于革命的浪漫蒂克幻想,往往以狂热的叫喊和廉价的乐观自欺欺人。1930年代左翼文坛出现了一些刻画工农形象的作品,其中有些作者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大刀阔斧,乱砍乱劈,他们画农民偏要涂上满脸血污,画工人故意画成斜视眼,拳头比脑袋还要大,鲁迅对这种全凭主观想象,随意涂抹的创作倾向提出严肃的批评: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随意涂抹工农和盲目赞颂革命的作品,表而上雄壮威烈,实际上歪曲了革命。这种“硬装前进”说假话的做法,“其实比直抒他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书信·350616致李桦》)
1925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强烈声讨“瞒和骗”的文艺,并向20世纪的中国文坛大声疾呼: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血和肉来的时候旱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旱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真正的艺术家把“真诚”视为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托尔斯泰甚至认为“缺乏真诚的,执着的态度,那么就不可能产生艺术作品。”“真诚”的本质就是艺术家对描写对象的关怀和热爱,这种爱促使艺术家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深入地揭出社会矛盾和斗争,推动艺术家去寻找最完美的形式,将生活中的真善美艺术地表现出来。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提出“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创作原则,对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20世纪最可宝贵的文学传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