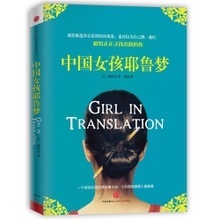读完谢泳《储安平与观察》。谢泳把储安平和《观察》撰稿人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应的名词还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p71,这些词究竟是何所指,似乎没有弄得清楚。在一个不清楚的前提下,谢泳就把这批人与胡适傅斯年这一代人联系起来,笼统地称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其中的问题很多。储安平自己提出一个“自由思想分子”名词p68。我也可以再加一个名字“独立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类似的名字,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正因为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才要有不同的名词。
如果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被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且同时称胡适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就表示了一定的意义。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都主张言论自由、坚守道义责任。这一界定未尝不可,但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这个词就无法区分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之间的政治主张不同,也无法区分他们几位和胡适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那么既然他们被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又用什么名词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巨大的不同呢?难道把储安平称为空想自由主义?梁漱溟称为“儒家自由主义”?如果这些名词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再考虑其他的名词?
我倾向于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理论、方法、观点和态度的集合体,而不仅仅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主张和道义责任的担当。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么就会看到,把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等人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恰当的。
在储安平的语言里,到处都是“国家”、“牺牲”、“代表”,“理想”、“公平”这些词语。“这个刊物(《观察》)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p68“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p69“我们这一代,大概也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p71“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p113《观察》复刊后,一篇无疑出自储安平手笔的文章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自以为站在独立的立场”。另一篇《编者简复》虽不出自储安平,但想来也能代笔他的想法,“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即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储安平的“国家”、“牺牲”、“代表”,“理想”、“公平”一套话语,很难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话语。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与储安平的话语对比强烈,这是两套不同的话语。对英美的政治制度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就是“自由主义”,对言论自由的认同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至于道德责任的坚守,虽令人起敬,但其本身也与“自由主义”是两码事。
我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理论、方法、观点和态度的集合体。这样的“自由主义”是表现为一组价值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一种观点,赞成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那么就不再以“自由主义”称呼它。
构成“自由主义”的一组价值包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财产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这一组价值之背后,又有一个核心的哲学观念做基础,这一基础,以肯定的陈述即渐进改良的态度,以否定的陈述即非理想国的态度。
梁漱溟根本否定欧美宪政在中国的可行性,主张中国新制度的建立,还是要依靠中国固有文化,p86而如欲实行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则必寻找能够实施的政治操作者,p87正因为这一点,梁漱溟仍在儒家的政治哲学里徘徊,故被称为“新儒家”,其去“自由主义”远矣。
再看张东荪。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p104这显然不能算作“自由主义”的观点了。固然,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财产自由”与“放任”有其修正,但是其基本原则仍为一致,所以名之为“新”自由主义。张东荪认同苏联式计划经济,再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就完全不合适了。

困难在于,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如何定位储安平。储安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么?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储安平似乎应该是的,从行为上来讲,储安平在国共武争的时候并没有偏袒一方,保持独立的姿态。从思想上来讲,储安平推崇胡适等“第一代”自由主义学人,留学英国,认同英美政治制度。可是细读储安平在《观察》的文字,其态度语气与胡适等人颇不同。储安平动辄谈自我牺牲,动辄谈国家大于个人,这与自由主义观念是相抵触的。虽然储安平认同与鼓吹英美的制度,但是在道德自由这一点上,他所持的是非自由主义的观念,而自由主义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一点足以否定对他的“自由主义”者的定位。储安平鼓吹英美制度,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无异,可是追本溯源,我们发现其出发点是“国家”。排除了个人之上的原则,英美政治制度,只能成为实现某种国家目标的“工具”。自由主义并不反对个人选择牺牲,但是自由主义反对以牺牲自任,反对以道德推人,反对鼓吹国家之上。
有一种笼统的说法,称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为“自由主义”道路,并以《观察》撰稿者这一群体为例。也是一个糊涂不明的意见。“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这个词语,是“两党武争”的产物,与“两党武争”对照着看才有意义,而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两党武争”不存在,则中间道路亦不存在。这与“自由主义”道路不同,“自由主义道路”这个词,有其本身的意义,无需依靠“两党武争”的背景即可独立存在。
再一层,为什么当时有一般用“中间道路”而不用“自由主义道路”来称呼这一群体和潮流呢?实因当时这一群体与思潮的主流并非“自由主义”,而仅仅是无数独立意见的大杂烩。
自由主义者可以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这是由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决定的:自由主义不主张个人的牺牲,相信秩序和渐进的改良。在没有其他现实的道路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作为现实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在可选择的现实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会坚持某种“理想”走向一个虚幻的目标。在国共武争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者会考虑:哪一方自由更少?哪一方专制更多?而不会考虑:哪一方腐败更少?哪一方清廉更多?
围绕着《观察》的一批人,显然都不是在政治和历史方面无知的人。国民政府的历史渊源、合法性基础、宪法规定、战时临时措施,他们不可能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渊源、组织原则、辖区状况、宣传策略,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清楚,那么是什么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国民政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12年《临时约法》,其合法性基础倾向于英美政制,1947年《宪法》更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而《临时勘乱条例》只不过是战时措施。战时之言论管制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是合理与必要的。(美国海外战争因为不触动国家根本,故无言论管制)从这几点看,民国政府无论有多糟糕,都不应给予“毁灭性的批评”,所谓“毁灭性的批评”是指在战时进行颠覆性的鼓动,或者发表不利于战场形势的言论。反观共产党,其渊源于俄国革命,其组织原则为绝对集中,其合法性基础为阶级斗争,其辖区状况为消灭一切质疑声音,其宣传策略为充分利用民国言论自由之空间。在这样一个对比下,围绕着《观察》的一批人,站在“独立”的立场上,走第三条道路,不能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这条路没有任何可以自我支撑的基础,只要两党最后只剩一党(国民政府允许独立政党存在),他们就会立刻消散。国民政府胜,则他们还可以继续发言或不发言,共产党胜,则他们欲不发言而不可得。
一般来讲,围绕着《观察》的一批人,还有和他们的立场相近者,既然无法左右政局,所以也不能要求他们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负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自身的理想主义情绪和非自由主义的立场,从而成为局势向有利于共产主义方向变化的参与者。如李闻血案后,大批知识分子由义愤驱使同情共产党;如政协会议上站在超然立场,这一行为在两种政制原则上超然而立,其实在客观上给共产党以巨大支持。这显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的1945年到1949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分裂这一说法,在事实上恐怕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分裂。那么以什么名字来统称围绕着《观察》的这一批人呢?我觉得不必一定给予某种主义式的统称,他们本来不在某种主义下集合,他们只是一些勇于担当责任的知识分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