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学的角度上看,荒诞是一种现代审美品格,它的实质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荒谬性的一种审美感受。当这种荒诞性被引入到戏剧当中时,戏剧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没有精确对立的人物刻画、清晰完整的主题、严密理性的逻辑,荒诞派戏剧以非理性的反戏剧形式表现荒诞,从而达到了荒诞的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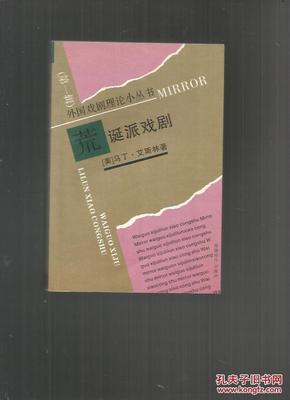
由于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成为了“物”的奴隶,人与人之间变得生疏冷漠,再也没有田园牧歌般的温情脉脉,于是人们的内心普遍地滋生独孤、焦虑、痛苦与失落,从而以无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来对抗传统与秩序,荒诞便由此而生。之后表现主义、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都在表现自身主题与创作特征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荒诞性的运用,经过一系列的继承与变异,各种荒诞因素集合为一个整体,即以荒诞为名的荒诞派戏剧。
一、表现主义与荒诞派的荒诞性
表现主义文学兴起于19世界末20世纪初,他们厌恶大城市的机械化生产生活,对于所谓的城市文明持排斥的态度,同时他们也反对模仿自然,强调只有表现自我内心直觉感受、情感世界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在对传统反叛的过程中,表现主义写出了人的个性的压抑,以及压抑的个性导致的一系列荒诞的行为;在揭示城市文明的罪恶的过程中,表现主义表现了人的异化,以及异化后的人的荒诞和异化本身的荒诞性。表现主义者反叛西方传统的“模仿”与“再现”,突出作家的幻想和创造力,往往荒诞便隐匿于其之中。
在卡夫卡的《审判》中,主要人物是K;在《群众与人》中,主要人物是“一个女人”;在《到大马士革去》中,里面的人物都没有姓名。这些都被荒诞派戏剧很好地继承下来,在戏剧《椅子》中,就只有老夫妇和客人们,前后并没有对任何人的背景和性格特征进行交待,而不像其他作品一样,花浓重的笔墨去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人物的矛盾和冲突。只不过表现主义旨在把人物形象化、抽象化,目的在于揭示一类人的本质,而荒诞派旨在淡化人物形象对于剧情的作用,从而突出社会的荒谬、人生的悲哀以及整体的荒诞感。尽管表现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已从形式和手法上,很好地诠释了——荒诞。
从内容上看,表现主义在对传统的反叛,在对自我的表达的过程中,其实也在无意识地走向荒诞的异端。比如卡夫卡的《城堡》,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就近在眼前,可是无论K怎么努力,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进入城堡里面,他在村子里行走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无法走进城堡,不知道城堡的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在读者的眼里,城堡可以象征着很多种事物,可以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解读方式,但是所谓的“城堡”已经变成了失声的谜底,走向了神秘,走向了荒诞……又如《变形记》里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异化成为了一只甲虫,从喜欢正常的食物到喜欢腐烂之物,从拥有正常的习性到喜欢吊挂在天花板上,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只禁闭的甲虫,他所体验的是人与虫双面的痛苦,是人异化的荒诞。但这个看似荒诞的虫变,看似荒诞的异化,却是必然的,因为甲虫的孤独表达的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希望和绝望。再如人猿将自己的经历感受写成报告的形式交给科学院,饥饿的艺术家所表演的内容竟然是绝食,一切的一切都源于表现主义者内心世界必然导致的悖谬与怪诞,而这些都不只存在与作者的想象和幻觉之中,它本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表现与发展荒诞性的一个载体。
荒诞派戏剧同样也是表现了荒诞性这样一个主题,继承了荒诞的创作特点,但是在侧重点和发展上看,是与表现主义有所不同的,这就体现为荒诞派对荒诞性的变异以及发展这个方面,现就堪称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之作的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剧中只描写了六个人物,史密斯夫妇在客厅里闲聊,谈论的话题和周围的事物都毫无逻辑,女仆上场,告知马丁夫妇应邀来吃晚饭,走进来竟互补认识,在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和了解之后,才得知对方是自己相处多年的另一半。从故事情节发展至此,就可以明显的看出,荒诞派所表现的荒诞性确实要比表现主义来得直接、夸张与不可思议。后来消防队员莫名其妙地急促地按着门铃,被告知没有火要救,又喋喋不休地毫无边际地讲个几个毫无联系的故事,然后离去。联系两种流派来看,表现主义的荒诞是有故事发展的情节的,是理性的;荒诞派的荒诞是不需要情节的串联的,是感性的。之后,两对夫妇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对话,而且越来越不知所云,越来越荒谬,直至后来一切都变为一串串毫无意义的符号……突然,灯光熄灭,马丁夫妇如戏剧开场时史密斯夫妇一样坐着,说着一样的台词……这个结果好像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开始,里面所蕴含的讽刺和荒诞意味似乎是一个转折,对比表现主义来说。
总的来说,表现主义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荒诞性,荒诞派戏剧也很好地继承这一种不可思议的、发人深思的荒诞,并赋予其更浓厚的幽默滑稽成分,以让人在这荒诞中看到更深意味的讽刺。若提及两者不同的侧重点和变异之处,我认为,其一表现主义把荒诞作为表现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用来表现主题的其中一个途径;而荒诞派则是把荒诞当作主旨和本质,一切的方式都是为了这个中心服务。其二表现主义的荒诞是理性的,客观的影响要大于主观的作用;而荒诞派的荒诞是感性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要大于客观外在的因素。其三表现主义的荒诞是有逻辑的,在故事的铺陈中一切的荒诞都是必然的;而荒诞派的荒诞是没有逻辑的,荒诞与故事的铺陈没有联系,是偶然中的必然。
二、存在主义与荒诞派的荒诞性
存在主义文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对于50年代后出现的荒诞派戏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以萨特为主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一派,他们鲜明地提出了“世界荒诞,人生痛苦”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人所生存的周围世界是荒谬的、冷酷的,人只是荒诞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者而已;面对痛苦的人生、荒谬的世界,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可以从中看出“存在”与“荒诞”的关系,存在主义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对社会和人类存在的价值进行思考,对社会与人类存在的荒诞性进行拷问。
荒诞派戏剧创作的理论依据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以荒诞派戏剧必然继承了存在主义文学当中关于荒诞性的相关表现和表达。存在主义作品《恶心》以洛根丁在布维尔城定居的平庸生活,来反映主人公在平庸的视角里看到的现实的令人恶心的现实,以及无意义的荒诞的人生,而他试图避免与外界发生一点儿联系的想法也是荒诞的,理想的。荒诞派戏剧《椅子》通过写一对年过九旬的老夫妇邀请大批来宾,要向世人宣布他们发现的人生秘密,客人陆续到来,舞台上只有一个哑巴,在说着咿咿呀呀的无意义的音节,而老夫妇被不断增加的椅子挤到了两边,最终双双从窗口跳海自尽,从而反映了社会的荒诞,和人存在的悲哀。两者都是表现了人生的荒诞性。存在主义作品《西西弗神话》写了一个叫西西弗的人对诸神蔑视,而受到推石头到山顶的惩罚,每当巨石被推到山顶时,又落了下来,西西弗用尽全力到最后还是不能成功,其实西西弗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象征。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讲了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在等待一个叫做戈多的人,可是等来等去戈多也没有来,戈多到底是否存在,又亦或他象征了什么都指向了一点,戈多的存在就是荒诞的。从而又可以得证荒诞派戏剧中的荒诞感有一部分是继承于存在主义的。
但是这两者之间看似相近关系,细细研究起来,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首先,存在主义发现了人生状态的荒诞,试图运用理性来超越荒诞,从不放弃努力,恢复理性的权威。如《局外人》中的莫索尔,母亲的死,以及外部的一切事物好像都与他无关,他的行为存在着不可理解的荒谬性,但是其实他却是一个具有荒诞意识的正常人,具有荒诞式的清醒和坚定不移,他的意志不受别人的强加,甚至的神父和法律。然而荒诞派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处在荒诞中,无论如何,在劫难逃,所以荒诞派对于荒诞是接受的、无反抗的,把存在主义的一点理性的微光都覆盖了。如《动物园故事》中,杰利与彼得坐在长凳上攀谈,杰利源源不断地说着,而且容不得彼得听不下去,慢慢一步步地把彼得挤下长凳,最后丢下一把短刀,让彼得维护自己的尊严,最后自己扑向刀尖,随即死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荒诞派并没有想要超越荒诞的意思,面对荒诞,他们认为是在劫难逃的,所以在连死都是荒诞的。
其次荒诞派戏剧是以反戏剧非理性的方式来表现荒诞的,从逻辑上看,是没有逻辑的,从语言表达上看,是语无伦次的,从舞台形象上看,是支离破碎的,这些都不像存在主义运用传统方式来表现荒诞,这也是其变异之处。比如,《莫洛伊》里,一切都给你很朦胧、很扑朔迷离的感觉,故事的前后没有一点儿连续性,就连人物的名称也不同,让读者很是摸不着头脑。一个受环境所控制的机能不健全的梦游者,一个恐惧症患者,没有客观的真实图像和逻辑秩序,语言和心里语言都只是只言片语,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符号化。内容和形式上的荒诞化使得荒诞派戏剧少了存在主义的理性思想,但却把荒诞深入到骨髓里去了。
荒诞的意义就是意义丧失的感觉。人拼命寻找幸福的生活,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毁灭幸福,永远在劫难逃,这就是荒诞。荒诞的历史的长河之中有着它的继承、变异与发展,在其背后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