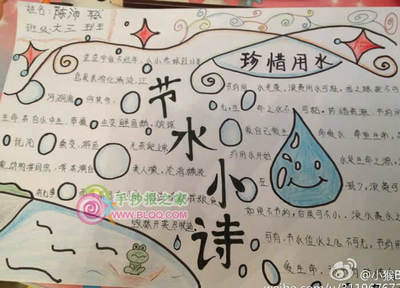田小娥---旧时代悲剧的牺牲品(本文发表于2013年5月初的文化艺术报,并在2013年12月获“文化艺术报”征文大赛优秀奖。)
田小娥是上个世纪初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子,她出身于书香门弟,具有八百里秦川古朴民风的很多优点,比如善良,比如能吃苦,甚至还有些妥协和软弱。假如她能和白鹿原上千千万万个农家女子一样,嫁给邻村的一户老实的庄户人家,应该也会凡俗而平静地聊过一生。
可田小娥的美貌和懵懂的追求自我的本能反抗导致了她最终被那个落后的旧时代摧残、所毁灭。在那个封闭、固陋而宗法统治异常强大的社会里,田小娥注定是一个悲凉的渺小的牺牲品。
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像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女子一样必须得逆来顺受地屈从于传统礼教,屈从于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安排。
于是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年过花甲的郭举人做小。在郭举人家里,田小娥其实就是一个女佣勤杂的角色,给主人夫妇倒尿盆、做家务、给长工做饭。在那个封建专制森严的家庭里,她也没受到过爱情的滋润,没享受到人伦的快乐,偶尔也只能做郭举人这个糟糠老头的性奴隶。更而令她感到难以言语的屈辱是几乎每晚都要在寂寞空房中用自己青春女性身体最隐私的地方为老迈的郭举人“泡枣”。
中国传统中男人有很多莫名其妙而荒诞不经的养生法,就像荒唐的“夜御十女而不泄”可固精、长寿、轻身、消百病一样,据说把枣放到女人湿润的身体里浸泡一夜再食用,可采阴补阳,延年益寿。
女人的身体被男人当做奇技淫乐的工具,在今天看来,这不仅毫无道理,愚昧可恶,暴露了男权社会里某些男人的淫秽狭暗的变态心理,更是对女人身心与人格的一种极大的羞辱和作践。
可是,小女子田小娥却不敢或者没有能力反抗这种强加给她的屈辱,她只能用近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暗自消极对抗---等没人的时候悄悄把含在身体里的枣拿出来扔进骚烘烘的尿盆里诅咒一番。
在那个黑暗的旧时代里,这是一个压抑、孤苦而可怜的女人。
直到偶然间遇到了长工黑娃,电光火石般的男女交合激情改变了她一潭死水般的日子,但也把她彻底推向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黑娃年轻强壮的男性力量不仅唤醒了田小娥潜意识里对性本能的渴望,让她感受到了作为女人生理上最原始的快活,使她本来逐渐麻木而濒死一般的日子显现出了一丝鲜活气息。于是,她义无反顾地抛却了传统的伦常道义和所谓的妇德,飞蛾扑火般地扑向了黑娃贫穷而并不踏实的怀抱,她自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不幸的是这个黑娃也仅仅只是挣扎在社会最下层的贫苦阶层一分子,他除了能给田小娥带来身体上新鲜的快乐刺激之外,并不能改变这个小女子的生存状态。相反,由于他们这种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对旧礼教秩序的背叛和反抗行为,田小娥被赶出了富户郭举人家的大门,灰溜溜地回到了娘家。
这很是让她的父亲田秀才脸面无光,气得病倒,只求“尽快尽早地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锹铲除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不惜倒贴钱把自己的女儿让黑娃领走,全然不管不顾亲生女儿今后的命运。男权社会虚伪、无情的面目暴露无遗。
当黑娃惴惴不安地把田小娥领回自己在白鹿原的家里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无情的拒绝和痛击。左邻右舍的指指戳戳让黑娃父亲鹿三不惜以断绝父子情份要挟要赶走田小娥,而族长白嘉轩更是黑着脸断然拒绝他们进入宗族祠堂完婚。
这两个可怜的年轻人顿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连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无奈之下,只能栖身于村外的一孔废弃破败的窑洞里,凄惶度日。
如果说黑娃和田小娥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厮守着活下去,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庆幸的状态,日子虽然清苦了些,但是凭着黑娃给人扛长工下苦力也能凑合着过活。用田小娥的话来说就是“黑娃哥啊,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
可现实却给了这两个追求最简单的自由和朴素爱情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
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动荡让不甘心的黑娃似乎看到了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他受鹿兆鹏等人的鼓动在白鹿原闹起了农会,斗地主、砸祠堂,也算是轰轰烈烈了一回,连田小娥一度也参加了妇女协会,风光了一阵子。
可惜好景不长,国共合作破裂,恶霸和地主反攻倒算,疯狂残杀农会积极分子,黑娃和鹿兆鹏等人只能仓惶外出逃命,被扔下的田小娥又一次陷入了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近乎绝望的悲惨境地。
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毫无生存保障的混乱环境下,在那种兵匪盗贼四起的动荡社会最下层,孤独无助,怎么活?何况,田小娥本来就是一个被周遭的人们白眼的、被那个社会族群所不齿、所唾弃的一个所谓的伤风败俗的坏女人。
田小娥根本无法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欺凌的命运。
她的美貌让道貌岸然的乡约鹿子霖垂涎三尺,先是利用她的无助和乞求生存的本能骗奸了她,后来又威逼利诱使田小娥成为他和老族长白嘉轩明争暗斗的工具,引诱了白的儿子白孝文,拉其下水,毁其名利。
至此,原本那个单纯而美丽的小女子田小娥破罐子破摔,彻底沦为了一个为了活着而不顾脸面、不顾廉耻的女人,被白鹿原的人视为瘟疫一般的“那个窑里的烂货”。
说起来,田小娥除了和黑娃过了几天快活的穷日子以外,后来和白孝文那一段短暂的孽缘倒也让她完全放下了心理的重负,感受到了几分作为女人本能的沦落的快感。白孝文“早晚都泡在小娥的窑洞里,两人吃饱了抽大烟过瘾了就在炕上玩开心”。
这种不计后果、醉生梦死般的日子加快了她悲剧命运的结束。当白孝文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弃她而去时,可怜的田小娥这一次是彻底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
黑娃的父亲,老实巴交而又犟牛一般认死理的鹿三,把儿子不知死活的亡命异乡和东家长子白孝文的堕落统统归咎为“那个窑里的烂货”,抱着为民除害的心理,残忍地刺死了肚子里还怀着白孝文孩子的田小娥。
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就这样在悲惨、屈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的除了坍塌的破败窑洞的腐臭尸骨以外,只有白鹿原上人们对她“荡妇、烂货”的骂名和诅咒。
田小娥是烂货吗?是荡妇吗?
这只是一个善良、柔弱、而不幸的弱女子,在她短暂而坎坷的生命中,她几乎没有过正常女人该有的平静生活,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幸福,她一直生活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以及无穷尽的担惊受怕中。
她毁灭在了一个愚昧而无耻的男权社会形形色色的男人手里。
她的父亲田秀才把她嫁给郭举人本身就可能是一桩肮脏的交易,白白牺牲了女儿的处女之身。在郭举人那里她只是一个被蔑视的下等女佣和“泡枣”的工具,没人视她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黑娃是唯一一个给过她一丝可怜的温暖的男人,只可惜这个男人力量太弱小,不仅不能给田小娥哪怕是吃糠咽菜的最基本生活,反倒在客观上更快地把她推向了孤独无助的绝境,直接导致了田小娥被迫成了阴鸷的鹿子霖的泄欲工具和家族争斗的牺牲品。
而白孝文也是因为性的诱惑乱了心智,挥霍家产、醉生梦死的一段日子成了田小娥被杀的导火索。老实厚道而愚昧的鹿三以为民除害的愤怒心理杀死了田小娥,更是给田小娥的命运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宿命与悲剧色彩。
把一个本来单纯美丽的女人变成荡妇的是黑暗的男权社会和封建宗法制度;杀死田小娥的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固陋虚伪的男权社会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们。
在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制度和愚昧秩序的社会惯性笼罩下,除了懦弱地忍受或者因绝望而自甘毁灭之外,任何的反抗与对爱情的追求都是羸弱的、全民共诛的、自取毁灭的。
劝君莫为女儿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田小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那个典型的旧时代男权社会里,生为女人就是不幸的,美丽而不甘心的女人更是不幸的,田小娥的命运与死亡是一种必然。
母系氏族社会以后,这个世界始终是个男权意识主宰的世界,只是男权的控制程度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演化表现得不同而已。千百年以来,女性的解放首先是性的觉悟与反抗,而男权主义因为传统惯性思维恐惧女人的性觉悟,视性觉悟的女人为淫荡、无耻,这是赤裸裸的精神暗示与控制。
田小娥最开始遇见黑娃就是本能的性的感受得到了激活,从而萌发了追求个性自由与爱情的愿望。不幸的是这一切都被沉重而巨大的所谓社会伦理和道德所淹没、所吞噬了。
这个世界对于女人来说,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她的命运只能是被动的、不堪风雨的,她必须依附于某一个男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某一个男人身上。而事实上,这些男人其实一个也靠不住。
对于可怜的田小娥来说,她的父亲田秀才靠不住,郭举人靠不住,鹿子霖靠不住,白孝文靠不住,就是那个黑娃也靠不住……在关乎她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男人只会因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抛弃她、牺牲她。
卑微的小女子田小娥为了活命,只能扔掉女人的人格与尊严,被动或者主动地用自己赤裸裸的肉体周旋、委身于一个个的男人之间,用让自己身败名裂的“荡妇、烂货”的骂名给自己换来苟延残喘活下去的物质基础。
这个美丽而令人怜惜的女子本来不应该有着如此凄苦悲凉的命运的。想到她在短暂的人世间所遭受的那些罪孽,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在田小娥用自己青春的身体给郭举人“泡枣”的时候,谁看见了她眼里含着的屈辱泪水?
在田小娥赤裸着身体给鹿子霖丑陋的嘴脸报复性撒尿的时候,谁看见了她内心玉石俱焚般对自己荒唐行为的痛悔与羞耻?
在暗夜旷野破败的窑洞里,谁又看见了这个苦命的弱女子面对四周强大的危压和欺凌下美丽、惊恐而绝望的眼神?
除非,田小娥选择了以死亡来逃避这人世间无穷尽的苦难---但她也是惧怕死亡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相信,在被鹿三以锋利、冰冷的铁矛刺穿胸膛的时候,美丽的田小娥凄婉的长长的喊出的那一声“啊……大啊……”应该是对终于能离开这个丑恶而苦难世界的一种解脱般的哀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