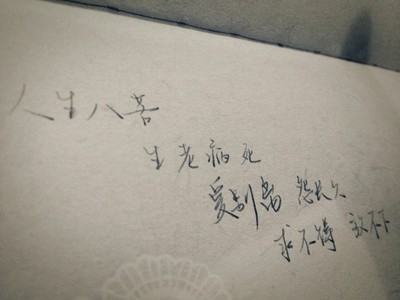老百姓更愿意把包拯供为心中的神。家乡的人们自发捐献,正在改建包公祠,配享太昊伏羲氏陵前左侧。包公是老百姓心目中崇高的清官形象。政治清明时,人们怀念他;世道衰败时,老百姓更加怀念他。自宋至今,世事变幻不定,人们对于包公的怀念却是永远的。
北宋庆历年间,陈州(今淮阳)大灾,春蚕遭害,二麦不熟,饿殍遍野,而刘衙内的子婿等贪官污吏趁机搜刮民财,鱼肉乡里。包公为救灾民,惩治贪官,于京城汴京(今开封)下陈州。刘衙内严密封锁陈州城门,不让包公进城。包公碰巧就替妓女林氏赶驴,扮王八,冒充妓女老鸨混进陈州城。包公时年45岁,因此直到现在,陈州人还忌讳45岁,凡是45岁的人都称到了“骂年”的年龄,或者说成46岁和44岁。包公进了陈州城,查清了刘衙内子婿的罪恶,在金龙桥铡了他们。后来,金龙桥旁生长的结巴草根都是红的,老百姓说那是贪官污吏的血染的。包公开仓放粮,把他们在米中掺的砂子筛出,光筛出的砂子堆积几丈高,现在城东有个大土堆叫平粮台,当地人说就是包公从米中筛出的砂子堆积的,包公下陈州放粮,救了数万生灵,陈州人在放粮处建了“包公祠”,以纪念这位不畏权贵、清正廉明的“包青天”。处理完这起案件后,包公在陈州按法粜米,解救饥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整顿吏治,使社会复趋于安定。
包公特别孝顺,信守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直到36虽才出山。流传里,他拒收端州名砚、反对覃恩、三弹张尧左、参倒张方平、抨击宋祁、七斗王逵,重惩贿赂,执法如山,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被百姓称为“包青天”。

历史上的包拯担任过监察御史,对贪官污吏的行径多有揭露,与他后来的公众形象颇有联系。但终其一生,多数时间他只是担任地县州一级的地方官。50岁左右终于被提拔进京,不过,在京城期间,也多是以任闲职为主,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学士”两个职务,就是典型的赐给文人的可有可无的虚职。
包公从元杂剧时代开始逐渐被偶像化,成为“清官”的符号。流传甚广、颇具代表性的还有《铡美案》和《赤桑镇》。包公审理这些案件时的困难不在于案情扑朔迷离或是非难断。
《铡美案》里,我们对传统社会中法律的限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普通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是有限度的,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微妙但却有着十分关键的区别。《铡美案》最终能让观众十分满意,是包公最终让百姓看到了“公道”。其实,包公能够给秦香莲的是“公道”而不是“幸福”。论私情,“幸福”当然远比“公道”重要,但是论国法,“公道”的意义就远非“幸福”能比了。只有把“公道”看得更重要,把国法看得更重要,秦香莲才有活路——“铡美”并不能保证秦香莲似的怨妇过上幸福生活,她们还能在世上忍受,缘于起码的公道。如果能有公道,法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工具,不如说是普通百姓的护身符。
将国法置于私情之上,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国法比私情更重要,公道比幸福更重要。对他人是如此,对包公自己也是如此。《赤桑镇》,让国法和私情的冲突及于包公自己,进一步拷问这位“清官”的良心。包公之为“清官”,铜铡就不能仅用于铡别人家的脑袋。《赤桑镇》里欺凌百姓、贪赃枉法的罪犯是他的侄儿包勉,而且包公和这位侄儿的关系很不一般。在重亲情讲恩义的传统社会语境里,《赤桑镇》里的情感冲突更尖锐。铡陈世美时,包公的担当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足够的道德支撑和力量。要对亲侄儿包勉行刑时,他虽坚毅而刚强,却也许会意识到看起来天经地义的清正廉明,一定伤害了同样重要且不可逾越的人伦亲情与恩义。
亲情与恩义是维系人类社会的根本,一点都不比国法和公正轻。因此,为国法不徇私情的包公要努力修补亲情与恩义遭受的损伤,对他嫂子唱出“劝嫂娘休流泪你免悲伤,养老送终弟承担,百年之后,弟就是你戴孝的儿郎”时,我们深切体会到他的歉疚之心。正由于国法和私情都拥有合理性与正面价值,冲突与抉择才意味着必须做出巨大牺牲。而因为亲情和恩义更贴近人的根本,更难以割舍,且更无处不在,因而与权势相比,会更容易更经常地成为公正的障碍。所以,考验包龙图不仅需要《铡美案》,还需要《赤桑镇》。
我以为,改建包公祠,道理不简单,凝聚着普通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理解和渴盼。包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既是民众对于清官的期待,同时又表现出中国百姓在政治与司法领域足够清醒的意识。包公遭遇的困境就是追求与维护司法乃至于社会公正所需要解答的难题。从《陈州放粮》《铡美案》直到《赤桑镇》,中国民众加之于包公身上的重重考验,就是对司法乃至于社会走向公正之道的导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