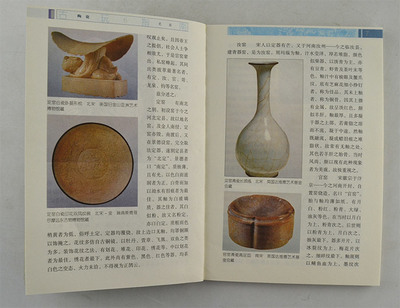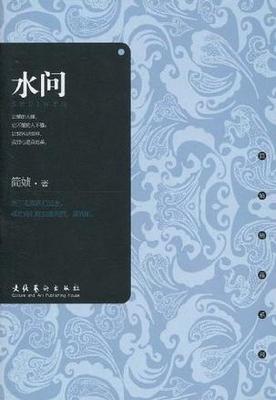《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品,人道主义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在作品中,雨果通过对法国十九世纪前半叶社会现实的描写,控诉了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黑暗社会,对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给予深切同情,谴责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残酷,对共和党人的英勇斗争精神赋予崇高礼赞,塑造了冉阿让这一由恶到善的光辉形象。这些都体现了雨果浩博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基于童年经验中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成人后对社会不公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和憧憬而产生。但他反对暴力,用仁慈、博爱作为改造社会的良方,主张以爱制恶,用道德感化教育来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也体现了雨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悲惨世界》自诞生以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的精神飨宴。在经历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无穷读者手捧此书仍心潮澎湃。这不是雨果这位伟人头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领袖和旗手的光晕因而人们对他顶礼膜拜,也不是因作品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具有史诗风格令人倾倒,而是作品宣扬了作者一生高蹈的人道主义思想震撼着亿万读者的心灵。小说以高超的构思,娴熟的技巧,诗化的语言和博大的思想,成为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小说分五部分:《芳汀》、《珂赛特》、《马吕斯》、《卜吕街的儿女情和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及《冉阿让》,塑造了人道主义理想式的人物米里哀和冉阿让两个人物形象,并描绘了法国从拿破伦帝政时期开始,经过滑铁卢战役、波旁王朝复辟、百日政变、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七月王朝、1832年巴黎起义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主人公冉阿让出身贫苦家庭,因为失业,为了养活几个外甥,为生活所迫,饥饿中在面包铺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五年苦役,四次逃跑不成,反被加刑至十九年。他成了苦役犯后,这个罪名永远依附在身上,再也无法解脱,终身在警察追捕中颠沛流离。获释后,冉阿让又偷窃主教银器,结果被主教感化,于是化名为马德兰,在另一个城市经营工业,同情穷人,做了不少改良社会的好事,最后被选为市长。不久,冉阿让被沙威认出,无奈之下,被迫向法院自首,再次入狱。机智的他从狱中逃出,履行自己的诺言,重金赎出芳汀的女儿珂赛特,隐居巴黎。珂赛特长大后,与青年革命党人马吕斯相爱。冉阿让为了促成她们的婚事,冒着生命危险去找马吕斯,却和仇人沙威狭路相逢,他以德报怨,放走了沙威,使沙威良心发现,投塞纳河自杀。巴黎起义失败后,冉阿让将重伤的马吕斯救出,在成全了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婚事后,溘然长逝。
通过冉氏的生活经历,法国整整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坟场,郊区寒怆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惨厉绝伦的滑铁卢战场,战火纷飞的街垒,藏污纳垢的下水道。这是一幅辉煌的画卷,雨果在这一幅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宏伟画卷中,描述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并给予他们深切同情,控诉了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黑暗社会,谴责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残酷,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对共和党人的英勇斗争热情歌颂,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想
《悲惨世界》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故事内容的展开和主题思想的表现上,都体现了雨果浩博的人道主义情怀。
首先,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世界”,暴露了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强烈的控诉。在作品中“男人12岁就落入感化院,18岁去坐牢,40岁被送上断头台”。之所以出现这样悲惨的现象,并非这些人天生就是恶魔,而是当时的黑暗社会造就了这些可悲的人民。处在一个黑暗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无吃无穿,没有住所,更没有人权和利益。他们饥寒交迫,为了生计,愿意做常人不能做的事,但微薄的酬劳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男人不得不去偷、去抢、去骗,女人不得不卖身为奴为婢,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这一切都只为一个简单明确而又最基本的目的———赖以生存的一口饭。主人公冉阿让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在失业情况下,为养活姐姐的七个孩子,在饥寒交迫中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监禁,几次逃跑不成,反被加刑至十九年;芳汀,一个纯洁的少女,被纨绔子弟玩弄后遗弃,为了养活自己的私生女珂赛特,拼命工作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先卖掉自己一头美丽的金发,后再卖掉自己的牙齿,在出卖了健康和美丽后,仍无法维济的情况下,终于完全出卖自己的肉体,被绅士调戏反被判监刑,最后在贫病中死去;幼小的珂赛特过着猫狗不如的生活,5岁便成了德纳弟家的仆人,遭受非人的虐待。林林种种,这都是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是黑暗社会酿出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更可恶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忠实鹰犬沙威,这个国家机器的代表,却时时监视着这些悲苦人的举动,不允许他们做出丝毫对统治阶级不文明不礼貌的事。穷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在描述了“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的社会黑暗和丑陋后,雨果在小说中指出:“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些制造黑暗的人”。人道主义要求每个人都有权过上正常的、平等的人的生活。这与雨果的看法殊途同归。可见,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批判和无情揭露上。
其次,雨果的人道主义还体现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同情。小说描写的黑暗社会扼杀了生活中善良美好的事物,把无数穷苦的人们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生活的人物。冉阿让本是贫苦农民,在失业情况下,为养活几个外甥,砸碎面包铺橱窗偷了一块面包,被前后累罚十九年苦役。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但他是在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愿意劳动却无劳动机会的情况下,为关爱别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他认识到自己所受到的处罚不仅是不公,而且是不平等。他认为不仅社会有罪,上帝也有罪。芳汀,这位纯洁善良的母亲,少女时代被人始乱终弃,为养活自己的孩子,只得冒险把孩子托给路途中只见一次面的旅馆老板夫妇,去工厂做工。选中孩子养父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旅馆夫妇也有同龄女儿。因为她想,为人父母,将心比心,他们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女儿。哪料事与愿违,德纳弟夫妇不断借孩子需要之名,向其索钱,芳汀在工厂的酬劳根本无法让她单独养活孩子,社会对未婚母亲又极度鄙视,经过多方努力无果,无奈之下,只得卖掉自己的一头美丽金发和几颗牙齿,最后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来维持,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她辛勤劳作一生,奋斗一生,临终也未能见到自己的女儿,只得将女儿托附给冉阿让。雨果在小说中写道:“在社会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于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理呢?”表达了他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审视。冉阿让的前半生是可怜的,芳汀的一生是悲惨的,而雨果笔下的幼年的珂赛特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骇人听闻。她的衣服被典光后,只能穿德纳弟家小姑娘的旧裙和旧衫(倒不如说是破裙和破衫),只能吃德纳弟一家人吃剩的东西,吃得比狗好一些,比猫差一些,猫狗经常与她一同进餐,一同在桌子底下吃,碗具是和猫狗进食一样的木盆,极小时是德纳弟两个孩子受罪的替身,五岁未到就成了德纳弟家的仆人:办杂事,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搬运重东西。雨果力求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社会讲坛,他对德纳第夫妇对小珂赛特的虐待这样评论“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时,罪恶便从那儿滋生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透过雨果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悲惨境遇之后发出的评论,无不显现他对凶残社会的憎恨,对这些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第三,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悲惨世界》中,也表现为对虚伪残酷的资产阶级法律的谴责。法律是维护国家秩序的一种有力手段,但它的前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地位、利益、权利的一致和平等。而小说描绘的“悲惨世界”的法律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有产者对无产者专政的工具。剪枝工冉阿让本出身贫苦,失业后生存成了问题,法律没有保障他的权利,反而是他在饥饿中为养活七个外甥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监禁,在狱中由于心里挂念着待哺的几个孩子几次越狱,没有人性的法律却让他加刑至十九年。出狱后,他已老气横秋,苦役犯的身分使他无生存的空间,在走投无路时,是仁慈的米里哀主教收留了他,这位在监狱里心又冷又硬的仇恨社会的“恶人”,法律的惩罚教育并未让他走上正路,倒是米里哀主教的宽容仁慈之心感化了他,让他弃恶从善。在他身上,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法律的作用,远不如人类一颗慈善怜悯之心的召唤!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有用吗?芳汀被骗遭蹂躏后,本想靠自己拼命做工获取报酬来养活自己的女儿,可冷酷的社会却逼得她出卖了一个女人引以为豪的健康和美丽,即使这样,仍无法维持,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赖以生存和维济女儿,遭到绅士调戏,绅士逍遥法外,她这位受害者却被判六个月监禁。法律没有为她主持公道,而是维护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德纳弟夫妇索取了芳汀的钱后,并没有将钱用在珂赛特身上,善待她的女儿,贪婪反而使夫妇俩毫无节制地敲诈芳汀,变本加厉地虐待幼小的珂赛特,让他过着猫狗不如的生活,让这位私生女5岁不到就成了他家的仆人。法律默认和纵容德纳弟夫妇虐待凌辱儿童的行为,却无视芳汀和珂赛特的人权。我们从雨果上面几个例子的描写,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法律对广大劳动人民权益的漠视,连妇女儿童这些弱势人群的权益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它的实质是保护有产者的身分、地位和利益,上层阶级在这样的法律保护下可以为所欲为,下层人民即使是一句不文明的话,一个不礼貌的举动,都是对法律的亵渎。有着鹰隼一般的眼睛、猎犬一样的鼻子、作为法律化身的沙威,恪尽职守,逮捕的是因吐了一口唾沫有侮辱绅士罪名的芳汀,穷其一生追捕的是为生存因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的冉阿让,形象地阐释了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雨果正是通过这些贫苦人民的悲惨境遇的描写,来谴责资本主义法律的虚伪和残酷,在揭露其不合理性的同时,宣扬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第四,小说对共和党人英勇斗争精神的热情歌颂也是雨果人道主义的表现。人民为什么起义和革命?因为现实的不合理,不人道。雨果饱含激情地讴歌了1832年的人民起义,礼赞了街垒上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共和主义战士。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和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安佐拉是街垒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雨果用饱满的笔墨将他塑造成为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形象。马百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生命保卫了革命的红旗,作者用庄严的颂歌笔调写出来,对他发出了热情礼赞。伽弗洛什,这个巴黎街头的流浪儿童,在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乐天开朗、轻松幽默的性格。同时,他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醋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时,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通过这些全景式的描绘,雨果旨在告诉人们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手段,是实现人道主义的有效途径。在他心里,革命和起义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有人道的社会,革命是为了实现它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也是“为了实现未来所必须交纳的通行税”。那所谓的未来,就是雨果在作品中描绘出来的滨海小城蒙特猗市。在那里,没有饥荒,没有罪恶,没有不公的现象,没有严醋的法律,人人怀着一颗仁爱的心,人们安居乐业,如同我国诗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园”。这个“乌托邦”之地,是雨果不满龌龊现实,同情劳动人民,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而设计出来的,它寄托着雨果对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乐观期盼,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塑造了他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米里哀主教是他描绘的“悲惨世界”中让人感到温暖的一丝微弱的烛光,他是人类良知未泯的一片余辉。他有着优厚的待遇,却简衣陋食,把钱施舍给穷人和最需要的人,自己和妹妹、女佣仅靠着一点钱辛苦度日。他把申请到的乐城区的车马费和巡视费分文不剩地分给穷人,把病人接到主教府,自己却搬进医院的五六间狭小屋子。他对人宽容和气,充满智慧,言语风趣。他用道德人性为评判标准,敬仰上帝,关心爱护穷苦人,在冉阿让灵魂几乎掉进深渊时,他收留了冉阿让,并在冉阿让不顾收留之情,偷走他的银餐具被警察抓住时,用他的仁慈和博爱的宽大胸怀,为冉阿让开脱,使冉阿让从作恶之路走上了施惠之路。在他的身上,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冉阿让是在米里哀主教感化下弃恶从善的人。他是在米里哀主教收留他,把他当作“人”时,第一次听到主教大人称他为“您”时,第一次平等地与主教大人一同进餐时,心中的仇恨坚冰才开始融化。他在米里哀主教仁慈的关爱中,找回了失去的尊严和良知,才决心一生从善。在蒙特猗市成为市长后,他以米里哀主教为榜样,关心人民,爱护孤寡,竭尽所能帮助穷人:有暴露身分的危险也要用肩膀扛起压在车下的老人,不顾侮辱和被人怀疑命令沙威释放无助的芳汀,即使再次入狱也要救助被误认为“冉阿让”的商马第,不惜冒生命危险,跳车逃跑去寻找苦难中的珂赛特。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巷战中碰到混入革命营垒中被当作奸细抓起来的死敌沙威,他也以德报怨,放走了沙威,唤醒了这一机器似的冷血人物的良知,让沙威也感到冉阿让的许多举动都是令人尊敬的。雨果通过塑造的米里哀和冉阿让两个人物形象,以及米里哀感化冉阿让,冉阿让感化沙威的故事,旨在向人们昭示:人心本善,人类良心未泯,仁慈、善良、宽容、博爱是改良社会的有效药方,人道主义能惩恶扬善,善定能胜恶,只要人人守住心灵中最圣洁的那一抹爱的微光,世上便无恶,人类社会就会变得美好。
此外,雨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在《悲惨世界》中,精心设计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他用笔为武器,愤然直斥这个不人道的世界,把社会的罪恶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来破除社会的毒瘤,疗治社会的痼疾,从而修复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也试图以此来挽救人类沦丧的道德,重塑人类的良知和尊严,把人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完整建立。为达到高蹈人道主义的目的,他把各种矛盾、痼疾、斗争都归结为人类道德的善与恶的较量,他深信,只要“仁慈”、“博爱”的恩泽遍洒人间,人道主义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人类的前途就会是一片光明。米里哀主教是善的化身,是黑暗世界里的一抹亮光,正是他的存在和出现,雨果描绘的那个黑暗混乱的世界才不会沉沦得让人畏惧,才让人感到一丝温暖,才让人看到一丝人类前途的希望。他奉行的道德教义高于一切,接近于上帝。他用心中仁爱的明灯,给被社会当作垃圾扔掉的冉阿让指引了从善之路,使这个曾经浑身充满罪恶的人回到人间,接过他爱的圣杖,不图回报地帮助别人。冉阿让也在这位主教的感化下,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主动扬起仁爱、慈善的风帆,锲而不舍地用实际行动去援助他人,感化更多的人。他的义举,消除了芳汀的误会,解除了割风的仇恨,唤醒了沙威沉睡的人性,得到了珂赛特和马吕斯的谅解,在滨海蒙特猗市建立了伊甸的乐园。他的行为,否定了资本主义利己主义哲学,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这个曾经的“恶棍”,法律的教育没有剔除他的恶性,倒是米里哀主教的爱心唤起了他的良知。作品中的沙威是个冷酷的执法者,是法律的化身,是恶的代表。他为人正直,工作上特别敬业,但他却不能引起人们的敬重,原因在于他对统治者的愚忠。他一生恪尽职守,思想基石是对虚伪、残酷、甚至荒唐的资产阶级法律的信仰。他捍卫的是荒淫地游戏人间的无人性的上层统治者,监视追捕的是为了生存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具有美好人性的劳动人民。当冉阿让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放走他时,内心善良的人性复活了,自己长期坚守的法律信仰动摇了,认识到了自己身上长期以来被强加的精神桎梏,终于投河自尽。雨果正是通过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和冉阿让对沙威的感化成功来说明爱能胜恶,爱才能制恶,法律的惩罚只能让社会滋生更多的恶,法律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有用爱的感化教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
雨果是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幻想用人道主义来改造社会,通过人道主义来缓和阶级斗争和替代革命。他有一句人道主义思想的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雨果看来,“革命是为了恢复人的天性”,是为了唤起人们善良本性的回归。革命需要暴力,但暴力并非万能。革命的利益固然合理,也是正确的,但未必是人性的,革命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非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革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却往往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认为“革命是以为达到某种目标以非人道的手段对践踏和侵犯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做法显然是非人道的。所以,在作品中尽管他对人民革命进行了讴歌,但革命的结局却是失败,革命的暴力只是导致了人民更多地流血,而仁爱精神却能够征服最凶恶的敌人。这就是说,用革命暴力所未能达到的目的,可以、而且也应该用道德感化来完成。。在雨果看来,改造社会的道路,不应该是圣丹尼街的道路,而应该是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不使用暴力的、温和的、改良的道路——海滨蒙特猗的道路。出现在蒙特猗市的冉阿让,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好善乐施、恩泽广被的慈善家的形象。在他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萎靡的。他兴办工厂后,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失业和苦难都已经被消灭。在这一乡已经“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也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他用自己的钱慷慨地为医院增设了床位,建造了两座小学校,创设了贫儿院,又为年老和残废的工人们创办了救济基金。“他的工厂成了一个中心,在厂址附近,原有许多一贫如洗的人家,到后来,在那一带却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区域繁荣”。这正是作者心中理想社会的完整描述,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他以为,只要有一些像冉阿让这样的慈善家,能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肯于慷慨地向穷人施舍;只要建立起海滨蒙特猗市这样的世外桃源,劳动人民的苦难就能够解除,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就能够消灭。雨果正是通过米里哀改造了冉阿让,让冉阿让建立了理想的社会形态模式和对沙威被感化、革命失败结局的描写,来表达他反对暴力,主张“仁慈”“博爱”是改造社会的良方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这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鸿篇巨制里,雨果力求使自己作品成为社会讲坛,用高昂、激烈、热情的语言来证明他写这本书是因为“在文明鼎盛的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并表示“只要20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的这本书就是有用的”。小说原名“受苦的人们”,就清楚的说明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宣扬“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犹如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也预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它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启迪人们去探索生活的意义,懂得人生的价值———去做一个能为他人牺牲的人,去做道德高尚的人。尤其是那维护每个人的尊严而富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那善恶分明和爱憎分明的人道主义、那关注同情每一个人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源泉之一,这也是小说经历百载后仍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艺术高峰的真正所在,也正因于此,它被列入人们最喜欢的百部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在19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可与之媲美。罗曼•罗兰曾说雨果“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不仅指他的艺术成就,还指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高贵的人道主义思想。乔治•郭尼峨在分析雨果的思想时也曾经指出:“在雨果著作中寻找他的社会思想的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不断地、庄严地努力提出人民群众的贫困、失业、卖淫、被遗弃被剥削的童年、因不幸而加剧的罪恶等问题。甚至最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使刽子手们、审判官们、良心压迫者们、混帐法官们、酷刑吏们感到畏惧”。
出身贵族的雨果,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了如此撩人心弦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创作出具有如此魅力的巨著呢?从他的生平不难看出。雨果出生于1802年,1885年谢世。他一生生活的法国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在浪漫的时代里,雨果也不无浪漫的气质,他写了大量的浪漫主义的诗、戏剧和小说,但是,在浪漫的背后,雨果在一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人道主义的力量。雨果从小就是一个有“爱人之心”的人。在他记事的那年,他随母亲去了西班牙,回国的途中,他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发指的景象:一座座断头台,一个个马上要受绞刑的人,一个个十字架上钉着的人的肢体。残酷的肉刑,在幼年雨果的心中种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以后他对死刑怀有一种病态的反感。雨果真诚的希望能为废除死刑尽一份力量,他认为死刑与其说有用,不如说残酷。《一个死囚的末日》是他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明确提出废黜死型,主题是教育人要有怜悯之心。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极认真的查阅文献资料,去外地考察,了解到了一些苦役犯服役的情景。从1831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法国大革命,政权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王室的争权,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使雨果大为失望,因为他要求的是和平,而路易带来的是战争;他要求的是自由,而查理倾向于专制;他要求的是富裕,而金融者给人民的只是贫困;他要求的是光明,而七月王朝给他的只是阴谋;他要求的是平等,而所有的政权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因此通过体验各种生活,他开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开始到郊外去,到贫民窟去,亲眼看一看什么是贫困,并开始下决心把这些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于是有些题材,象不公正的判刑,囚徒的赎罪,贫困的景象等,以及一些素材如关于苦役犯监狱的,关于迪涅城主教卫奥利斯大人的,关于一个可怜的妓女衣领里被粗汉塞进雪团的故事等,开始在他手中积累。加上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以及在1848年大革命前后,雨果见到了足以多的贫困、灾难以及不自由的事实,不禁使雨果抱着对人类灾难的极大同情、抱着对人类的爱,发出了长长的叹息。苦役犯比埃尔•莫兰刑满释放后,家家客店都因为他的黄色通行证而闭门不纳。终于,现世的一幕幕,引发了他思想的翰海。伟大的雨果进入了对社会的深层思考。他在《悲惨世界》序言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有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由此,这部自1828年开始构思,1845年开始动笔的巨著,终于在1862年付梓了,创作过程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作品精心塑造了挣扎于黑暗年代、社会底层、悲惨世界里的各类人物形象,如在逃的苦役犯冉阿让,失业女工芳汀,孤女珂赛特,流浪儿伽弗洛什和老植物学家马百夫等,寄寓着作家对人民苦难生活和不幸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形象地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的强权统治、法律不公、贫富不均等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也正是在这些方面,表现了雨果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尤其在卞福如、冉阿让等人的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作为主教卞福如深深懂得他的职责是帮助穷人和病人,他认为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是来保护世人的灵魂的。他从不伤害一个人,甚至是损害了他的人,把人作为真正的人来看待。既然是人,就有人的尊严,他要维护这种尊严,而不是伤害它,并借此来拯救人的灵魂。他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人以后改名为马德兰,当了蒙特猗市的市长。作为蒙特猗市市长的冉阿让,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为尊重人权,为被社会凌辱、遗弃的穷人主持公道,争取他们做人应有的权利,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和道德之美。当他看到失业女工芳汀含冤被警长沙威拘捕并判罚时,执意将她释放,并向沙威指出,根据实情抓住诬陷芳汀的绅士才是公正的。当沙威提醒他,芳汀将唾沫吐在他脸上,是无视市长先生,是侮辱法律时,他向沙威严厉指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冉阿让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窘迫和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既感受到过穷人连猪狗都不如的冷酷,也感受到过灵魂被拯救时的温暖。此时,他既然有为被屈辱者争取权利的机会,有救人于危难之时的机会,当然就不能放过。雨果作品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正是由于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不公平的认识,对于受迫害者的尊严的维护,对于平等社会的美好理想和憧憬,这一切都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

然而,读完小说,细细咀嚼后我们看到,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是完美的,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小说在有力地批判和暴露的同时,指给人们的出路却是无力的、空想的。它让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让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让马里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翻然忏悔,向世人昭示: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的道德感化手段,任何人心都可以弃恶从善,任何社会罪恶都可随之消逝。这无疑给他的人道主义裹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他一再申明世间存在着以沙威为代表的低级法律和以米里哀为代表的高级法律,罪恶不能靠惩罚来解决,而应以“饶恕”和“仁爱”的感化教育方式去解决。这一切充分表明雨果希望用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解决阶级的矛盾,作为对付社会痼疾的武器。历史证明人道主义思想的“仁慈”、“博爱”事实上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反而会在社会斗争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反而容易成为人民精神的腐蚀剂,陷入幻想不能自拔。
第二,没能正确反映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上,也只能提出带有空想性质的改良主义主张。人道主义思想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他真诚而单纯地希望用它来使悲惨世界改变为幸福世界。在他看来,穷人只要安分守己,辛苦劳动,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富人只要一心向善,关心穷人,敌对矛盾就可以消失,社会罪恶即可随之消逝。他塑造的冉阿让以善举使得蒙特猗小城消灭了穷困和失业,变得欣欣向荣,友爱和谐,令人欣然向往。但是,这无疑带有主观唯心论的幻想色彩,是一种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起到真正效果的。
第三,他一向反对暴力,主张仁爱,但又肯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对起义进行了有如史诗般的歌颂,对起义者英勇献身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却给人民革命设计了一个失败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的现实面前的一种自我矛盾的表现。
尽管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完美无瑕,带有理想主义产物的味道,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蒙上了较多的宗教神学和唯心论哲学的灰尘,始终未能正确揭示他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本质,但正如西方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慈悲”,绝不失历史与现实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雨果这样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社会历史现实,关注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并尽力参与其中为之奋斗、呐喊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所以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斗士。正如高尔基所说:“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象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已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将永垂史册,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国内外读者的心中,给人带来黑暗中的光明和孤立无援时的慰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