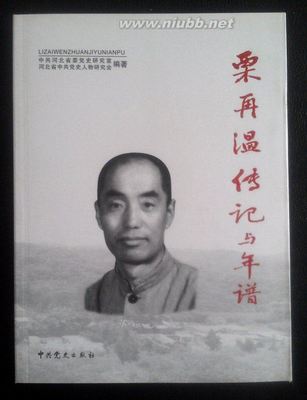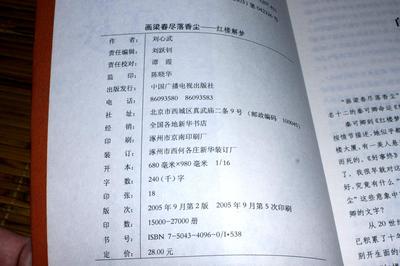一位沾亲带故的妙龄少女,飘然而至,来拜访我。我想起她的祖父,当年待我极好,却已去世八九年了,心中不禁泛起阵阵追思与惆怅。和她交谈中,我注意到她装扮十分时髦,发型是"男孩不哭"式,短而乱;上衫是"阿妹心情"式,紧而露脐;特别令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她脚上所穿的"姐妹贝贝"式松糕鞋。她来,是为了征集纪念祖父的文章,以便收进就要出版的,他祖父的一种文集里,作为附录。她的谈吐,倒颇得体。但跟她谈话时,总不能不望着她,就算不去推敲她的服装,她那涂着淡蓝眼影、灰晶唇膏的面容,也使我越来越感到别扭。事情谈得差不多了,她随便问到我的健康,我忍不住借题发挥说:"生理上没大问题,心理上问题多多。也许是我老了吧,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打扮,是为了俏,还是为了'酷'?总欣赏不来。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时尚。可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时尚裹挟着走呢?"少女听了我的批评,依然微笑着,客气地说:"时尚是风。无论迎风还是逆风,人总免不了在风中生活。"少女告辞而去,剩下我独自倚在沙发上出神。本想"三娘教子",没想到却成了"子教三娘"。
前些天,也是一位沾亲带故的妙龄少女,飘然而至,来拜访我。她的装束打扮,倒颇清纯。但她说起最近生发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想尝试性解放,乃至毒品,以便"丰富人生体验",跻身"新新人类",等等;我便竭诚地给她提出了几条忠告,包括要珍惜自己童贞、无论如何不能去"尝尝"哪怕是所谓最"轻微"的如大麻那样的毒品……都是我认定的在世为人的基本道德与行为底线。她后来给我来电话,说感谢我对她的爱护。
妙龄少女很多,即使同是城市白领型的,看来差异也很大。那看去清纯的,却正处在可能失纯的边缘。那望去扮"酷"的,倒心里透亮,不但并不需要我的忠告,反过来还给我以哲理启示。
几天后整理衣橱,忽然在最底下,发现了几条旧裤子。一条毛蓝布的裤子,是四十年前我最心爱的,那种蓝颜色与那种质地的裤子现在已经绝迹;它的裤腿中前部已经磨得灰白,腰围也绝对不能容下当下的我,可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遗弃它?它使我回想起羞涩的初恋,同时,它也见证着我生命在那一阶段里所沐浴过的世俗之风。一条还是八成新的军绿裤,腰围很肥,并不符合三十年前我那还很苗条的身材;我回想起,那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讨到手的;那时"国防绿"的军帽、军服、军裤乃至军用水壶,都强劲风行,我怎能置身于那审美潮流之外?还有两条喇叭口裤,是二十年前,在一种昂奋的心情里置备的;那时我已经三十八岁,却沉浸在"青年作家"的美谥里,记得还曾穿着裤口喇叭敞开度极为夸张的那一条,大摇大摆地去拜访过那位提携我的前辈,也就是,如今穿松糕鞋来我家,征集我对他的感念的,那位妙龄女郎的祖父;仔细回忆时,那前辈望着我的喇叭裤腿的眼神,凸现着诧异与不快,重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只是,当时他大概忍住了涌到嘴边的批评,没有就此吱声。
人在风中。风来不可抗拒,有时也毋庸抗拒。风有成因。风既起,风便有风的道理。有时也无所谓道理。风就是风,它来了,也就预示着它将去。凝固的东西就不是风。风总是多变的。风既看得见,也看不见。预报要来的风,可能总也没来。没预料到的风,却会突然降临。遥远的地球那边一只蝴蝶翅膀的微颤,可能在我们这里刮起一阵劲风。费很大力气扇起的风,却可能只有相当于蝴蝶翅膀一颤的效应。风是单纯的、轻飘的,却又是诡谲的、沉重的。人有时应该顺风而行,有时应该逆风而抗。像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兴趣爱好,在这些俗世生活的一般范畴里,顺风追风,不但无可责备,甚或还有助于提升生活情趣,对年轻的生命来说,更可能是多余精力的良性宣泄。有的风,属于刚升起的太阳;有的风,专与夕阳作伴。好风,给人生带来活力。恶风,给人生带来灾难。像我这样经风多多的人,对妙龄人提出些警惕恶风的忠告,是一种关爱,也算是一种责任吧。但不能有那样的盲目自信,即认定自己的眼光判断总是对的。有的风,其实无所谓好或恶,只不过是一阵风,让它吹过去就是了。于是又想起了我衣柜底层的喇叭口裤,我后来为什么再不穿它?接着又想起了那老前辈的眼光,以及他的终于并没有为喇叭裤吱声。无论前辈,还是妙龄青年,他们对风的态度,都有值得我一再深思体味的地方。

第 2 页
不止一次,村邻劝我砍掉书房外的柳树。四年前我到这温榆河附近的村庄里设置了书房,刚去时窗外一片杂草,刈草过程里,发现有一根筷子般粗、齐腰高、没什么枝叶的植物,帮忙的邻居说那是棵从柳絮发出来的柳树,以前只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行"的话,难道不靠扦插,真能从柳絮生出柳树吗?出于好奇,我把它留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它竟长得比人还高,而且蹿出的碧绿枝条上缀满二月春风剪出的嫩眉。那年春天我到镇上赶集,买回了一棵樱桃树苗,郑重地栽下,又查书,又向村友咨询,几乎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伺候它,到再过年开春,它迟迟不出叶,把我急煞,后来终于出叶,却又开不出花,阳光稍足,它就卷叶,更有病虫害发生,单是为它买药、喷药,就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直到去年,它才终于开了一串白花,后来结出了一颗樱桃,为此我还写了《只结一颗樱桃》的随笔,令它大出风头,今年它开花一片,结出的樱桃虽然小,倒也酸中带甜,分赠村友、带回城里全家品尝,又写了散文,它简直成了明星,到村中访我的客人必围绕观赏一番。但就在不经意之间,那株柳树到今年竟已高如"丈二和尚",伸手量它腰围,快到三拃,树冠很大又并不如伞,形态憨莽,更增村邻劝我伐掉的理由。
今天临窗重读安徒生童话《柳树下的梦》,音响里放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沉郁风格的弦乐四重奏,读毕望着那久被我视为赘物的柳树,樱桃等植物早已只剩枯枝,惟独它虽泛出黄色却眉目依旧,忽然感动得不行。安徒生的这篇童话讲的是两个丹麦农家的孩子,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常在老柳树下玩耍,但长大后,小伙子只是进城当了个修鞋匠人,姑娘却逐渐成为了一位歌剧明星,这既说不上社会不公,那姑娘也没有恶待昔日的玩伴。小伙子鼓足勇气向姑娘表白了久埋心底的爱情,姑娘含泪说"我将永远是你的一个好妹妹--你可以相信我。不过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办不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在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频繁地发生着吗?人们到处生活,人们总是不免被时间、机遇分为"成功者"与"平庸者"、"失败者",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天道?安徒生平静地叙述着,那小伙子最后在歌剧院门外,看到那成为大明星的女子被戴星章的绅士扶上华美的马车,于是他放弃了四处云游的打工生活,冒着严寒奔回家乡,路上他露宿在一棵令他想起童年岁月的大柳树,在那柳树下他梦见了所向往的东西,但也就冻死在了那柳树的臂弯里。我反复读着叶君健译出的这个句子:"这树像一个威严的老人,一个'柳树爸爸',它把它的困累了的儿子抱进怀里。" 自己写作多年,虽也有养樱桃的兴致,却总撇不下这老柳树的情怀。2003年我发表出的两个中篇小说《泼妇鸡丁》《站冰》,就全是此种意绪的产物。我想,尽管在多元的文学格局里,自己已经甘居边缘,但写作既是天赋我的权力,那就还要随心所欲地写下去。一位比我年长的同行在电话里对我说,写不出巨著无妨写小品,写不出轰动畅销的,写自得其乐的零碎文字也不错,记得那天晚报副刊上恰好刊出他一则散文诗,淡淡的情致,如积满蜡泪的残烛,令人分享到一缕东篱的菊香。这位兄长的话,更激励我超越狭隘功利。我目前精力还算充沛,短文之外,也还能写些篇幅较大的;以中篇小说为社会中的"未成功者"画像测心、引出对天道人性的长足思索,是我在2004 年仍要持续下去的写作旨趣。
我会更好地伺候窗外的樱桃明星,我不会伐去那自生的陋柳,手持安徒生的童话,构思着新的篇章,我目光更多地投向那株柳树,柳树的臂弯啊,这深秋的下午,你把我困累的心灵轻柔地抱住,而我又将把这一份支撑,传递给那些更需关爱的生命。
2003 年10 月29 日写11 月29 日改于温榆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