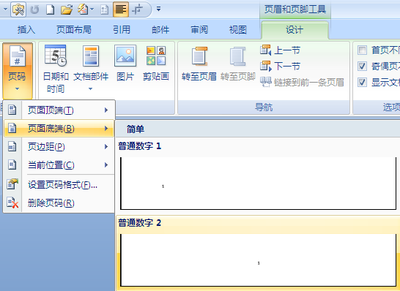1
去的是海滨城市。
两年前,他走过那个方向,但选的是另一个地方。那一次,出了点儿意外。他躲着那儿,并非心有余悸,而是她的话仍挂在耳边,风向不好,妈的。冒粗话,她眉宇间便透出一股豪气,仿佛被西风吹散的并蒂莲花粉。收拾东西时,他看见几天前在地摊上买的铜镜。他犹豫了一下,缓缓放进包里,没人窥视,但他却用身体挡住自己的动作。
车站广场乱哄哄的。他刚到那儿,后脑便被啄了一下。不轻不重,那是她特有的击打:五指并拢——她说那是凤凰的嘴巴。他突然回头,那个熟悉的身影闪了闪,消逝在人流中。他的目光迅速滑了一遭,然后慢慢移动。模糊的背影,陌生的面孔。逮她可不易。她喜欢藏在哪个角落,捉弄他取乐。有一次,火车要开了,她还没露面,他急了,支住车门,央求列车员再等一分钟,哪怕一分钟。他忘了他的腿是怎么进去的,似乎被谁猛拽了一把。他再次扑向车门,大叫,我要下去……忽然瞥见她的鬼脸。天晓得她几时溜上车的。进站。检票。上车。找到座位,他把包放在目光触及的位置。她飘过来,如一段浅浅的影子。却不坐,在车厢荡来荡去,假装看不见他,直到他站起来。她挤着他坐了,头靠在他肩上。他把头偏向一边,让她睡的舒服些。她有忽儿劲头十足,数夜不眠,忽而睡瘾大发,就像现在这样。怕惊醒她,他喝水都小心翼翼。对面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女人从他落座就盯着他,当然,也盯着身边的她。他看女人,女人马上移开,等他转到别处,女人又摆过来。如果她睁开眼,准会瞪得女人低下头,然后,她得意地冲他说,咋样?目光真会杀人呐。他没她那么冲,他甚至朝那女人笑笑。女人受了惊似的,有一瞬间,她目现惊恐,嘴巴发出一个低音。女人自己未必听得见,但他听见了。她在睡梦中,常常发出轻轻的却充满力度的低吼音。他收紧脸,目光冷冷地投向窗外。春天到了,树木已经泛青,偶尔能看到枝丫间黑黑的窝。乡间,燕子已开始筑巢了吧。
到站是下午。晴空万里,橘红色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流淌,顿觉神清气爽。她高兴得跳起来。他买了张地图,另一个推销地图的动作慢了点儿,有些失望。他又朝他买了一份。他和她头对头研究一会儿,她的鼻息小虫子一样挠着他的脸。他说,可以了,我们出发。出租车司机问他到哪儿,他说了一个地方。他和司机聊天,司机问旅游还是做生意。他说做生意也旅游,司机说一看你就是个会享受的人,挣钱图啥,图的就是个乐子。下车,他和她在那个区域转了一圈,目光不时碰在一起,会心地一笑。有时,她会冒粗话,妈的,就它了。
我都饿得抽筋了哎。她的声音泛着啤酒样的泡沫,她撒娇时就是这个样子。
她喜欢吃辣鸭头,但附近并没有这样的饭馆。他过了两道街,才看见一个重庆火锅店。他就说它吧,这地方人不喜欢吃鸭头。怕她不高兴,吃饭时他掏出那个铜镜晃了晃。她瞥一眼,不屑地说,我以为是什么稀罕玩艺呢。他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镜子,瞧背面。她的眼睛顿时亮了,她眼睛大,放彩时犹如爆开的玫瑰。拿过来,我瞧瞧。他把铜镜放在对面。图案不是很清晰,但能看出那是一对凤凰。她所有的收藏都与凤凰有关。扇子、手绢、画册、烟盒、花瓶。她反复端详,说给你个面子,这礼物我收下了。不,不,我先替你保存着,活儿还没干呢。他抢过来,放进包里。
登记房间,服务员问他是否要大床,他说要双床的,服务员瞧他一眼,又问,先生,是要双床的吗?他说是,然后回过头。他看不见她,她准是逛大厅一侧的商品店去了。她不但要逛,还要一一问遍商品价格,搞得服务员很烦。她劝过她,她说哪条法律规定不买就不可以问?看我不像买的,我偏要问,问晕她我兴许就出手。他再劝,她就瞪眼,你和她伙穿一条裤子咋的?行啊,什么时候搞上的?我是不是能吃喜糖了?他投降。
午夜时分,他和她溜出宾馆。城市的夜依然清得洗过一样,不过罩了层黑色的纱。他惊奇她在这方面出色的记忆力,走过一遍的路,她从不出错。当然,现在是他领着她走。他们从路边的栏杆钻进小区,只一扇窗户有灯光,其余黑乎乎的睡得正香。这个小区不是他们的目标,走到头,翻过墙,便是另一个世界。用她的话说,是标准的富窝。似乎从开始或在他遇见她以前,她的选择就很明确。帮那些家伙减减肥,她如是说。他转了转,在一处楼前停住。他早已关机,可还是掏出手机确认一下。两年前那次意外,是他的疏忽造成的,他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叫出声。他问,我先上,还是你先上?她说老规矩。永远的老规矩。他无条件地服从。他和她贴在墙上,如斑驳的在风中晃动的树影。一楼窗户关着,二楼三楼也没有得手的可能。或许这一排会踏空,这是常有的事。钓的就是万一,当然,危险也伏于万一的边缘。终于把四楼窗户弄开了。他和她先后挤进去。他和她不喜欢在外放哨,一同进入觉得更安全。他拧着笔电筒,小心翼翼地搜寻。客厅、厨房,可能存放钱物的角落。他不期望有什么意外收获——那段日子已经逝去,现在他更在乎的是仪式,和她一起的仪式——有枣就摘几颗,没枣也罢。不空手怎么办?豁达一半是因为无奈。电视机上放了二百元钱,还有一张纸条:家中无钱,不要乱翻。他咧嘴笑了。有意思的房主,肯定被人下过手,这也算豁达吧。但聪明处也难免失策,他马上断定房子没人。当然,他并没有麻痹,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门,一一查看了。如他所料。怎么样?他的口气不免有些得意。他打开灯,她跟在后面,看着室内的陈设。这家伙是干什么的?怎么连个照片也没有?他和她曾进入过没人住的房间,那时她就这样问过。在那个房间,他和她喝掉一瓶红酒,从容离开。她对主人不在场的宴请念念不忘,所以在卧室停停便返回。架子上不但有红酒,还有两瓶酒鬼。红的?白的?他问。她喝酒很猛,不等她答,他就说,喝红的吧,我们上次喝的就是红酒。他启开,给她和自己各倒一杯。然后,他关掉所有的灯,坐她对面。意外的收获,很久没和她这样对坐了。她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黑暗中,她的脸忽隐忽现,捉迷藏似的。他闭上眼,陷进逝去的光阴。
他:什么时候收手?
她:怕了?还是烦了?
他:不能永远这样。
她:我喜欢,我要逛遍天南海北,怕了你就走开,我没逼你,对了,你是半拉子大学生么,我才不想那么远呢。
他:我担心你。
她:别给我念败兴好不好?
他:那好,我们就此分手吧。
她:你敢?我的老底都告你了,你说走就走?
他:我不会的。
她:不行!你走哪儿我跟哪儿,我缠你一百年。
他:……
她:好了,我不过吓唬吓唬你,再干两年,咋样?攒够钱,咱们买个房子住下来,我可不是非要嫁给你啊,不过,你表现好,我可以给你生一堆孩子。
他扑哧一笑。
第二天,他和她睡了个大懒觉。他早醒了一会儿,躺在那儿,凝视着对面,直到服务员叫门。他忘了设置请勿打扰的灯示。上午,他和她打车到海滩,这一天,他是属于她的。痛痛快快疯一天,她的声音夸张着,已显出疯样。好吧,那就疯吧,他说。
还没到那儿,妻子的电话就追过来。
2
乔丁本打算先回店里放包,可收到妻子讯问的信息,马上改变主意,让司机拐弯儿。他为之前的决定汗颜。仿佛为了弥补什么,他催促司机快点。司机不知没听见,还是不把乔丁当回事,依然四平八稳。乔丁不由骂娘,当然骂的是连接不断的红灯和拥挤的车辆。离第一附属医院还有很远的距离,车就走不动了。医院与信访局一条街,相隔不远,要么这头堵,要么那头堵。一头堵整条街便塞得满满当当。乔丁扔下二十块钱,擦着行人和自行车急行。他一路说着对不起,身后还是丢过骂人的话。
妻子半歪在外科病房的椅子上,乔丁露面,她马上弹起来,比他步子更快地迎上来。怎么样?他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和她疲倦的脸一样瘦巴巴的。她说刚输完药,他睡了。妈在里面?她说妈熬了一夜,回去了。他轻轻推开病室的门。岳父躺在门口的床上,嘴角脸颊都旋着青色。乔丁有些恍惚,这张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突然有些陌生,再望,他的目光没有摇摆。不是岳父又能是谁?
妻子讲述,乔丁始终抓着她的手。她讲得有些零乱,可能是紧张兼困乏的缘故,但乔丁听清了。岳父挨了打,打的倒没多重,可他跌倒了,脑袋磕在地上,没什么大问题,但头疼得厉害。他安慰妻子几句,问报警没有。妻子忽然醒悟似的,哎呀,我一着急就忘了,现在不晚吧?乔丁说余下的事交给我,你回去休息。妻子不走,被他逼回去。
妻子和岳父都是谨小慎微,打喷嚏也生怕惊了别人的人,可谓父女相传,但妻子喜欢静——这一点又随了岳母,岳父爱动。不是动粗动武,四处游逛,而是找乐子。从文化馆提前离岗后,岳父每天背着手风琴到公园义务为唱歌的男男女女伴奏,当然多是一些退休没事干的人。风雨无阻。无人唱的时候,岳父就在亭子里自娱自乐。乔丁的店距公园不远,他常坐在门口听岳父的琴声。打岳父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乔丁猜出大概。类似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没想怕事的岳父居然成了主角。岳父面皮白净,高高大大,招人喜欢也很正常,但乔丁怀疑岳父未必有胆子。能干出什么?暗送点秋天的菠菜而已。怎么会忘记报警?妻子昏头昏脑,没想到是正常的,但岳母不会。岳母文静,却是家里主心骨,遇事极少慌乱。乔丁想岳母必有别的想法。不管咋样,不能白白挨打。乔丁不爱寻事,但绝不惧怕。岳父挨打,乔丁正好替岳父或替这个家做些什么。是的,该做些什么了。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一直潜伏着某种欲望。
乔丁再次进去,岳父已经醒来,眼里掩饰不住的羞涩和委屈,他躲闪着乔丁,大约拿不准把羞涩藏起来还是把委屈藏起来。乔丁叫几声爸,岳父的目光方犹犹豫豫地和乔丁对接。好些了吗?乔丁轻声问。岳父不大自然地说好多了。乔丁掖掖被子——其实没必要,病房并不冷——乘势靠在床边,又问岳父喝水不,想吃点儿什么。岳父摇摇头,指指桌上的水果。乔丁说,我吓坏了,你没事就好,躺几天,正好睡几天懒觉,像你上次让马蜂咬了那样。乔丁竭力说得轻描淡写,岳父的羞涩一点点儿褪去。
那人叫啥?乔丁刚刚想起似的。
岳父看乔丁几分钟,像不明白乔丁指什么,目光渐渐暗下去,说我不认识他。
乔丁问,以前没见过他?
岳父说,没。
乔丁瞄一眼邻床——是个孩子,正玩手机,——小心而又随意地说,那个女人……我是说,找到她就能找到那男人。
岳父声音哑然,我认识她,但不知道她叫什么。好多人我都叫不上名字,我只记得她们的嗓音,会唱什么歌。
乔丁说,你放心,我会查出来,肯定有不少人在场。不能这么放过他,打了人,面儿也不露。不由愤然了。
岳父忽然哎呀一声,头又疼了。
乔丁说,我去喊医生吧?
岳父摆摆手,没用的,过几分钟就好了。
岳父似乎害怕乔丁替他讨公道。乔丁犯了嘀咕,难道岳父真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但握着把柄也不能随便打人,乔丁想让岳父明白这点,可岳父已不给他说话机会。直到岳母进来,岳父的头疼才止住。
岳母既没有妻子天塌下来的无措,也没有岳父那躲闪的羞怯,更无对丈夫的愤怒和怀疑,只是平静中多了些凝重。她责备女儿吴欢,我不让她给你打电话,她不听,事办完了吗?乔丁说办完了。岳母让乔丁回去,这儿有她就够了。乔丁要留下来,岳母看他一眼,那个也要照顾呀,还有果果。很简单的一句话,乔丁再没有反对的理由。他和她深知那句话的含义。岳母很清楚该说什么。或者说岳母很清楚说什么他会听。
在这个家庭中,乔丁显然是和岳母,而不是和妻子的对话在一个层次上。一点就透并非心里明白,而是明白对方的心理。不错,乔丁挺担心妻子的,但乔丁没有离开,他有别的话要和岳母说。他站在那儿,看着岳母利落地削一只苹果,切成薄片,递到岳父嘴里。岳父似乎要说什么,但岳母制止了他。岳母看上去比岳父年轻许多,可能和她的职业有关吧——舞蹈教练。身材也没有她这个年龄女人的臃肿。如果说他们是父女,肯定有人相信,但岳母完全是一个妻子的神色,内敛或是关切,看似淡薄,却柔韧无比。乔丁突然有些感动,情不自禁地叫声妈。
可能是声音大,岳父和岳母吓着似的看着乔丁。乔丁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小声叫声妈。
岳父依然看着乔丁,似乎等他的后话,岳母却扭转目光,说,顺便买点儿饭,娘儿俩怕还饿着呢。已带出责备。
乔丁说那我先回。他把包放回店里,再回家。如岳母所料,女儿果果边写作业边啃方便面,妻子在餐桌边发呆,旁边是削了一半的土豆。乔丁告诉她情况——多半是她告诉过他的,他不过用自己的方式表述一遍。但话从他嘴里出来,意义大不相同。若说相信,还不如说那是深深的依赖。妻子问报过警没有,那个人会不会再大打出手。乔丁说,放心,我会处理好,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他不说得那么细,他知道怎样让妻子踏实,怎么捋顺她杂乱的目光。待吃完饭,她打开电视机,他彻底松了口气。
乔丁再次返到医院,岳母没和他争执。乔丁送她出来,她前他后。她的走姿甚是轻盈,带着弹性。但走得很慢,仿佛等乔丁,可乔丁赶上她,她又加快。走廊上弥漫着浓浓的气味,并非医院特有的来水味,更像深秋田野上混杂的果实的香味。乔丁不知道鼻子出了问题,还是幻觉——可他清楚置身于什么地方,他没有深思,只是贪婪地张着鼻孔,整个人有些癫。阴暗的走廊就以那样奇怪的方式嵌入记忆。此后几天,乔丁以同样的方式穿行,再没出现那种感觉。
走廊并不长,到了电梯口,乔丁叫声妈。岳母从摁钮上撤回手,轻轻叹息一声,说吧。岳母已然猜到,乔丁还是讲了自己的理由。岳母不赞成找那个女人,更没必要报警,她说,我相信你爸,肯定是冤枉,但较真有什么好处?你爸是躲事的人,吵吵嚷嚷只会让他生烦,我也不想。乔丁说,他们可不这样想,还以为咱理亏。岳母说,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你爸也没多大事。乔丁说太憋气。岳母说没必要跟这样的人计较,自己走路还跌跟头呢,出了院,照样拉他的手风琴去,那女人管不住自个儿男人,不会再往你爸跟前凑了。她大度地笑笑,谁还没个坎儿?
乔丁无话可说,岳母的态度自然也是岳父的态度。若是别的,乔丁也就罢了,他并不刺儿,可这是挨打啊,打岳父,也就是打这个家。乔丁是家的一部分,如果岳母是左腿,他就是右腿,如果岳母是左眼,他就是右眼。可以闭一只眼,可以缩一条腿,但同时闭两只眼缩两条腿,那就不仅仅是跌跤的事了。他甚至想起那句不搭界的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心底那个东西鼓胀着,像破土的蘑菇。
乔丁行动了。没费什么事,不但打听到那女人叫什么,连她丈夫的名字、住址都摸得清清楚楚。那女人无论身材长相都比岳母差远了,更没有岳母年轻,她的头发染过,头顶处已露出寸把长的白发,倒是她的眼睛有一种勾人的力量,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
岳父出院前一天,女人和那个粗短身材、其貌不扬的男人终于露面。两人提着廉价的保健品,虚浮的笑在迈进门那一刻便不断脱落,很快剩下干巴的一绺,像花朵枯落后的秸杆。岳父和岳母甚感意外,尤其岳父,竟显局促不安。女人向岳母解释男人喝了酒,岳父几次张嘴,乔丁巴不得他泄泄怨怒,但知他不会。岳母及时调整了表情,礼貌,冷淡,得体。乔丁掩饰着自己导演的角色,掩饰着那一点点得意,再次退到幕后。
岳母没问乔丁,第二天,在办理出院手续的窗口,才淡淡地说,你根本就不该找她。
3
遇见她那天,他记得很清楚。阴天,没有阳光,像他被击得七零八落的人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他被逐出那个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说起来有点儿冤,他不外乎想挣点儿钱。他老家在农村,土圪塄——单听地名就能想象出那是个什么地方。每次开学,父亲四处借钱,他放假,父亲的债不过还了大半。然后再借再还。他没有最初回家的喜悦,放假便惴惴不安。他是不折不扣的黄世仁。他的上铺也来自农村,和他一样紧紧巴巴的。不知什么时候,上铺变得出手阔绰,让人生羡。又一个假期临近,上铺问他愿不愿赚点钱,他求之不得。他没想到上铺干那样的勾当,没想到他的运气那样差,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给铐上了。也亏得他运气差,上铺被法办,他被放出来,但是学校没饶过他。他没敢回家,也没脸回去,在那个城市浪荡着。他干过搓澡工,饭店跑堂,还在一黑中介当过几天托。什么都干不长,要么他干不下去,要么人家不让他干下去。忧伤,烦躁,灰暗,绝望。
那天,他又被炒,憋了一肚子气。那个旅店老板当然也是他的老板居然怀疑他偷了烟,他再三辩解,老板说只有他进过那个房间。他火了,进过房间就是贼?还有苍蝇呢?怎么不说苍蝇偷的?话一出口,他就知道不可能干下去了。老板肥厚的眼皮缓缓仄起,眼球便格外地大,格外地硬。老板说一条烟不值得报警,也算对他留情,他半个月工资正好一条烟。老板限他一小时之内离开,否则……老板的声音切断了,寒气如潮。他的拳头握紧松开,松开握紧,终于控制住。
他在大街上搜寻着招工启事,电线杆上贴的也不放过。他没地儿住,兜里的钱撑不了几天。那是他全部家当,不到两千。仿佛是想更清楚一些,他掏出数数,一千九百二十。之后,他又在兜里捻着,这一下吃惊不小,钱少了一张。于是,他蹲在一个电线杆下再数。还是少一张。怎么回事?第一次数错了吗?他恍惚着,又数一遍。一千九百二十。为了确认,他又数一遍。没再出现差错。他站起身,一个女孩向他问路。大眼睛尖下巴,齐腮短发。女孩说声谢谢,忽然绊了一跤。他扶住她,她再次致谢。他的手插进兜里,头皮猛地抽紧,那个女孩走出十几米远,竟然回头扫他一眼,然后飞奔起来。
他没喊抓小偷,只是恼怒地喝叫她站住。那时行人很多,如果他喊,可能哪个人会绊住她。他还记得穿越一个路口时,交警用手势阻止她闯红灯。但他没喊,只有初时短短的一喝。他无声地追着她,像赛跑。后来,她问过他,他说想亲手抓住她,太想了,他一肚子的火终于可以发泄。她问还有呢?他说没了。就这么简单?是的。她狠狠瞪他一眼,说他一定想占她便宜,还凶蛮地逼他承认。
她是有机会逃进商场的,商场四个门,顾客熙攘,滑进去便大海捞针。但奇怪的是,她没进去。一个女孩竟这样能跑,出乎他的意料。如果他有些积蓄,或许就放弃了,他的眼睛已快冒烟。可那是他全部家当啊。还有,他那么需要撒气。他慢下来,她也慢了,还频频回头。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觉出她在戏弄他。怒气再次卷上来,他又加快了。
竟然跑到城外。她没再沿着马路跑,而是拐上一条便道。也许有她的老巢,还有同伙……他犹豫一下,追上去。
没路了,前面是一面大湖。她站住,他也站住。她瞪着他,他也瞪着她。他说,跑呀,怎么不跑?
她说,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他不由龇了牙,她竟然威胁他,真滑稽。他慢慢逼过去。
她说,我真跳了。
他冷笑,你跳呀!
她一步步后退着,退到不能再退,顿时可怜巴巴的,哥呀,好男不和女斗,你放了我吧。
他说,休想!
她忽然怒道,大白天的,你明抢啊。并环顾左右,企图求救。
他说,你倒是个演戏的料。
她竟然又荡起一丝浅笑,哥呀,你想不想演戏?我领你去,挣钱比抢得还快。
他往前迈了一步,演啊!
她突然凶起来,你想逼死我吗?
他用鼻腔哼了哼。
她纵身一跃,伴随着他的惊叫。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仿佛跳的不是一个,而是一串,他的耳膜被连续击打数声之后,才醒悟似地扑到湖边。一片水草,几只野鸭,水面突然又空又大。他疯狂地脱衣,匆忙中撕断两粒扣子。他跳进去,在水底搜寻。他是在大学学的游泳,水性并不是很好。好在水没多深,他很快抓住她,拼力拖上岸。她的头耷拉着,眼睛紧闭。大概呛住了,奇怪的是嘴里并不喷水。他没有救人经验,凭着书本上学的那点儿,猛拍她的后背,忽又翻身,抓着她的胳膊抢救。他似乎往她的脸侧瞅了一眼,又似乎没瞅,目光稍一僵,马上集中到她脸上。她的脸忽青忽紫,忽灰忽白,眼睛依然闭着。他越发慌乱得不得要领,跪下去,打算做人工呼吸。
她突然睁眼,你便宜还没占够?
他重重往后一跌,惊愕地张大嘴巴,你……
她坐起来,目光如针,你想干什么?大白天的你想干什么?
他做了亏心事般,心慌着脸也红了,我想……救你。
她呸了一声,谁知你安的什么心?又是揉又是捏的。
他说,我认为……
她抢过去,你以为我死了?死人的便宜你也占?
他已经回过神。让这个女孩耍了。但他一肚子的怒气像被水溶解了,怎么也动不起火来,只是伸出几个指头。
她问,干吗?
他说,别装,把钱还我。
她瞪着他,你欠我一条命,还冲我要钱?
他说,少废话。
她说,你把我逼到跳河,还不放过我?我没钱!
他说,我要我的钱。
她说,你搜吧,搜出都是你的,算我倒霉。
他却迟在那儿,目光胡乱地瞄着。她很瘦,胸脯又扁又平。
她挑衅地,怎么?怕了?
他豁出去似的,我凭什么怕你?
她又阻止了他,你占便宜占惯了是不?我自己来。
她一个一个翻着兜,彻底翻过来,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他很是纳闷,她并没有机会藏,他的钱飞了不成?
她气乎乎地,看清了?
他的目光软了硬了,松了紧了,却没离她左右。她毫不躲避,大有针尖对麦芒之势。无赖,他碰上一个无赖。她嘴巴这样硬,他又没有证据,算他倒霉。他无言地拧拧衣服,就那么湿嗒嗒地套在身上。
她问,你要走?
他斜着她,咋?还得你许可?
她说,你逼我跳河,差点要了我的命。还趁机摸了半天,捏了半天,噢,你说走就走?
他的脸肌弹了几下,你还倒打一耙了?你想咋样吧?
她脱口道,给我赔礼道歉。
他说,你等着吧,什么时候太阳从西边出来,我还要给你磕头呢。
她喝了一声,跳起来抓住他,想走?没门!
他说,放开!
她说,不!
他奋力推甩,她拽得反更紧。两个人吁吁气喘的。他气急败坏,你想咋?想咋?
她说,找警察主持公道。
他说,好,我求之不得呢。
她气鼓鼓地哼一声。
她放开他。两人走得很急,飞离地面似的。拐上公路,他步子慢了。他的心重了。没有证据,他能说得清吗?万一……她嘴巴那么利害,他害怕了。那个地方,他去过,阴影尚存。自投罗网,这个词忽地冒出来。他定住,目光极虚地说,还是别去了吧。
她说,咋?害怕了?
他说,我不想折腾。
她说,那就道歉。
他看看她,又看看四周。天已经暗下来,远处雾蒙蒙的。不时有车疾驰而过。如果……他掐断思绪,说,我认错人了。
她说,光这样不行,我肚子饿了,怎么也得请我吃顿饭吧。
他说,我身无分文。
她轻轻吐出三个字:穷光蛋。忽然说,算我倒霉,我管你顿饭。
她和他吃的是辣鸭头。他直哈嘴,可她仍嫌不辣,一次次往碟子里加辣椒。他问她是湖南人还是四川人,她回答得干脆痛快,不知道,连父母是谁我都不知道。干吗这么多废话?别跟我套近乎,惹恼我,小心AA制。他低下头,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那个问题,她把钱藏哪儿了?末了,他也没搞清她怎么结的帐。
他欲离去,她喂了声,你住哪里?
他摇摇头。
她道,你什么意思?怕我去你家住啊。
他说,我不知道,我今天才没了住处的。
她审视他一会儿,说,没想到你这么可怜,比穷光蛋还穷光蛋,难怪在大街数钱呢,几个钱就烧成那样?得,算我倒霉,让你粘上了,去我那儿借宿一夜吧。丑话说前头,你别趁机占便宜,我可没那么好欺负。
他踌躇着。
她说,咋?怕我害你还是等我用轿子抬你?急欲甩掉他似的,跳着离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