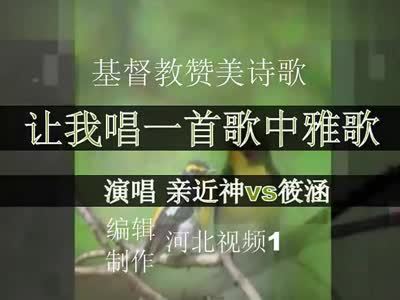论卢仝的《饮茶歌》对宋诗的影响
Lou Tong′s" Drinking tea songs "of theinfluence of the song dynasty poetry to thediscussion
周圣弘 林君妍
ZhouShengHongLinJunYan
(武夷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Wuyi universityinstitute of humanities, Fujian, Wuyi shan,354300
内容提要:唐代卢仝的《饮茶歌》是茶诗中的千古佳作。它对宋诗的影响是深刻而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题材的生活化和内容的典故化,审美情趣的世俗化,语言运用的口语化,艺术手法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颠覆和文本对宋人精神生活的辐射上。
关键词:卢仝;饮茶歌;宋诗;影响
Abstract:The tang dynasty Lou Tong′s " Drinking tea songs "tea in poemhistoric works. It has a deep effect on the song poetry and notallow to ignore: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in the theme of life andcontent in the story, the secularization of aesthetic appeal, thecolloquial language use, the innovation of the art, art style ofsubversion and text to take the life of the mind onradiation.
Keywords: Lou Tong; Drinking tea songs; The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influence
《饮茶歌》全名《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又称为《七碗茶诗》、《七碗茶歌》)或《茶歌》,作者卢仝,约作于元和七年。元和六年,卢仝的挚友孟简由谏议大夫贬为常州刺史,卢仝前往常州抚慰好友。元和七年春,卢仝尚在孟简座上。一日,孟简派军将赠送阳羡月团茶三百片,卢仝有感于孟简深情,遂作《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以酬。
卢仝的《饮茶歌》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茶学价值都很高。作为中国茶诗之最,作为能与陆羽的《茶经》齐名的茶学经典,它的研究价值是很高的。
卢仝《饮茶歌》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稀少的,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比如作品的审美情趣、艺术手法、语言运用、艺术风格、传播影响等方面少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作品的内容,更多的是从对文本的整体把握来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评释诗歌获得审美体悟,如曹望成、周巨根的《得知天下苍生命,且尽卢仝七碗茶——唐诗<</SPAN>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评释》(《茶叶》,2004年30卷)。对卢仝《饮茶歌》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
本文在对卢仝《饮茶歌》的理性把握和审美体认上,结合卢仝的其他诗歌,以及他的传记及他人给予的诗评来探讨它的诗学价值和诗学效果,以及这种诗学价值与诗学效果的关系。首先,本文将从卢仝《饮茶歌》的题材内容、语言运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审美情趣等方面来全面分析卢仝诗作的诗学价值、审美价值。以及这种诗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所带来的诗学效果,对后世诗作特别是宋代诗作诗人的影响;其次,本文将从卢仝茶歌的诗学价值出发,分析它带来的诗学效果以及传播影响。尤其是着重从卢仝的《饮茶歌》给宋人精神生活带来的强烈影响和宋代及以后的诗歌作品(尤其是茶诗)的深刻示范性入手。
一、《饮茶歌》对宋人精神心态的影响
宋代的茶诗茶词多有提及卢仝及其茶歌。无论褒贬,都透露出这样的心态:一、卢仝在饮茶方面的造诣十分精深,与陆羽并肩,堪称“亚圣”、“茶仙”;二、卢仝对饮茶境界的独特体认得到了宋人的认可与赞赏。
第一种心态中,宋人对卢仝推崇备至,认为其人在饮茶上的造诣很深,其茶歌是千古佳作,为茶诗巅峰。胡苕溪云:“《艺苑》以此二篇皆为佳作,未可优劣论。今并录全篇,余谓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1]9644《艺苑雌黄》认为卢仝的《饮茶歌》与范仲淹的《斗茶歌》都是千古佳作,未有优劣之分。而胡苕溪、蔡正孙等人却认为卢仝的茶歌远胜范仲淹,宋人对其推崇可见一斑。且宋人常在诗中频繁地提及“卢仝”“玉川子”“卢郎”,或为自比自矜,或者赞誉贬低。
陆游对陆羽及其《茶经》激赏非常,自称是陆羽的后代,诗中也常常提起陆羽,对于与陆羽齐名的卢仝,他的态度显得十分的微妙。在《昼卧闻碾茶》中他这样写道:“玉川七碗何须尔,铜碾声中睡已无。”[2]70虽然他在诗中讽道像卢仝一样连饮七碗以除睡魔是不必要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卢仝七碗传播之广。
在宋代,更多的诗人对卢仝都是抱着赞誉倾慕的态度,他们以卢仝为尊,从内心深处认可卢仝的成就遵从卢仝的品味,并以能与其相媲美为荣。这种狂热的崇拜心态,在他们的茶诗中表露无遗。文同《谢人寄蒙顶茶》:“玉川喉吻涩,莫厌频寄来。”[3]33文同自比嗜茶、识茶的卢仝,毫不客气地向友人提出要求希望友人能多寄些茶来润润喉吻。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4]191诗人认为他所品尝的北苑茶要远胜李白曾经赞誉过的仙人掌茶,在茶香中激发出无限的诗兴,所以能效仿卢仝走笔龙蛇出华章。苏轼也甚是推崇卢仝,屡屡在诗中提及玉川子,如《马子约送茶,做六言谢之》:“惊破卢仝幽梦,北窗起看云龙。”[5]2785诗中苏轼以卢仝自居,也说自己也跟卢仝一般被代替友人前来送茶的信使从梦中惊醒,兴奋中便起身观看煎煮云龙茗茶。
卢仝茶歌对宋人最重要的影响,是表现在对饮茶本身境界的体悟上。这首诗形象生动地把饮茶中不同层次的感觉细致清晰地表达出来,从一碗至七碗的海饮中,诗人饮茶时的感受也从生理上的“甘甜”“解渴”进入到心理上的“涤烦”“飘飘欲仙”。于是,诗人从解渴似的喝茶过渡到满足审美感官的品茶,最后诗人甚至进入了茶所带来的茶我两忘茶通仙灵的审美境界。卢仝的《饮茶歌》深含佛道精粹。六祖慧能曾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认为只要修心便可成佛,并不需要每天拜忏念经。而《饮茶歌》中恰好流露出这样的意境。卢仝宣扬只要饮茶便可摆脱身体这副臭皮囊,超脱自我,飘然成仙。羽化成仙是道教的理论支柱,但诗人认为无须炼丹求药才可成仙,只要饮茶便能体味成仙的境界。
这种审美境界是卢诗所独有的,然而也影响了宋人饮茶的品味,他们认为“茶通仙灵”“飘飘欲仙”是饮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审美享受,他们也以能达到这种浑然忘我的境界为荣。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风雅之举,而且是士人洗涤心灵升华精神的途径。于是他们在诗词歌赋中频频表现这种审美境界。如:
孙觌《饮修仁茶》中:“亦有不平心,竟向毛孔散。”[6]95是化用卢诗“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认为饮茶能消除人世之不平,使人获得暂时的精神欢愉。黄庭坚《满庭芳·茶》:“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7]185、蔡松年《好事近》:“无奈十年黄卷,向枯肠搜彻。”[8]237语出卢诗“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认为饮茶能激发人的诗性,使人下笔如有神,才思如泉涌。更多的是化用卢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有惠洪《与客啜茶戏成》:“津津白乳冲眉上,拂拂清风产腋间。”[9]94苏轼《行香子·茶词》:“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10]175毛滂《西江月·侑茶词》:“留连能得几多时。两腋清风唤起。”[11]189谢逸《武陵春·茶》:“两腋清风拂袖飞,归去酒醒时。”[12]192王庭珪《好事近·茶》:“今夜酒醒归去,觉风声两腋。”[13]194史浩《画堂春·茶词》:“欲到醉乡深处,应须仗,两腋香风。”[14]201刘过《临江仙·茶词》:“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15]220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16]224等等。“茶通仙灵”是卢仝开拓的一种新的审美体悟,它表现了饮茶境界的极致之美(清雅的、脱俗的、自由的),创造了一片广阔的精神世界,使封建士大夫们能暂时从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飞升到理想的精神世界去。
品茶与饮酒截然不同,饮酒是关西大汉行侠风尘的豪迈,而品茗则是江南名士独坐莲花间的清雅。这种清雅才使得它为宋代的学者诗人极度推崇。茶与卢仝一起,开始以精致雅洁的形式来传达一种高情逸趣,成了雅化的茶文化象征,这便是卢仝茶歌在宋代产生的最大影响。
卢仝《饮茶歌》对宋人精神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其爱国恤民精神对宋人的感召和同化。卢仝的《饮茶歌》全篇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情怀,感怀兴寄,既同情命如蝼蚁的普通民众又讥讽高高在上的至尊权贵们。诗中先写因皇权的霸道与威严,百草不敢在阳羡茶成熟前开花,尽为之让道。又写如此奢华珍贵的阳羡茶,平民百姓哪里有机会能够品尝呢,大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之意。再写他自拟为被谪入人间的仙人,现借连饮七碗阳羡茶所带来的清风重返仙山,与仙人们交游。“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则是嘲讽那高高在上的群仙啊,犹如王朝的统治者们,掌握着人间百姓的生死苦乐,仙人们只顾着自己享乐而玩忽职守,不闻人间百姓的苦楚。
诗的最后诗人爆发出一声强烈的呐喊,天下苍生如履危崖,生活毫无希望,什么时候统治者们才能给百姓一点苏息的时间啊?如此微薄的愿望,只因诗人看透了统治者们的不识人间疾苦,所以不问如何才能解救苍生,只问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得到休息。这种心怀苍生的精神,在苏轼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苏轼在《荔枝叹》中,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进贡北苑团茶和洛阳牡丹,跨越度极大。诗中充满了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对欺下媚上的官员们的憎恨以及对宫廷生活穷奢极欲的嘲讽。这种因细物而虑及天下苍生的情怀与卢仝类似。
卢仝诗歌深受宋人推崇,这不仅与其诗歌风格有关(对传统诗歌的颠覆)且与其诗歌中流露出来的胸怀天下苍生的志向有关。他虽是一介布衣,却能时时记挂着民生疾苦,即便是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也不忘记。韩盈《卢仝集外诗序》:“其为体峭挺严放,脱略拘维,特立群品之外。要夫指事措意於救物之为忠愤切身者矣。”[17]386直言卢仝诗歌事之所指意之所明是诗人忠于天下愤于救民的情怀,托物寓意,承《离骚》之传统。
二、卢仝的《饮茶歌》在题材内容上对宋诗的影响
(一)题材的生活化
诗歌发展至中晚唐时期,诗求新变,诗歌题材对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越来越关注,诗歌中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
贞元、元和之际,随着中唐士人锐意的政治革新,唐诗经大历中衰后再一次崛起。纵有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诗派诗人力挽狂澜,唐诗终究还是现出了颓唐之势,不复从前风光。士人寄希望于政治革新,希望能重现盛唐声威,但生活的贫苦、政治的昏昧、宦途的坎坷折损了他们的信心疲累了他们的身躯,他们的政治激情和革新热情已经远远不如盛唐时候的士人。他们虽然也关心国家政治,民生疾苦,但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审视自身上。盛唐诗歌骨气端翔、兴象玲珑的韵致顿失,诗歌从原来的雄厚恢弘、明朗壮大的风格追求转向平易浅白或雄奇怪异,诗歌意境也从外放阔大转向内敛狭小。而诗歌题材,也从边塞、田园、山水等雅生活的神坛上步入世俗和日常生活。这在韩孟诗派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韩孟诗派一意追求创新,希望能一扫诗坛陈弊。这种大胆创新、破坏传统的精神鼓励黄庭坚、陈师道等宋代诗人破除诗坛旧弊,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建立诗歌流派。为了具体说明这种创新的积极影响,以卢仝的《饮茶歌》为例,这种创新在题材方面的表现为:
1、题材的生活化
卢仝的诗歌关注日常生活,吟咏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者是烦杂的似乎没有美感的生活琐事。他似乎总能在为诗人墨客所厌弃的题材中找到值得吟咏的题材,找到值得表现的对象。他细心地观察生活,认真地体味生活,诗歌于他不再是雅道,专用来言志载道,而是更贴近生活的世俗的,以一种生活的俏皮与艰辛、诙谐与庄重来填充诗歌。这种趋势的形成不仅是因为诗人个人的原因(诗人天真的个性、对现实生活的热爱),更是反映出卢仝身处中晚唐时期,当时社会审美心态的转变(从俯仰天地包含宇宙到体察自身关注细物),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寻求诗艺上的进步和题材上的开拓)。
卢仝的诗较少宏大广阔的题材,他写身边细碎的琐事、生活遭遇、路途见闻,又喜志与朋友的相处往来及送别思念之情,善于表现和家人的深厚感情,写物记事,皆深情动人,其间又有可喜之处,读之令人欣然而忘言,拍案而称奇,搵然而泪下。在卢仝的笔下,纵然生活艰辛人世苦难但总有一种豪放旷达之气在其中,以苦为乐,所以他的诗歌并不凄楚可怜,苦涩清冷,如苏轼的《安国寺寻春》所云:“玉川先生真可怜,一生耽酒终无钱。病过春光九十日,独抱添丁看花发。”[18]277纵是无钱又多病,他还是不忘关注、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自娱自乐,并不戚戚自哀。因此卢仝常为生活中的一些小玩意(或是小动物或是生活必需品)写诗,比如《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龟铭》、《梳铭》、《夏夜闻蚯蚓吟》等。
初盛唐时,茶只是一种普通的饮品,它首先只在寺庙僧人中流传,僧人们又赠茶与平时有所往来的的诗人墨客,又以这些诗人为中心向整个文人圈子辐射,茶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向外传播,最终流入民间,成为一种风气。所以一开始虽然有诗人写诗咏赞茶,但是数量极少,且只是偶一题之,并无对茶进行全面的表现,而饮茶这一活动的真谛更是尚未被阐发。直到中晚唐,饮茶之风日炽,有更多的诗人开始以茶为题材写诗,卢仝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可以说卢仝开拓了茶诗这个题材,他虽不是第一个咏茶的诗人,但他绝对是咏茶诗写得最好的诗人,在他之后,茶诗才真正地成为不容为历史所忽视的诗歌题材,才没有被淹没在众多的诗歌中。
卢仝爱茶,茶于他来说不只是解渴的饮料,也是他心灵的慰藉品。他在品茶中得到了苏息,得到了精神的宁静和平和,在茶香悠悠中所有的疲惫与人世的艰辛都被洗去,只剩下美好。卢仝一生爱茶成痴,茶体现着他对于生活最细微的感悟。卢仝爱茶至深,恨不得全世界都能知道它的好处,将其写入诗中大肆表现也是入情入理。在《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中他这样表现自己的美学理想和人生理想:“君家山头松树风,适来入我竹林里。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喜。莫合九转大还丹,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闲来共我说真意,齿下领取真长生。不须服药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君爱炼药药欲成,我爱炼骨骨已清……”[19]695他苦劝沈山人,何必要读经书炼丹药才能求得长生。在齿下茶香中自有人生的真意,不必服药就能成仙。君欲炼药药难成,我自炼骨骨铮铮。茶已经成为了他风骨的寄托和心灵的自白。人皆有癖,无癖而此人不深情。而人的癖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身某些特质的反映。林和靖“梅妻鹤子”,远离尘俗,梅之清高、鹤之自洁未尝不是他性格的某种表露。卢仝也是如此,茶外貌之丑,如他面目黧黑其貌不扬;茶之芬芳,如他腹有诗书气自华;茶入口之涩,如他之高古介僻;茶味之清淡,有如他为人之雅洁。物肖其主,说的大抵是这种情况吧!
在卢仝茶诗的广告效应下,茶不再是一种解渴的饮品,它步入雅文化的范畴。饮茶这一活动以其自身芬芳醇雅的特质,迎合了封建士大夫的审美品味和审美情趣,它的雅既有楷书的风雅温润,又包含了水墨画的氤氲清俊,大受文人欢迎。饮茶逐渐形成风尚,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吟咏对象,与琴棋书画并称“琴棋书画诗酒茶”,是文人高雅生活的象征。
对于宋人来说,唐诗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就题材表现方面而言,唐诗巨细无遗地表现社会生活,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拓的新领域,也不能在已有领域内超越唐诗的成就。他们只能在唐人已经发现了但是并未充分表现的领域内向前前进,而诗歌题材的生活化无疑给宋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在卢仝诗歌中这种生活化的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宋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宋人们沿着韩愈、卢仝等中晚唐诗人开拓的方向,继续前进,在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文化巨人的努力下,宋诗最终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题材风格——贴近日常生活的选材。欧阳修曾在《六一诗话》中说:“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20]1957故士人闲居野处、送往迎来、谈禅说道、品茶饮酒、题画咏墨,品诗论曲,都是宋代诗歌中最为常见的题材。
2、题材的定型化
卢仝的《饮茶歌》为开辟出新的诗歌表现领域——茶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茶诗的群山中,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无疑是最险峻高耸的一座山峰。他对于茶诗这种题材并不只有开创之功,还有着规范的作用,它为后代茶诗提供了一种审美规范和范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卢仝茶诗给中晚唐及宋代诗歌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卢仝的茶诗与陆羽《茶经》的示范推动下,饮茶之风大盛于中唐。而这种好茶的风尚,对于中晚唐诗歌变革盛唐诗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诱因。天宝之乱虽然平息了,但时代遭受的创伤是巨大的,难以愈合。这种创伤也深刻地印在了诗人的思想情感上,他们再无从前豪迈的气度,这也与诗歌的发展规律相关(盛极难继),诗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已经到达了极限,诗人们开始转向关注自身的痛苦表现不幸的人生遭际。政治不复开元盛世的清明,社会经济水平下滑,人们的生活比起盛唐更加地拮据和不幸福。这种不幸福感在中唐及其以后的文学表露得十分明显。韩孟诗派的求怪逐险、“不平则鸣”更多是自身内心痛苦的呐喊;元白诗派的通俗浅显、“歌诗合为事而作”则是对黎民百姓痛苦的陈述;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众多诗人一直在贬谪中挣扎,纵然有明快的诗调也湮没在时代的大潮中。这种不幸福感,促使着诗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处境,为自己设想和寻找出路。好茶风尚的出现刚好是一个契机,它使诗人们获得一个心平气和的外部环境能够观照自身,也为诗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精神世界可以暂时逃避烦杂的世俗。茶本身“清淡”的特质,在诗人们冷静思考和反省中,给中晚唐的诗歌带来“清寒”的审美特征。这在卢仝的诗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而茶味的清新淡薄,又会给人带来空寂清幽的审美感受。这种空寂清幽也正是中晚唐诗歌有别于盛唐诗歌丰情韵致的又一特征。盛唐诗歌那种“上马击狂胡,下马写草书”的豪情意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中晚唐品茗谈道的淡然飘远。茶以其“清寂”“清新”的审美品味渗透入诗境,这种空寂清幽的追求和崇尚,也是中晚唐诗人审视自我、理性把握、崇雅尚格的体现。
中晚唐诗歌是宋诗的滥觞,宋诗受其审美特质的影响很深,表现出了几近相同的审美追求。宋代文学以“平淡美”为艺术的极境,未尝不是中晚唐“空寂清幽”审美追求的一种发展。现试以卢仝的《饮茶歌》为例,来说明这种传承关系。
好茶风尚延续到宋代,并在宋代形成高潮,这不仅是因为茶本身的审美特质与文人清高儒雅的气质相契合而得到文人的追捧,而且也与陆羽《茶经》和卢仝茶歌传播感召有关。有宋一代,饮茶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蔚然成风。诗人们写下了许多茶诗茶词,或酬唱赠答,或自抒情怀,或感兴寄托。这些茶诗或多或少都受到中晚唐茶歌的影响,特别是卢仝的《饮茶歌》。可以说中晚唐茶诗(以卢仝的《饮茶歌》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限制了宋代茶诗的表现范围、表现对象、表现领域和固定化了茶诗的表现手法、艺术构思。
如宋代茶诗多酬唱赠答之作,此情源于卢仝。卢仝因挚友孟简赠送新茶,饮茶时有感而发,故写下《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以酬其深情。这种赠诗活动在宋人茶诗中表现得十分地普遍。宋代诗人们相互馈赠茶叶,受赠者欣喜,作诗而答谢,赠者回信唱和,一来二往,留下了不少佳作。如欧阳修的《尝新茶呈圣俞》,王安石的《寄茶与平甫》,梅尧臣的《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谢人惠茶》、《答建州沈田寄新茶》,晁补之的《张杰以龙茶换苏帖》,曾巩《寄献新茶》,苏轼的《谢毛正仲惠茶》、《次韵答程朝奉谢送新茶》,黄庭坚的《双井茶送子瞻》、《谢王炳之惠茶》,秦观的《次韵谢李安上惠茶》,陆游的《谢王彦光提刑见访并送茶》、《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杨万里的《谢福建提举应仲实送茶》、《送新茶与许道人》等。可以说但凡宋代稍有名气的诗人都留下了或酬赠或答谢的有关茶诗。
如宋代茶诗又以茶事讽喻时政,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应兴于卢仝《饮茶歌》的“便为谏议问苍生”的淑世情怀。如东坡先生的《荔枝叹》:“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名出意,今年斗品充贡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焉?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21]9134
如宋代茶诗多写茶效,写饮茶带给人的极其强烈的审美感受和神奇功效,也起于卢仝。卢仝“七碗茶”的精彩描写,既是对饮茶审美感受的艺术化具现,又是对茶的药性功效的具体阐述。此类茶诗有曾巩《尝新茶》,文同《谢人寄蒙顶新茶》,苏轼《佛舍饮茶戏书》《赠包安静先生三首》,黄庭坚《戏答荆州王克道烹茶四首》、陆游《昼卧闻碾茶》等等。或写茶具有祛烦醒神的功用,或写饮茶给人带来的飘飘欲仙的审美感受。
宋代茶诗多如繁星,但大体不脱中晚唐茶诗的表现范围,如题材不离歌咏名茶、名泉、采茶、制茶、烹茶、饮茶、茶具、茶功、茶宴几类,体裁不离古诗、律诗、绝句、宫词、联句、唱和诗以及宝塔诗几类。卢仝茶歌开拓了一个广泛的领域,为诗人们提供了新的题材和写作方向,丰富了茶文化。他们所表现的无非是卢仝已经表现过的,他们所表现的又是卢仝尚未表现全面的。他们的诗作与卢仝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是不能否认的。
(二)内容的典故化
卢仝诗歌对于宋诗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体现在他的茶诗广泛传播和再创造上。我们还是以最为脍炙人口广为称颂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为例,来分析其诗的典故化。其诗如下: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22]693
这首诗与陆羽《茶经》齐名,是茶诗中的千古佳作。卢仝也因此诗获得“茶仙”的美名。陆羽为“茶圣”,“圣”之一字尚且带有人间气。而“仙”之一字,却是飘渺脱俗、飘逸可喜。“飘逸可喜”恰是此诗的意境。全诗从人间到仙土,诗情浪漫诗兴飘逸,从隐士的悠闲自得起笔却落实到天下苍生的辛苦苦痛,似是虚笔,皆是实情。以饮茶之欢欣反衬茶农之艰辛,以后事之怡然寓前情之苦痛,以乐衬苦,全诗的基调立显。整首诗写得潇洒自如,一气呵成,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
诗中写到,元和七年的某一日,春阳明媚,诗人尚且拥被高卧。忽然篱外有人叫门,却是挚友孟简遣人来信。随信而来的却是一包新近贡上的阳羡月团茶,诗人且惊且喜。索性关了柴门,谢绝访客,一个人自煎自饮,方不负挚友美意。第一碗茶水且先润润喉咙,尝尝茶味甘甜。第二碗茶水可消除一人独居的孤独苦闷,恰似有好友深夜来访,做一回剖心夜谈抵足而眠。第三碗茶水激起了无限诗情,才思如泉涌。第四碗茶水可消除胸中块垒,平生不平事,皆付茶烟中。第五碗茶水使人身轻骨清,似是脱胎换骨。第六第七碗茶水使人飘飘欲仙,几欲乘风而归去。这七碗茶歌把诗人饮茶时的心理感受和生理感受描绘得淋漓尽致,表达了诗人对茶的深切喜爱。此诗一出便被奉为圭臬,为后人竟相引用。
自宋以来,此诗便成了人们吟唱茶的典故和诗料,被广泛地使用和再创造,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符号和象征,有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意蕴。它不仅是爱茶人士的代称,还是饮茶感受的升华,更是茶道精神的代表。文人们饮茶至兴味酣浓时,常以“两腋清风”“七碗”这类意象代称。这是审美感受的内在升华和审美感官的深层体验,它不再是简单的“清甜”“先苦后甘”等生理感受的描述,它还是复杂的“消除块垒”“飘飘欲仙”、“泉思如涌”等心理感受的体验。有梅尧臣《尝茶和公仪》:“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23]191杨万里《饮茶》:“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边生。”[24]176卢仝的《饮茶歌》为后世文人品茶烹茶吟茶时都平添了许多深情和意趣。
卢仝描述的饮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神奇美妙的感受,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要提及饮茶烹茶,卢仝及他的七碗茶歌就不能被忽略,总是被屡屡提及,广泛传播。因其嗜茶成痴,卢仝亦被后人称为爱茶诗人,并拥有“茶仙”的雅号。两宋诗人所作茶诗在不同程度上,总是以卢仝茶歌的意境入诗,或化其诗意,或用其意象,或对其褒贬,但是总关卢仝深情。
在宋人对此不断的题咏中,卢仝和他的茶歌渐渐雅化,成了文人风雅的典范。卢仝《饮茶歌》不仅激起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而且也成为了画家们的表现对象。以“卢仝煮茶”为题材的中国画,在宋代已经出现,著名的有刘松年、牟益和钱选三人的三幅同名画作《卢仝煮茶图》,到了明代又有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洪绶的《玉川子像》,清代又有金农的《玉川子烹茶图》等等,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作品。画中古槐老松交错,幽篁摇曳,下覆小亭,卢仝拥书闲坐,赤脚女婢冶茶具,长须男仆肩壶汲泉。画意闲适,深得卢仝茶歌其中三昧。
三、卢仝《饮茶歌》的艺术风格对宋诗的影响
(一)审美情趣的世俗化
1、以俗为雅、以丑为美的转变
唐诗发展到韩愈、孟郊、卢仝等为代表的韩孟诗派上,开始出现了以丑为美、以俗为美的审美取向。这主要是由他们的审美追求和诗学理论所造成的。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认为诗歌“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用以‘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25]257“感激怨怼”就是强烈的情感(不平),“舒忧娱悲”就是将郁结于心中已久的情感或者愤怒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宣泄出去。因为韩孟诗派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有意背离了传统诗歌中温柔敦厚的抒情方式。而这种情绪宣泄是不加修饰的直白的尽情的,这种宣泄中还带着一种长期积累的苦闷怨愤以致情调激变的特征。为了与这种强烈的情绪宣泄相配合,诗人们选择世俗生活中险怪丑陋的意象、奇特的语词入诗,用来表现自己胸中的难消的块垒和深沉的痛苦。如卢仝在诗中写虾蟆、写蚯蚓、写山魈、写瘴气,有“扬州虾蚬忽得便,腥躁臭秽逐我行”(《客请虾蟆》)[26]691“扬州蒸毒似潭汤,客病清枯鬓欲霜。”(《客淮南病》)[27]690等诗句,读来便觉生涩不堪,极丑极俗。卢仝又有“反关柴门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句是写诗人烹茶前所作的一些准备,先是关上柴门,又戴上纱帽,整好衣冠,以示对烹茶这一行为的恭敬郑重之意。写的本是俗事小事(整理衣帽),似乎难以入诗也无甚可以入诗,但在卢仝笔下,却从对这种俗事的文化观照中,透露出雅的意蕴。对于诗人来说,这是一次审美情趣的大变革,诗人有意而为之,写怪奇丑陋之意象,描世俗琐碎之事,混淆了美丑、雅俗的界限,颠覆了传统的观念,认为大丑即美,大俗即雅,完成了一次文学观念的转变。这对于宋诗的影响很大。
沿着以俗为美这条道路向前发展,宋人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即:以俗为雅。自古雅俗之辨十分严格,但到了宋代却有了转变。宋代士大夫在禅宗的渗透和儒学的转变下,形成任缘随运的人生哲学,采取的是与俗俯仰、和光同尘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审美态度也随之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情趣和品质,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苏轼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超然台记》,《苏轼文集》卷一一)黄庭坚也曾说过:‘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无论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皆可入诗,便是这种审美情趣的体现。”[28]9
2、幽默诙谐、浅俗调笑的审美趣味的辐射
卢仝一生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但是诗人却不以为意,诗中自有一种豪迈的气象和幽默的意味。他以超脱的精神来对抗生活的不幸,通过对生活和人生遭际的调侃、戏说和反讽,他的诗歌在幽默诙谐中透露出一种笑对人生,孤标傲岸的骨气。以《饮茶歌》为例。“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表面上是写阳羡茶的习性,在百草尚未开花之际的寒冷初春就可采摘,但实际上却是对皇权的调侃。为了满足天子的任何私欲,似乎可以反天道而行之。天子想要在寒冬之时品尝阳羡茶,便可如武则天一般责问花神改变时令,命令阳羡茶必须在此时成熟,而百草不能与之争春,必须为其让道。这是何等的蛮横无理,骄奢淫逸!他并不直接批判天子的穷奢极欲,而是在轻松幽默的叙述中,寓含着对皇权威严与霸道的调笑反讽。又如“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自嘲嘲人,阳羡茶既如此珍贵难得,只配天子与王公贵族享用,竟然会入我平民之家!饱含着诧异和转折的字句中,是对“我”的自我调侃,流露出诙谐调笑的意味。
(二)语言运用的口语化
卢仝诗歌多运用口语、俗语,生动自然,朴实可喜。这与卢仝诗歌的内容和题材有很大的关系。卢仝诗歌多写生活琐事,如果使用过于典雅的语言会妨碍生活气息的传达,使诗歌有不伦不类之嫌。所以卢仝诗用通俗语写日常事,便贴近了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充满生活气息,读来令人感觉亲切可喜,如邻家阿翁絮絮闲谈,十分亲近。《饮茶歌》中有:“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堕在巅崖受辛苦!”等句皆是口头语原汁原味地运用在书面表达上。诗人平平白白地讲到:“蓬莱仙山到底在何处?我玉川子,乘着这清风想要朝着仙山飞去。”“他们哪里知道有百亿万的苍生,像是吊在悬崖上受尽辛苦啊!”如此句意,明明白白,没有运用任何的修辞手法,既无典雅也不古奥,平易朴实,即使是老妪幼童,也能琅琅上口,明了其意。
宋诗在语言趋于通俗化上,深受韩孟诗派等人的影响。语言的通俗化,采用俚字俗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经中唐韩愈、孟郊、贾岛、卢仝、白居易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宋代诗人基本上是沿着这股趋势向前发展。宋诗以“平淡美“为艺术的极境,未尝也不是受这种朴实平易的语言风格的影响。
(三)艺术手法的创新
1、以文为诗
作为韩孟诗派的成员,卢仝“以文为诗”写了大量散文化特征明显的诗歌,便展现了独特的风格。散文化的倾向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影响较大。欧诗的散文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他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送龙茶与许道人》,开头便叙述许道人的出身、来历、性情,直接平白,有如人物小传。
卢仝部分诗题直接借用了散文体裁。如《龟铭》《梳铭》借鉴了铭文这种散文体裁,《孟夫子生生亭赋》以赋这种散文体裁为名。
他的部分诗歌句子长短不一,错杂混用,常见的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和八言的混用。如《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就是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的混用,这种混用除了使诗歌的表现方式更加别致以外,还增加了诗歌的意趣,整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错落感,既不拘泥于体式,也不拘囿于格律,十分地自由散漫。而这种自由和散漫给诗歌平添了许多生气和活泼。卢仝诗歌多杂言诗,句式长短不齐,长句有利于愤郁情感的强烈喷发,短句有利于沉郁情感的缓慢抒发。
他作诗不避重复,如《饮茶歌》:“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四句诗中用了两次“谏议”。如《走笔追王内丘》20句中用了7处“夫子”,重叠率相当高。这种重复使诗歌具有了回环往复的美感。卢仝诗又多用叠字,如“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风梅花落轻扬扬,十指干净声涓涓”(《听萧君姬人弹琴》)[29]701,多用叠字,使诗歌在吟诵时,音节舒缓悠扬,缓若丝竹声。
他作诗不避铺叙,不重对仗工整。“日高丈五睡犹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开篇即叙述道,日高五丈,诗人睡意尚浓犹在梦乡,忽闻篱外有人叫门,说是孟简叫人送信来。犹如小说的开头,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俱有。叙述这种表达方式在卢仝诗歌中常常被大篇幅地运用,他抛开了诗歌重在抒情的传统,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变含蓄委婉为显露直白。卢仝诗歌也不太注重对仗,许多诗句因为遵从了散文的语法规则,用的都是正常的主谓宾结构,尽力消融了诗与文的界限。如“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就是正常的散文句法。因为散文句法的运用,所以卢仝的诗歌不受韵律、节奏和对称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
2、“以议论为诗”
在以文入诗的同时,卢仝还无视诗歌重抒情、重意象、重比兴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事物、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形成“以议论入诗”的特点。“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在诗尾大发议论是卢仝诗的一个特点,在茶香的悠然中,他并没有忘记天下仍有许多在受苦受难的百姓,他们如履薄冰,生活艰难,却无人关注他们。他从隐士的悠闲生活中脱出身来,将目光投向命如蝼蚁的广大民众,最后两句议论颇有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意。
卢仝诗歌以散文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文之流畅,韵散通体的佳作。“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自杜甫、韩愈始,经过卢仝、刘叉等韩孟诗派诗人的实践,到了晚唐在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中已经屡见不鲜了,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我们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诗人的诗作中可窥见一斑。他们的诗歌也多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能将议论、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能得韩孟诗派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如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及“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30]148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31]33这两首诗都是咏史诗,根据“昭君出塞”的史实敷衍而成。欧诗认为昭君悲剧的根由在于她过人的美貌,而王诗认为昭君的悲剧是古今宫嫔的共同命运,议论精警,而又富于情韵,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征。
3、夸张与浪漫艺术手法的运用
卢仝的诗歌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如《饮茶歌》中写到饮茶时的奇特感受,诗人觉得自己飘飘若仙,仿佛随风而去,一直飘到仙人居住的蓬莱山上,他并不关注仙山风景,而是与掌管人世的仙人们谈起了天下苍生的苦楚。诗中充满了浪漫天真的幻想,诗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天真地希望能有地位崇高的仙人们能看到百姓们在尘世中苦苦挣扎的艰辛,从而能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
卢仝诗中的比喻也用得十分地雅致清新,如“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中“仁风”意指春风,以“仁”喻春风之柔和温暖,“珠琲瓃”则是以珍珠来比喻茶树所结出的蓓蕾,而“黄金芽”则是喻茶芽比黄金还要珍贵。卢仝的诗歌也常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如“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自言其胸中有万卷诗书将要随着才思喷薄而出,这里用的就是夸张的手法,用来极言其学识之丰。
因其诗歌中奇特的想象、别致的比喻和夸张手法的运用,使卢仝诗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浪漫色彩。卢仝因其以童心写作,所以诗歌显得十分地天真浪漫。
4、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奇怪僻异的字词意象
元和元年到元和六年之间,韩愈先任国子监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人得以相聚;后韩愈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李贺、刘叉、贾岛等人陆续来到,张籍、李翱等人也时来过往。在这些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相互酬唱赠答,彼此切磋诗艺,相互奖掖,于是形成了审美意识上的共同趋向(即崇尚雄奇怪异)。如卢仝自称:“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32]701。。卢仝作诗不不喜平凡,他的诗歌中多用一些奇怪僻异的字词意象,主要表现在:
(1)他喜用僻字。如《饮茶歌》中的“仁风暗结珠琲瓃”本可用“蓓蕾”,但作者却用了“琲瓃”这两个僻字,增加了诗的深度这样会使诗多几分古奥,也有出新出奇的效果。
(2)喜用数字。如《饮茶歌》中“白绢斜封三道印”“手阅月团三百片”“惟有文字五千卷”,用这些具体的数字来达到作者夸张和表情达意的目的。还有诗中“一碗”到“七碗”的排列,连续用了七个数字,一气呵成,如黄河直下九千尺。
(3)喜用险韵。如《饮茶歌》有韵为“片、面”,《客答石》韵为:“癖、逆”等等,均是险怪的仄声韵,与当时普遍押平声韵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就造成了他诗歌奇僻怪异的特色。
(四)艺术风格的颠覆
严羽曾经这样高度赞誉过卢仝:“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沧浪诗话·诗评》)[32]8427还认为卢仝的诗歌独具一格,虽在险怪上与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人同是一路,共属“韩孟诗派”(“险怪诗派”“怪奇诗派”),但是他还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质和诗歌风格“卢仝体”。“卢仝体”主要是指卢诗艺术个性上之“怪”,所以刘克庄又有:“卢仝、刘叉以怪名家。”[33]272这样的评价。苏轼也曾评论道:“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34]207卢仝诗风中“怪奇”的一面,在宋代很受青睐,有许多人都认真研读了卢仝的诗作,对卢仝推崇备至,并有不少诗人拟其诗风为诗。
宋代韩盈十分喜爱卢仝的诗歌,但恨其歌诗数量太少,从友人处偶得卢仝尚未刊刻的集外诗十五首,欣喜若狂,为之作《卢仝集外诗序》并附旧本一起刊刻。宋代王令曾模仿卢全《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并序》做《答问诗十二篇寄呈满子权》。在诗序中诗人坦言他十分喜爱卢仝的诗歌,于是效其体作诗以示对其诗歌的重视。王令诗风雄伟奔放,语言奇崛有力,其诗的构思新奇、造语精辟及意境奥衍、气象磅礴与卢仝的诗歌很是相象。
徐积曾习卢仝之《与马异结交诗》做《李太白杂言》,苏轼曾评论徐积道:“徐积,字仲车,古之独行也,于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35]309
苏轼也对卢仝颇感兴趣,在艺术趣尚和审美追求上都十分崇尚韩孟诗派的雄奇怪异。苏轼曾在诗中自言:“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呼过韩退之。”诗人自鸣道我前生恐怕是卢仝吧!诗意中对卢仝的推崇以致顶峰,甚至认为自己是卢仝转世而来,所以才有其豪放,知其怪奇,诗歌中也展露出卢仝独特的风格,既有雄奇又兼谐趣。
总的来说,卢仝的《饮茶歌》对于宋诗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深刻地烙在宋人的日常生活、诗歌创作和思想精神上。宋人推崇卢仝,既是对他嗜茶品茶精神的一种传承,也是对其诗歌诗意的追摹。宋人受到了卢仝诗风及其个性的陶冶,为宋代文学增添了不少亮点。
参考文献
[1][32]吴文冶主编.宋诗话全编九[M].南京:凤凰出版社, 1998:9644、8427
[2]张家坤主编.寄与爱茶人:历代咏茶诗词集[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8:70
[3]庄昭选注.茶诗三百首[M].广州市: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3:33
[4][18][23]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M] .北京市: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191.277、191
[5](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1-8册[M] .北京市:中华书局, 1982 .02:2785
[6][7][8][9][10][11][12][13][14][15][16]李莫森编注.咏茶诗词曲赋鉴[M].上海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95、185、237、94、175、189、192、194、201、220、224
[17] 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M]. 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386
[19][22][26][27][29][32]黄钧,龙华,张铁燕等校,全唐诗8[M].岳麓书社,1998:695、691、690、701、701.
[20][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28)诗话[M].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01.03:1957
[2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9134
[24]刘景文编著. 中国茶诗[M]. 太原市: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04:176
[2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257
[2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9
[30]杜立选注. 历朝咏史怀古诗[M]. 北京市:华夏出版社, 2000:148
[31]范文瑚,钟仕伦主编. 阅读欣赏与应用写作[M]. 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08:33
[3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M].北京市:中华书局,1989.03:272
[34][35]顾之川校点.苏轼文集上[M].长沙市:岳麓书社, 2000.08:207,309
周圣弘,湖北洪湖人。武夷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诗学与茶文化。
本文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54-62页。全文约16000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