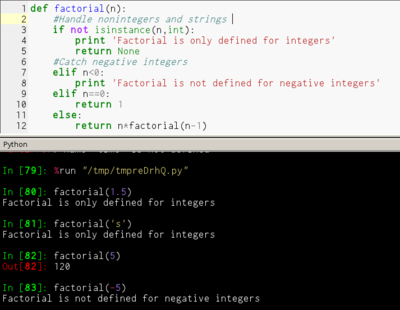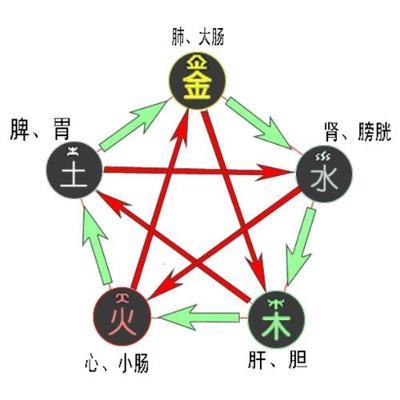归化异化归于化
【本案:翻译只有关联与趋同两个原则,所谓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嫌僵死,而究其本质并不存在,今贴出《归化异化归于化》一文,就教于方家。】
在翻译界不难听到这样的声音:“归化异化之争,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伸”1;“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2。还有人说过,翻译中直译不可取,应该尽量使其中国化,刘英凯将这概括为“归化”的趋势,并认为这是翻译的歧路。3且不论孰是孰非,这类论述无异于将归化与意译、异化与直译画上了等号,即归化为意译,异化为直译。但我要说,这种归并是很值得怀疑的,倒不在于内涵上有什么差异,而是这种简单归并经不起逻辑的考验,自然也不会得到实践的支持。
词位或语码的对等切换可以视为直译,这当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直译意译从根本上说是子虚乌有的。不过,我们还是认定直译意译的说法。那么直译就一定是异化吗?且看,“DamonandPythias”是规约性的说法,它不可随意拆分、组合,所以可以看作一个语码——这规约性说法正暗合“成语”之义。既是语码,自然可以换易为意义相同的另一种语言的语码,如汉语的“管鲍之交”——说它是语码,是因为它与“DamonandPythias”一样,具有规约性、稳定性,你不可以随便换成“管鲍之好”、“管鲍之谊”、“管和鲍”、“鲍和管”之类。根据语码的对等或对应切换这一界定,这种译法便属于直译。可是按照前面的说法,直译就应该是异化。可是谁也不会把它看作异化的,明明是归化嘛,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归化。“管鲍之交”不是地地道道的汉语,且是源远流长的地地道道的汉语吗?从转换单位看是直译,从文化内涵上看又是归化。可见直译不等于异化。
反之,归化也不见得就是意译。LePèreGoriot译成“高老头”算是归化——多像那高老庄走出来的老爹。但按质直的直译标准,这倒是对应词语的调整、切换,即直译了。如果说“père”译作“老头”有意译之嫌,那也只是嫌疑罢了。在法国,社会地位偏低,够不上“monsieur”(先生)的中老年男子就称作“père”。傅雷的这种译法曾遭人诟病,被指责为过度的意译,而其实竟是“李老头”、“张老头”等“老头”这一义项的精确对应,直得很呢。至于“Goriot”译作“高”,这看似意译,其实不然。这是简略的音译法,正如“AdamSmith”译作“亚当·斯密”,“mara”译作“魔”一样。再说,“Goriot”只是姓,与“远近高低”无涉,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高”的意思。
译界中的一致看法是:翻译成语或典故常采用归化法。的确如此!除以上成语或典故外,我们再援引《译学词典》4上的例子:“cryupwineandsellvinegar”译作“挂着羊头卖狗肉”,“seekahareinahen’snest”译作“缘木求鱼”。既是成语或典故,就是规约化的语码了,那么其与译语相应成分的对译自然应该算作直译。
综上分析,归化不是意译,反倒是直译了。就此,直译等于异化,意译等于归化的看法便显得过于随意、肤浅,而终不能成立。
就翻译而言,有时由于术语界定的含混性我们很难说何为直译何为意译,有时两者又都能说得过去。“DamonandPythias”与“管鲍之交”的互译即属此类。
说它是直译,原因在于语言转换单位是语码的对等切换。要以理据不同而否认这就是直译的话,那么理据不同而意义相同的双语词汇是极其普遍的,如“mountain”之于“山”、“university”之于“大学”等等,理据与意义都相同极其偶然,如英语的“cuckoo”和汉语的“布谷”,英语的“oldfox”和汉语的“老狐狸”。这种偶然性意味着,如果以理据不同而否定直译,那么直译便不复存在,翻译也就无所依托。
说它是意译,那肯定也是不无道理的,译者不也是跳出源语句法结构的束缚,组合成地地道道的汉语结构,醇化出地地道道的汉语来吗?你看,那“高老头”还沾着汉文化的泥腥味呢。
如果以直译意译的含混来维护归并者的观点,也是枉然的。既然直译意译含混,又如何能确定直译等于异化,意译等于归化的立论呢?
我们还可进一步琢磨琢磨归并者的虚幻。
姑且认定传统意义上的直译意译是成立的。那么,有没有既非直译又非意译的情况?恐怕没有。既是直译又是意译的情况倒是存在的,如上文“honeymoon”与“蜜月”的对译。但是,归化异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翻译中似乎存在着既不属归化又不属异化的现象。比如“strikewhileironishot”译作“趁热打铁”是归化还是异化呢?哪怕极普通的互译,如“drinkwater”和“喝水”之类,我们也无由做出归化异化的判决。似乎,越普通的翻译越无所谓归化异化。简言之,如果按照传统对直译的理解,这些译例可算作直译的话,那么这既非归化也非异化,而且这种现象极其普遍。
可见,直译不等于异化,归化也未必就是意译,再加上直译意译的含混性,就更难一对一地划上等号了。
我们可以论证传统译论中直译意译的虚妄,以及直译等于异化、意译等于归化的不合理归并,但并不是断然否认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之类的提法,作为方法取向的通俗说法是勉强可以的。只是就其本质而言,直译意译融于译,归化异化归于化。
前文已就直译意译进行了分析,按下不表。现就异化归化问题进一步陈述。
按照施莱尔马赫的意思,归化就是“将文本拉近读者”,也就是使译本便于读者理解;异化就是“将读者拉近文本”,也就是使译本传输作者的原味5。归化异化体现为两种方法取向,可以视为一种策略性的抉择。而且两者可能相差很远,比如苏曼殊和袁可嘉译过彭斯的“ARed,RedRose”,趣味相异,读起来就像两首不同的诗6。不过,如果既能“将文本拉近读者”又能“将读者拉近文本”,那不是翻译的理想境界吗?两端兼顾正是翻译的趋同原则所要求的。不过,还必须强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外延上界定归化和异化。如果归化、异化只是“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只保留归化或异化,即只以归化度高或低抑或异化度高或低来认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归化与异化成反比关系,归化度越高异化度越低,反之亦然。这恰恰说明了归化和异化之间没有界限,也没有度高或度低的认定标准。
如果说直译意译是从具体的角度考察翻译,而归化异化属于文化层面的宏观视野,这也欠缺逻辑上的说服力。如果说直译意译指的是语言结构和特点而归化异化属于文化层面,那么文化层面最终还要由语言结构来体现;如果说直译意译属于翻译技巧或方法而归化异化属于翻译策略,那么策略最终要靠技巧或方法来实现。可见这样的区分也只能是含混的。
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人们对于归化异化的误解。
韦努蒂(Venuti)、罗宾逊(Robinson)是反对归化的7,他们认为归化将译语文化强加给了源语,是对原著或源语文化的施暴。他们所谓的归化、异化的确是文化层面的,但必须强调就翻译而言文化必然要通过语言来体现,所以归化、异化终归还是语言层面的。韦努蒂等人的异化观对于解构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异语文化的霸权是有一定意义的,但不可矫枉过正,尤其不应以颠覆源语文本的通顺为代价。而且,意识形态与翻译学问题是本质不同的两码事。岂可以文化意义上的异化否定翻译系统中的归化?
如果我们遵守翻译的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那么翻译问题归根结底将是蕴涵文化问题的语言问题。即便存在所谓的归化,这也将是文字层面的,不会存在多少“强加”或“施暴”。如果“强加”或“施暴”之说成立,那么将英语译成汉语,可不可以说翻译将汉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了英语,并对英语施暴了呢?源语、译语是二元对立的术语,无所谓强势文化的某某主义或价值观。可见,韦努蒂、罗宾逊等人的归化异化问题不具有严格的翻译学意义。
我们不容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归化的确使译文少了点“异味”,但我们不应该如此计较,因为原文作者也未必有“理据”意识。当作者说“seekahareinahen’snest”时,他无非是说“方法不对头,达不到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译作“缘木求鱼”并非过度归化,而属于正常的语际转换。再说,语言应用也可以是一种体现关系。对于同一种块茎植物,我们可以说“番薯”、“甜薯”、“白薯”、“红薯”、“白芋”、“红芋”、“地瓜”等等,我们哪会在意其间的差异呢?反之,异化也并不意味着陌生与晦涩,就是文学陌生化的翻译也不能说就是异化,其实“陌生”与“不顺”也不能划上等号。就成语、典故之类,我们也可以采用异化手法,挖掘出原文成语或典故中的“异”来,这也丰富了译语的表现手法。只要译语读者能领会其内涵,“seekahareinahen’snest”自然可以译作“鸡窝求兔”,正如“killtwobirdswithonestone”译作“一石二鸟”。
我们对比下例中所谓的归化和异化译法:
DoinRomeasRomansdo
入乡随俗
身在罗马城,要学罗马人
BetterbefirstinavillagethansecondatRome.
宁为鸡头,不为牛后
宁在村里当头头,不在罗马当副手
异化法不也挺好吗?异化出的译文也不见得晦涩,也不见得拗口。这就佐证了我们的观点:从文风上说,异化并不等于不顺。归化异化都是行之有效的翻译手段,都是服务于关联原则与趋同原则的。两者的关系是:形式相异,意义相关,意图相同。译者可根据语境因素进行适当的、辩证的选择。
不过,以上的异化处理实际上就等于给译语输入了新的语码。这是通过意译8输入的语码,不同于玄奘所谓的“五不翻”。“五不翻”属于音译,也是异化,也等于给译语输入了语码,如“菩提”、“薄伽梵”之类。当然,当这类异化的译文成了译语的规约用法,融入译语的血液之中,就不能算作异化了。“葡萄”、“苜蓿”、“石榴”、“狮子”、“玻璃”、“魔”等等,本来都是异化译法,现在已闻不出“异味”了。那么,这类译词什么时候还算异化,什么时候可以称作归化,谁也说不清,也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如果英语的“laser”译作“镭射”可以算作异化的话,那么将梵文的“mara”译成“魔”时,我们还会像晋代首译该词时那样坚持这就是异化吗?
可见,归化异化具有相对的历时性特点,两者不可能像肝胆楚越那样分明,体现于语言的共时系统也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其实,鲁迅早就否认过归化异化的分野。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说:“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格辨起来,它算不得翻译。”鲁迅的话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意义,但说明就整体而言归化不是绝对的。既然没有完全的归化,那就不可能有完全的异化。
我们回到前面的例子。将文前的归并问题限定在成语、典故的翻译之上,这对归并者倒是有利的。不过即便如此,其归并若能成立也只能成立于假设之上。
我们搁置语码的对等切换为直译的界定,那么“DoinRomeasRomansdo”译作“入乡随俗”可以算意译吧,这自然也是归化,那么意译等于归化这一说法便可以成立。那么“身在罗马城,要学罗马人”算直译还是算意译呢?如果是直译,且是异化,那么直译等于异化也成立。在此意义上,归并论者便是合理的。但问题是,这是不以语言系统作参照系的假设,是假定直译意译有着明确外延和内涵情况下的假设。若以逻辑审视之,这种种假设都不成立;若以本质考察之,直译意译都不存在,直译等于异化之类的归并便无所依托;若以动态参照之,何时是异化何时为归化,鬼都说不清。
综上,归化异化只是相对的说法,都是相对于语言的语码操作系统而言的,相对人对事物含混性、模糊性的不同识解而言的。基于此,在翻译的概念系统之内,归化与意译、异化与直译应当有着本质的逻辑区别,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只是相关,其本质是不可能相同的,由此也不应进行简单的归并。
在实施两种语言的语际操作时,有良心的译者往往逡巡于“同”和“异”之间,不敢过分也不可不及。过分归化,将会抹杀源语所蕴含的民族特点,钝化读者和译者对不同语言的感觉;过分异化,则意味着非文学意义的陌生化,稀释了语言的亲和力,甚至造成不堪卒读的后果。理想的译文应该是归化异化适度,乃至既看不出“归”也看不出“异”来,悄然入于钱钟书所说的“化境”。一言以蔽之,归化异化不是对立的,两者聚合而终归于化。
注释
1见王东风2002,《中国翻译》。
2见孙致礼2002,《中国翻译》。
3见刘英凯1987,“归化——翻译的歧途”,《现代外语》(2),第27页。另见杨自俭刘学云(主编)1992,《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第269页。
4见《译学辞典》,方梦之(主编)200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见Schulte,R.&Biguenet,J.1992.TheoriesofTranslation:AnAnthologyofEssaysfromDrydentoFrrida.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42页。
6彭斯原诗与苏曼殊、袁可嘉译文如下:
彭斯原诗:
OMYLuve'slikeared,redrose
That'snewlysprunginJune:
OmyLuve'slikethemelodie
That'ssweetlyplay'dintune!
Asfairartthou,mybonnielass,
SodeepinluveamI:
AndIwillluvetheestill,mydear,
Tilla'theseasgangdry:
Tilla'theseasgangdry,mydear,
Andtherocksmeltwi'thesun;
Iwillluvetheestill,mydear,
Whilethesandso'lifeshallrun.
Andfaretheeweel,myonlyLuve,
Andfaretheeweelawhile!
AndIwillcomeagain,myLuve,
Tho'itweretenthousandmile.
苏曼殊译文:
熲熲赤蔷薇,首夏发初苞。
恻恻倾商曲,眇音何远眺。

子美谅夭绍,幽情中自持。
沧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
沧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
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
掺祛别予美,隔离在须臾。
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踟蹰!
袁可嘉译文:
啊,我的爱人象一朵红红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初开;
啊,我的爱人象一支乐曲,
它美妙地演奏起来。
你那么漂亮,美丽的姑娘,
我爱你是那么深切;
我会一直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
一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
到太阳把岩石烧化;
我会一直爱你,亲爱的,
只要生命之流不绝。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让我和你小别片刻。
我要回来的,亲爱的,
即使我们万里相隔。
7见Venuti,L.1995.TheTransaltor’sInvisib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第60页;Robinson,D.1997.TransaltionandEmpire:PostcolonialTheoriesExplained.ManchesterSt.Jerome.第58页。
8“意译”一词很是含混,取决于我们的识解或界定。现在可以归纳为三种含义:其一,对等语码的切换是直译,对等意义的切换是意译,有时对等语码就意味着对等意译,所以何为直译何为意译取决于我们的识解;其二,直译派反对的意译实际上是滥加文饰,这所谓的意译与语码并不对应,可视为非译;其三,意译可以看作是类比中的一类,不是文字层面的对等或对应,但体现于原作目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