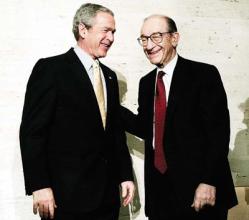毕希纳关注的问题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吸引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在《丹东》一剧中就同样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答。《丹东》(1900)大幕打开时,正是共和国经受血的洗礼的关头。恐怖气氛笼罩着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大家对自己的性命和革命前途表示担忧。被同伴指责为“自暴自弃”的丹东刚从外省休假归来。他长得一幅“恶狗似的嘴脸、公牛似的嗓音……身强力壮,血气旺盛。”丹东并不觉得需要为自己脱离革命寻找借口,他直言,此时此刻他“除了女人之外,见人就要作呕”。他只求“能够变成一个无知无识的粗人,只求别人留给他一个位置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去的雄狮变成了缩头乌龟,好友们纷纷失望而去。然而丹东并不是简单的厌倦战斗,在接下来一场,他向好友卡米尔进一步袒露心声,声称自己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保全祖国”。在接下来的一大段独白中,丹东认为共和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少庸才”。由于领袖间的互相吞噬,现在只剩下自己和罗伯斯庇尔两人,而他丹东基于不愿动摇共和国的根基的苦衷,愿意做一个牺牲的榜样。他说:“我不像阿克琉斯那样不忘旧恨,我忍耐地等着他(指罗伯斯庇尔)来和我携手。”[1]友人卡米尔反问丹东是否就此不顾朋友的安危。骄傲的领袖回答:“当罗伯斯庇尔的嫉妒心稍微平息一点,他便会听我的话。而在我这方面,当我不代表一个政党而代表人类的时候,就更好自由地行动了。”
接下来情节迅速发展。罗伯斯庇尔来找卡米尔,巧遇丹东,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年龄相仿,“中等身材,体质孱弱,薄薄的嘴唇显出轻蔑和忧虑”。他首先警告卡米尔,说他的刊物“诽谤时政”从而“成了反动派的武器”。卡米尔回应“共和国不该怕说实话的人。”罗伯斯庇尔反驳道:“共和国还不存在,不是用自由可以建立自由的。受着危难的国家所以服从一个独裁政权是为的要清除障碍,战胜敌人。”卡米尔提醒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自由和幸福。而他卡米尔不过是保卫了革命的目的。对此罗伯斯庇尔回敬道:“我们赠给人们的不是伯尔塞波里斯(原注:古波斯的都城,风俗奢侈。)的幸福,而是斯巴达的幸福。”卡米尔败下阵来,丹东旁观许久,终于站了出来,朝罗伯斯庇尔伸出了和解的手:“为了对法兰西的爱,大家休战罢,朋友也好,仇敌也好,只要大家都爱法兰西!让这种爱情消除一切猜疑和一切错误!没有这种爱情便没有德行,有了它便没有罪恶。”他仿佛是降低身段,其实是要给双方一个台阶,“我甘心蒙耻受辱,请和我握手。”而丹东“爱”的表白丝毫动摇不了下定决心了的罗伯斯庇尔,后者提醒丹东“对待所有不幸的人”的仁慈不过是“敷衍一切党派”,并直指丹东的病灶说道:“没有德行,便没有祖国”,点明了后世无数革命都验证过的一个命题:腐化必然危害革命,必然动摇共和政体。
然而,罗曼·罗兰却把观众的视点从这大是大非关系共和国前途的问题上引开,虽然他并没有刻意回避历史的这个真实细节。他把矛盾归结到双方性格的不同和冲突。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说明: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要处死丹东是因为昔日的同志已经腐化,对革命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然而罗曼·罗兰却努力地把罗伯斯庇尔塑造为一个小人,在讨论是否处决丹东的节骨眼上任人唯亲。身为人道主义者,罗兰对丹东进行了某种美化。丹东放下屠刀是由于看到共和国事业的黑暗一面,并劝说罗伯斯庇尔仿照他的榜样。后者拒绝,并怀恨在心,故而有了丹东的受难。丹东所以束手就擒是因为他看到“法兰西遍地的血腥感到恶心”。当丹东被告知好友埃罗因为私藏罪犯而被捕,他终于暴怒,并向罗伯斯庇尔挑战:“狮子要抖他的毛了……号召国民来扑灭专制魔王。”(第一幕第四场)

接下来的一幕,罗曼·罗兰没有展现丹东如何反击,而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清教徒般的个人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圣茹斯特、法节和皮约·瓦连这三位红色恐怖的首脑一一上场。圣茹斯特,从历史书上我们得知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诞生之前的共产主义者,清贫,坚定。罗兰对他的塑造十分符号化——口吐革命语录,置身事外,与其说是人,不是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而法节和皮约则被塑造成了患渴血症的屠夫。在这三人的鼓动下,罗伯斯庇尔也表现的正如第一幕丹东所抨击的那样,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断头机”。他先是假惺惺地保护丹东和少年时的知己卡米尔。然而,当法节等虚张声势地批评他意图保护自己党羽之后,罗伯斯庇尔很快灭绝了他身上的所谓人性的一面,放弃了同志和同窗的情谊。于是,在一番令人厌恶的“杀无赦”的叫嚣声中,四个貌合神离的革命者达成共识,密谋消灭所谓革命的障碍,意即他们个人专政的障碍——丹东及其同党。第二幕以闹剧收场。圣茹斯特最后那一句“共和国就是德行”变成了一个荒诞而极具讽刺意味的脚注。比较对丹东派的塑造,第二幕的四个罗伯斯庇尔派显得面目可憎。由此我们不妨可以得出结论,罗曼•罗兰同情丹东。
然而,尽管作者在丹东的台词中,隐约流露出一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但似乎并没有将丹东塑造成一个英雄。第一幕丹东想要脱身,第三幕却不得不加入唇枪舌剑的辩护,与罗伯斯庇尔交锋中的“博爱”的丹东在法庭上变化成《李尔王》中的弄人:巧舌如簧,愚弄对手,一边自娱一边娱乐群众(观众)。革命法庭上,丹东不急着为早年的贪污和通敌辩护,反而口若悬河地例举他的功绩,并利用群众的市侩心理,津津乐道地嘲笑罗伯斯庇尔的清教徒生活。“我和女人亲热并不妨碍我和自由亲热。”;“一种可恶的虚伪有毒化全国的危险。它以天性为羞,以魄力为可怕。古代的阿克琉斯每餐吃一整个牛脊。丹东既然需要,你们便扔给他好了,不必计较其他:那里头是烈火,它的光焰可以保护你们。”丹东沉浸在自己的口才中,享受听审的群众的欢呼,埃罗(这个贵族出身的美男子)冷冷地说:“你们出卖熊皮,而自己的皮却早就交出去了。”他不冷不热的调侃似乎可以视作为罗曼·罗兰的评论。在这一幕中,作为剧作家的罗兰在“超越混乱”的高处凝视着这一场政治斗争。
听审的群众就像急流中的浪花,时而爆发时而骚动;一会附和原告,一会又赞同被告,经常因为达不成共同意见而内部争吵。他们“愣着。默默地骚动。一直到终场,继续骚动、聚谈,像发寒热病似的。”后来,狂怒的群众捣毁桌椅,占据法庭。圣茹斯特上场,众人突然静默,有些畏缩。这时法节通知民众:“今晚有面粉和劈材船到岸。”于是全场星散,群众互相拥挤,抢着出门。极端的革命者法节瞧着群众,挖苦地说:“心是好的,然而胃更好些。”
对于所谓群氓的蔑视甚而仇视,丹东派早有流露。埃劳在第一场就说:“人民的脑子是一个海,里面攒动着妖魔和恶梦。”卡米尔则说:“人民是不会动的。他们并不要一个什么共和国,是我领他们上路的。”至于丹东,他早知道即使自己曾经对革命有过很大功劳,这个时刻人民也不会动手救他,因为“他们是来看戏的。”罗曼•罗兰对这一阶段革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看法很明确,与他反对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一致:革命胜利之后的党派之争血腥而无谓,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不过是《格列弗游记》中的大端派和小端派之间的闹剧。“革命的激情消失了,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不再是民众的英雄主义本能,而是热衷争夺权力的任何没有决定能力的知识分子。”[2]
剧本以丹东及其追随者在国民公会被宣判死刑为结尾。当军人出身的魏德曼再次问丹东为何不先发制人时,丹东一方面固执地说:“没有我和他的两个脑袋,革命便会失败。除非消灭他,我才能自保;可是我爱革命胜于爱我自己。”下场前他又不无遗憾地说:“自由这个女流氓骗了我,她今天牺牲了我,明天会牺牲罗伯斯庇尔;随便一个浪子溜到她床上,她会顺从他。”在死亡面前,丹东再次显示出他在热爱自由的本性和呼唤博爱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这与其说是丹东的真面目,不如说是作者的某种理想境界,此境界到是与白壁德对人文主义者的描述约略相似:“人文主义者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3]
戏剧作为一种公众话语,在这里如同在此前历史中无数次那样,被用来表现重大的公众话题。毕希纳和罗曼•罗兰在雅各宾派的问题上,各自通过独立思考得出了结论。罗兰有意将丹东描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将这段历史公案变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而人道主义在这里是以反对革命暴力的面目现身的。在反对革命暴力这一点上,罗曼·罗兰笔下的丹东的态度比毕希纳的丹东更加鲜明。
[1]罗曼·罗兰,“丹东”,见《罗曼·罗兰革命剧选》,齐放、老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以下此剧引文均见《丹东》)
[2]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传》,云海译,团结出版社,2003.11,p93
[3]欧文·白壁德,《人文主义:全盘反思》,美国《人文》杂志编,三联书店编辑部,2003,p76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