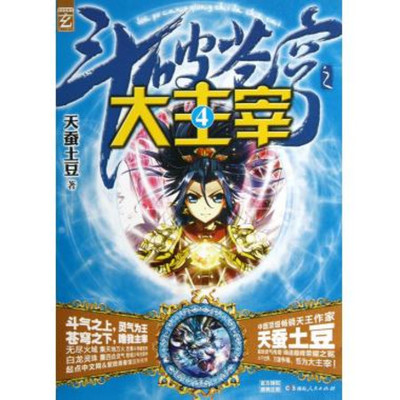1、写一首诗就是一次修行。
吴小虫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陕西,后来来了太原。他住的那个地方,是太原的城中村,叫后北屯。那里租住着各路打工仔,显现着底层生活的实相。这必然会遭遇一个诗人的愤怒。此时,吴小虫写下了后北屯系列诗歌。
后来,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包括试图经历一次不着边际的婚姻。以及去流浪。
生活没有可怜他。
他继续写诗,发怒。一心想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并经常参与组织一些意义不大的诗歌活动。
前年,他去了重庆。在华严寺抄写古碑文。
佛陀安慰了他。
他回到内心。甚至,连博客也关了。他断了那些浮名和慌乱。
他回到了写作本身。
“比起寺庙外的红尘/曾元超先生问我/这素斋可吃得惯/我答饮食神今日赠我/炒萝卜、焖洋芋、蒸米饭//比起寺庙外的红尘/曾元超先生又问我/这素斋可吃得惯/我答饮食神今日赠我/炒茄子、冬瓜汤、蒸米饭”
写出这样诗歌的吴小虫,必然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诗人了。
这样的变化,就是一个由外向里的变化,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变化。
写作不大于写作本身,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定力。
很多作者每天寻来寻去,言必称大师,知道几个大师就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唯独不去寻找自己。
这样的写作都是多余的。
小虫把这组诗歌命名为《本心录》,我想他的心已经亮了。在绕了很多弯子之后,他回到本心、本性、本真。
一首诗就是一次修行,修行是自己的事情,不要指望别人去代替。
2、吃大苦头,得大自在。
以前的小虫,一脸悲苦。这次相见,面色暖洋洋的。去重庆之后,住在华严寺,这就是奇缘。
他受了很多苦,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某世我也是女性身/长乳房、流月经、妊娠/窒息的空气,被称为弱者/某世我也是残疾/残缺地度过了余生/某世我还是那个杀人犯/同样地举起屠刀/我是叛国贼、不肖孙/吃屎猪、案板肉/这一世的你,每一世的/流转中千般滋味/在午后的长椅上沉睡/醒来并不认识枯萎的荷叶”。
佛陀等着他。白居易有诗云:“坐倚绳床闲自念,前身应是一诗僧”。诗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于晚唐形成。《全唐诗》收了一百一十五家,四十六卷,约占全唐诗的二十分之一。可见僧人写诗比重很大。现在也有人提出“现代禅诗”。这个概念还是狭隘很多。禅宗只是一个法门。我想,禅诗也好,佛理诗也好,诗僧也好,不能徒具名相。要实修实证,要静观深观,才能见心见性,这样的诗才是本心录。花架子要不得。3、说到佛理诗。许多人很容易把所谓的山水诗、禅诗和佛理诗混在一起。比如把陶渊明与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混在一起,或者把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混在一起。佛理诗是那些深研佛法的信众深观宇宙人生实相的表达方式。作者的世界观就是缘起性空,就是因果轮回,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寂灭“三法印”。但不论是山水诗、禅诗、佛理诗,最终都必须是诗,是创作。这很难。比如很多诗人对杨健诗歌的解读,各说各的话,很自信。这和杨健的诗歌有什么关系呢?杨健语言的起点是佛法。而很多诗人语言的起点是“不法”。比如有人提到李白和王维的陌生,李白在诗中是要极致张狂那个“我”,王维则是要消除“我慢、我能、我是、我所”。李白的张狂在王维面前,只是小风一吹,非有非无。现在,吴小虫的诗歌写作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诗人绝然分别的路子。“我的心啊,时常落满尘土/如果能辛勤拂拭/必将如释重负/我的心啊,有时雾霾遮盖/如果能重见阳光/必将唱腔山歌/禅师说,不必念佛了/贪时就念你的臭袜子/嗔时就念你的臭袜子/痴时还念你的臭袜子/我说我没有臭袜子/禅师当头一棒:/谁让你念臭袜子”。
4、再谈吴小虫的《本心录》。
吴小虫的诗歌写作一直不装、不端,但之前的写作还都是生活的哭喊。《本心录》之后,小虫彻底告别。
他选择了新的语言。
诗歌艺术是一条绝路。没有多少人能找见一条绝路。
找,这是一种诗歌艺术的自觉。
“藏经楼前,一位老人在扫地/她扫地的动作/使她暂时忘了自己/而我因为看见/(以前我从未看见/这位老人天天在此时扫地)/也暂时忘了自己/我还看见菩萨身后的小院/一尾金鱼寂然地游弋/鱼儿对着天空照镜子/看见了窘迫、羞耻和虚无/这使我在看见金鱼时/在水缸清澈的水面/看见了自己的执念和愚痴/正当我要痛哭流涕/这时钟敲了三下”。
在《本心录》里,小虫已经不在乎用什么手法了,或者说不再刻意用什么手法了。这是写作的一个高点。
但他依然贴着“眼见为诗”这个地面去写作,这就是脚踏实地。
“眼见”很要紧,这样才能让自己和周遭(或者叫时空)发生关系,得到一个诗歌的“实在”,让诗歌回到当下。
当下性、现代性没有了,一个人的写作就模糊不清了。
5、杨健与吴小虫
吴小虫《本心录》之前,放着杨健的诗歌,这就是写作上的挑战。
杨健先走了一步,留给小虫的只有小路。
小虫怎么写?
杨健诗歌里的那个“我”太多,不管他。
杨健诗歌里抒情太多,不管他。
杨健诗歌里文化太多,不管他。
自己写自己的,自己写自己经历的,如此而已。
6、吴小虫谈《本心录》写作
心外无法,所以我开始了《本心录》的写作。
无意为诗的诗。粗糙的、笨拙的、浑厚的。
《本心录》应该趋向无意义的存在,但不想放弃慈悲喜舍。
一种“钝”的力量的存在。
《本心录》重在去蔽,不是去语言之蔽,而是去自我之蔽。
难度写作与写简单的诗并不矛盾。简单的诗里往往包含了难度,里面有智慧的闪烁。
《本心录》录的是最初之心、婴儿之心、不退转之心。
写作就是一种忏悔,从此当中,作者获得了更新。
“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过去是逆气写作,强写、硬写,现在是顺气写作,自然写甚至不写。
三流诗中的一流意识。
诗中的自我转换,他——
相对于之前的写作,我谓之“破”,《本心录》相反,谓之“合”。
对自我的诘难和对法的叹赞。
把欢喜心掺进去,把寂静与空掺进去。
从一个诗人的自我标榜回到了诗歌爱好者的自我认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