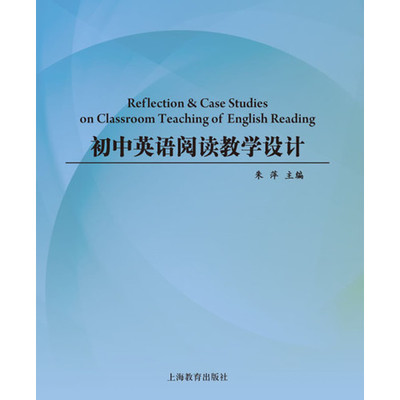木兰陂北宋史料三篇
位于福建莆田的古代水利工程木兰陂是能与四川都江堰相媲美的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实施《农田水利法》取得重大成效的生动的历史见证。与木兰陂相关的史料较为丰富,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篇北宋史料即方天若的《木兰水利记》、谢履的《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含宋神宗批答《赐木兰陂不科圭田敕》)和詹时升的《木兰誌序》却只见于协创木兰陂十四功臣裔孙所编印的《木兰陂誌集》书中,而该书现只见于收藏在莆田市图书馆上、下册各一,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福建省图书馆的各种目录中都不见收藏,或成为孤本;其中所涉史事,在有关木兰陂的研究论文方面似未见提及,三篇史料中的方天若《木兰水利记》1990年曾见于莆田县政协内部刊物,其中片断语句曾被莆田作家郑国贤和黄国华文章中引用过,笔者在本文中将其全文引录,并在史料形成背景、史料价值和史料真实性等方面加于初步研讨,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史料之一:方天若的《木兰水利记》

木兰陂水利工程建设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完工于元丰五年(1082),历时八年,在竣工庆祝时,莆田士人方天若写了《木兰水利记》一文。全文如下:
木兰水利记
莆南洋自唐元和间观察使裴次元始塍海为田,然而溪涨左冲,海碱右啮,农不偿种,吏安取科?议水利者谓:筑陂堰之,凿河以导溪流而潴之,设斗门涵泄以待河溢而尾闾泄之,庶几蕰隆弗能虫,怀襄弗能鱼,下济民艰,上输国赋,诚一方之急务也! 顾海若诲妒,河伯害成,以钱四娘之筑焉而溃,以林进士之筑焉而又溃。时蔡公兄弟京、卞,感涅槃之灵谶,念梓里之横流,屡请于朝,乃下诏募筑陂者。时福州有义士李宏,家雄于财而心乐于施,蔡公以书招之,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谒。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馀缗,助成本陂。
先引水从别道入海,乃于原溪海相接之处,掘地一丈,伐石立基,分为三十二门,依基而竖石柱,依柱而造木枋,长三十五丈,高二丈五尺。上流布长石以接水,下流布长石以送水,遇暴涨则减木枋以放水。又叠石为地牛,筑南北海堤三百有余丈,而陂成矣。
然海虽有障而溪未有潴,膏液甘润尽流入海,见者惜之。李宏与十四大家计议,谓惟凿河可蓄水。然难毁民间之田,且犯堪舆家之忌,为之奈何?十四大家佥曰:“水绕壶山遗谶在验,况予等私田半在陂右,毁私田以灌公田,捐家财以符古谶,誰复矫其非者!”于是各出私力,遇十四家之田即凿之,为大河七条,横阔二十余丈,深三丈五尺,支河一百有九条,横阔八丈有奇,转折旋绕至三十余里,而河成矣。
然溪涨河满,又溢于田,甚至溃堰而出,民甚苦之。李宏又问计于十四大家。佥议曰:“今日水利如人一身,陂则咽喉也,河则肠胃也,咽喉纳之,肠胃受之,而不以尾闾泄之,其人必胀。今洋城、林墩、东山等处是亦木兰之尾闾也,泄之可以药水病”。于是倾家赀,募乐助簿,得钱七万馀缗,立林墩陡门一所,洋城、东山水泄二所,东山石涵一所。皆鞭石为基柱,伐木为门闸,以河满处为辦,遇旁溢则减闸泄之,水稍落即闭之。又恐泄水不足,立东南等处木涵二十九口,以杀其势,而陡门涵泄又成矣。
一日李宏与十四大家泛舟木兰,为落成之宴,忽报陂北堤决十馀丈。宏叹曰:“八年之间,柱倾者一,堤崩者再,闸圯者四,后来智力两殚之时,恐前功俱弃矣!”十四大家沉思良久,有一扬杯言曰:“曩者开河之土,堆积乱塘,此不可垦为田以贻厥后乎?”遂相与垦塘为田,岁得租二千七百馀石。众谓多积无用,不如布散有用,乃舍入郡学及诸寺为租,仅存留一千三百九十馀亩,备后来修理之用,而赡陂之田又立矣!
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盖经始于熙宁之八年,完功于元丰之五年,计钱约费百万馀缗,计田约毁四千馀亩,计佣四十余万工。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
是举也,李君之力居多,十四家次之,其余助力钱者亦不可泯,今具揭于匾。而蔡公奏请之功,又非诸君之领袖乎?诸君嘱予纪其事,予窃闻邺旁稻梁之咏,谷口禾黍之谣,至今谈水利者,称史起郑国不衰,岂非水势得哉?莆自入中国来,日虞昏垫,一旦奠海滨于邺旁谷口之安,虽有财力亦得其势故也。
今国家自庆历间筑长桥以便漕路,水去渐澁,黄浦之口渐湮,而三吴多水患。予以为当事者未得其势耳!倘以治吾木兰者治之,固陂障以防其溃,濬河渠以增其蓄,又度其冲射所至,预穿大渠以导其入海,行此以治东南三江,又行此以治西北九河,何忧水患哉?
蔡公兄弟父子不日典枢,必有大建白者,诸君子姓名蒸蒸迫人,他日阴隲所酿,皆未可量。涅槃之谶,駸駸有征。予因不辞而为之记,以贻蔡公及诸君,为他日经济地云。
文中较为详尽地回顾了木兰陂的蕰酿和建设过程。唐宪宗元和间(806-820)观察使裴次元在莆田首倡塍海为田,从那时起,莆人就有“议水利者”提出把永春、德化、仙游三县流来的木兰溪之淡水与海潮上溯的碱水隔断,引以灌溉南洋大片沿海田地的设想,认为“诚一方之急务也!”这一愿望生动地体现在异僧涅槃的谶语中,在文中有三处提到:在讲到蔡京兄弟向朝廷和民间倡建木兰陂时,说“时蔡公兄弟京、卞,感涅槃之灵谶”;在叙述李宏与十四家商议凿田开沟时,说“水绕壶山遗谶在验”;在文章近结束时,又说:“涅槃之谶駸駸有征”。异僧涅槃出家前黄姓,名文臣,莆田人,生于唐宪宗时,主要活动当在唐僖宗时,唐昭宗时赐号“妙应”。他出口成谶,言必有验,相传曾作过赵匡胤统一天下,陈洪进纳土、五代中莆仙不动兵戈等多种预言,关于木兰陂的谶语是“白湖腰欲断,莆阳朱紫半,水绕壶公山,此时大好看。”预言在莆田白湖(今阔口)处伐木筑桥以跨海,改变以船渡海的南洋和莆田城关交通不便状态,又预言在木兰溪上筑陂引水绕壶山以灌溉南洋,将可以使莆田人文兴盛,当官食禄者大增,此谶到北宋英宗年间已流传了二百年左右,反映了莆田士人兴建木兰水利的长久而强烈的愿望。
文中提到与建陂有关的历史人物有钱四娘、林进士、蔡京、蔡卞兄弟,李宏、十四大家等。莆仙在唐末五代的全国性大动乱中未受兵戈祸害,先经王审知据闽三十年,又经留从效、陈洪进据泉漳(时莆仙属泉州)三十七年,在经济和文化上不是退步而是进步了,入宋后七十年来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正如文中所言是“有财力亦得其势”,开发木兰溪水利,使南洋数万顷农田由贫瘠盐碱地变成良田,成了莆田及福建沿海邻县人所关注的事情。
北宋英宗治平(1064-1067)中,长乐县退休官员的女儿钱四娘年方十八,携钱十万緍,在今木兰陂的上游五六里的将军岩(又称将军滩)处筑陂开沟,陂成摆酒泛舟庆功时,上游突发山洪。冲跨主陂,钱四娘悲愤跳水自杀,尸体被水冲至渠桥乡沟口村,后莆人在此处建有香山宫纪念她。紧接着又有另一长乐县的退休进士林从世再次携钱十万緍,吸取钱四娘所筑之陂被山洪冲跨的教训,在今木兰陂的下游七八里处靠近海口处筑陂,主陂临近建成时又被海潮上涌攻击毁坏,林进士家财丧尽,从此流落莆田。钱、林两处败陂遗址今还依稀可寻。钱林筑陂失败发生在英宗治平的四年间,又过八年左右,正当神宗与王安石大行新法提倡水利之时,蔡京、蔡卞兄弟向朝廷提出招募筑陂者,得到朝廷允准。蔡京、蔡卞是熙宁三年刚及弟的进士,其时还都是基层官员,任职在浙江和江苏。文中提起蔡京、蔡卞兄弟有三处,其第一处说:“时蔡公兄弟京、卞,感涅槃之灵谶,念梓里之横流。屡请于朝,乃下诏募筑陂者”;行文至建陂有功者时,又说:“而蔡公奏请之功,又非诸君之领袖乎?”在结尾时又说:“蔡公兄弟父子不日典枢,必有大建白者,……予因不辞而为之记,以贻蔡公及诸君,为他日经济地云。”着重地肯定了蔡京、蔡卞在创建木兰陂时的作用。元丰五年(1082)木兰陂工程竣工方天若作此记时,蔡京、蔡卞刚要升迁朝廷中枢职位(中书舍人),所以文中说“兄弟父子不日典枢”,其父蔡准此时约七十来岁。
李宏是闽侯县人,如从下篇史料谢履奏疏中看,他是道土出身的富户,此文中说蔡京“以书招之”,他率家干七人来莆,他吸取钱林两人失败的教训,选择木兰山下溪流较为宽阔缓慢处施工,在今木兰陂处筑陂,后因资金不足,蔡公复奏天朝,于是又发动南洋当地十四大家,又凑了资金七十万馀缗,才筑成主陂和陂上游堤岸。这十四大家身份据下一史料所举都为致仕小官,可能是南洋当地有较多田地的地主或周围能享受水利的有田地者的代表。钱、林、李是莆田外县人,能看好莆田南洋水利的良好经济前景,大举陂事,前仆后继,不惜倾家荡产;蔡京兄弟是仙游县籍年青士人,刚出茅庐不数年,在外省作官,能热心家乡兴化军的水利事业,屡向朝廷呼吁,使朝廷直接出面倡筑木兰陂,又在民间牵线发动;南洋十四家能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在李宏带领下,集体协调一致,全靠民间力量,完成这一千古不杇的巨大工程,充分反映了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人们积极向上、开发进取的精神面貌。
《木兰水利记》详尽地描述了木兰陂施工的全过程,先是主陂和堤岸(大约两三年)后是配套灌溉工程长达三十多里的七大河沟,一百零九支沟,(估计也用两三年),再是陡门涵泄的泄洪工程,最后又立陂田以备修费用,头尾总计用去八年,在工程的每一阶段李宏都能与十四家紧密配合,商议对策,克服困难,无私奉献,令今人读来倍为感动。
文中多处涉及工程费用数据作为史料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先是李宏应诏来莆时,倾家得缗钱七万,“陂未成力竭,”后有十四家“慨然施钱七十万馀缗,助成本陂”。这只是主修筑陂和堤岸的费用,在讲到陡门涵泄工程时,又说“倾家赀,募乐助薄,得钱七万馀缗。”在总结工程耗费时,说“计钱约费百万馀缗。”可见开沟工程所费亦在数十万缗之上。(缗与两相匹,一缗即一贯,1000文或一两)如此浩大的费用不靠官府公币完全民间自筹,还能以赡陂之田建立修陂基金以应付陂司处理日常陂事和维修开支,实为难得。
文章结尾自豪地指出了木兰水利经验对全国修治江河湖海水患的意义,认为倘“行此以治东南三江,又行此以治西北九河,何忧水患哉?”
史料之二:谢履《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
和宋神宗《赐木兰陂不科圭田敕》
据明弘治《兴化府志》载,谢履知兴化军从元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元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满。是他在元丰四年为奖酬协创木兰陂的十四大家舍田开沟的功绩,向朝廷上疏,在《木兰陂志》中题为《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全文如下:
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
宋知军谢履
福建路兴化军知军臣谢履,谨奏为酬水利以风天下事:
切见臣提封之内,永嘉乡维新里有木兰溪之水,自永春、德化仙游合流至此,以入于海。古议于此截海为陂,可灌维新里至仙游县田数万亩。治平间长乐钱四娘、林从世接蹱筑陂,俱溃于水。熙宁八年侯官县道人李宏,应诏挟赀来莆筑陂,幸有本军所辖感德乡大姓致仕司法参军余子復、从事郎朱伯震、武显郎余彬、承信郎通判余騶、承奉郎林国钧、承信郎顾筠、武翼郎朱公廙、承信郎县尉朱珪、校尉朱桂、推官朱拱、作院使吴诹、将仕郎陈汝翼、推官朱赓、运使朱枚等十四人,捨钱七十万余缗,助筑成陂,海无泛滥之灾,民有得食之渐。前知军李川以大孤屿东、小龟屿北沿海白地酬奖李宏讫。
然溪海虽分,水无积注,莆南洋万有余顷之田,仅资六塘之水。数日不雨,则禾苗立槁,上下嗷嗷,犹陂未筑也。又幸原助陂十四人,捨田四千九百九十五亩二十八角四十八步,募工自陂右创桥开沟直下,导水东注,为大沟七条,股沟一百有九,计三十余里,以灌南洋上、中、下段田万有余顷,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成岁得军储三万七千斛。
又思贮水有沟,塘无所用,将开沟之土,移筑五塘为木兰陂田。岁收租谷二千六百六十五石,尽输本军以赡国赋。
切念有莆无陂,二县皆海,有陂无沟,三农苦旱。今十四臣前既捨财助陂,且捐田凿沟,非惟水不能涝,抑且天不能旱,不特下开粒食,抑且上裕军赋,费罔损官,役非妨民。覩迹叹功,沐恩颂德,诚盛世所稀靓也!
臣承乏守土,未有成绩,罪宜万死;而挂冠逸叟,乃能奉承德意,立莆人世世命脉,若不重加酬奖,何以励宇内而风天下?臣议将以原筑塘田内拔若干亩以赐十四人,世收租利,仍免本田粮差,庶上尽报功之典,而下鼓向义之风。未敢擅便,仅本专差里正林贵诚赍奏,伏侯勅赐。臣不胜僣言待罪之至。
宋神宗皇帝于九月初一日批准这一奏请,在《木兰陂志》中题为《赐木兰陂不科圭田敕》,全文如下:
赐木兰陂不科圭田勅
勅通直郎秘书丞知兴化军谢履并本军感德乡致仕具官司法参军余子復、从事郎朱伯震、武显郎余彬、承信郎通判余騶、承奉郎林国钧、承信郎顾筠、武翼郎朱公廙、承信郎县尉朱珪、校尉朱桂、推官朱拱、作院使吴诹、将仕郎陈汝翼、推官朱赓、运使朱枚等:
盖闻君人者握符御宇,岂以一人肆于氓上,亦唯奉天子民,兴利除害为兢兢。故朕即位以来,遣程颢等察农田水利,屡诏诸路监司州县,如能劝诱兴修塘堰者,当议旌赏;又下司农贷官钱募民,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以修水利。徒增烦费,谁报底债?朕甚厌之!
今秘书丞知兴化军事谢履题朕旧臣余子復,朱伯震、余彬、余騶、林国钧、顾筠、朱公廙、朱珪、朱桂、朱拱、吴诹、陈汝翼、朱赓、朱枚等弃已捐财,共成陂功,今又捐田以开沟,且筑田以充赋,国计民生,实两赖之。是固十四臣者,体朕至意乃劝导诱激,尔实与有力焉!其以尔转承议郎,勉图后功;而以原筑陂田四百九十亩七分赐十四臣,免其粮差。盖尔不为子孙谋,而为国家谋,故朕既拨田酬尔勋,而并蠲赋为尔子孙计,永为圭田,昚乃世守。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元丰四年九月初一日(恭承天命之宝)
时给事中兼直舍人院 月 日己时
都主事王受
司农卿兼左司吕
付吏部
右丞相同知权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孙固
吏部尚书
待郎
户部尚书
待郎
告通直郎秘书丞兴化军知军谢履,转承议郎仍知兴化军。
兴化军感德乡致仕原具官司法参军余子復等十四人,赐木兰陂田四百九十亩七分,不科粮。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郎中主事蔡江
令吏黄球
主管院事书令吏李议
元丰四年九月初一日下
这一疏一勅形成于元丰四年,比上篇元丰五年方天若所作《木兰水利记》早一年。文中提到:“前知军李川,以大孤屿东、小龟屿北沿海白地酬奖李宏讫。”李川是谢履前任,《兴化府志》载其知兴化军从熙宁八年六月一十三日至元丰元年闰正月初二日,同此可见木兰主陂工程于元丰元年,即工程开始二年后完成时,兴化知军李川就以大孤屿东、小龟屿北的沿海白地(荒地)作为对李宏的酬奖。以后原助陂十四家又捨田四千九百九十五亩二十八角四十八步,以开挖木兰陂配套的灌溉工程,大沟七条,支沟一百有九。时任知军谢履遂上疏朝廷,拟将因水利工程建成后,废塘所填之田中的一部分酬奖十四家永不科粮。
文中开列十四家姓名,有三余七朱陈、林、吴、顾,他们都曾经是地方基层官员。官阶有从事郎、武显郎、承信郎、承奉郎、将仕郎之类,职务有司法参军、县尉、通判、推官、校尉,作院使、运使之类。勅中称其为“朕致仕旧臣”,看来是莆田南洋感德乡的大户田主,或是田主们的代表。谢履在接到朝廷批复诏勅后曾于十月吉日立石,开列各家姓名、官秩并捐田开沟亩数,见于《木兰陂志》中。
谢履在奏疏中赞扬十四家“挂冠叟乃能奉承德意,立莆人世世命脉。”勅书中皇帝神宗说:“朕即位以来遣程颢察农田水利、屡诏诸路监司州县,如能劝诱兴修塘堰者当议旌赏”。强调了他在王安石变法中对农田水利的重视,又说他曾经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以修太湖一带水利,但是没有取得可观成效,“徒增烦费,谁报底绩?”感到很遗憾,“朕甚厌之”,因此对李宏和十四家“弃已捐财,共成陂功,今又捐田开沟,且筑田以充赋”,深为感动,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决定批准以废塘所填陂田四百九十亩七分赐十四家,免其粮差,还勉励他们:“尔不为子孙谋而为国家谋,故朕既拨田酬尔勋,而并蠲赋为尔子孙计,永为圭田。”为奖励兴化知军谢履,把他的官阶由通直郎升转承议郎。勅书中落款处除盖有玉玺:恭承天命之宝外,还开列了相关办事官员姓或名,有王受、吕、孙固、蔡江、黄球,李议等,对研究宋代行政文书,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奏疏中指创陂者李宏的身份是“侯官县道人” ,对研究木陂的历史也有一定意义。
史料之三:詹时升的《木兰志序》
詹时升政和四年(1114)担任兴化军通判,七年以朝奉大夫知兴化军事,宣和元年(1119)八月为《木兰陂志》写此序,这时木兰陂已建成四十四年,目睹木兰陂水利工程根本地变了莆田经济和人文状态,感动不已,如文中所说他本人在前参与过治理漕河的事情,对水利建设有过切身体验,所以他来后主持了木兰陂陂司制度的改良事务,应十四家子孙的要求,将不科陂田的三分之一租谷收入官仓收貯,专项应付陂事,免得陂司在收貯支付中出现弊病,他又主持编写《木兰陂志》,并亲自为之作序,就是这篇史料《木兰志序》。《木兰陂志集》除在正文中排版外,还以詹本人字迹稿置在全书目录前。全文如下:
木兰誌序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司马相,而临川新法罢革殆尽,唯留水利一科,谓百害中获一利,予未有所验。及守兴化,览木兰陂,趾石中流,幹溪右注,翼以石堤,导以支沟。询其颠末,则钱林开基,李君缵绪,而捐钱助役,捨田开沟,则十四大姓之力。当其时,诎私钱数十万缗,赢公钱数千万缗;毁私田数十百亩,溉公田数十万亩;倘所谓害中获利,信然哉?信然哉?
然枕石于渊,石微罅则址脱;决水于沟,水暴涨则岸颓;不为修茸计,恐墜厥前功;修而支官币,敛民储,又或假经费而开亁没;在当时为害中之利,在后日又为利中之害,积蔽流蠧,势有固然。乃木兰见其利不见其害,余又莫测其故!既而按其籍,则有修陂之田,岁积谷若干,钱若干。叹曰:千百年果修陂,此足矣!兹其所以有利无害也欤!
初垦田瞻陂,多十四姓之力,前守谢君请于朝,拔陂田四百九十余亩,赐酬其劳,立其子孙为陂正副,迭主陂事,是以四十四年间,屡坏屡修,不费官币,不削民储。近者十四姓欲释其负担,乃抽酬劳田三分之一寄官科米,收貯在仓,遇陂损坏,支给修理,既为官民计,又为子孙谋。若十四姓者,询所谓长虑却顾,而其智力,似足补临川、司马之所不逮者矣!
语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予尝与治漕河,濬其源,导其所归,人皆以为难,已而运饷入汴,舟楫流通,予自以为利。矧今蒞兹土而汲兹润,其又何敢秦越而享予已享之利,而没若德也!乃覆其事迹,检其田亩,刋为陂集。因想钱、林、李及十四姓之功勋,而黎簿类宣勤,冯僧类圮者,间亦附识考之。
周礼有稻人、遂人之官,以司水利蓄泄之节(责),略载于职方氏。斯集也,聊效职方遗意而申厘尔,成尔十四姓之子若孙,尚其載君恩,思祖德,护而陂如爱而田,以嘉惠枌榆,则泽与天壤同流,祉如冈陵未艾矣!
宣和元年八月望日知兴化军事武夷詹时升书于官署中
这篇序文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水利观点冲突说起,说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元佑中回朝掌权,将王安石(临川)变法各项变革罢革殆尽,但却留下水利一科,说是“百害中获一利”,詹时升在莆田看到民间才花了“私钱数十万緍”修建木兰陂后,却能为兴化军嬴来军储数千万缗,十四户人家才毁去私田数十百亩,却实现灌溉公田数十万亩,认为这是大大有利的事,还说是百害中才获一利?能令人相信吗?能令人相信吗?
文中着重地指出水利工程的“利中之害”往往因维修引起,不加维修会前功尽弃,使用官币或从民间收敛维修费用,又容易引起贪污腐败弊端,詹时升认木兰陂十四家以酬劳陂田积谷积钱以备工程维修是个很好的经验,而且称赞和批准十四家子孙愿意改革由陂司来收貯积谷的方法,直接将陂田三分之一租谷收入官仓备用,以免陂司在收付过程中发生舞弊。认为十四家的经验“足补临川(王安石)司马(司马光)不逮者(没认识到的不足处)矣!”
序文作于王安石新法被高度评价和宣传的宋徽宗宣和中,但从语气看,对司马光认为兴修水利是“百害中获一利”只是婉转批评,并无辱骂训斥之语,依“足补临川司马所不逮者”一句来看,詹对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都持尊重态度,笔者认为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詹时升在这次“覆其事迹,检其田亩,刋为陂集”时,对民间已经流传成为神话的黎主簿和异僧冯智日的事迹也收入陂集,“间亦付识考之。”而前二份史料方天若《木兰水利记》和谢履奏疏中都未涉及神话。黎姓主簿与钱四娘之死有关,异僧冯智日在李宏筑陂时有策划指导的功绩,可见黎、冯两人与陂事有关但以前不处于重要地位。几十年后人们纪念木兰陂的创建者,对此两人的事迹逐渐加于神化。南宋刘克庄《协应庙记》中说:钱四娘跳水自杀后,尸身被水冲至渠桥乡沟口村,莆田县黎主簿前去查验,结果主簿“知其无他”(没有其他自杀的原因),乃叹曰:“钱氏室女(少女)负大志节,不克就而终!”(因理想不能实现而死),“言未毕旋暴中而卒。土人妄传以配女”。可见起初乡下人以黎主簿与钱四娘作阴婚相配,后来两人神象也一起在庙中受祀,詹时升作序时还是如此,但到南宋后期士大夫认为这样不妥,有损两人清誉,于是让两人神象另室而居。异僧冯智日原是李宏好友,为李宏选择陂址,插竹作为标志,相传唐末有人问妙应祖师“陂何时筑”?祖师作谶曰“逢竹(与“筑”莆仙话音同)即筑。”詹时升文中说黎主簿的事迹类似于宣勤,即忠实地执行官府派给他的职责;冯智日的事迹类似神仙(圮者)故事,詹时升对神话的产生持理智的看法,但初步认可了对黎、冯两人事迹的神化,写入陂集,而后世随时间延长,神话成份就不断增加。
史料来源和相关史事真实性的讨论
木兰陂历史悠久,自北宋熙宁创陂到今已近一千年,历北宋、南宋、元、明、清至现代,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生产效能,也一直进行着维修、改造,因此相关史料甚为浩繁,有关陂事,庙事的碑文不下百篇之多,还有更为大量的传说、诗歌、笔记。这些史料散见于明弘治《兴化府志》、明《八闽通志》、清《福建通志》、清《莆田县志》等书,《宋史》、《皇宋十朝纲目备要》、《宋会要》以及许多宋人文集笔记中也可找到有关木兰陂的零星史料,然而集中地收集木兰陂史料的古籍,是创陂者李宏裔孙和十四家裔孙分别所编的《木兰陂志集》。最早詹时升主持编成的《木兰陂集》早已失传,创陂者后代对收集保管有关的历朝诰书、官府文书、契据、碑传当然最为细心。李氏裔孙和十四家裔孙在明朝正德和清朝雍正间曾两次因争论木兰陂历史和神庙折迁等事兴讼,官司由兴化府打到福建省,再打到朝廷,两家都先后出有《木兰陂志集》。所以我们在讨论木兰陂史料时,对两家所出陂志都应给予注意。这里不妨将李宏后裔所编陂集及其衍生书籍称作“李氏陂集”,将十四家后裔所编陂集称为《十四家陂集》,以示区别。从陂集中两家讼词和各级官府间呈文、判词来理解,木兰陂工程元丰五年完成之后,元丰六年(1083)李宏去世,七年灌区民众请于兴化知军陆衍,在陂附近立庙(今钱妃庙处),祀李宏和钱四娘,林进士配祀,过后不多年,协创木兰陂的十四家当事者亦相继去世,绍圣四年(1097),其子孙又请于兴化知军饶方,以十四家木主配享。建陂四十四年后的宣和元年,兴化知军詹时升题庙额曰:李长者庙,并主持编写木兰陂集。南宋间多次重修陂、堤、渠、陡门和庙宇,著名史家郑樵写有《重修木兰陂记》,林大鼐写有《李长者传》,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知军赵与禋请准朝廷颁给协应庙额并封钱四娘为惠烈协顺夫人,李宏为惠济侯,著名诗人文学家刘克庄著有《协应庙记》记此事,南宋后期士人因男女之间关系的观念演变,认为钱四娘与李宏共祀有男女混杂之嫌,还认为以前以黎主簿和钱四娘阴婚之配有污神灵,于是以李宏和钱四娘神象分室而居,李在前室,钱在后室,还取消了钱、黎阴婚配合的安排。入元后又在廻澜桥旁原见思亭处改建协应庙,专祀李宏,配以冯智日和妙应祖师,以旧协应庙祀钱四娘(后世称钱妃庙),配以林进士,黎主簿和十四家木主。从两宋直到元朝200多年间,李宏后裔与十四家后裔都能相安无事,维持着木兰陂灌溉工程良好运行状态,入明,洪武年间朝廷又经地方上报再次下文认可了不科圭田的数量和李宏、钱四娘二人封号和庙祀。
李宏原籍闽侯县,入元后李氏后裔中入莆一支缺乏后嗣,明洪武四年,主持协应庙香灯事的李宝鲁思无后,以旁支李桂英继承庙事,此后又经六代,子孙旺盛起来,至明弘治和正德年间,又有李熊入府学为生员,已是俨然乡绅之家,此时李姓后裔与十四家后裔开始不和,亦演亦烈。李熊与莆田退休布政使郑岳、莆田知县雷应龙以及府学和县学的教谕们都较为熟稔,弘治十年(1497)有山东道监察御史周进隆为李宏祭祀事所上奏书中,认为林从世、钱四娘前筑陂以失败告终,对木兰陂无功不应祀;以后在周瑛编写的《兴化府志》中,又吸纳了李熊提供的一些碑传,十四家裔孙认为其中对原文作了改动,忽略和否认了十四家参加筑陂和开沟的事迹;正德八年,李熊在县府认可下,折去旧庙改建为李家私房,将钱四娘神象迁去见思亭以西较偏避之处,将林、黎和十四家木主丢弃;正德十二年,李熊又将其家所保存的封诰和文书,各种碑记文章向县令雷应龙要求出集,雷应龙交郑岳删节整理后成书,题为《木兰陂集节要》,雷应龙序中说:李熊把陂志初稿送他审阅,“予得之又自幸甚,持归夜读,若多繁舛相与,求删正于山斋郑岳”,要求郑岳把他认为的“若多繁舛相与”的文章和词句去除。郑岳序中说雷应龙“顾以卷中失于诰繁,属岳节取其尤者付之梓。”可见郑岳是对李熊所送各种史料加于节取,故名为“节要”,涉及颂扬蔡京、蔡卞兄弟倡修木兰陂的方天若《木兰水利记》被删去显因蔡京奸臣恶名;,涉及十四家协创和管理木兰陂工程的谢履奏疏和宋神宗批答被删除则因李氏陂集原有意否认十四家事迹,也和蔡京、蔡卞所提倡的王安石新法、新学被否定的原因有关。正德十四年,十四姓后裔上控省按察院,告李熊毁庙灭功,冒充李宏后代,说李熊之祖桂英仅是协应庙庙祝李宝鲁思收留的一个泉州浪人。讼争进行了三、四年,察院周鹓判李熊冒认李宏后代,将120亩香田收归官管以供协应庙香灯,李家是否继续照管协应庙听其自便;折去李家私宅以恢复旧庙祀祭钱、林、黎和十四家木主;《木兰陂集节要》与《兴化府志》中相关木兰陂的对原文不当改动之处,责令予以改正重版报查;李熊被罚米八石并革去衣巾。李熊之父李崇孝则在郑岳等人帮助下赴京告御状,力说其为李宏后裔是实,部批福建按察院和兴化府审明呈报,最后在莆田乡绅们的劝和下,双方以承认李熊一家为李宏后裔,仍然掌管香灯田以供协应庙香灯,李熊拆去新盖私宅,宅地由十四家自行复盖钱妃庙以供祀钱、林、黎和十四家木主,《木兰陂集节要》和《兴化府志》改正重印报查,李熊罚米和革除衣巾不变了事,兴化府分别发给双方照帖,李氏方面称为“复宗照帖”,十四家方面称为“十四家照帖”。清康熙初年余颺在《木兰志略》中说双方“互相诋毁,皆为蛇足,所谓两家当分就其咎也!”
经过这场官司争讼后,十四家后裔也组织编印了《木兰陂志集》,现存十四家协创功臣后裔重印的陂集中有余洛所著《木兰陂志叙》一篇,说:“乃考宋詹公陂集,及历代钦准、章疏、文移、宋志、国朝郡志、名公文集等书”,又得到了郡、县主官朱袞、李缙等人参订和认可出书,落款为嘉靖乙酋年(1525),即双方息讼后不数年,该陂集中收入本文所述三篇史料。莆田市图书馆所藏《木兰陂志集》中还有明末清初莆田著名士绅余颺所作文章二篇,落款康熙五年,可见十四家陂集在康熙时重修和印刷一次。现存陂集则可能印行年代更迟。
又过二百年后,双方子孙再起争讼,事起清雍正七年(1729)福建省编修省志,名《福建通志》,编修者原根据《莆田县志》将十四家事迹入《福建通志·孝义部》,而到第二年雍正八年,修志馆却上报福建巡抚说:十四家协创木兰陂和舍田开沟事迹入孝义部系误修,说修志修到选举部时,发现与十四家余子复数人相同的名字出现在南宋绍兴等年的进士及第者的名单中,于是认为十四家事迹为假,要求把《福建通志孝义部》中的十四家文字给予取消,这件事十四家后裔朱载等人认为是李氏后裔李正榛在修志馆中活动所致,朱载等人上书福建巡抚争辨此事,认为同名系偶合,列举了很多当地同名不同人的事例,并出示了十四家陂集作为证据,还说:“如十四家事迹为假,则历经北宋、南宋、元、明、清的几百亩不科之田从何而来?前钱四娘十万緍、林从世十万緍都连主陂都完不成,单靠李宏一家钱七万緍如何能完成主陂和长达三十多里的凿田开沟工程?”福建巡抚审阅了许多史料后,要求修志馆重新考虑,修志馆方面则提出十四家陂集为私家所出,李氏陂集经县令雷正龙和名乡绅郑岳所编为官集,对十四家陂集的史料真实性提出质疑,朱载等人则以明朝正德一案的控告和审结过程和结果上报,最后福建巡抚要求双方不再争论此事,一切照旧,不必改动,“各安其故,毋得异议!”他认为这“于长者李宏子孙何所益?于十四姓子孙何所损?而为此哓哓乎!徒见其多事耳!”
雍正之后,出有姚文崇、李嗣岱所编《续刻木兰陂集》,基本上沿续李氏木兰陂集节要,光绪时又有陈池养所编《莆阳水利志》,书中涉及上述十四家后裔官司争讼时,还能照顾双方观点,对双方陂集中所载传记中文字不同处有的予于注明。十四家方面在雍正后所出陂集《木兰陂志》上下两册,笔者仅见于今莆田市图书馆,在国家国图书馆和福建省图书馆目录中未见收藏,上述三篇史料即在《木兰陂志》上册中查到。
李氏陂集中虽没有收入上述三篇史料,但在明正德的两家争讼的所有材料中,不论两造和办案官方皆无一语加于否认,清雍正时修志馆人员虽说本馆所查新刻木兰陂志(指十四家陂集)乃出十四姓后人之手,此勅(指宋神宗赐田勅)另无载籍可据,但巡抚祁建批语却说得很客观:“宋知军谢履碑记中田亩数目言之凿凿也,舍田捐币,功亚李侯,去取不可不慎!”兴化府看语中也说:“查得莆邑木兰陂之建,始于钱妃、林从世,成于李宏,助成于余子复等十四家,开沟筑塘则十四家实专其力。倘无余子复等其人,则李侯后裔岂不争于当时,而肯容之于后代乎?”
作者认定上述三篇史料真实性的一个有力理由是:史料中所涉史事和当事人语境心境都与当时历史记载相符合,决非后代杜撰得来。例如宋神宗皇帝勅书中提到“朕即位以来,遣程颢等察农田水利”,此事发生在神宗即位不久的熙宁二年四月,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相(参知政事),成立讲议司,开始变法,程颢当时是王安石主持的讲议司属下,四月朝廷令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十一月,“诏诸路监司州县,如能劝诱兴修塘堰者,当议旌赏颁”。程颢曾经赞成新法,在―度王安石辞职在家时还臻书劝王复职,王恢复上朝视事,程后还登门相贺,以后才与王安石闹翻。宋神宗皇帝赐江宁府常平米事,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发生在熙宁七年七月,当时是为了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事,朝廷下决心加大力度整治太湖水利。神宗、王安石讲求农田水利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善漕运,防避黄河水害,但变法反对派对此持反对态度,司马光认为水利是百害中才获一利,苏轼曾上书辨论利害关系,认为与其劳民伤财,不如无为而治,反对派面对自然被坏力不取积极对抗和进取态度,而取消极忍受态度,对于积极奔波效力于水利工程的程昉、沈括等人,尽管成效卓著,却一再地都被反对派人土在工作上挑毛病,或在人格上无端攻击,何况人类在对抗自然灾害时原非事事能尽如预计,工作中时有可供挑剔处。连治水工程中出现的重大机械创造发明如铁龙爪的出现和使用,也被反对派极尽挖苦嘲笑。当两派激烈争辨时,王安石当然力主作为,神宗虽然也主张有所作为,但往往夹在两派之间,被反对派弄得头痛不已。因而勅书中有“谁报底绩?朕甚厌之!”句,难怪他对东海一隅的莆田木兰陂的成功,感到由衷喜悦,发出“是固十四臣者,体朕至意乃劝导诱激,尔实与有力焉”的赞叹和“盖尔不为子孙谋,而为国家谋,故朕既拨田酬尔勋,而并蠲赋为尔子孙计”的恩赐,还把兴化军谢履由通直郎提为承议郎。这种语境、心境决非轻易编造得来的。落款中孙固职位是“右丞相同知权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孙固在元丰元年闰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月改樞密院副使,四年正月知樞密院使,五年八月(或九月)乞解机务不允,勅书下时官职落款与史书所记相合。
不妨假定这一勅书为假,则编造肯定不是在两宋,因为这时还是宋朝天下,编造当代敕书要犯逆天大罪,如编造在元、明时,则只有熟悉史料的专家才能熟悉当时环境和行政模式,作为协创木兰陂捐田开沟的十四家的元、明后裔是很难编造得天衣无缝。致于数百亩不科之田则从宋至元、明、清历代相授,本身就是谢履奏疏和神宗批勅真实性的根本性证据。
方天若《木兰水利记》所记载蔡京、蔡卞倡修木兰陂事,言之凿凿,工程之先,“数奏于朝”,工程之中,“复奏于朝”,工程结束论功时有蔡“非诸人之领袖乎?”文末提此记“以贻蔡公诸人”,特别是“蔡家父子兄弟不曰入典中枢”句,决非十四家后裔所能杜撰。方天若作此记时距离他绍圣二年以榜眼及弟尚有12年左右,蔡京此时也远未显赫,所以方天若无特意奉承巴结蔡京之意,北宋亡,蔡京在南宋中期以后即名声很不好,十四家后裔应无自身利益需要去捏造蔡京倡修木兰陂故事的需要,所以方天若一文,应在李氏和十四家后裔都世代保藏,只不过明代李熊、郑岳、雷应龙在整理编辑《木兰陂集节要》时不予收入罢了。蔡京参与木兰陂的事在宋代史籍中屡有记载,其他史料也可进行印证,如陂成27年后的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星变,蔡京第二次罢相,太学生陈朝老和御史张克公乘机攻击蔡京十多事,其中就有“决水而灌田,以符兴化之谶。”在这前一年的大观二年,蔡京指示福建路转运使发民夫为木兰陂灌溉系统开凿新塘(后为地名),有莆田士人方轸(安乐里人)上封事弹劾蔡京:“臣与京皆壶山(莆田)人,谶云:水绕壶公山,今朝更好看。京讽部使者(福建路转运使)凿渠以绕山,臣以是知京必反也。”宋钦宗靖康中诸人弹劾蔡京,也有把修木兰陂“以符兴化之谶”作为蔡京罪状的。方轸之父方通与蔡京友好,曾得蔡京提拔,但方轸本人因持反对新法观点,上书论事反对新法,朝廷清查上书人政治观点时,方轸与其他四人遭到处分(见皇宋十朝纲目备要),方轸在蔡京第二次罢相的前一年,上封事揭露蔡京,封事攻击蔡京指示福建转运使使用民力凿通新塘灌溉渠道之事,全文见于《挥麈后录》,又见于《兴化府志》艺文志,方轸因此被发配岭外。南宋大儒林光朝有《木兰即事》诗:“济渡清源颂蔡襄,如京如卞亦同堂。兰水果符兴化谶,功比万安差雁行。可怜误国翻自误,身窜家流名垂锢。顿使行人口里碑,尽付当年诸大户。大户捧诏还自猜,莫是太师嫁祸胎?谁知财散身随显,何如身剖不藏财。昨过惠安探遗迹,今过木兰重叹息。莫云忠佞天懵懵,就此亦堪辨黜陟。”诗中说京、卞与蔡襄是同堂兄弟,京、卞倡筑木兰陂与蔡襄修洛阳桥(万安桥)的功劳相比,其实差不多。蔡京因被认为误国有责,就埋没了倡修木兰陂的功劳,都让给了当年李宏等富户去了,其实那些大户当年接到朝廷要他们参加筑陂的诏书时,还怀疑是蔡京要把灾祸带给他们呢!谁知道破了财去筑陂,会带来身后显赫和子孙享福的好报应,真是合算极了!明朝郑思亨辑莆田诗文40巻为《冈凤集》,收入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一文,并跋其后曰:“木兰一陂大半皆蔡京之力,蔡京造陂时官知开封府,累官至右仆射转司空,封鲁国公。”又说由于蔡京政治上被否定,“莆人遂讳京功,并讳天若记。予不以人废言,姑特存之。”身为修陂十四大户之一的余姓后裔,明代知府余文《重修木兰陂记》说:“水利之兴,自治平也,迨神宗采王安石之言,诏诸路劝修陂塘,又准蔡京之奏,诏莆阳协兴水利,时则侯官李宏倡之,吾家十四祖助之,陂之创也,自熙宁始也。”十四家陂集收入方天若此文是为了说明其祖先十四家协创木兰陂和捐田开沟,蔡京是否倡建木陂与他们在明朝时与李氏后裔争讼的目标无关。
詹时升《木兰志序》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关于水利的利害观的叙述,司马光认为水利是“百害之中获一利”,在他元祐中秉政时尽废临川王安石之法,只留水利一科,詹时升的这些说法不见于普通史书,后世统治者和士人为圣人司马光讳,不大谈司马光曾经对水利重视不够之事,王安石则极力倡修水利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措施。木兰陂建成后十四家在管理和维修机制上有创造,詹时升认为,司马先生和临川先生“有所不逮”(没有考虑到),詹时升的这些话也是后世人编造不出来的。
致于李氏陂集中不收入这三篇史料价值很高的文章,作者本人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李熊出自于私家利益的考虑,极力想还抹去十四家曾协创木兰陂和捐田开沟的事迹,二是参加勘定陂集的退休在籍高官和当地府、县官员如郑岳、周瑛、雷应龙等人出于忠诚于程朱理学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觉卫道心理,对牵涉到与有违“千古名教”的“奸臣”蔡京和王安石新法的材料宁可摈弃删除,也不愿兼收并蓄。十四家后裔为证实他们祖宗业绩,对如此重要和有力的史料证据,当然就不愿放弃。
作者认为上述三件史料是真实的,它们体现了北宋王安石新法实施过程中地方民众面对自然破坏力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为后世所罕见,应为后人所吸取。作为史料,也应予记录流传,使其免于湮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