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写给爸爸
逸兰原创
老爸来大庆检车了。
三百公里路,老爸开着他的宝贝小车,拉着我老妈,一路驰骋,顺顺当当。
进入大庆境的时候,我开始和老妈电话联系,给老爸指路。老爸开车来大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能顺利找来。可我仍是不放心,以自己搬了新家为由,执意要为老爸指路。
怎奈我天生路痴,虽也经常开车游走于这个城市的诸多大街小巷,对街边那些有特征的建筑和景物却几若视而不见。我曾经在走过八百次的公园桥上把车开上去,转下来,再开上去,再转出来,兜兜转转不知几圈之后仍摸不清要走的方向。窘得要哭。
和老妈把手里的电话煲到发烫,我仍然说不清他们现在在哪儿,老爸开始心烦气躁起来,还是老妈耐心,把街边的不动景逐一说给我听。终于听明白了一个地方,我驱车直往。
到了――我看到了站到路边雨中的我的爸爸妈妈,一对黧黑清瘦的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
第二天检车,一切顺利。爸说车有一点小问题,我们就把车开到了一家修理厂。修车的时候,老爸一边看着,一边抽空去附近的轮胎店,他想买几个备用的钢圈。他在两个店里出出入入,逢人就介绍我,“这是我儿子。”说得人家一愣一愣的:眼前这个人,明明是个雍容富态的女儿,这老爷子怎么一口一声“儿子”呢。可能我司空见惯的神情也感染了大家,大家的诧异也转瞬即逝了。这个老爹,他都叫我四十年“儿子”了,我能不习惯么。只可惜那天我着急出门,也没收拾一下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给老爹丢脸了。
第三天,老爹就张罗回家了,说家扔给扔给邻居看着,不放心,地里农活又紧,他的小楼还需加紧施工。
我又自告奋勇,要把老爹送到高速公路。中央大街一段,车行缓慢,好不容易开出市区,我说这下可以撒会儿欢儿了。正开得起劲,前面出现了收费站的指示牌。老娘一看,马上喊不对,就不可能这么快就到收费站了。我只好停车,问路,打电话。一番折腾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路。
把车停在路边,我要穿过大马路到对面坐公交返回的时候,老爹又把我揪住了。唠唠叨叨地跟我讲,要我在裤子上缝个兜儿,把钱和重要证件放在里面,那样丢不了。我也是的,爹娘来这两天,我就丢了两次包了。我这人美女无脑,就算有一天我出息到长出胡子来,也断不了让父母操心的毛病。
叮嘱完毕,爹娘仍是不走,竟是要看着我过马路。老爹还训着老娘,你操的什么心,她那么大孩子了,还不会过马路啊。说着老娘,他自己却不挪窝,就站在那看着我。我无奈,只好在他们的目送下,穿过马路,头也不回地走向公交站牌。然后,停住,回过头来,冲他们挥手。老爹这才拉着老娘,上车,缓缓地开走。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爹啊娘啊,我都四十岁了啊。
据姑姑讲,我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虽然胆小,但总能不失时机地在可允许的范围内任意妄为。
姑姑至今津津乐道: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啊,坐在炕上,还东倒西歪的呢,就巴巴着小嘴伶牙利齿地骂人;家里焖小米饭,你偏要吃苞米馇粥,你姥推开饭碗,就去邻居家给你要来;外屋地放着个老猪头,你怕那东西,可越怕越去看,看完就用力嚎哭,害得你姥爷把个老猪头东掖西藏的……
这样的事,在我的童年不胜枚举。“没见过那么惯孩子的!”姑姑谈起小时候的我,就愤愤不平。
这样的坏事累积起来,导致了一个结果的出现,那就是:爸爸打了我。
他打的方式也特别,他把我拎起来,扔到了柴禾堆里。
柴禾堆软软腾腾,我当然毫发无损,可这却引发了一场家庭战争。
姥姥姥爷大怒,要将我爸这个养老女婿赶出家门,因为他竟敢欺负到我这个宝贝太岁的头上来。我爸也犯了犟脾气,走就走,可必须把孩子带走。他拎着个小毯子,就来包我,姥姥姥爷就疯了一样来抢。这场家庭战争的最后结果,是双方妥协,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没法将我分成两半,而要舍开我,对谁都是要命的事儿,只好作罢。
春天来了,房后的老榆树结出了厚厚的榆钱儿。小小子儿们开始爬到树上去摘榆钱了。我上不了树,就在树下巴巴地等,期待着谁能施舍给我一串儿吃。可他们都不管我,我馋得不行,就哇哇大哭着回家了。爸爸就去爬树,掰下来长长的一段树枝,扛回家,放在外屋地,让我管够吃。我解了馋,又有了炫耀的资本,更可以把榆钱儿拿出去,给那些同样上不去树的女伴儿们吃,让她们跟我玩儿,自是得意得不行。
老爸出身地主家庭,没捞着像传说中的地主那样作威作福,却尝透了身为一个“地主崽子”的苦。我在读莫言的《生死疲劳》时,更加了解了那个时代,也似乎看到了我爸爸曾经的苦难生活。可惜我没出息,不能为爸爸的苦难人生写出点出色的文字来。
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爸爸心地良善,脾气却暴躁,反抗性极强。这点,我的女儿,写在了她的作文中。
爸爸不认得几个字,似乎也不会写字。我见过他写得最多的一个字,是“正”字,他画在墙上,用来记别人赊欠的牛奶帐的。
我小的时候,就总有小画本读,是爸爸从奶奶家背来的。我爱读它们,可总是经管不好,要不了多久,我那些喜欢的小画本就长了翅膀,飞到哪个小伙伴家去了。害得我再想读的时候,还得低三下气地去跟人家借,好像并不知道那曾经是我的东西似的。我的爱读书的习惯,可能就是在那时养成的吧。没有文化的老爸,执拗地把他的理想灌输给了我。使我这个忠诚的女儿,不知不觉,竟把读书当成了毕生的事业。
小时,爸爸总是用自行车驮着我上街,一半是玩,一半是给我看病。
爸爸带我逛公园,看电影,这些我现在都记不大清了。妈说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动物,看过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电影。我看《红楼梦》的时候,说什么也不在影院里呆,不爱看。我诧异,竟还有这样的事,多年之后,这《红楼梦》可是我的枕边书啊,看得很多情节都能成诵了。爸还给我买玩具,说我不喜欢娃娃,就把枪啊棒啊小飞机什么的都给我买回家。可惜我终究不会经管东西,多好的玩具,玩一段时间之后,就都成了别人家孩子的了。
还有看病。我从小体弱,这肯定是事实。但具体有什么病,就连爸妈也说不清楚。最常见的情况是:我又病了,而且似乎病得不轻。爸就急忙用车子驮着我,到街里去给我看病。看了一通之后,连那最有名的老中医也说不清我得了什么病,爸给我买点好吃的,就驮着我回家了。我的病也就好了。
我记得一个最清晰的细节,爸爸骑着车子,我坐在后座上,一路哼哼叽叽,不知是生病,还是哼着玩,反正就是哼哼叽叽。
哦,那坐在爸爸身后,哼哼叽叽的小女孩。
爸爸也有不乖的时候,于是,我就真病了。
那年的六一,爸爸竟然不陪我去公园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妹妹,但妹妹似乎还小,她还不知道公园好玩儿。爸爸和两个舅舅要忙地里的农活,竟然没人理我了。我就哭,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无奈,家里协商,结果是,让妈妈用送牛奶的车子驮着我先走,爸爸趁天凉,铲完几根垄之后,再去公园陪我,反正公园里的运动会得八九点钟才开始呢。
那天早上下了小雨,妈妈骑着笨重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两大桶牛奶,前面横梁上坐着我。上了大桥之后,刚蹬起来,走了没几步远,车子就倒下了。我摔得并不痛,挣扎着往起爬的时候,却发现糟糕了,我的右腿直不起来了。我一站,它一拐弯,我再站,它还拐弯,直不了了。我大哭,喊妈妈,妈妈这才发现事情的不妙。她惊慌失措,把我扔到大桥上,就跌跌撞撞往爸爸干活的地里赶。
我的身边很快围了一群人,大家七嘴八舌。
爸爸跑来了,顶着小雨,趟着泥泞,跑得不管不顾。
我的腿断了,右小腿断得利利索索。医生说,如果我再往起站几下,断了的骨头就要从皮肉里扎出来了。接骨手术之后,我的腿很痛,夜里大声哭叫。爸爸守在我身边,抱我到这儿到那儿,把我拉屎撒尿。还得一天几次喂我吃云南白药。我有腿好了之后,家里的云南白药瓶装了满满一大洗衣盆呢。
这样的故事,太多,够我一生回忆。
……
可惜我的人生之路,走得并不顺当。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浮华与物质方面,却几乎一无所有。
于是,也有医生给我做了诊断:我没有一个好爸爸。
当然,我不承认这一点!
我承认我的爸爸偶尔暴躁,可暴躁的爸爸反倒能养育出千娇百媚的女儿来。
爸爸爱吸烟,但只抽家里种出来的旱烟叶儿。爸爸爱喝酒,但如果我不坚持,他就会买最便宜的散酒喝。酒量也不行,喝点就多,然后,就有点云山雾罩,有点胡说八道了。
我的理解,是爸爸实在不会表达。
他说不清他对我和妹妹,有多惦念有多担心,他说不清他的人生之路有多辛苦有多迷茫,他说不清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事情,他羞于怯于表达他对家人对世界的诸多情感。于是,他就用变了调的语气,用走了形的方式,表达他自己。如果你陷于他表达出来的字面,你就和他一样误入理解的歧途了。
我的爸爸,不是不爱,只是不会爱。
如果你看到了我爸爸盖的大房子,看到我爸爸种的庄稼地,你就能理解,他是多好的一个农民,多好的一个男人了。
我家的房子,几经变迁。
最初是马架子,然后是平房,再由平房发展成一面青(就是农村那种表面贴钻的平房),然后是现在的大四间砖瓦房。后来,又把院子都铺上了水泥。秋天的时候,我家的院子是自家与邻家的晒谷场,夏天的时候,我家的院子就是邻人们闲坐聊天的好去处。
后来,老爸又在院子的南面,盖了马棚车库,马棚里有好马,车库里有轿车。这两年,老爸又在马棚车库的东面,复制了同样的几间楼座。今年,老爸就开始盖楼了,二层楼。他的房子,永远遥遥独领那个小屯子的潮流。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从来都找不到自家的地,但只要走到我家地的附近,我就能从那庄稼的颜色辨别出我家的地来。因为爸爸种的庄稼,从来都长得黑绿黑绿的,那是上了大量农家肥的结果。
记忆中的冬天,爸爸从外面拉完农家肥回来,戴着小破帽子,脸冻得青红,清鼻涕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他一边擦,一边瞅着我咧开嘴笑。
现在,六十多岁的爸爸,我仍然看不出他和二十年前有什么两样,长年干农活,他不发胖,依然硬朗。我领他检查了一下身体,从头脑心脏到肝胆脾肾,一路查下来,竟然一路绿灯。这种身体状况,是多少养尊处优的身体望尘莫及的。
我爱爸爸,起初爱,永远爱,深深爱。
我接受我是他的女儿,他是我奶奶的儿子,奶奶,爸爸,我,我们都太不完美的现实。有怎样的人生,我可以试着去改变,但我不恨。
父亲节了。我不懂洋节,爸爸更不愿意过洋节。但今天的报纸上,刊了莫言写给他老父亲的一封信,今天的报纸,因父亲节而少了许多喧哗的内容,让我想起来我朴素的,并不完美的爸爸。
于是,深深感恩,深深想念,那远在家乡的,仍在固执地执拗地偏执地构筑他理想的房屋的,我最亲爱的人。
我的爸爸!
附:
莫言写给父亲的信
大:
自从家里安装了电话,再也没有给您写过信。最近刚写完了一部名叫《四十一炮》的小说,胡编乱造的故事,与家乡无关,更与村子里的叔叔大爷们无关。自从在《红高梁》里使用了村子里人的真实姓名惹得人家不高兴后,我汲取了教训,再也没有犯这种错误。今年春天北京闹“非典”,我们被封闭了三个月,憋得慌,很想回老家去,但听说从北京到山东的人,先要隔离半个月,怪麻烦的,只好罢了。我知道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家中已经吃上了用新麦子面粉蒸出的馒头了吧?我们在这里吃的面粉,都是陈年麦子磨的,其中还添加了增白剂什么的,白得发青,不好吃,没有麦子味。想起老家的馒头和大葱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葱也不好吃。北京管什么都不好吃。北京的大蒜也不够辣。这次闹“非典”,山东一例也没有,我坚信这是吃大蒜吃的。昨天高密的王大炮来了,扛来了半麻袋大蒜,紫皮,独头,辣得很过瘾,“后娘的拳头独头蒜”。他说前几天去看过您,说您身体很好,我们很高兴。中午包饺子给他吃,白菜猪肉馅一种,胡萝卜羊肉馅一种,都很饱满,煮出来白胖,小猪似的。捣了满满一臼子蒜泥,我捣的,加了酱、醋、香油,味道真是好极了。
大,我们家那盘大石磨还有吗?千万保存好,别被人弄了去。将来找个石匠琢磨琢磨,支起来,买头小毛驴,拉着,磨新麦子。石磨磨出的面粉,比机器磨磨出的好吃。高密火车站前,有一家卖石磨火烧的,面特别硬,很好吃。但我知道他们使用的面不是用石磨磨的。将来咱们自己磨。
还有那柄腰刀,可别当废铁给我卖了。我听俺爷爷说那刀是毛子扔下的,也许杀过人的。
我前几年回家,跟俺二嫂子要那把刀,她说不知道让大藏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咱家还有两把铁锏,很沉,就是秦琼使用的那种武器,后来就见不到了。听说是被一个表叔拿去了,还能找回来吗?大,您帮我安一把小锤吧,这里有核桃,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
前几天父亲节,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父亲的严厉》,写得不好,但还是抄给您看看: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们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他既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是啊,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怕父亲。我们弟兄们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我们弟兄们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我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瘳人毛。
我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
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怀里撒娇。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屁滚尿流吗?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们说:你爹早就后悔了,。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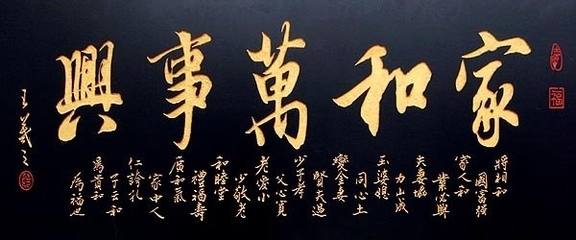
大,文章写得不好,您看了不要生气。今年春节我们会回去过年,您能做点黄酒吗?用黍子米做,不要用地瓜。另外告诉俺二嫂子,让她用酱包上几个地瓜放着,我好久没吃地瓜咸菜了。
无论是谁,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官多大,在爸爸面前,你都是小孩子,爸爸永远都是那个高大的,让你仰止的,爸爸。
附:女儿作文中的姥爷。
他是位性格慈爱的人
我的姥爷是一位慈爱的人,只是,你从他的外表和语言上实在是看不出这一点来。
姥爷的头发很短,长长一点就剃了光头。因为长时间在地里干活,他的脸被晒得很黑。他中等个,干瘦干瘦的,但是很硬朗。他说起话来很豪爽,但有点粗鲁,尤其是喝酒的时候,都有点说胡话了。
上面写的这些,可能让大家感觉到我姥爷不是一个慈爱的人,而是一个粗鲁的人了。但是,你看了我下面写的事,就会知道他有多么慈爱了。
姥爷会干木匠活。我在看电视时,看到了爬犁这个东西。看着电视里的人坐着爬犁在雪地里“驰骋”,我动心了,真想去坐一坐。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可是妈妈说,在城市里哪来的爬犁呀。我很伤心,沮丧极了。
有一次妈妈打电话给姥爷,唠着唠着,无意中说出了我想坐爬犁的事情。姥爷听了后说:“没事儿,不就是爬犁么?我给她做一个。”姥爷让妈妈把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是想坐爬犁吗?等着,姥爷给你做一个。”听了这话,我以为姥爷是为了让我开心,才故意这样说的,也就没放在心上。
等回到了姥爷家,我看到姥爷在忙乎着什么,问姥爷,姥爷说:“我在给你做爬犁啊。”原来姥爷不是在逗我开心,而是真的爱我,要给我做爬犁呢。
几天后,爬犁做好了。姥爷拽着爬犁绳,拉着我走,越走越快。我玩得可开心了,也感到无比的幸福。有这样的一个姥爷,真好。
这就是我的姥爷。虽然我只写了一件姥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它们让我感到我姥爷有多么慈爱,有多么爱我。我很幸福。
节日快乐,我亲爱的,爸爸。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