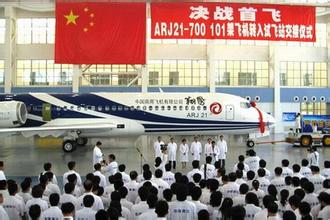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博士1995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退休,目前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社区与区域规划学院的荣誉教授(2001—)。1955年,弗里德曼获得芝加哥大学(UC)规划教育和研究系博士学位。此后50年来,他在政府规划部门、学术界和私人咨询公司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弗里德曼博士早年曾经在著名的田纳西流域发展局(TVA)从事区域规划,也曾代表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在巴西和韩国参与规划工作,实际工作经验使他对城市发展问题有着深入而直接的理解。在学术界,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筑与规划研究生院城市规划系的奠基人,并在1969-1996年的14年间担任该系的系主任。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智利天主教大学(PCU)、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UM)等大学担任教授。弗里德曼博士同时也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规划顾问。由于他对规划学科的贡献,1988年他被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授予杰出规划教育奖,并曾经获得智利天主教大学和德国多特蒙德大学荣誉博士的头衔。
弗里德曼早年曾经参与过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项目——田纳西流域的区域发展规划。他在学生时代的几位思想上的导师包括塔克威尔(R·Tugwell)等,都是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带有相当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相信市场有盲点而政府的合理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而规划则应该有社会作用,应该代表政府引导社会的合理发展。其后,1930年代到1940年代从德国流亡来美国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又带来了他们面对纳粹暴力而增强了的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如曼海姆(K·Mannheim)和波普(K.Popper)。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乃成为有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国际讲台。
弗里德曼的规划生涯漫长而丰富。从1955年获得规划博士学位以来,他在政府公共规划部门、私人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过规划工作的经验。长达50年的规划实践,加上不倦的学术探索,为的他规划著作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弗里德曼的著作思想体系恢宏博大,立论精辟清晰,每每发人深思。同时,弗里德曼也是一位诗人,他自己曾创作及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诗歌作品。他的文学修养和诗人情怀从他的笔端流露,表现为著作中遣词造句内蕴涵的激情,以及文章意境中洋溢的诗意。
弗里德曼的著作包括14本专著,11本合著,以及150多篇论文、文章和评论。其中包括国际规划界认为经典的《“执行规划”理论》(1973)、《公共领域的规划》(1988)、《为市民的城市:全球化时代中规划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M·道格拉斯合著)、《城市的前途》(2002)等。近年来,弗里德曼先生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的城市转型》一书中,他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见解(该书正在准备出版中文版)。他的著作大致集中在三个主题:城市和区域规划,规划理论,全球化及世界大城市问题(包括他近年来感兴趣的中国城市发展问题)。弗里德曼的全部著作都表露出五个明显的特点,即他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具有的历史观点、哲学观点、文化观点、比较观点、以及综合观点。
1历史观点
和规划界其他的著名前辈如芒福德(L·Mumford)一样,弗里德曼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他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城市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地提出所谓的规划对策。他认为任何城市不可能脱离它存在的文脉,脱离它根植的文明,所以研究城市规划不可能不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甚至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在1988年发表的经典规划理论著作《公共领域的规划》一书最充分地说明了他的历史观点。在该书中,他勾画出了一条两百年来人类追求美好社会不懈努力的历史主线,而规划则是这条主线中的一股,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规划师所做的一切,应该符合从历史高度俯瞰而仍然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美好的社会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当时当地一个美丽城市的外壳。
《重温规划理论》是弗里德曼对50年来美国和欧洲规划思想的历史回顾,目的是讨论困惑规划界的一个中心问题:什么是规划学科的核心?为什么规划理论仍然不能对规划学科的定义达成一致?在规划行业的具体业务已经取得社会公认的今天,对于某些规划师而言,这样的问题也许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规划似乎就是从事决策者所喜好、市场有需求的物质建设,不必近乎苛刻地着意于规划师自身的社会定位。弗里德曼不这么看。他认为规划的理论定位,规划师对自己社会功能的认定,都极其重要,因为如果规划师没有对自己社会功能的自信,就无法理直气壮地进行工作。弗里德曼认为:规划理论面临的挑战在于四方面的看法不一致:在定义规划理论的目标时看法不一致;对规划是否可以和制度及政治环境分开看法不一致;对规划研究的模式看法不一致;对如何论述规划和权力的关系看法不一致。《重温规划理论》一文围绕这四方面就如何认识规划的社会功能作了论证。他的结论是,随着社会变迁,规划师的工作发生了明显变化,起码在欧美国家,规划越来越成为一种协作和协调,所以“规划作为社会整体中一只调停的手,不断靠近政治学的层面。”
《美好城市:为乌托邦式的思考辩护》的题目就点明了弗里德曼的理念。他指出:在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延绵两百余年乌托邦式的思考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乌托邦式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选择一条通向我们相信正确的未来道路,因为它的具体意象来自于那些我们高度珍视的价值观。”通过对规划历史中乌托邦传统的回顾,他强调规划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内心深处升起的正义冲动和追求真理的欲望,规划工作就会沦落为一门谋生的手艺,而规划师也将和芸芸众生一致无二。他特别在文章中就“谁的城市?”为题,讨论了公共利益问题。在“公共利益”甚至作为一个理念提出都可能受到攻击的今天,弗里德曼在2002年写的这篇文章中说:“和所有这些高水平、目空一切的评论家们相反,我要强调继续为城市寻求公共利益状态的必要性。”因为城市发展的历史,人类进步的历史,都证明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正确性。
弗里德曼的历史观点并不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在本期介绍的《世界城市的未来:亚太地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作用》一文中,弗里德曼指出:“历史对城市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城市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结果”,所以也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对城市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在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中国的城市转型》(China′s UrbanTransition)一书中,他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历史观点。他认为中国的转型不能仅仅理解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转型(Transition),而且应该理解为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伟大文明的变形(Transformation),因此必须把中国的城市转型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
2 哲学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弗里德曼的主要规划理论著作都可以看作是哲学著作。《公共领域的规划》以极大部分篇章讨论哲学史和哲学问题;《重温规划理论》重温的也是二次大战以来哲学思潮的演变;《美好城市:为乌托邦式的思考辩护》同样围绕哲学的基本命题。他在规划著作中引用哲学著作、讨论哲学家的观点,几乎和讨论规划师著作的篇幅一样多。早在1973年,弗里德曼就写过一篇文章《公共利益和社区参与:重新构筑公共哲学》(ThePublic Interes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Toward a Reconstructionof PublicPhilosophy),直接将规划问题提升到哲学问题的层面来讨论。应该说,将规划理论和哲学理论并列,是近年来一些重要规划理论家的共同认识。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两位规划系主任卢德温(L.Rodwin)和萨亚(B.Sanyal)在《论城市规划行业》(TheProfession of CityPlanning)一书中把规划学和哲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放在一起讨论,比较这五门社会科学从1950年到2000年的变迁,就是例子。其理由是:只有哲学家才能超越具体事件而以“理性的眼睛”批判世俗,审视世界,从而把握人类思想和行动(包括城市建设行动)的本质。弗里德曼曾经提到自己受到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波普(K.Popper)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确实反映出他的批判主义的哲学观点。虽然胡塞尔说过“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往往(被认为)是个坏公民。”但弗里德曼正是通过他对现存秩序的不断质疑,提出了对未来新城市、新社会的美好理想。
在《生活空间和经济空间:区域发展的矛盾》一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生活空间和经济空间这对矛盾。他认为生活空间是具形的、有边界的、连续的、有历史、有不同文化价值的空间。而经济空间则是抽象的、不连续的、和历史无关、服从于“统一的价值观”(追求利润)的空间。这两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他把这种分析方法称为“一个辩证的研究框架”。这里,我们读到的几乎已经是“正宗的”哲学论述了。
在城市和规划研究中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剖析问题,跳出具体琐碎的事件而抽象出问题的实质,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本质,从根本上发现城市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
3文化观点
弗里德曼认为城市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而且是广义的人类文化、文明的物化体现。对此,我理解为:城市行为乃是文化行为,建设城市就是建设文明,所以在讨论规划问题时,必须十分注重所涉及城市的文化、所代表的文明。弗里德曼在写作《中国的城市转型》时,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例如,他在考察了中国古代“衙门”的作用后指出:传统中国行政体系中最基层的单位是“县衙门”。县太爷代表远在京城的皇上,却往往只驻足于县城内,极少走出城门“下乡”。县太爷们只关注两件大事:收税、治安(审案)。在县域内、尤其是在村镇内的大量其他公共事务,如修桥筑路、挖井引水、消防救护等等,大都依靠“地方士绅”出力管理。他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具有现代城市管治“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共同管理城市的内涵。这个见解不但新颖,而且对当代城市管治的讨论有相当的启发。弗里德曼认为:发达的公民社会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将是人类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参见他和M.道格拉斯在1998年合著的《规划的新政治经济学:公民社会的兴起》)
在《建立在优势之上:可持续发展中城市邻里的角色》一文中,弗里德曼分析了中国城市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街道委员会”的功能演变,建议通过加强街道委员会和居委会的功能构筑新型的地方管治模式。这无疑也是建立在他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理解的基础之上。
4 比较观点
弗里德曼丰富而漫长的规划工作经验,使他得以在研究问题时采用一种比较的观点。在时间上,将历史和当代比较;在空间上,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和其它国家、其它城市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的异同,从而提出结论。
例如,在《建立在优势之上:可持续发展中城市邻里的角色》一文中,他引入巴西和日本的社区管治方法,由此作为中国街道委员会和居委会工作转型的借鉴。在《重温规划理论》中,他比较经典规划理论和今天的规划实践,作为当代规划理论发展的借鉴。他的其他著作,如1986年发表的《世界城市的假设》(TheWorld City Hypothesis,其中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世界城市理论”)等书中,也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引发新的观点。
5综合观点
弗里德曼主张以综合的观点全面分析问题,反对只抓一点、以偏代全的政策倾向。在《世界城市的未来:亚太地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作用》一文中,他重温了世界城市形成的空间动力,认为: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四个主要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一,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第二,全球性的经济重组以及城市对此的应变能力;第三,城市之间的理性竞争;最后,可持续的公共政策。这样的理论框架包含了政府、企业、社会等外部和内部的多方面因素,而不是盲目强调通过“增强城市的竞争力”来决定城市的未来。
在文章中,他特别指出:“无论在城市—区域层面,还是国家层面,不顾社会和环境代价而最大程度地追求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除了经济上的不合理外,他认为这种过于重视物质增长的倾向“导致了公共道德的下降”,危害到迈向民主社会的进程。所以“(城市)发展规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建设基础设施决不是所需的全部,甚至不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全体市民的长期公共利益。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弗里德曼作为一代规划宗师的广博胸怀和对规划工作社会责职的深刻理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