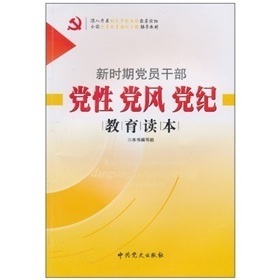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对中国的影响
香草山
洋务运动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教育在近代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单一封建正统文化独尊的局面,为近代文化重建创造了先决条件;兴学校,废科举,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大量西文书的翻译出版、报刊的创办和出版机构的成立,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所遵循的“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形成;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求学和开办学堂,培养了掌握科技知识的新兴人才。
一、开办“新学”加速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崩溃并冀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赖以产生和发育的东亚大陆疆域广大,回旋余地开阔,由于周边各类自然屏障的围护,使其远离其它文明中心,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的半封闭性对文化物质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制度又从经济、政治诸侧面强化了这种封闭性,农业经济下追求稳定、安逸的心态和自我禁锢、夜郎自大的心理根深蒂固[1]。而以农业为主,注重实际,讲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特性,使中国古代贤哲一向提倡“君子务实”,久而久之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玄想。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基于实用的农学、天文学、医学等十分发达,而纯科学性的玄思,不以实用为目的的探求自然奥秘的文化人极少。就生活方式而言,追求生活的稳定和安定,无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的欲望,具有一定的保守性[2]。
洋务运动之前的封建中国的教育是以儒学为核心的“选仕”教育。在教育的体系上,基本是以私塾为主,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在教育的内容方面,多以“四书五经”为主体,很少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在考任制度上,实行“科举制”,只看八股文写得如何,缺乏对人才的全面评价。
然而,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阶段,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大量可贵的成果。正如洋务派巨擎张之洞的弟子张继煦所评论的“虽为公(指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种豆得瓜”的洋务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变革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尤以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的影响最深。
由于日渐纷繁的中外交涉,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专门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不久,奕诉与桂良、文祥三人联名上书,奏请开办外语学馆:“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妥协?”(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朱有献主编) 1862年6月11日,英文馆正式开课。不久,学馆定名为“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之后,同文馆内先后设置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1876年,馆中正式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学生还要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以及译书等课程。后又添设格致馆、翻译处、东文馆。这样,同文馆变成了一所以外语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训练制度均与旧式书院大相径庭,初步具备近代学校的特点。洋务派创办的外语学馆,除了京师同文馆之外,还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和广州的同文馆。同时,一批军事学堂也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的纷纷建立,开辟了中国近代军事科技教育的新领域,也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它们为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这些洋务学堂除了广泛学习西学知识之外,还采用了绝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法、风格与模式。在新时局、新思潮的逼迫下,清政府对科举制度及旧式书院、学塾进行了局部的改良,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形式都渐渐接近新学堂。在此影响下,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停科举以广学校”,这样从606年(隋大业二年)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这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标志着以儒学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科举的废除,扭转了教育的方向,开始了由八股取士向全面培养人的素质的过渡。
新学的开办,虽成效不够显著,但它改变了千百年来重文轻理的教学弊端,使得运行逾千年的沉闷死板的“科举制”迅速崩溃,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文化教育制度上奠定了基础,尤其在课程及教育模式上的改革。
二、新型教育模式和课程为中国教育开辟了新道路
与封建科举教育相比,新学在课程设置上有明显的进步。京师同文馆最初只设英文馆,一年后,增设法文、俄文馆。此时课程内容只有语言文字,没有涉及科学教育内容。1866年12月,增设天文、算学馆。1867年6月21日,天文、算学馆正式举行招生考试。自此,京师同文馆不再是初级的外国语学塾,而成了综合性的实用科学专门学堂。西方科学教育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壁垒,终于进入中国课堂。此后,同文馆的课程,大加扩充,进行极为顺利。许多自然科学都逐渐的介绍进来。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上任后,按照美国的学校教育模式改革京师同文馆,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规划,为不同程度的学生拟定八年制和五年制课程表。如八年制课程设置[3]: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词句。二年:浅解词句、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八年制课程是为年纪稍幼、“由洋文而及诸学”的学生制定的;对于年纪较大,无暇肆及洋文,仅能借助译本学习各科的学生学习五年制课程。这些课程表除了讲求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注意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外,还突出了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特点。它标志着近代课程设置开始摆脱传统课程设置的偏狭、单一和陈旧,逐步向西方先进课程体系靠拢。在学习西文的同时,开设算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科学教育在这些学堂中都占有很大比重。1866年清末最早的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创办。船政学堂先后设有制造、驾驶、绘事、艺圃、练船和管轮等六个专门学堂,学制五年。在课程设置上,以学习和掌握外语、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由于学制较长,船政学堂比语言学堂更系统广泛地向学生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其中外语和数学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这是洋务派认为要“借法自强”,“必通泰西语言文字”并且是“必由算学入手”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
与课程设置的更新一脉相承,洋务学堂中的科学教育的教材也发生巨大变化。如:
1.数学。洋务运动时期的数学教科书主要有两方面来源,即中国传统算学著作和翻译著作。主要有李善兰、华衡芳及西方传教士翻译的数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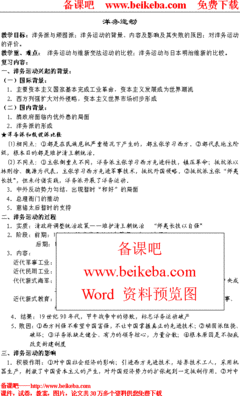
2.物理学。关于物理学知识介绍的译书著有《格致入门》(1866年) 、《格致须知》丛书(1882-1894年),其中有《气学须知》、《声学须知》、《重学须知》、《光学须知》等。
3.化学。京师同文馆中最早的化学教材是化学教员法国人毕利干自己编译的《化学初步》、《化学阐原》。19世纪末在洋务学堂中流行的化学教科书,是由徐寿、傅兰雅合译的六卷本《化学鉴原》(1871年)。
4.天文学。1859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原著是赫歇尔的《天文学纲要》),对包括哥白尼在内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进行较全面的介绍。《谈天》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太阳系的结构以及太阳系各行星的运动规律。此外,对万有引力概念、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等也都有论述。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也有所介绍。80年代后,各地兴办了一批海军军事学堂,这些学堂中都开设了天象测量、经纬度测算等航海天文学的有关课程。
5.地学。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地质科学缺少独立的学科结构。鸦片战争之后,为了解西方世界,中国有识之士,编著了一批介绍西方地理概貌的著作。如江文泰编著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1844年);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1848年)等等。葡萄牙人玛吉士(Martins—MsrquezJose)编译了10卷本的《外国地理备考》;英国人幕维廉(MuirheadWilliam)编译了《地理全志》一书。其中大部分为自然地理学范畴的知识介绍,内容颇为广泛。地质学方面,作为铁路矿山等路矿学堂以及其他需要讲授地质学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流行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是《地学浅译》。《地学浅译》由华衡芳和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共同翻译。此书第一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
6.生物学。洋务时期影响较大的植物学著作是李善兰和传教士韦廉臣(Alexan2der Williamson)合译的《植物学》(1858年)。此书介绍了西方18、19世纪以来,特别是显微镜被使用之后形成的以器官形态和功能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近代生物学知识,这对中国传统的生物学知识而论,都是全新的内容。动物学的译著有傅兰雅编译的《动物需知》(1894年)。另外,在各种编译的农学著作中也有一些动、植物知识。
虽然洋务派缺乏重视科研的主导思想,缺乏科研的社会环境和机制,没有把科技的引进和本国科学研究和实验相结合,使得科学只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国内传播。但在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的科学教育,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此时的科学教育具有种种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相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洋务运动时期科学教育的贡献是意义深远,不可磨灭的。(待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