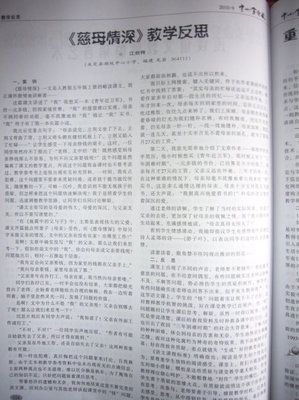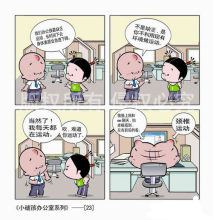姐弟情深
文蓝雪儿
上篇祸兮福兮
“石头也能卖钱,石头也能卖钱?”
一整个下午,普志就像失了魂似的,痴一阵,笑一阵,妻子姜翠花提醒他上山收荞麦,说了几次他都疯疯癫癫的,自言自言着。
九十年代初期,荞麦算是山里的摇钱草,山乡有的是土地,荞麦秉性善良,不挑肥拣瘦,在哪里都能开花结籽。荞味微苦,性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山里人生活不算富裕,不过很少生病也是事实,这也许是与常食荞麦有关吧,常吃,心火不旺,心平气爽。普志家栽了3亩,还养着十几只羊,5头牛,家里有个什么紧急情况,拉只羊去买了,就解燃眉之急啦。
普志何许人也,蜻岭县者么乡人,今年26岁,妻子姜翠花小他一岁,后山洼娶的。小两口打理十几亩土地,50多岁的老母亲普丽梅照料牛羊,每天早上拿上花鞋垫,与隔壁张四嫂一同去放牛,明为放牛,实际上是牛羊一起上山的,羊跑得快,不像牛那样老实本分,羊专找草尖儿吃,虽然吃的好了,但是体能消耗很多,要长肥还真不容易。还有个刚出生的儿子,小名叫小程程,儿子活泼可爱,走出去村子里,他心里觉得喜滋滋的,别看他自己没多大出息,可他还有个姐姐是山里的金凤凰呢,刚考进上蜻岭师范,出来就是当老师,老师啊,时间一到,就数钞票,多神气。
普家、张家是多年的邻居,关系一直很要好,然而,就在前几天,因春耕时放水的事,两家有了芥蒂,农村的水务纠纷,事情不大,却会影响团结,社区领导还没有找到机会调解。所以这几天两家放牛都有是各走各的,可是人争气,牛不争气啊,更可气的是两家的牛好上了。那天下午,两家本来不是一起上山,可牛们常在山上跑,哪能不识路,尤其是时常幽会的两头牛,剩主人不注意,偷偷跑在一起卿卿我我,把张四嫂气得够呛,骂起牛来,骂道气性头上,不管不顾,也骂了姜翠花,说那头母牛就和主人一样风骚,而普丽萍年轻时候是有料的,因此最忌别人在她面前说风骚,两个女人起了口角,张四嫂说话刻薄,两个牛也不管了,开口对骂。普丽梅心性小,回家以后就病倒了,休息了两天,就争执着要山上,在山上一脚踩空,挣得个腰椎骨折,到了县医院检查又外加一项子宫癌。经治疗切除子宫,病情是稳住了,可是家里欠下许多外债,妻子姜翠花生孩子时就捞下月子病,找了草太医开中药,药土锅一直没有断过。
这家,哎,以后的日子咋过啊。
普妈妈出院以后,普志家的生活跌入低谷,本来供妹妹普艳艳读师范,积蓄就一天天见少,家里的那几只牛羊也卖得差不多了,给母亲看病就显得捉襟见肘。普艳艳很懂事,几次哭闹着不读书了,说要省下钱来给母亲治病。母亲也说自己得了癌症,是前世造孽过多,老天爷对她的惩罚,不看了,不拖累儿女。两个女人一台戏,听谁的都不合理,也不合情。普志的压力很大,他走路都想踢踢脚下,看能否捡到钱。
再说,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生产力大大提高,大批的农民工涌向城里,衣食住行的问题就压到了城市身上,几年间城里盖起了许多新房子,普志也想进城打工,可是家里两个病人需要他照料,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目前这状况,顶梁柱不在,行么?
事情总会有转机的,何况好人有好报。村里有个叫张二狗的人,张二狗,原名张其冰,向来懒惰,就钻营着到哪里可以变出更多的钱来,为了钱,不择手段,六亲不认,扎到钱眼里了。他在家里排行老二,加上德性不好,村里人都叫他张二狗,久而久之,别人也忘记他的大名了。村里没几个看得上他,见了他就远远绕开。
张二狗在外面跑了几年,多少有点见识,他看到城里盖了许多房子,而盖房子是需要石料的,他们山窝窝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靠石头来挣钱,真是好主意,可是炸石头是要费神费劲的,对了,找普志,一来普志人老实干活肯下力气,二来,他家里正需要钱,就是村里的人都看不起他,不愿与他合作,而普志断没有不应的道理,人穷志短嘛。
张二狗从城里回来以后,穿上六成新的衣服,背着一个包,提着一瓶二锅头,外加一只烧鸡,去找普志,他不敢穿得太光滑,怕引起反感把事情搞砸了,山里人,最好还是离泥土近一点。
到了普志家门口,张二狗老远就叫到,“普志兄弟,在家么?我来你家坐坐。”
“是谁呀,进来吧,嗯,是.......”,普志差点要把张二狗的名号叫出来,又一想,人就在外面跑了几年,算是有见识的人,听说别人都叫他张老板,若自己还叫他张二狗,多不雅。连忙改口,“嗯,是张老板来了,稀客,稀客”。随手指着一条板凳说,“你请坐”,山里人家里常年火塘不断,到处是黑乎乎的,张二狗也就走过去,想坐下来,在坐下的一瞬间,突然他一个激灵跳起来,“呀,鸡屎”,他的声音大得有点夸张,普志满脸通红,张二狗说,“没什么的,普志兄弟,你家里有两个病人,不容易的,我理解,理解”。并把酒把和烧鸡递给普志说,“兄弟,这个你拿给翠花妹妹,拿去灶房弄一下,一会我两兄弟喝几杯,走,我想去看看你母亲。”
普志在前带路,进普妈妈的房间,一股药味老远就闻见了,张二狗皱下皱眉,普志老远就说“妈,这个是村西老张头家的二儿子,来看你了”,张二狗走到普妈妈床边,假装亲热的说,“普大妈,我来看看你,本来早就想来了,又有事耽误到现在,我们这些晚辈的真是不孝,你好些了吗?”,普妈妈挣扎着要起来,“好些了,好些了,谢谢你”。张二狗连忙上前一步,从包里拿出一包大白兔奶糖放递给普大妈,推辞一番之后,他把大白兔放在枕边上,在九十年代,大白兔奶糖就是稀罕物,尤其在闭塞的山村见到,而这奶糖就躺在普大妈的枕头边,普大妈心里很激动。
不一会,姜翠华就抄好了几个小菜,青椒腊肉,素炒茄子、花生豆、鸡蛋洋洋片,还有普志带来的烧鸡。
张二狗一走,普志就一个人喃喃自语,“石头也能卖钱,石头也能卖钱?”
姜翠花以为他疯了!
普妈妈以为他疯了!
普家的生活在混乱中......
三天过后,张二狗又一次来到普家,他走后,普志清醒了,他去了一趟张二狗家里,商量妥后,就去找了村里的五六个青壮年,在自家的后山捣鼓起来。
翠花想,难道这就是他那几天说的,石头能卖钱的事吧。
普艳艳自小能歌善舞,加上学习刻苦用功,考入蜻岭师范以后,有了更广的发挥天地,几次学校的文艺演出,无论是清唱还是独舞,她都出尽了风头,她最佩服音乐老师,雪白细长的手指在键盘上几下拨弄,美妙的旋律就流泻而出,美极了。因经济紧张,她很少回家,想省点车费钱,尤其看到音乐老师周末教几个孩子学钢琴,还可以有收入,她更羡慕,要是我以后学好了钢琴,也办个钢琴学习班,就可以挣钱补贴家用。她勤奋好学,加上很有音乐的天赋,音乐老师也对她作了悉心指导,她进步很快,没多久就能独立弹奏了。
普志同意了张二狗的建议,在自家后山开了一个石场,并找了村里的几个精壮劳动力,把石头从山里掏出来,小一点的直接撬,大一点的就用炸药,埋得深的,炸药雷管同时使用。开石场是需要力气活与技术活同时进行的,九十年代挖山工具没有,不像现在,挖机推土机开过去,轰轰轰几下子,山体纷纷往后倒,石头乖乖走出来。那时要先用撬棍把石头一个个撬起来,再用錾子把石头打磨平整,遇到石质坚硬一点的,就在中间凿一个孔,叫炮眼,把炸放进炮眼里,炸药的长度80厘米左右,用一张枯黄色的纸包裹着,那色泽很像失宠的线装书,中间埋一根长长的引线,称为火引线,引爆时,把火引线拉出来,点燃,人迅速离开现场,5分钟以后,“轰”的一声巨响,炸石工程完成。遇到不响的,就是哑炮了,至少要等10分站左右才能走近查看,你要是提前走进去,哑炮突然发声,那可是不得了的。把炸药放进去,引爆之前,还要在山上大吼,“放炮了,放炮了”。离得近的人,就目测一下,石头飞来会不会砸着自己,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包容一点,自己的事慢点去办,先躲避好,等炮声响过石头滚过,再离开。
石场开起来,小山村热闹了,张二狗一会城里,一会乡下忙个不停,他买了两辆小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响个不停,石头一车车运出去,钞票一张张数进来。事先他就跟普志签了一个协定,他负责投资、销售,普志负责开采,三七开。还特意请了村里念书最多的普三魁写了字据。每人手执一份,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各自负责,要是依照今天的民法相关条例来说,这样的协定是漏洞百出的,可当时老百姓法律意识淡薄,有个字据,就像拿了律令,都严格执行的。
开了石场的者么乡欢腾起来。
家境改善了的普志家愉悦起来,普妈妈的脸上有了笑容,病情虽不大见好,可也没有进一步恶化,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她不操心,至于姜翠花,她的月子病,不好也不坏,一会儿浑身大汗,一会儿手脚冰凉,老天给这个家庭的打击够大的了,现在雷声已过,有了一点点光亮,没有走漏风声的土墙内也有了些许温暖。难得的是,眉头紧锁了很久的普志,脸上也有了笑容。
两年过去了,普艳艳进入了三年级,她选择的是音乐班,当时成绩优秀的就有保送进省城的坤和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的机会,聪颖而好学的她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勤学苦练,文化基础也不放松,毕业之时,蜻岭师范笔业的许多同学都走上了工作岗位,而她却带着一脸的灿烂,走进了坤和师范大学。
真大啊,大学校真大,省城的房子那么高,车子那么多,山村跟这里相比,真是天上的地下,人啊,为什么要有那样的差别呢,现在我从小山村来到了这里,毕业以后也会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生和呢?想到以后,想到母亲,想到哥哥,普艳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那时的师范类学校是热门,品学兼优的才可以进入,谁家要是出了一个师范生,走出去都可以大声大气的说话,为啥?国家补助。饭菜票发到手里,伙食问题国家解决了,自己掏几个零花钱就行。
富了的普志没有怠慢妹妹,女孩子要富养,他虽识字不过,这道理却懂,每个月的普艳艳都是富余的,她不乱花钱,却可以自由购买自己喜爱的乐器,购买更多的书籍。
更令人兴奋的是普家又添男丁,普志给取名为小松松,普家三代单传,小松松的到来,给这个家平添幸福和荣耀,普家摆上宴席,请了全村的人来吃,满打满实的八大碗。
好事成双,喜上加喜,因心情舒畅,加上药物和饮食的调理,普家婆媳的身体算是康复了。
张二狗发财了,在村里声气更大了,油光的头发,程亮的皮鞋,真正人模狗样起来。村上要建村小学修路之类的,他也舍得掏几个钱,他还娶了邻村郝二爷家的闺女郝巧珍。郝巧珍大字不识几个,几年前曾骑着猪去冲坏了一家的门槛,名声在外,没人敢娶。而张二狗恶名不浅,没人敢嫁,虽一夜暴富,山民纯朴,不稀罕那个臭钱,不会把闺女嫁给那货色,自然,无人愿嫁的娶了无人敢娶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啥呢?相帮,绝配。
绝配啊,他俩。
挣了大钱的张二狗,本相外露,当初他与普志联手,并非真心想帮他家,实在是看中了普志家后山那座质地坚硬的石头,能买到好价钱,他除了到石场指手画脚,在外联系点业务,几乎不做啥,更可气的是,有时,他为了省几个小工钱,遇到收工以后来的生意,大多时候让普志把石头背到车上,自己在一边陪人聊天,抽烟,普志找他要过钱,他眼一瞪“哦,你跟我要工钱啊,是为自己干活,还要工钱,不合适吧。”
在一个貌似晴朗的下午,有一桩业务需要赶工,到了下午六点半,计划中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越往里开采,石质越坚硬,一撬棍下去,才冒几个火星字,大多时候需要使用炸药,加之雨季,炸药受潮,不好用,大家都心烦意乱的。
那天下午,怎么就无风呢?心怎么就会跳个不停呢?是要发生点什么吧?普志心惶惶的。
六点半了,撬石头这样一个力气活是需要体能的,肚子饿着干活,能行么?而处于经济节约方面的考虑,每天的炸药使用次数,有最大限量,这一点张二狗把得紧紧的。一人在凿好的炮眼上,放了四节炸药,引爆线拉出来,点燃,哧哧哧的响着,半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
5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
10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
“又是哑炮,今天真他妈的霉运”,普其聪边骂,边走进炮眼,普其聪是者么乡的放炮高手,张二狗愣是把他请来,当然,他来主要还是冲着普志的人品,你张二狗算个逑,有钱又咋了?
普其聪走近炮眼,小心的蹲着观察,凭经验,他认为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可是,怎么就没有想到可是呢?你普其聪是灰土呛多了吧,不要动手多好啊,偏偏他伸出了手,用力一拉,“轰隆隆”一声巨响,普其聪的半截身体飞到了空中,飞起的石头又砸中了一个人的脑袋,那脑袋像一块蛋糕,被谁挤压了一下,血汩汩直冒。
不出事则以,一出事就是两条人命。那责任,背上一条都够呛,何况是两条,老天就会欺负老实人,尤其像普志这样,没长几个心眼的老实人,双方协定早有协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各自负责,张二狗撇得一干二净,“炸药受潮,你们不会拿没有受潮的使用啊,你们不会把炸药晒干了再使用,自己没脑子出了事来找我,扯球蛋,赔钱,老子一分都不陪。”
当时的民事法不健全,而且人虽然死了,却不是故意伤害罪,老百姓法律意识淡漠,请了几个大队干部,坐下来,几杯酒穿过,摆平啦,普志每家陪三万元,在那样一个鸡蛋三分钱的年代,三万元就好比是天文数字。酒是张二狗买的,红山茶烟也是张二狗卖的,不用说,村支书的相好张香芸手腕上亮晶晶的银镯子也是张二狗卖的,他俩还是挂角亲戚。
除了这档子事,开石场的事是合作不成了,别看张二狗平时像个闷头葫芦,可要是谁给他惹毛了,也是憋着力气红着眼睛往前冲的人。每家三万元,咋个整啊。
狗急了也会跳墙呢,普志不是狗,是家里有着两个病人需要照顾的大男人,他可以贫穷,可以得不到分文,就是不能容忍言语上的侮辱。他到了张二狗家,想讨要说法。千不该,万不该张二狗不该拿女人的裤头去套他,还丢下一串砸心砸肺的话。“你真是心着狗吃了,当初你穷得响叮当,要是老子不帮你,你那痨渣媳妇和老娘早埋黄土了”。
“你才心着狗吃了,你想想这几年,我为你苦了多少钱,你就会在外面跑烂摊,还说是联系业务,找销路,大头都你拿了,石场上的活计你去做过几回?”
咽了下口水,普志接着说,“良心着狗吃了的人才会只认钱不认理,老子遇到你算是背时霉运。”。这时二狗媳妇去院子里收衣服回来,红艳艳的短裤很醒目,普志平时也就闷葫芦一个,张二狗眼珠一转,顺手拿起红裤头套在普志的头上,说“红色辟邪,用女人的红裤头套在你头上,以后你就不会有霉运了”。二狗媳妇也在一边破口大骂。
在农村,用女人的裤头套在一个男人头上,是极大的侮辱。
看着他家两口子盛气凌人的样子,“你们太欺人,”“你们太欺人了,”
普志只会反复说这句话,事实上,他也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二狗媳妇郝巧珍,是村里有名的吵架高手,她可以连续骂人两小时,而中间不会有重复的。
回到家了的普志越想越气,你在明处整我,我就在暗处还击,看你以后给还敢欺负人呢。
在一个有雾的早上,他拿了一把錾子来到张二狗家附近,为什么不拿刀子呢?刀子醒目,路人问起也不好说,錾子短小,放在身上就行。
到了张二狗就家附近,等了半小时,张二狗家两口子出来了,穿戴一新的,大概是要走亲戚,还边走边议论着普志。普志气坏了,冲过去,一拳打在张二狗鼻子上,二狗被打懵了,待看清是普志,这世道真是变了,普志也会打老子,得好好给他点教训。
九十年代的山区,出门随手可以捡起棍棒石头的也不足为奇,张二狗抄起一根半干的树杆,迎头打过去,普志躲过了,两人你打我躲,持续了一会,普志的身上挨了几下,愤懑、屈辱一股脑儿涌上来,他散失理智,拿出錾子,铆足力气,一把抓住张二狗,没头没脑的一阵猛砸。
完了,这下子完了。
张二狗没死,肺撕裂,肾脏大出血,他是不能再欺负普志,可普志也得进班房了。
这个家怕是起不来了,病倒的病倒,坐牢的坐牢,两儿子,还有一个大花钱的主儿。
普家出事的时候,普艳艳正读大三,普志进班房了,普妈妈进医院了,这次是进了宜川州医院,如今的宜川州医院搬到了新区,而老州医院在市政府斜对面,离蜻岭师范也就几百米,姜翠花去照顾婆婆,还有两个孩子也一同带上去,大儿子两岁多,小儿子8个月,尚在哺乳期,姜翠华顾了婆婆,顾不得孩子,老的是老的哼,小的是小的叫,家里的牛羊,都是请妹妹家帮忙照看。
没多久,姜翠华也倒下了。
那年头,英雄救美不是说假话的。
早在读小学期间,张增就对普艳艳有好感,怎奈普艳艳太优秀,他就把自己当做一株葭草,静看花儿的美丽,在暗处收获愉悦。初中毕业以后,张增出去社会上混了三年,靠老父亲的人脉关系到县政府财政局谋了一个吃皇粮的差事,做了驾驶员。他想自己如今也是国家正规的工作人员,与普艳艳的距离缩短了,自己可以挺起胸脯去追求她啦,找了几次,都被普艳艳以读书时期,不能谈恋爱为由,婉拒了。
文艺的熏陶,知识的滋养,普艳艳出落的更加标致,张增更加爱慕,不管她接不接受,他发誓痴心一片,此生不渝。
总不能丢下普妈妈一个人在医院吧,现在是自己拿表现的时候了,张增对自己说,“心诚所至,金石能开”,古人说得有道理。
当时的大学专科三年就毕业了,因此,最后几个月的实习很重要,实习表现好了,关键是实习学校老师的评语写得好听了,将来就会有个好去处,师范生是财宝,国家包分配呢。
22岁的张增个头不高,1.72米少不了的,普艳艳1.65,两相一比,还是马虎含混。
该死,找对象要看精神气质,看良心还不好,哪能比相貌呢。
普家失了火,普艳艳还在一个小镇学校实习,自从三个月前哥哥寄出500元给她,现在没有了,要钱的信已经寄出,者么乡就算山路再难走,一个月也该到了吧,不会是家里出事了?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一定是。
等普艳艳实习结束,心急火燎的回到家里,才发现家里塌天了。嫂嫂呆愣愣的守着几只羊子和两个孩子,说姜翠花的心被狗吃了那才叫冤枉,她也才回家两天,回家干嘛,借钱。没钱,人家不会给婆婆看病的。当普艳艳得知哥哥坐牢母亲住院的事实后,傻了,呆了,一整天不吃不喝,晚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嫂嫂怎么叫都不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上了楚雄,找母亲去了。
宜川的秋天暖意不多,尤其对于心里冰冷的普艳艳来说,每一缕风都是刺骨的刀,妈妈会冷么,她想。
当她找到病房的时候,惊呆了,张增你算什么东西,怎么可以给母亲擦屁股?普妈妈癌症恶化,老年痴呆,神智不清,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在被子上涂着口水,大小病失禁。
人心都是肉长的,一个女孩子,人家男人不嫌脏不怕臭,给你母亲倒尿倒屎,作为女儿,你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人家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你还无动于衷,那就是心被狗吃了。
那一刻,普艳艳的心似乎被什么蛰了一下,泪离开满面,她下了一个决定,此生非张增不嫁。
下篇拨云见雾
半年后,普妈妈因医治无效死去,她是笑着死去的,看以来很恬静,像一个睡熟了的孩子,闺女有了那样一个贴心贴肺的对象,自己也可以瞑目了。
普志因愤伤人,进了班房,要两年以后才能出来。
少了男人的家,就少阳刚之气,普家塌了,母亲去世,张增坐牢,对这个家是致命的打击,姜翠花继承了婆婆的事儿,做了病捞子,药土锅不断啦,这次是真的不断了。走进家里,大白天都冷飕飕的,风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时不时伸出手,在你身上摸一把,躲不得,骂不得。
普艳艳进了城区的一所中学-碧野中学当老师,第一年教英语和音乐。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她,踏实、认真,就是寡言少语,母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太大,哥哥还在牢里,家里的这些这状态让她揪心,是时候了,是该她撑起这个家的时候了。
家庭变故以后,姜翠花与先前判若两人,动辄发脾气,虽没有说不给婆婆治病,背个不孝的骂名,她可不敢,她再无知孝悌之心还是有的,可是她两岁多的儿子就倒霉了,俺生养的,俺不打不骂,留给谁打骂啊,可怜的大儿子成了母亲练手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了来说,打起孩子来,你不要怀疑一个女人的能力。
8月份普妈妈已经去世一年多,普艳艳也放假了回家了。普志在监狱了里表现良好,还在做工的时候协助狱警抓捕一个伺机逃跑的犯人,得到了一天假期与亲人在家团聚人的奖励,普志回到家里,看着熟悉的家,宛若隔世,他们在家坛上祭奠过母亲以后,一家人围着火塘,普艳艳说:“哥哥,你回去以后,再好好表现”,看着嫂子浑浊而沧呛的目,她接着说,“老大这个孩子快4岁了,我带去县城读幼儿园,嫂嫂在家带小的那个孩子,等到他到了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也带去城里”。
普志用火钩拨了一下火,火苗“嗤”的窜得老高。
“咋过行呢,你一个女娃子,怎可以带小孩,再说你对象会同意吗?”有妹妹如此,一股暖流从心底冒出。“你有这份心意,哥哥心领了”
“我是认真的”,普艳艳噙着眼泪说,“当初如果没有哥哥,我读不完师范大学,我们彝族老古辈子传下来的说人不能忘本,谁有困难要相互帮助,大家一起相亲相爱,和乐融融的日子才过呢好啊。”
就这样,普志的大儿子走出了小山村,进了城区幼儿园,他有个响亮的名字,普成高,成高成高,愿你成得了大气候,远走高飞。
高原地区紫外线强,者么乡树木不多,遮挡不了紫外线的辐射,普成高小小年纪,皮肤黝黑,讲起话来嗓音有点沙哑,像个饱经风霜的小老头,家庭的变故,让他过早的品尝到了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上创伤,幸有姑姑关怀,心的伤口结痂、温软,他会笑了,会跟小朋友玩了,回到家里,没人注意的时候,还唱几句老师教的儿歌,一听到脚步声就停止,脸红红的,憋着一口气蹲在墙角。
普志在狱里的努力改造,有意思得到减刑的机会,四年减为三年。
普艳艳读书期间学习努力,工作时又认真钻研教材,有甜美的嗓音,加上扎实的乐谱知识,她就把一门心思放在教研教改上,教书这个行当,大讲究技巧,你纵有深奥的知识,还需具备把知识倒出来让别人听得懂的能力,大学教授水平在吧?可让他来教小学生,结果未必赶得上一个师范生,你大学教授有知识有能力,那好,俺不跟你玩知识,比技能,你行么?
两年过去了,普艳艳在教学上如鱼得水,因才华出众,工作积极,很是得校长的赏识,给她分配了一个好差使,辅导学生的音乐,为啥是好差使呢?你若还要说二话的话,那可就是外行了,音体美谓之特长,特长生的取分低啊,要是考取了艺术类的学校,学生榜上有名了,老师面子上光鲜着呢,人家议论起时只会说,某某学校考取了几个音乐特长生,他人一听,哎呀,这个学校不错啊,音乐老师的水平在,是谁教的呢?
每个月她都会回老家一趟,一来,她的根在者么乡,山村虽穷,有她的快乐,有她割舍不下的乡土情节,她就算扮得再时髦,再怎么像个城里人,可骨子里,乡音她记得。再说,母亲去世了,哥哥不在家,嫂嫂不拿事。这个家不能散,一定要振作,一定要腾飞,自己都飞了,一定要引领家人飞翔。
普艳艳结了婚,那么优秀的老公,她没有理由不要,且不说当初母亲住院期间他比亲儿子亲闺女还好的表现,就算他把普艳艳成功追到手以后,也没有像那些从奴隶到将军的男人一样变脸,对普艳艳深情如初,对普家体贴如初。普艳艳有睡懒觉的习惯,女孩子晚上抱着琼瑶岑凯伦的小说做做梦,梦做长了,早上就特困,早上送大侄子上幼儿园的事,张增包了。真爷们!
两年过后,大侄子普成高读大班了,城市的诱惑,不,应该是蛋糕、巧克力、游戏的诱惑,他早已从郁郁中走出来,活泼、阳光。现在是轮到小侄子普成松见人生分了,虽然在老家他可以以一曲亮晶晶的山歌横贯云霄,可到了城里,还是紧紧的拉住姑姑,几天也适应不了。
一天晚饭后,张增和普艳艳带着普成高去逛密尔湖,密尔湖,位于县城东侧,两年前一投资商看中了蜻岭县这块有核桃有金马碧鸡传说的风水宝地,投资2亿元,建了一个人工湖,湖中有个池心岛,湖的两侧种些花花草草,平整的石板路以及晚归的云霞,交映着小城的和谐静美。
张增看着漂亮秀美的普艳艳,心里有说不出的甜蜜,在他的前面,有一个小男孩拿着风车边走边玩,路上还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小男孩跑着跑着风筝从手里脱落出去,不时打断行人的脚步,张增真希望自己有个孩子,一家人慢捻斜阳,笑看闲花,然而结婚前,她俩有过君子协定,不到二十七岁,不要孩子,二十七岁女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完成成熟,是生育的最佳年龄,当然,他们不能过早要孩子的理由不是这个,是普艳艳的家庭,是对家庭的责任,是对哥哥的还贷,人生就是一个还贷的过程,还自己的债,还前世的债。
“艳艳,你看小程程的弟弟今年三岁了”,张增说,“要不我们也把他接来城里读幼儿园”。
“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么?你家爹妈会怎么看?”,听到丈夫能说出如此话语,她很感激,丈夫的关心,公婆的呵护,让她倍感幸福。可毕竟家里要多出两张嘴,她不得不顾及公婆的感受,结婚三年,一直没孩子,她觉得愧对张家,在公婆嘴里,她是小燕,“小燕给哥哥带孩子,懂得感恩”,“我家二小子娶的媳妇,好相貌,好良心”,公婆常在街坊夸她。一个家庭,公婆夸媳妇,媳妇敬婆婆,要是还不和谐,你尽管来找我。
一个月之后,张增开着车子把小松松接到了城里,普艳艳要到州上参加一个大型文艺汇演会,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小松松喝着橘子饮料,哥哥碰了他一下,黄色的橘子水泼在胸前的地米鼠上,哇的一声,他大哭了,正是他的哭声,加快了普艳艳回家的脚步。
普艳艳又流泪了,偷偷跑去卧室擦干。
晚上,普艳艳特意炒了几个丈夫爱吃的小菜,拿出红酒,一杯为自己倒满,另一杯倒满直接递给丈夫,她今天表情有点严肃,心情更是激动。
“张增,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今后我会好好报答你,加倍还给你的。”
“燕,你说什么话”,张增深情的说“我们是夫妻,是患难与共的夫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要是这点事都为你当不了,就不像爷们,更没有资格说爱你。”,他拿起纸巾,轻轻擦去普艳艳脸上的泪痕,“以后不许说这样的话了,知道不?”
每天早上,小两口开着车子,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园,到了学校门口,一声姑姑叔叔再见,引得周围注目,更多的是对她们姐弟情谊的赞叹,对普艳艳情操的赞叹。
四年晃眼一过,普志出来了,出来时大儿子读小学了,小儿子也读幼儿大班啦,父亲的事,并没有影响两个孩子的成长,他们快乐得像小鸟,见了父亲不生分也不亲热。
张增的大爹是搞建筑的,他给普志找了一份活计,工作不复杂舍得下力就有钱挣,他说现在先到底层干几个月,等有机会了,再给安排轻松的活儿。
获得新生的普志,靠着心灵手巧,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取得张家亲戚的好感,而普艳艳在张家慈孝有加,邻里皆赞。有了这些铺垫,没多久普志就换了个轻松点的活计,做了仓库管理员,每天清点货物,做好货物的出库入库记录。闲起来的普志毛病出来了,啥?喝酒,一个人在偌大一间仓库,忙时一整天脚不离地,小便憋着算了,反正憋多了也不会得阳痿。闲的时候就跟酒亲热。温饱思淫,眼闭眼闭的上工,昏昏沉沉的睡觉,只有每到周末到妹妹家吃饭的时候,会正正衣冠,两个儿子叫爸爸的时候,精神会闪耀一下。
到了二十七岁的时候,普艳艳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张增的公婆、妹妹以及大哥的孩子都投入到照看普家两兄弟的阵容中。孩子一岁以后,普艳艳找了第二份工作,利用晚间做钢琴老师,张家富裕,不缺她那几个辛苦钱,人活尊严,普艳艳心又不安。
几年过后,普成高读初中了,在碧野中学就读。跟普艳艳在一起。一次,学校来了一群大学生,他们以社团的形式组织“手拉手,献爱心”活动,普成高是帮扶对象,普艳艳也作为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参加了活动,在学生上台发言的时候,普成高说了一段让满座落泪的话,他说“今天,我要把最感动的话,送给我的妈妈普艳艳,这么多年来,她很辛苦的养育着我,她对我付出了很多,她虽然不是生我的妈妈,但她是养我的妈妈,我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合格的中学生,长大以后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边说边抹眼泪,最后还深深的对着普艳艳鞠了一躬,“妈妈,谢谢你。”,整个会场骚动,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后记:
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普艳艳的大侄子大学毕业了,小侄子正读高三,仍是碧野中学,我好友在那儿做图书管理员,爱好文学的我喜欢到她那儿,每次她都要跟我说起普艳艳,当一个人被熟悉的人经常提起,而且还与佩服的口吻,那么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行的镜子,他所生活的场域以及相关的社会链条,都是我们的中国梦。
“普成松,你给是要借《中学生散文选编》”,好友一嗓子把我从书堆中震醒。
“是的,就借那本”,一个穿着丹杰仕牌青蓝色运动服的大男孩答应着,他手里还拿着《高三物理课课练》,目光和外面的蓝天一样湛蓝,澄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