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混蛋”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曾经名动京城的“大顽主”,按其“对立面儿”之一叶京的说法,他是“第一个敢跟军队干部子弟作对的地方流氓”。没有一点儿叛逆的青春是植物人儿的青春,但绝少有人能叛逆得像“小混蛋”一样血肉横飞。上个世纪60年代末,“小混蛋”的青春和那个残酷的夏天一起结束了,画的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和惊叹号!
“小混蛋”虽然只活了短短十八年,但在他死后的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那些从老北京的胡同里走出来的孩子们,以及军区大院、部委大院的子弟们,依然在热情澎湃或者小心翼翼乃至信口雌黄地谈论着这个诨号,甚至更久的四十八、五十八、八十八年后,当那一代人都带着各异的心情去和“小混蛋”会师的时候,这个响当当的听起来不太着调的名字,注定会继续伴随着各种各样乃至互相矛盾的传说,作为“北京记忆”的一个生猛插曲,更作为一种传奇与精神的符号,像难以出头却更难以磨灭的手抄本一样,在非主流的世界里流传下去。
关于“小混蛋”的故事,尤其是震动北京顽主圈儿的“小混蛋之死”的谜案,民间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版本,比吊诡的中国史还混乱。当代表“大院文化”的王朔、姜文、叶京以及行走在这种文化边缘的都梁等人在自己的作品和访谈中不断地把“小混蛋”描绘甚至直接定性成“流氓”的时候,那些曾和“小混蛋”称兄道弟、被大院子弟称呼为“野孩子”的老顽主们,也终于在神奇的网络上抢到了话语权——边作君、四横竖等人,在一群仰慕“小混蛋”的年轻人的呼唤和追随下,频频发声,打起“还原真相”的大旗,断断续续讲述着“小混蛋”的孝与义,以及顽主群体对抗社会不公的或无奈或悲愤的壮举,慷慨地驳斥着大院派对“小混蛋”的诋毁以及江湖上的种种讹传与恶传,试图重新定位“小混蛋”的社会角色。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院派”人,对这种反击或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或用沉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逍遥、谨慎也许还有心虚,总之,“真相”在他们那里,肯定是另一副面孔。
其实,何尝有过“完美的真相”。一个人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真正了解,却要说自己掌握了别人的真相,险些就幽默了。所谓“真相”,只在无数“罗生门”的夹缝里喘息或者窃笑着。那个有着爱恨情仇的真实的“小混蛋”,不管正在天堂还是天堂的隔壁,或许都不会想过:自己电闪雷鸣般穿越人间的短暂一瞬,竟然会留下如此漫长而纠结的尾巴。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回忆的只是与他们结交或拼杀过的“小混蛋”,至多是“小混蛋”的某一面,盲人摸象也不过如此。而更多的传说,甚至那些以讹传讹的演义,则像正史之外的野史一般,貌似偏颇无据,却往往有着卡通画一样的效果,摒弃临摹、夸张细节,避实就虚、弄巧传神,谁能说这些“编外别传”所描述的不是另一种真实的“小混蛋”呢?这时候,他们传诵的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特质、一种梦想和精神。
不可否认,每个人心中都埋着一粒“小混蛋”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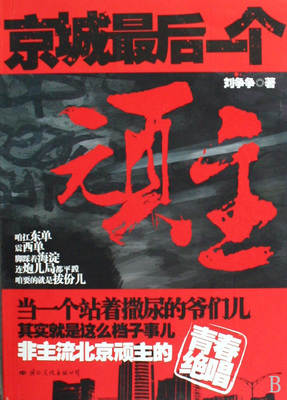
那是一对儿狰狞的狼牙,时刻准备着为生存与尊严去厮杀;那是一双带着钢钩的利爪,死死抓住命运的岩壁,抗拒着滚滚潮流暴虐的裹挟;那也是在一场必败无疑的战斗中,于无界的黑暗里,撕裂青春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勇猛又绝望的嚎叫。每个人都该有那样一对狼牙,只是太多人一生都不敢露出来;每个人都会有那样一双利爪,可太多的人只是奴才一样用它们护着裆部,随遇而安地苟且偷生着;而那一声嚎叫,同样被压抑在太多太多的胸膛里,不知憋屈死了多少英雄好汉与才子佳人。
“小混蛋”是一个叛逆的灵魂,魔鬼和上帝都无法收购它;“小混蛋”是一块拒绝被雕琢的顽石,那些试图把玩它的人只会撞得头破血流;“小混蛋”是一只桀骜不逊的狼崽子,任何的牢笼只能让它更癫狂。
这样的灵魂与躯壳,一直让他的“对立面儿”敬畏交加、恨惜杂糅,而他的朋友以及拥趸,提起“小混蛋”三个字则永远是情怀高涨。追捧、怀念“小混蛋”的人们,最终把他的精神推崇为“顽主精神”。“小混蛋”的血,在1968年6月24日那场最终被定性为“流氓斗殴”的阻击战中已经流干了,那一刻,他的时代也结束了,今天,在这个被陈丹青称为“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的世界里,他的“精神”真的留下来了吗?或许,这是另一个传说吧。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