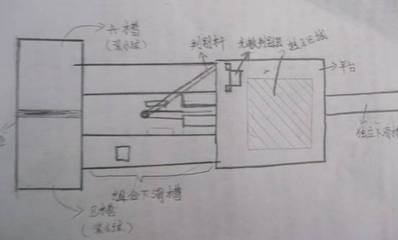一、结论的简述
贵州省的穿青人是什么民族成分?他们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调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说来是这样:
民初由内地迁入贵州的许多移民中,有一部分是从江西强迫随军服役而来的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曾在贵阳、清镇一带居住。当时这一带正是彝人土司统治的水西地区的边缘,也正是汉人势力的前线。明末,土司势力削弱后,他们向西深入现织金、纳雍地方。清初改土归流,移入的更多。这地区,特别是织金、纳雍,成了他们主要聚居区;他们也是这地区农民中的主要部分。他们具有当时较高的农业技术,在这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土司经济没落过程中,发展了封建地主经济。从土地剥削中产生地主阶级。
另一方面,同时或稍后一些,不断地有许多外来的汉人,做官的或经商的,在这地区落籍,大多住在城市和街场。这些官僚和商人凭借政治和经济势力,霸占或收买土地、成为地主。随着,也有从各地来的汉人农民进入这个地区。
因此,在这个地区有了来历不同两部分汉人,他们在方言、服饰、风俗、信仰上保持着一定的地方性区到,那个早期移民集团的后人后来被称为“穿青”,当地其他的汉人被称为“穿蓝”。
穿青祖先移入贵州时是随军服役的“民家”,社会身分较低。他们又是农业劳动者,僻居乡间。而穿蓝中有做官和经商的人,在城市和街场上居住,保持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穿蓝看不起穿青,穿青受到歧视。
穿蓝、穿青在早期共同和土司残余势力作斗争时是联合的,矛盾不显著。在封建经济发展中,穿蓝占优势。咸同年时农民运动中有穿青的农民领袖,而地主阵营内却以穿蓝为主。穿蓝、穿青在这地区经济中的不平衡性已经明显。清末民初,国内民族市场形成,破坏了这地区割据性的经济,现代商业势力开始进入。这新兴经济的领导势力,几乎完全被穿蓝所独占,和外界缺乏联系的穿青受到排斥。在地方经济中原有一定地位的穿青地主是不甘心的。他们不愿新兴的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向他们榨取高额利润。他们中也有企图分享这种剥削机会。因此乡间的穿青地主和街场上的穿蓝商人间发生了显著的矛盾。穿青地主利用移民集团的内部传统的乡土感情,和穿青农民对日益增加的削剥和压迫的反抗情绪,以穿青反对受歧视为口号,领导起穿青向穿蓝进行斗争。从那时起到解放止这一段时间中,穿青聚居区的各街场上曾发生过大小规模的局部械斗。穿青和穿蓝伤了感情,产生了隔阂。
这种心理上的隔阂并没有阻碍这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地区的经济和国内民族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穿青在生活各方面也密切和其他汉人发生联系。他们传统的地方性特点逐渐消失。近五、六十年来,在方言、服饰、风俗上已和其他汉人趋于一致,虽在信仰上还保留一些特点。穿青、穿蓝的界线在交通较发达的地区,即聚居区的边缘,也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但是在聚居区,尤其是较偏僻的山区,穿青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后于穿蓝,社会上还受歧视。这种情况一直推持到解放。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这地区贯彻了民族平等的政策。过去受过压迫而不敢公开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他们的民族名称,要求在民族大家庭的行列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当时长期受到歧视的穿青,热烈拥护这种平等政策。他们对于民族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觉得凡是受过歧视的人都是少数民族,穿青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可以并不否认自己是汉人,而同时却又说自己是少数民族。普选登记时,穿蓝都报汉族,大多数穿青不愿和穿蓝没有区别的同称为汉人,所以报“穿青族”或“青族”,但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也有不少坚决认为穿青是汉人,报了汉族的。
由于对穿青的情况了解不足,我们政府对穿青的民族成分问题一直没有作出决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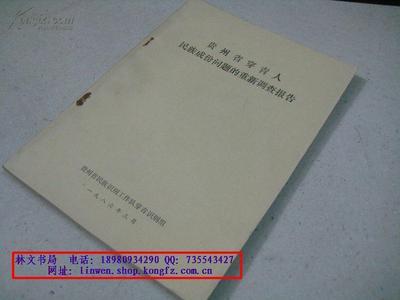
经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穿青原是汉人中的一部公,在历史过程中也没有和汉族割断过联系,没有独立发展为一个部族和民族。他们所具有的地方性特点是部族时期汉人内部的区别,而且这些特点在近代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已基本消失。由于历史原因,穿青虽则曾受当地其他汉人--穿蓝的歧视和排斥,政治上、经济上发展不平衡,而且心理上还有隔阂,但是这些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民族的过渡时期必然很快会消灭的。穿青脱离汉族、另外形成一个民族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如果我们承认穿青是一个单独民族,对于穿青的发展是没有利益的。我们认为,在加强地方上穿青和穿蓝的团结,并对穿青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情况予以适当照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心理隔阂是可以消除的。
所以,我们认为穿青人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
下面,将说明我们是怎样得出上述的结论的,并分段提出主要的论据。
二、穿青的基本情况
称作“穿青”的人现在主要居住在贵州省西部,乌江上游的六冲、三岔和鸭池三条河的流域。
据一九五三年普选登记,自报“穿青”的人有二十四万八千多人,其中有一半以上聚居在纳雍和织金两县(每县都超过七万人),其余分布在大定、水城、关岭(都超过一万人),和清镇、普定、郎岱、兴仁、盘县、普安、晴隆、毕节等县(都超过一千人)。
为什么这些人称作“穿青”?说法很多,都难征信。他们过去认为这是别人侮辱他们的名称:在聚居区边缘,如黔西、大定、普定、郎岱、镇宁等,亦称“里民子”,也认为是侮辱性的名称。他们并没有自称的专名,必要时自称:“大脚板的”。
“穿青”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开始的,也难考查。文字记载中出现这名称最早是平远川州续志(一八八八年修)和大定县志(一九二五年修)都是记载同治年初(十九世纪中叶)农民运动时提到的。这名称在民间口头上使用应当更早些。较早的文献中有“里民”或“土人”,按所记内容看是包括后来称为“穿青”这种人的。
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是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一个形容词,如“白汉人”、“穷汉人”、“大脚汉人”、“蒿子杆汉人”、“吃蒿麦的汉人”、“穿大袖子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可见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看来他们是有一些特点的汉人。
“穿青”这个名称主要是用来区别于被称为“穿蓝”的人,穿蓝是当地穿青以外的汉人。
穿蓝和穿青在这个地区是杂居在一起的。穿蓝的人口在这地区总数比穿青多。就是在穿青人口最多的纳雍,穿蓝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二,而穿青只占百分之二九,其他地方穿青的比例就更低了。
穿青聚居区里纯碎穿青居住的村寨不多。很多和穿蓝杂居。这些村寨又一般是和穿蓝的村寨插花分布,所谓"杂村不杂户",很少见到儿十里地全是穿青人家,这是说穿青和穿蓝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隔绝的。他们的经济也是密切联系,依赖着相同的街场,受同一的地方经济中心的支配。
外来的人从表面上来看,除了少数老年人和少数偏僻地区以外,已分不出穿青和穿蓝。他们的语言、服饰都已经一样,据说只有在妇女草鞋的结上还可以看出穿青的特点。
但是在五、六十年前,穿青和穿蓝还存在着下列区别:
1、穿青的老辈话和穿蓝的话口音不同。
2、穿青供五显坛,穿蓝供赵侯坛。
3、穿青妇女穿大袖滚花上衣,梳三把头,和穿蓝服饰不同。
4、穿青妇女大脚,穿蓝妇女小脚。
5、穿青早年新娘出嫁不坐轿,后来坐弟兄抬的轿,穿蓝一直坐轿,不用弟兄抬。
这些区别现在还存在的只有第二和第五两项,但是也并不是绝对如此;穿青中也有不供五显,穿蓝中很多也供五显。穿青穿蓝也都有结婚不坐轿的了。
穿青和穿蓝表面上的区别虽则基本上已经消失,但是在穿青聚居区内,谁是穿青,谁是穿蓝是分得很清楚的。这条界线要到聚居区的边缘,交通方便的地区,方形模糊,甚至消失。穿青和穿蓝之间心理上的隔阂还是存在的,穿青觉得被穿蓝歧视,低人一等,而且觉得穿蓝狡猾,难于相处。
穿青和穿蓝过去既有一定的区别,又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阂,他们是否可能原来并不是一族的人?穿青是否可能不是汉人而是另一个民族的人呢?
三、穿青的老辈子话
我们首先应当调查穿青的老辈子话,如果不是汉语,他们过去也就不可能是汉人了。
调查的结果,穿青老辈子话完全是汉语,并没有其他民族语言的痕迹。
但是穿青老辈子话和贵州通行的官语却有下列方言上的区别:
1、f变h(例:房子念成黄子),
2、f变h(例:回来念成肥来),
3、鼻尾音有半鼻音(ieu-ie)或失落的(例:“半边”念成“拜别”“盐巴”念成“耶巴”),
4、有人分别l和n(例“川南”不念成“穿蓝”,而当地官话是南蓝不分) ,
5、语调有些“别”,
6、声调分类都是四调(阳平、阴平、上、去)但调值不同。
穿青老辈子话并不是从贵州通行的官话中演变出来的,而另有来源和早期的赣、鄂、湘通行的官话有渊源。这说明穿青不可能在贵州学会这种方言,必须是先说了这种方言才进入贵州。他们一直要到五六十年前才普遍学会贵州通行的官话。除了一些偏僻地区,一般说现在日常生活中已没有说老辈子话的了。中年人还有极少数能讲老辈子话,但也有老年人已不会说。大定八十一岁的穿青老人,已不会讲,但说给他听,他还能知道是他幼年时说过的老辈子话。
老辈子话的调查结果不能证明穿青不是汉人,但也不能得出穿青就是汉人的结论,因为“各个不同的民族却不一定需要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凡是说同一语言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
四、穿青进入贵州
从语言调查中可以推论出:穿青的祖先曾在赣、鄂、湘斟一带居住过,然后进入贵州。这种推论和穿青自己的传说和家谱的记载恰相符合。
穿青都说他们祖先是从江西吉安府来的,绝大多数说是明洪武年问“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来的。调北征南是指明大祖南征云南元朝残余势力的梁王的战争,调北填南是指明大祖在南征时和南征后强迫移民填实这些地区。
贵州很多民族,如布依、苗、彝、甚至仡佬族,也有传说是江西来的,而这些传说有许多很明显是附会。为什么穿青传说是江西来的却可信为事实?我们的根据是:
1、穿青的老辈子话是有江西通行的官话的特点。
2、穿青所强调的特点之-,五显的信仰,明初已在江西流行。
3、穿青和江西联系还找得到线索:有些家谱中记着有人回江西去的。有人告诉我们几十年前还见到穿青人有从江西来的亲戚。有个穿青复员军人到过江西和当地同姓人字辈排行联得上。
4、明初确有从江西的大批移民进入贵州,贵阳还有一个古钟上还刻着江西吉安匠人所铸,黔西有碑记筑城的人是赣州人(俱见《贵州通志,金石志二》。穿青家谱也有记筑城的事。
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们是明初来的人呢?我们的根据是:
1、穿青主要的四大姓:李、张、王、郭的家谱所记到黔后的世代都在二十代左右。穿青注重字辈,每姓都先定有每代的字辈,每人的名字都要插入自己这一代的字辈,因此按字辈计算世代的数目不容易错误。按二十代推算,他们的始祖落籍贵州应当是在明初。
2、据穿青各姓家谱记载,以及祖坟所在地,穿青最早落籍的地方是在贵阳和清镇一带,有一部分可能在贵定和龙里一带也住过。贵阳府城是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建的,清镇明初是威清、镇西二卫,城是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建的,这些地方在明以前还是很荒凉。现在贵阳市中心当时还是森林地带,称黑羊大菁,属彝人土司统治。这些地方汉人的聚居区要到明初才开始,所以穿青不可能在明以前居住在这些地方。
穿青为什么在明初要迁移到贵州来的呢?他们迁来时是什么社会身分呢?
上面已说过,穿青的传说和家谱记载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洪武“调北征南”、“调北填南”,随军入黔的。
历史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出兵二十五万南征,分两路进攻云南:主力自辰沅(沅陵、芷江),入普定(安顺),进兵曲靖,克昆明,趋大理;另一路自永宁(叙永),出乌撒(威宁)。十七年(一三八四)凯旋班师,并留重兵驻守上述两线。这两路正是对当时水西土司地区的包围线。在这包围线上,建筑了十一个城。清镇一地就驻军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二户。按明代制度,驻扎在边区的军队须在当地解决粮食的供应。所以军队驻扎地方,占有土地,分给驻军耕种,生产粮食,称作田。没有军籍的人享受不到配给土地的权利。而当时贵阳、清镇这一带地方农业还没有发展,即使有些已经开垦了的土地,全部配给军队还不足,其他的人不容易得到土地是可以推想得到的事实。
穿青的祖先是“随军入黔”服务于军队的劳役和商人。我们还没有确知他们在江西时是些什么地位的人。但是据他们的传说当时是强迫服役的,“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甚至很普遍的说是捆着来的。军事结束后,这些人得不到配给的土地,有些家谱记载得很具体,起初欺骗他们“军民一体”,而后来“好田好土,堆屯军所”,土地都给屯军占了,(张氏族谱)。当时军屯建有城楼,还有炮台自卫,但是却“与民无涉”(陈氏族谱)。所以穿青人说:“军强民弱”。谱书所载和历史情况是符合的。穿青是当时社会身分较低的“民”,不是“军”。
所以,穿青人的祖先是明初从江西随军入黔的一个社会身份较低的汉人移民集团。
五、穿青聚居区的历史情况
穿青入黔时是一个汉人的移民集团。从这个事实还不能得出他们后来没有演变为少数民族的结论。
部族和民族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任何历史现象都受变化规律的支配,原来是一个部族或民族的人,由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分别形成几个部族或民族。美利坚民族和英吉利民族的分离,斯拉夫人分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大俄罗斯三个民族,蒙古人分成了几个民族,都是具体的例子。穿青有可能是从汉族(严格说,明初还是部族时期)分离成为单独的部族,发展成为单独的民族。
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穿青所进入的地区各时期的社会性质和演变;穿青在各时期所处的地位,所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和经济上所发生的联系。
现在穿青的聚居区的历史简单地说是这样:
古代属且兰、夜郎地,为战国时楚将庄矫所征服。且兰、夜郎土著可能是仡佬,他们的政权要到唐代才结束,他们的社会性质估计可能是奴隶初期。
三国末年,蜀后主遣济火征服普里的“仡獠”。济火是夕(下加横)人,普里是安顺,仡獠是仡佬。
唐代夕(下加横)人领袖阿扯(济火的三十二世孙)袭杀比喇仡獠领袖巴慕蜡,夺其地。阿扯属卢鹿部,从镇雄一带地方强盛起来的。比喇是织金。
唐武宗时(八四一年)夕(下加横)人领袖阿坝内附封为罗甸王,当时已成为奴隶国家。五代时占领了贵阳一带。宋封其王阿更为矩州刺史。矩州即贵州。
罗甸园的地域大体上东至贵阳,西至曲靖、昭通,北至长江,南至盘江,曾一度臣服于南诏,但实际上是独立的。
元代蒙古军队从西康南下灭大理国,罗甸国降。但初期屡次反抗元朝统治,一二九五年才服。当时称有五万户,置宜慰司。这个地区称“亦奚不薛”,即水西之意。水西土司时期开始了。一三零*年又反,失败。从此元朝改变水西的贵族支派交替主政的制度,确立世袭制度。
元亡,水西附明。水西地区是在由川入滇和由黔入滇的两交通线所包围的内圈。高山重叠,道路险恶。明太祖估计如果水西不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实录一四六),但是要进水西,“必以十万众”(实录一四七),所以采取羁縻手段,沿袭元制封宣慰司。四围驻兵监视,估计水西“必不敢为乱”(实录一四六)。又令宣慰司设治于贵州城内,不得允许,不准离开。明朝和水西是这样维持了初期的和平关系。后来明的力量减弱,利用水西武力来镇压贵州各少数民族,水西也就强大起来。明末水西土司弟安邦彦自称罗甸王,不服明朝统治,进攻贵阳,奄有黔西全境七年之久,出兵至十万多。一六二八年安邦彦失败。明占据了鸭池河以西原属永西土司的土地,筑城三十六所。以兵四万八千人在鸭池、安庄(安顺)傍河经营屯田二千顷。“田为世业,而禁其私买卖”。当时又企图取消土司制度,直接遣派官吏统治这个地区,即所谓“改土归流”但条件不具备,未成。
元明两代水西在土司制度下,社会经济应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统治阶级一直维持着他们的统治,而且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原有的奴隶制度基本上不容易被破坏,估计当时已是奴隶末期。
水西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变革是发生在吴三桂击败水西,取消了土司制度之后。战争是一六六四年开始的,离安邦彦失败只有三十多年,经过这两次严重的战役,土司的实力才基本上被摧毁。这两次战役都是激烈的。安邦彦之役,明朝损失主帅王三善。吴三桂之役如果不是土司手下有人叛变,还是胜负难定。土司手下人的叛变说明当时奴隶制度已到了难于维持的地步了。
水西地区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是取消了,但是土司手下的土目还保持他们的政治经济的地位。他们对自己的奴隶和佃客具有统治权,但是“不得擅予军民事”,军和民都是汉人。水西地区的汉人如果不是土目的奴隶或佃客就不受土目的统治和剥削了。
从我们所调查到的材料看,土目的经济一直没有超过封建初期的领主经济阶段。但是水西区在改土归流后,就发生了封建的地主经济。这是汉人,包括穿青、穿蓝,发展起来的。
很明显的,紧接着改土归流,就有了大批移民进入这个地区,经过吴三桂的战役,不但土司权力消灭了,土目势力削弱了,而且这地区的人口损失很大,特别是战争中心区的织金,织金是比较富饶的农业区,一直有余粮供应大定和毕节的。
六、穿青在水西土司地区
穿青和水西土司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设想如果穿青曾长期受彝人土司的统治,而和汉人隔绝,他们虽则原来是汉人?也可能因此而形或一个单独的部族。
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穿青并没有和汉人隔绝,也没有受彝人统治者的明显影响。为什么呢?穿青进入贵州后定居在贵阳、清镇一带。这一地方正是水西土司管辖地区的边缘,也正是、在明朝驻军筑城的防卸线上,穿青的地位正处在两者之间。一方面他们因为没有配给到土地,向土司讨土地种,要受到土司的剥削;而另一方面却也和汉人军屯和官吏有联系,可以取得支持,逐步脱离土司的管辖。而且在汉官的庇护下还可以夺取其他少数民族的土地,占为自有。
穿青各姓家谱中有很生动的记载:
清河张氏族谱(颖川陈氏族谱同):叙述他们刚到这地方的时候,“四里人民买土居住,耕山挖箐,梨霍未饱,以后尽被安家(即水西土司)磨折,每年要收盖头钱,烟火钱,做夫,日打夜吊,苦磨难当,是时四里人民哭思身无父母,举寨惶惶。”到万历年间,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穿青那时已经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有了土地,有了钱,申请当时政府立贵筑和新贵两县,出资报效,据称共计一千二百两。按所记每人捐二钱三分计算,当时这地区的穿青已有五千多人。立县的意思是“买主当差”,就是摆脱土司的统治,归汉人官府管辖,查史籍新贵县确是万历二十九年设置的。
李氏家谱:“永乐十七年,有三寨虎场猫(苗)头不服王化,钦命剿灭。选作向导。担荷乐酒于前,以为献寿之敬;暗伏精兵于后,以为剿灭之需,将三寨猫属,斩尽无存。封为平寇大将军,即以三寨猫属土田,载粮十九石,为报功之宀(下取)。----这是凭籍官府势力,夺取苗人土地的传说。有此传说的不只李氏一姓,而且清镇确有三寨虎场,李氏祖坟也在该地。
明末,穿青当时所居住的地方成了水西土司和明朝冲突的拉锯地带。当安邦彦势力强盛时,明朝势力退出这地区有七年之久。当时情况,穿青人的谱书中也有记载,“天启元年,安酋作叛,贵州人民尽绝,存剩一千人买(马),贼将民寨身住扎,日唤老人谈话,夜唤十七八岁之女子凌辱。四里人民寒心。杀牛祭天,杀马祭地,伙成一把,分为四万九千把兵,杀援贵州。”,事平后,他们的土地归入县治。
从这些材料看来,明末水西土司势力削弱以前,穿青主要聚居区是在水西地区的边缘,已经有几万人口。安邦彦失败后,一方面鸭池河以东地区脱离了水西的管辖,把“傍河可屯之地不下二千顷”授予军队,另一方面明朝的势力深入永西腹地,在现大定、黔西、织金三处筑城。这些措施和穿青的关系是密切的。他们原住的地方来了大批军队移民,把傍河的土地都占了,使他们不能在这地方再发展了。而织金一带富腴的土地却成了他们可以进去开垦的地方了。从这时起他们开始西移。
当吴三桂进攻水西时,在水西腹地已有穿青,而且参加在水西方面抵抗吴军。那时忠于明朝的汉人参加在水西方面的不只是穿青。现在大定穿青还有这样的传说:“到吴三桂同水西斗争时,恰巧我们有好多农民住在现在的纳雍勺窝、田坝到织金的以那架这条军事据点的要路下。当时水西喊的口号是‘若不跟随我们杀吴王,便叫你穿青归还江西,穿蓝归还湖广’。大批农民住户,逃不可逃,只得听命……。穿青便受到穿蓝的一种斥问:‘你们是汉人,为何又同水西来打吴王?’穿青无词可措,亦只得说:‘穿青衣,保黑王,各为其主’”。最后这句话,在贵州是流行的。
更多的穿青是在吴三桂之役以后迁到织金、纳雍去的。现在这地区的穿青大多有十一代,十代、九代或八代。
按照穿青居住地点和移动时间来看,他们一贯的是处在汉人和水西接触的边缘上,是向这地区逐步推进的移民中的第一线。这个前锋却并没有完全脱离汉人的基本队伍,但是也长期和其他民族相接触,保持了他们一定的独特地位。他们这种处境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一方面没有留下彝族影响的烙印,另一方面长期保持了他们原来的地方性的特点。
七、穿青和穿蓝的区别
应当指出,在同时或稍后一些,进入水西地区的移民并不只是穿青,还有来自各地的其他汉人,这些汉人在当地称作穿蓝,以别于穿青。穿青和穿蓝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当地群众都很强调穿青、穿蓝是籍分不同,就是说他们是从不同地方来的。“穿青来自江西,穿蓝来自湖广。”在早期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明初确曾有过指定一个地方的人迁移到一定地方去的办法,在贵州常听到这种传说:“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贵州、江南填云南,普定。”那时一个移民集团常是一个地方的人。穿青这个移民集团是江西人,乃是事实。但是从江西来的人并不限于这个集团,所以穿蓝之中也有江西人。而且只要不属于穿青这个移民集团的汉人,进入这个地区后,都被称为穿蓝,所以穿蓝也不可能都是一个籍分的人了。以籍分来区别穿青和穿蓝是不够的。
早期,穿青和穿蓝在社会身分上是有区别的。明初进入贵州的人,除了官以外,有军和民之别,军有军籍,他们带有家属,配给土地和农具,在军事据点的卫所附近屯田居住。按明初的制度这些军家是“世守”的,就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他们在社会上有势力,有地位。至于那些随军服务的,做小买卖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称为民。他们得自己设法解决生活问题,而且还要为政府服役、缴税和纳粮。这些“民家”的社会地位是低的。穿青不是军家而是民家,在毕节有一部分穿青现在还称“民家”,安顺区和毕节区都有一种人被称为“里民子”,经过我们的调查,他们也就是穿青。“里民”就是穿青家谱上常见的“四里人民”,也就是编里纳粮的“民家”。这也是说明了穿青早期的身分。
穿青初来时社会地位既然是低的,甚至传说是捆着来的。来了之后,又得讨土地来耕种,男女都下田。女的要劳动,保持了不缠足的风尚。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地位又是低的。穿青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官得势也就不容易,所以穿青早期做官的人极少,甚至可能没有。当然他们家谱上也有封侯进爵的祖先,但附会的多,而且些人却又总是“弃官务农”。对于穿青人他们不容易做官这个事实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来加以自嘲:清镇调查:“穿青早年没有当官或中举的,他们说李代龙(李姓穿青的始祖,也是穿青中最有声望的祖先)平服了三寨虎场后向皇帝报功。皇帝问他要什么?他说要苗王的地方和一石二斗芝麻的子孙,皇帝答应了。没有要做官,所以穿青世世代代只有耕田人,没有做官的。”当然后来到了清朝穿青也有功名的,但是并没有出过大官是事实。
穿蓝则不然。他们中间有的是到这地方来做官,后来落籍。这些人有地位,有势力。他们中间也有经商来的,发了财在这地方住下了。有钱也就有势。这些人瞧不起穿青。当然穿蓝中也有很多是农民和穿青一样劳动。穿蓝农民并不歧视穿青,有些地方甚至因为穿蓝农民干活没有穿青强,还受穿青的轻视。穿青、穿蓝的区别显然不在乡间,而在城乡之间。
大定调查时,有人告诉我们,穿青、穿蓝的名称是起初在城里面叫开来的。城里人瞧不起乡下来的那些衣服穿得古怪的人,称他们作穿青。这说法是否事实还不能肯定,但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城乡区别。“穿青住乡头,穿蓝住街头。”这是一句流行的话。
穿蓝中不论做官的,或是经商的,都是先到城市,站稳了,买土地,成地主。大多还是住在城里或是街场上。穿青是农民,在土地上劳动,住在乡间。即使从土地剥削中起家成了地主,还是大多在乡间住,是土地主。穿青不织布,不经商,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比较大的街场上都不容易找到穿青人家。
总的说来,穿青这一个早期的移民集团和当地其他汉人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地方性的、等级性的、城乡性的区别。他们在口音、服饰、风俗、信仰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这些特点是部族内部的差别,不能看作是民族特征。当然这些部族内部的差别,可以成为民族特征的萌芽,但是这只是可能性,没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是发展不起来的。穿青这些地方性特点曾否发展成为民族特征的萌芽呢?让我们看看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的历史情况。
八、新兴地主阶级和土目的斗争
上面已说明:
1、改土归流之后土目经济有一定的发展,由奴隶末期进入封建初期,主要是领主经济,而土目经济以发展到这个阶段为限。
2、改土归流以后,汉人(包括穿青、穿蓝)大批进入这个地区,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在这个地区发展封建后期的地主经济。
穿青、穿蓝要发展地主经济首先要从土目(彝人为主,个别也有汉人)手上获得土地,还要在这地区取得经济上的领导权。于是新兴地主(主要是穿青、穿蓝,也有彝人、蔡家、苗人和仡佬等)和土目之间的矛盾成为改土归流之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大约是从康熙到道光这一百五十年之间。
土目的土地在织金称“庄上地”,不属土目而交皇粮的土地称“里上地”。在这个斗争中,新兴地主之间的矛盾是不显著的,穿青、穿蓝的地主们联合在一起。道光初年织金穿青培修大佛寺,穿蓝朱家资助银两,而且“普化客商居士协力监造”。客商是穿蓝。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还没有听到在这一个时期中穿青、穿蓝地主间的斗争。
乾嘉时代,经济繁荣,这个地区新兴地主的势力也蒸蒸日上。农业的繁荣也反映在这个地区城镇的上升。大定在嘉庆十一年(一八O六)已有石木泥水工匠所兴建的祀鲁班师的寿佛寺。嘉庆十八(一八一三)建有楚省会馆,石碑上刻有捐款人二九三名。道十三年(一八一三)有屠行碑记在黑神庙。规模宏大的江西会馆是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重修的,嘉庆十一年(一八O六)重修时所立“吉府会馆碑”有人名四百二十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O)又重修,碑上名字有一八六个。毕节的江西会馆是嘉庆十二年(一八O七)修建的。织金的江西会馆万寿宫是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重修的,湖南会馆三楚宫是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修建的,鲁班庙是道光十年(一八三O)修建的。乾隆起到道光,各城会馆的修建都说明当时外地进来的商人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行会的兴起说明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也就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纳雍、织金乡村的经济中心街场(定期市集)上发生了一联串的新兴地主和土目争夺领导权的事件。纳雍大兔场的建立是一个例子。在一百多年以前这地方有一个安家土目所控制的老场,十二天赶一次。土目在场上打头钱(场捐)很高,而且随意拿东西。商业活动是不发达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新兴的经济力量感觉到了土目势力的束缚,穿青地主郭朝臣领导了十八寨的群众并联合了穿蓝地主,在大兔场修建了房屋,开辟不要捐税的新场。穿青、穿蓝是在一起和土目斗争的,有人说那时是“穿蓝出主意,穿青出力气”。(这也说明当时穿青较穿蓝人数多。)又组织武力保卫新场,结果土目的老场垮了。新场后来七天两头赶。
土目的势力在各地先后失去优势,代替他们控制地方经济势力的是封建地主。
九、农民运动
封建地主的上升,土地买卖(织金有碑文)和兼并,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分化日趋激烈,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尤其是因为当地的地主受了土目经济的影响,劳役地租严重,高利贷苛刻,农民的生活困苦。
织金为例:穿青王绍兴家在道光年间已有七、八百石租子:号称朱家朝门的大地主,道光年间据说由百余石租发展到三千石租。
在这个时期,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通过这个地区进兵四川。各地原已在暴发中的苗民起义,在新的鼓励和剌激下,扩大成了包括各族农民的起义。当时称民间武装集团为“龙杠”,最初是发生在土目、地主本身的斗争中,后来阶级斗争激烈了,也出现了农民领导的龙杠,这是说农民也武装起来了。
穿青在这个地区的农民中当时已有重要地位,织金的农民龙杠领袖之一就是穿青的陈友梅,他是挖煤的农民出身。对方是官军和地主武装,他们的领袖不是穿青而是穿蓝和彝人土目。
这一时期的斗争是复杂的,在农民运动中还插入了苗民和包括穿青在内的汉人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以民族为界限的。
这次农民运动屡仆屡起支持了二十年之久,就是咸同时代。最后,起义的农民是失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但是封建势力却也被削弱了。为接着来到的外来商业势力的发展敷平了道路。
十、商业势力的兴起和青蓝隔阂的形成
咸同之后、中国已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内民族市场开始形成,原属自足自给割据性的封建经济渐次崩溃。水西地区的地方经济也进入了民族市场之内。
清末民初,水西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农民战争的废墟上,许多新来的四川人和湖广人建立起他们新的农舍,农业生产恢复了。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这地区的街场出现了新的面貌。
这地区原来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被洋纱、布匹的输入,鸦片、粮食、肥猪、药材的输出所打破了。以洋纱朱说,光绪年间已大量输入,一八八九年,当时平远州(织金)的知州已经因为纺纱的妇女大量失业而惊觉起来。大定、纳雍原有的棉花行也在这时期纷纷倒闭。洋纱的输入推动了织布业的发展。民国初年扯梭陡机代替丢梭平机,出现了专业的织工。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纳雍街上一千三百户人家。有八百多架织布机。解放前五、六年织金以那架场上六百多户人家,也达到了八百多架布机。
清末民初,这地区主要输出品是鸦片。外来商人运入棉纱、百货,高价出售,低价收购鸦片。四、五月是旺季,纳雍卧这猫场,每场收购烟土六、七百斤、大兔场是集散中心,最高时据说一场成交达到千挑。那个时候,这地区儿乎家家种烟。
通过农产物商品化,这地区的经济,甚至每一个人,都和国内市场密切联系了起来。
商业日益发展。商品集散中心的街场,人口多,场期密,而且涌现出区域性的中心场。每个中心场都控制着一批初级街场,另一方面又和贵阳、安顺等城市相衔接。构成了一个商品流动网络。这个网络掌握在追求利润的商人手中,用不等价交换,榨取这地区的
广大农业生产者。
掌握这市场的是谁呢?是外来的汉商,也就是穿蓝。和外面缺乏联系的穿青在这新兴经济的领导势力中却没有分。上面提到的织布业,一个穿青都没有,穿青人是一向不织布的。上面提到许多中心街场上,穿青不但不参加,反而是日渐减少,他们退了出来。不但是“穿蓝住街头,穿青住乡头”,而且是“穿青卖生货,穿蓝熟货”。当然,乡间也有穿蓝,但是街头却实在很少穿青。
纳雍大兔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初大兔场的建立是以穿青为主的。新街上住的大半是半商半农的穿青人。穿蓝的唐、何、吴、姜、彭诸姓还是配角。但是咸同之后,形势改变了,穿青逐渐搬走了。唐姓出了举人,吴姓成了“吴半街”,晏姓做了地主。街上绝大多数是穿蓝。
穿青感到威胁,但不明白为什么原因。郭书奎(大兔场建立者郭朝臣的孙子)重修文昌阁,企图把街上的龙脉压断。风水并没起作用。据说穿青曾另外开了个新街,新街撑不起来。穿青在街上被排挤了。还不止此,郭家的土地也保不住了。穿蓝恶霸何定公霸占了他的土地,虽则在何定公初起时,郭家还帮助他修建营盘。
这一个时期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和国内民族市场领导势力没有联系的穿青是参加不了这新兴势力的。这个领导势力是汉人中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他们通过不等价交换榨取利润。穿青地主剥削来的农产品不值钱了,穿青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加重了。
就在这个时期,纳雍、织金、大定,各地都发生着不断的,大小规模的,穿青和穿蓝地方性的械斗。
也就是这个时期,到处可以听到穿青骂穿蓝是“野狗精”,穿蓝骂穿青是“通背猴”。例如大定猫场上在民国二十年出现这样的标语:“沙抱来了一只猴,上街下街随你游,猫场自有真人在,杀尽你这一群猴。”而另一方面也贴语“猫场出了一条狗,上街下街
落你手,老子施威给你看,杀尽你这一群狗。”接着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这个时期穿青和穿蓝的矛盾显著和突出了。这是新兴资本义商业所带来的矛盾所引起的。矛盾的双方实际上是被排挤在商业势力之外的乡间穿青地主和城市里控制着这地区输出和输入的穿蓝商人。穿青地主发动斗争的动机是在于他们所剥削来的农产品(包括鸦片)在市场上卖不起价钱,本来已被他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通过市场上的贸易,大部分转移到了穿蓝商人手中去了。他们不甘心,而且,城市里穿蓝商人手上钱多了,不能在商业里找出路,回到乡下来买土地,更直接威胁了乡间穿青地主的封建利益。他们利用了穿青这个移民集团传统的乡土感情,和利用了穿青农民对日益增加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情绪,鼓动群众,促起青蓝之间的械斗。械斗的触因常常是街上偶然的口角。参加械斗的常是乡下赶场的穿青和场上的穿蓝,乡间的穿蓝大多不参加这种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穿青和穿蓝群众也伤了感情。产生了隔阂。
十一、穿青地方性特点的消失
穿青和穿蓝的这种斗争,结果是否使穿青地方性特点更加发展起来,成为民族特征的萌芽?没有。相反的,他们原有的地方性特点,就在这五、六十年中逐渐消失了。
穿青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他们放弃老辈子话,三把头,并不像苗家的被迫改装。这些改装是穿青人自己搞的。他们说:出外走走的人,觉得这些传统方式吃不开,回来就提倡改装。还有说:孙中山先生提倡放脚,穿蓝已不缠小脚,穿青也该改头,不要再梳三把头了。
在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大定有若干穿青地主还在民国初年就要他们妇女改梳平头,不要她们穿大袖滚花的上衣,甚至要他们的女儿裹成小脚,嫁给穿蓝。有些把五显坛都送出了门。
这种倾向是不是和在街子上不断发生青蓝械斗的现象相矛盾的呢?如果我们把这许多现象看作是汉族从部族进入近代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尚未完成的过程,那就不会觉得是矛盾了。
穿青原是在明初封建时期从汉族这个部族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是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他们虽则是移民的前锋,在彝族土司统治的地区边缘上居住了相当长的时期,又在土司势力刚被削弱的时候,进入了水西的腹地,和汉人聚居区曾有过疏远,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一直受到汉人的庇护,经济上也维持着一定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割断过。他们所接触和进入的水西地区,在早期尚在奴隶末期和封建初期,他们在生产技术上和生产关系上都是比较先进的。他们没有受到彝族的深刻的影响,一般连彝话都不会说。他们在这个比较闭塞的山区里发展农业生产和封建的地主经济。但是近百年来外边的汉人却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了。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就在这个时期,汉人从封建主义地方割据的部族时代向近代民族发展。国内民族市场的形成,在清末民初,把水西地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打破了。部族时期遗留在边区的移民集团这时不可能再维持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和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使他们自动的放弃了地方性特点?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没有挫折的。当时形成近代民族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他们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要垄断国内民族市场,榨取最大的利润。他们排斥当地经济势力参加到剥削集团里来,于是引起了斗争。这种斗争并不使地方经济势力更向割据的路上发展,而相反的,是朝放弃地方主义的方向走。因为这样他们才容易和外界取得密切联系,不致更受排挤。所以结果也是放弃地方性特点,从部族割据进入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去。
穿青近百年所经过的历史就是这样。
十二、穿青和穿蓝在发展上的不平衡
地方性特点的消失并不是说穿青和穿蓝事实上已没有差别。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地位并不是相等的。因为有着过去这一段历史,他们在发展上是不平衡的。
上面已说过在历史上穿青的社会地位较低,遭到穿蓝的歧视。解放后虽已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态度,但是残余的心理还是存在的。
重要的是城乡区别所形成经济上的不平衡性。穿青主要是农民,农产品的生产者。他们没有商人。过去穿青的经济一直受着穿蓝商人所剥削和控制的。即在封建经济中穿青、穿蓝虽都有地主,经济势力上也不是相等的。穿青的地主是从土地剥削中产生的,而穿蓝的地主是从官僚和商人起家的。官僚有势力霸占土地,商人有资本,收买土地。所以穿蓝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多,势力大;穿青的地主,数目不少,而土地却少。
政治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上面已说过,穿青过去做官的人是极少的,据说有一个人当了县长,但没有到任便撤职了。如果和当地穿蓝相比,太相悬殊了。穿蓝中丁家、谌家都出过大官,有做到总督的,在当地政治势力上,穿青也总是在穿蓝之下。解放后,政府虽已大力培养穿青干部,但比例上还是不足,更少在外面服务的机会。
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落,在文化发展上也受到影响。穿青过去虽也有举人和秀才,但数目远不及当地的穿篮。民国初年起穿青上层会办学校,增加了穿青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穿青的知识分子出路狭小。有许多人只能去学做道士,以致有人指出穿青道士多。而当地的穿蓝呢,有科学家和大学校长。
穿青和穿蓝在发展上的不平衡也加强了穿青和穿蓝心理上的隔阂,而感觉到过去受压迫。
十三、穿青对民族成分的态度
穿青在解放后对民族成分的态度反映了上述的历史过程。他们大多数群众的态度是并不否认自己是汉人,但是和穿蓝一起没有区别的都被称为汉人,觉得不愿意。坚持不愿意当汉人的是少数,大多数在比较偏僻的地区。聚集区边缘交通方便的地方很多穿青人已报了汉族。
穿青人过去并没有否认过自己是汉人。
我们所收集到的谱书,没有例外的,把汉人中有名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祖先,比如张氏可以联系上张良、张飞,比如刘氏可以联系上刘邦、刘备。这种情况在苗人和彝人中是不易见到的。
在历史上凡是发生民族斗争时,穿青总是在汉人一边的。在吴三桂和水西的战斗中,他们站在水西一边,那是因为这次战争还包括着明朝移民和清朝的斗争。就是这样,在传说中穿青还要声名是出于不得已。
从当地少数民族对穿青的称呼看,也没有例外的被看成是汉人中的一部分。
日常谈话中,穿青都是很自然的不把自己归在少数民族范畴中。比如问:这里有哪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答语中很少把穿青数在里面。
穿青过去也从来没有自觉另外是一个民族或部族的单位。他们这个集团并没有一个自己承认的名称,穿青这个名称原来认为是别人对他们侮辱的称呼。过去绝不能当面问对方是不是穿青。我们知道有不少地方穿青和穿蓝争着做“真汉人。”。“穿青穿蓝是一家”的说法在青蓝杂居的农衬中是很普遍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并且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起来。水西地区原是多民族地区。民族政策的贯彻,鼓舞了这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深受压迫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纷纷的公开他们的民族名称,要求在民族大家庭中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胜利。
这地区的穿青,过去也受到歧视,他们深切感到不平等的痛苦,他们拥护民族平等政策。看到其他过去受过歧视的少数民族站了起来,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要求平等和反对歧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并不明白民族这个概念,也不明白他们受到的歧视的、性质。他们认为凡是被歧视过的人都是少数民族。
穿青原来并不否认自己是汉人的,但是解放后,特别是在普选登记时,穿蓝都报了汉族。穿青觉得如果也报汉族那就是否定了穿青和穿蓝之间的区别了。那是他们不愿意的。
也应当提到,解放不久,大定、纳雍、织金的穿青地主曾召开过会议。因为当时他们听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像汉族地区一般要进行土地改革,所以酝酿和鼓动穿青要求少数民族待遇。据说“穿青族”的名称是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名称群众是不满意的。
穿青一方面并不否认是汉人,一方面又自称少数民族,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但是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却并不如此。他们念念不忘的是穿蓝和穿青的区别。这种心理实在是反映了过去斗争的历史和发展上不平衡的现实。如果承认了这个事实,而予以适当照顾,他们作为汉族中的一部分是并不难于接受的。
我们在调查中接触到各阶层的人,大多数愿意称为汉人,但是有条件的。有的说:“穿青是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有的说:“穿青是古汉族”,有的认为被圈在汉族之外是不好的,但是在汉族之内如果和穿蓝一般待遇也不好。我们体会大多数的意见是这样:穿青、穿蓝的区别不应抹煞,穿青必须加以照顾才能发展,如果穿青一旦认为汉人而会和穿蓝一般待遇,那是他们不愿意的。
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事实上不平衡发展的情况已经不存在,大多数穿青坚决自认汉族,他们已经报了汉族。这一部分人数估计很不小。
在偏僻的山区,和穿蓝隔阂较深的地方,也有坚决不愿称汉族的。
十四、结论的重提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论应当是:穿青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