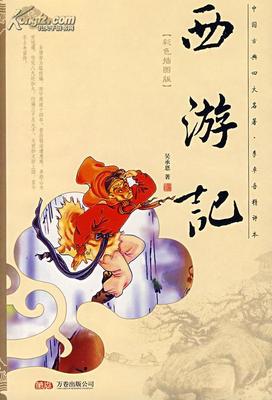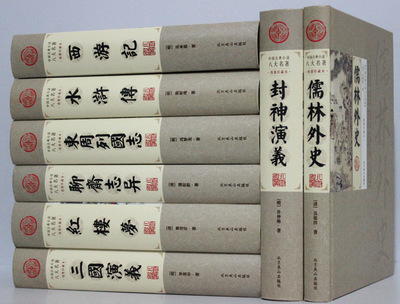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
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
在当时我国新诗作家们所说的意象,都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舶来品,是本世纪初到20年代意象主义(imagism)运动在西方兴起后的产物。由于image这个词,在英语中具有“肖像”、“形象”、“写生”、“意象”等等多种的含义,因此,当时的翻译名称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梅光迪把imagism译作“形象主义”,梁实秋把它译成“影像主义”等等。
但比较流行的译法是“意象”。
国内学者谈到“意象”往往就离不开“image”,认为是从西方输进来的。闻一多先生在《说鱼》文中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朱光潜先生1948年出版的《诗论》中,也认为“意象”一词来自西方,是英语image的译名。这些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国外的学者们,主要是一些外籍华人,在他们过去所写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凡涉及意象的,往往也不假思索地视之为意象主义的产物,这就不足怪了。
西方在本世纪初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传人中国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在那时颇热闹了一阵。后来也就逐渐趋于沉寂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而随着我国闭关锁国多年后开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近年来国内诗学界和批评界又有很多文章再一次大谈意象以及意象美;“意象”一词,又重新风靡一时,但大多仍把它视为舶来品。
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其实,关于“意象”的理论,在我国的美学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对于意象,我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过很多的、以至精辟的论述。而且,即使西方从本世纪初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也曾从传统的中国文学,主要是古典诗歌中吸取过丰富的营养。在本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我国的“五四”运动前后,当我国由于革命文学的兴起,而对传统的文学开始进行必要的、然而带着形而上学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时,西方在这时却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一时出版的汉诗英译著作竟有十余种之多。意象主义的“大师”或翻译中国文学的名家,如美国的艾滋拉·庞德(Ezra Pound)、英国的韦利(A.walev)等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中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座五光十色、美不胜收的艺术宝苑,并一致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并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竞相折服。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翻译,在客观上促进了意象主义的发展,而意象主义的兴起,又推进了汉诗的英译艺术;用格莱汉姆(A.C.Craham)的话说,就是:“汉诗英译艺术是意象主义的副产品”。这是说得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在谈到诗歌的意象问题时,我们虽然大可不必家有敝帚,视若珍宝,表现为国粹主义的态度,但也大可不必家有珍宝,视若敝帚,采取无视自己民族优秀传统的态度。
因此,本文想着重地论述一下我国美学史上有关意象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史学的和理论的探讨,为进一步研究中西诗歌意象的同异提供一些资料和看法。至于西方关于意象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意象的论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本文在论述中虽偶有涉及,但不做具体的论述。
一、我国意象论的两个源头
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典籍中,虽然不曾直接而明确地提出意象的概念来,但涉及意象问题的论述却有很长远的历史。意象论有两个历史的源头:《周易》和《庄子》。这两部书虽然并非文学著作,但它们对后世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先说《周易》关于“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
我们知道,《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关于“象”的著作,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由变化多端的卦爻之“象”,来表现流动不居的现实的吉凶祸福。所谓“八卦以象告”,“《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是故《易》者象也”(《系辞下》)等等,都是说的这一点。它关于“意”、“象”关系的论述,散见在许多地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系辞上》的一段话中:
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段话除了涉及“言”与“意”的关系之外,中心意思就是说“言”、“意”是不能完全表达的,可以由“象”来表达。从这里,就可以逻辑地推出一个结论:“象”比“言”“意”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那么,什么是“象”呢?《系辞上》回答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下》)的结果。这里讲的是八卦之象和象形文字之象。由于文字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也包含着文学。说明文字和文学都是和模仿现实有关的。我们知道,在西方早期美学史上,由于叙事性的戏剧比较发达,所以很重视模仿。柏拉图主张艺术是理念世界的事物的摹本,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艺术是客观现实的模仿,如他所说的:“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是模仿”。这里虽然有唯心、唯物之别,其强调模仿则一。而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由于最发达的是抒情性较强的诗、乐、舞,因此比较强调情感,较少关于模仿的理论;如果说有的话,我们从《周易》的上面一些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这类消息。这一点虽然在后世我国美学史上也有某些影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象其物宜”,但是,总的说,这方面的影响并不大。
《周易》所提出的“象”与“言”、“意”的关系,对于后世美学和艺术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它的由小见大、由具体表现一般的原则。因为“象”总是具体的和个别的,《易》的“象”则是要借助于具体、个别的形象去阐明一般的哲理。文学艺术的具体形象性,恰恰在这一点上和《易》是相通的。《系辞下》就言(辞)与象的关系所说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等等,与文学艺术创作中以小见大、以少总多的特点完全是相一致的。因此,常常为后世的美学批评所运用。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评论屈原创作的特点是:“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在《总术》中所说的“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在《宗经》中所说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等,都是《周易》的这一思想的发挥。
既然《易》象应该具有以小见大、以迩见远、乘一总万的特点,那么“象”就应该很自然地具有象征性的特色。而象征性,也恰恰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黑格尔认为,艺术的象征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意义”及其“表现”。具体的、个别的“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而“表现”的目的,则是“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这就是说,艺术的象征性应是具体、个别和广泛、普遍的浑然一体。《易》大量使用各种象征性的物象来表达《易》理,而很多爻辞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如《中孚》九二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屯》六二的“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否)九五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等等。所以陈骥的《文则》认为《易》之象,就类似诗之比:“《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这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比的手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象征性的。其实,兴也不例外,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周易》之象所以通于诗之比兴,在根本上就在于它的象征性上,以象征性的事物和手法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或哲理,也即以象达意,通过个别表现一般。
近年来,西方关于诗的意象的研究中,许多人都把修辞学上的各种比喻手法,如明喻、隐喻等等,看作诗的意象的范畴或意象本身,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和陈溃退骙、章学诚的意见相同或相通的。艺术总是离不开比喻的。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礼记·学记》所说的:“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就是广泛的譬喻。因此,提出这些看法来,虽有道理,却又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诗的意象的构成,虽然离不开象征和比喻,但又决非任何象征和譬喻都是诗的,或诗的意象的构成条件,事情并非如此。哲学或其他著作,同样可以使用比喻和象征。艺术创作的象征性和设喻,必须是艺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看到诗之象与《易》之象的相同或相通的方面,又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同,这区别是十分鲜明的,不能混淆。当代我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对这一点析之甚精。他说:“《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筏舍岸、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相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遽庐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以摭我春华,拾其芳草。……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达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妄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
在《周易》中,虽然并未将意象作为一个词组、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但对“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却是很富有启迪意义的,它对后世的“意象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庄子·外物》中的几句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庄子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应该说明的是:他的这一段话是专为哲学家而发的,而且是专为那种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神秘经验而发的。他并不重视“象”在表达抽象哲理中的作用。因此,从《周易》的重“象”(“立象尽意”)和《庄子》的舍“象”求“意”来说,两者是相反的或矛盾的。《庄子》重“意”的思想,认为“言”的目的在“得意”,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不应执著于工具性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其哲理被运用到文学艺术理论中来,对后世反对追求语言的华美而忽视内容美有过很大的影响,如所谓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落言诠”等等。还要看到,《周易》和《庄子》在求“意”这一点上,又是相一致的;都以“得意”、“尽意”为鹄的。这对诗文创作来说,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第一位的。有“象”有“意”的好诗自然多不胜数,但也有些诗虽然不一定有“象”,却必须有“意”。例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孤舟蓑笠翁,独钓塞江雪”,是“象”、“意”具备的好诗,而“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等,也都是好诗,但“象”却较差,似乎没有。庄子等奢谈舍“言”弃“象”而求神秘的、不能言传之“意”,“舍象”和“不恋着于象”都是可以的,因为“象”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借以明“意”的“理窟”,理之既明,“得意而忘象”自无不可;但“言”尽管被他们怎样视为累赘,不屑一视,终究还是离不开的。真的离开了,也就不会有他们传诸后世的著作了。至于文学家,实际上他们更加是离不开语言的。后世的文论家只不过是在运用语言的情况下,强调不宜执著于言,而应宣心写妙,意余言外,曲尽其情而已。如《诗品序》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六一诗话》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沧浪诗话》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水浒传》袁无涯、杨定见本第三十九回眉批的“情余言外”,等等,历代画论中类似的论点也很多。《庄子》的舍“象”求“意”而被引申为艺术应该含蓄、韵味无穷,近在咫尺、妙想天外的思想,从重“意”方面给了后世的美学思想、也给意象论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二、“意象”一词的出现
如果说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典籍中已经有了关于“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意象论的萌芽时期,那么,魏晋至唐时期,便是意象论的开始走向形成的时期。这和当时文学的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佛教的广泛流行及魏晋玄学的兴起有关。
佛教汉代输入中国,其广泛的流行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到处建造佛堂,塑造佛像。与此同时,人们在广泛地思考和讨论佛像(“象”)和佛理(“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普遍地认为:窈渺无边的佛理,存在于象外。如范晔《后汉书·郊祀志》论述佛教特点时所说的:“所求在一体之内,所明在视听之表”(袁宏《后汉记》也有类似的话),反对就象论象。还有的如所谓“执象则迷理”,而求“畅微言于象外”,“极象外之谈”等等。王弼的《周易略例》誉重一时,其《明象章》,对“意”和“象”的关系在《庄子》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明象章》可以说是沟通《周易》、《庄子》和佛学思想之作。从前者而言,要求求理于象外,被后人引申发挥而为美学思想中的“象外象”、“象外意”等等,成为意象论内容要求之一。从后者而言,王弼更加发展了庄子的舍“象”而求不可言传的神秘之“意”的思想。
而这对当时的文论是不能不发生影响的。
文学的特点是:使用语言这一思想的直接现实为手段,通过对社会生活和自然万物(“象”)的描写,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意”)。这里自然就会有一个“言”、“意”、“象”的关系。艺术在根本上离不开“象”,对生活的观察、感受是如此,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同样是如此。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就是说的创作中的“言”不达“意”,“意”不尽“象”,即对外物的主观理解和观察常常不够,而笔下的表现就更逊一筹的问题。这确确实实是古今中外作家们创作中最经常遇到的。陆机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却并未对它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刘勰《文心雕龙》则深入了一步,在专论艺术想象和构思的《神思》篇中,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意象”,而且将“意象”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论述了创作的各种准备后接着说:“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在这里所提出的“意象”,是指作家在生活中有了深切的感受和感动的艺术想象的产物。它既是外物(“象”)感召的结果,却又决不是外物本身,决非与作者本身的主观情感色彩和艺术想象无关的自在的、独立的外物,而是一个与作者的感情色彩、形象思维密合无间的特定的“物”。
应该说明的是,“意象”作为一个组词虽然被刘勰第一次提了出来,但他所说的“意象”和我国文论史后期所说的“意象”,或西方所谓的“image”含义并不尽相同,比之要广泛得多。《文心雕龙》由于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意象”实际上是一个偶词,其内涵实即一个“意”字(包括艺术想象),其实唐代司空图的《诗品·缜密》中提到的“意象欲生,造化已奇”,同样是如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张萱》中所提出的“意余于象”的观点,从画论方面对“意”和“象”的关系作了论述,和我国后来的意象论一脉相承。
当代西方关于“意象”的解释中,有一种把诗歌中出现的各种物象,例如梅花、兰花、柳丝、月亮、芳草、澄江等等都看作意象,如有些人对于唐诗的所谓“意象”的统计就是如此。这样的认识也是不妥当的。诗中的意象应该是借助于具体外物、运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一种作者的情思,而非那类物象本身。那些物象本身如果离开了作者的艺术想象和构思,就只能是单纯的“象”,而非诗歌的“意象”。至于有人说:“中国古典的'意象’是指用具体的形象曲传一个只能心会的玄妙的抽象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象征。”(着重号原有)则更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一论断,要么是把《易》之象和诗之象等同了起来,把《易》之象和诗之象都看成了“义理寄宿之遽庐”或“理窟”,或更通俗的说法,叫做理念的号筒。而不了解诗之象,乃“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其结果是“等不离者于不即”。要么是对中国“意象”理论的发展历史过于缺乏了解,不知道中国的意象理论所要求的,决非“曲传”一个“抽象意义”,而是通过作者心灵、情感浸染、重新组合过的物象。在这里,“物”感情化了,作者的情感又是以物化的形式出现。也既刘勰所说的,创作中的物我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5的关系。
三、意象论的成熟时期
意象的问题,虽然在我国提出得很早,但它的引起广泛注意,并趋于比较成熟的时期,却在明清。虽然这以前也有一些人提到它,如金代的元好问在《遗山文集·新轩乐府序》中称赞苏词所说的“自东坡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意象”,但并不普遍。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关于意象的论述才骤然多了起来。茶陵派的首领李东阳,前后七子中的王廷相、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谢榛、胡应麟以致清代的钱谦益、沈德潜、李重华、薛雪、朱承爵、方东树等等,都曾以意象论诗。这时所讲的意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象,或西方所说的image,而非六朝、唐人所说的意象。这里我们无法一一介绍他们关于意象的论点,只能将其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加以概括地叙述。
首先是强调诗的意象不宜过于质实和直露,而应该含蓄蕴藉,使人玩味无穷。这可以以王廷相为代表。他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说:

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斯皆色韫本根,标显色相,鸿材之妙拟,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卢仝)《月蚀》之词,微之(元稹)《阳城》之什,漫铺繁叙,填事委实,言外□帖,情出辐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嗟呼!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
这里关于意象的看法,很明显是吸收了严羽《沧浪诗话》中的镜花水月的观点,并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反对诗歌缺少比兴,“言征实”和“情直致”,强调诗的意象要蕴藉含蓄,旨远寄深,余味曲苞,耐人寻味。这一意见一般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对抒情短制一类的诗歌,更是如此,它的意象应该很富有暗示性和象征性,也即即兴的手法。上引闻一多先生之说:“《易》中的象和《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这个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不错的。富有暗示性或象征性的诗句,在诗歌中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兴句。《诗经》以后诗歌中的名句也常常都是兴句,这样的句子不仅在艺术上更精巧,并且往往凝聚着作者浓郁的情思。很富有感染力。正如明代的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为比、兴手法辩护时所说的:“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吟咏以候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王廷相认为诗的意象应该深远,富有情思,作者得于心,览者会其意,不能太实,影响读者的想像力;也不能太直露,略无余味,更不能“情出辐辏”,缺乏感染力。这意见无疑是好的。认为只有具备了以上特点的诗歌意象才是优美的艺术意象,才称得上是“鸿材之妙拟,哲匠之冥造”,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以这样的观点作为惟一的模式,甚至认为《北征》这样的诗史上的名篇,都非正体,而是诗坛的“变体”和“旁轨”,却无疑又是偏颇的。因为事情并不能概而论之,像《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除少数几句外,用的是赋体,但也叙述得维肖维妙,堪称化工,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卷四)中所说的:“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有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可见并不能以抒情短制关于意象的要求,去要求一切诗歌,譬如说叙事诗。但由于我国古典诗歌中,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因此,这一关于意象的观点,就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司空图、苏轼、严羽等等关于诗歌的不即不离、不黏不脱的观点,在基本上和这一要求都是完全相通的。
王廷相和上述那些论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诗歌意象的内涵不仅提出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和要求,而且,既重视了诗歌意象的现实物质基础,认为它来自现实生活:“凡具形象之属,生动之物,靡不综摄为我材品”;又十分重视虚构在意象形成中的作用:“摆脱形模,凌虚结构。”17就是说诗的意象既来自生活,又不能是对生活中事物原型的模拟,而是要在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这一见解无疑是十分精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能可贵的。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李东阳。他在《怀麓堂诗话》中通过对温庭筠《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名诗的分析说:“不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缀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若强排硬叠,不论其字面的清浊,音韵之谐舛,而云我能写景用事,岂可哉!”李东阳并没有正面提出对诗的意象的要求,如王廷相那样,而是通过对两句诗的分析,认为好诗除音律美外,最重要的是“意象具足,始为难得”。这两句名诗之所以被人们长久传诵而不衰,就在于它看来仿佛只是纯粹外在物象的罗列,实际上,这些纯粹的物象都是经过作者浓郁情思的熔铸,并被作者的情感的链条衔接起来的。或者用康德的话说,是经过想像力加工而重新建造起来的艺术形象。在这些物象的重新组合中,构成了优美的诗的意象;在这诗情画意的意象中,寄托了游子深切的羁愁,或者说游子深切的羁愁寄托在这些“野况”中。它含蓄、“不露本情”,却“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如同身临其境,真所谓“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这就是兴句或优美的艺术象征性在诗的意象中的作用,它所“曲传”的绝非用知性可以理会的“玄妙的抽象意义”,而是一幅具体、感性、生动无比的艺术形象。而如果缺乏优美的意象,如李东阳所说的,只是在字句、音律、用典方面下功夫,都是不可能产生应有的艺术效果的。
也许是一种巧合,美籍华人叶维廉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典诗歌与英美现代诗——语言、美学的汇通》中分析意象时,也曾以这两句名诗为例。他认为“这两句诗中的物象可以说是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构成一种气氛”,这种气氛的出现,是由于物象所具有的“同时并发性”(synchronous)引起的。他说:“在这种气氛中,我们在其中活跃而不从一特定角度来观看。我们不能从一特定的角度来观看,是因为我们一时无法知道(亦元意去分辨)究竟鸡、月、桥各自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应该说:'鸡鸣’是'月’(见于)'茅店’(之上),'人迹’在(满)'霜’(的)'板桥’(上)吗?我们都知道'月’不一定在'茅店’之上,它可能在天际刚升。”这些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符合实际的。只是好像未能切心餍理,把这两句名诗所构成的优美无比的意象、它所唤起读者的联想勾画出来,剖析出它之所以好的原因,似是一个不足。
其次,意象作为诗歌中的一个要素,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指作者在生活中因物有所感,选用最有象征性的物象最恰切地表达作者的情思,但意象本身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包含着客观的“象”和主观的“意”两方面的内容。因此,在这时的意象论中,从“意”和“象”两方面来论述优美意象的产生的,数量颇不少,如前七子的首领何景明所说的:“意象就日合,意象乖日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并认为李梦阳早年反对宦官刘瑾时的诗,意与象合,“众响赴会”,“尚中金石”。刘瑾死后,他被释出狱,起故官,诗的意与象乖,“一音独奏”,“独取杀直”,就再不能感人,也失却了“含蓄典厚之义”。后七子的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一中也曾从意与象的关系方面对产生于晚唐五代的《金缄诗格》提出过意见,不赞成它的“内意”、“外意”之分:
《金缄诗格》日:“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论,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贾至、王维、岑参诸联,皆非内意,谓之不入诗格,可乎?其实元人杨载在《诗法家数》中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妙。”这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诗的内意只看作理,外意则看作与理无关的象,又是明显地欠妥的。
对意与象的关系论述得最多的,最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他认为诗的意象要超妙,就“要外足于象,而内足于意,文不减质,声不浮津。”在《王少泉集序》20中,他曾更加明确地提出这一点,认为王少泉的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善于在意、象之间“折其衷”:“公于意非不能深,不欲使其淫于思之外;于象非不能极,不欲使其游于见之表……”称赞他的诗意深而不滥,对物象的描写又比较含蓄蕴藉,并不直露。王世贞对后七子的另一成员谢榛的诗颇多不满,曾经代为删削,去取的标准之一,就是意与象是否“衡当”。所谓“外足于象”、“内足于意”,所谓“意象衡当”,就是要求外在的物象、物色和内在的情思都要表现得很充分,既不能以象胜,也不能以意胜,偏诸客观或主观。两者在诗中都要表现得充分而又处置得允当。王世贞的这类意见虽然是比较合理的,却远说不上精当。譬如说,他和李重华在《贞一斋论诗》中的见解相比较,就差得多了。李重华说:“何谓意与象?曰:“物有声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称音也”,较为重视音律美,但他又说:“意”、“象”、“音”三者孰为先?日:“意立而象与音随之。”认为“意”属主帅,如果拿王世贞的意见和王夫之论意、象和情、景的见解比较起来,也更逊色了。王夫之说:“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合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这里对于象与意、景与情的精审卓识的论述,可以说是王世贞全未梦见的。王夫之对于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是意象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他不仅十分重视诗的意象美,而且对怎样使意与象合,达到象中有意、意中存象的辩证的、微妙关系的论述,都是鞭辟入里,前无古人的。而王世贞虽然大谈意象,但是由于他文艺思想中形式主义见解的影响,甚至把诗的音乐美的重要性放在意象美之上,如他在《李氏古乐府序》中,不赞成李伯承把意象美放在音乐美之上,所谓“稍稍先意象于调”,这显然是轻重倒置的。诗的音乐美无疑是好诗的一个因素,但比起意象美来,显然又是较为次要的。一首缺乏超妙意象的诗,尽管在音律上怎样铿锵,终究是不能感动人的。
关于意象的理论,在这一个时期中,主要表现在以上两个方面。我们把这一时期关于意象的论述和这以前的理论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这时的论述是更加细致入微、切中肯綮,从而表现了这一诗歌理论的成熟性的。在这一时期中,以意象论诗的,更是多不胜数。如胡应麟赞美《大风歌》等说:“《大风》千秋气概之祖,《秋风》百代情致之宗,唯词语寂寥,而意象靡尽。”在《诗薮》内编卷一中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同书卷二中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钱谦益以“意象萌茁,根□屈蟠”称赞汤显祖“晚年之文”。沈德潜以“意象孤峻”赞美孟东野的诗,在《唐诗别裁·凡例》中赞陶渊明诗“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认为“词家意象或与诗略有不同”,以至康有为在《书镜》所说的“意象”,凡此等等,可见意象的问题,在这时已被普遍地重视和注意。
四、意象和意境的同异
诗歌中的意象既然包含着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两方面的含义在内的,那么,它和意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国外的一些外籍华人学者,过去不认为中国有意象的理论,近年来有些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却又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象、兴象、境界等等,都是一回事,如黄国梁的《中国诗歌纵横论》等著作就是持这种观点的。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意见呢?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所使用的许多概念,虽然常常包含着很丰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经验,却缺乏严密的、科学的界说。这就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国古文论的概念,多少有些像中医的概念。我们只能根据这些概念的使用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的,给予它们以接近于它们本来含义的解释和界说。意象和意境同样是如此。
应该说,意象和意境概念的内涵是很接近、很相似的,却不完全是一回事。
所谓它们在内涵上很相似和很接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上:
首先,意象和意境确实都包含着作者主观的意和客观的景、象两个方面,并且都是要求在创作中,物我水乳交融的,即意与境浑,心与物共。二者既不能相离,更不能相乖。如王夫之一再精辟论述的:“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日: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29这些论述无疑既适用于意象,又适用于意境。
其次,无论意象与意境,都要求意余象外、咫尺万里。具有优美意象和超妙意境的诗。它们所描写的具体、个别、感性的物或事,都是不能止于这些物象、境象本身的,而要求它所曲传的意想、情思,要比它所描写的具体、个别事物深远得多。“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正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要求意余言外,运用比兴、明喻、隐喻等等,无论意象或意境,两者都是完全相同的。
但如果我们比较细致地考察一下意象与意境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不可能做详尽的历史考察,只能简要地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这区别首先表现在它们的渊源方面。我国意象的理论,是直接从《周易》和《庄子》两个源头演化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曾受到佛家思想的某些影响,但佛学中关于意象关系的见解,仍是从老庄哲学那里汲取来的。因此,可以说,它是最富有传统色彩、并具有最长远历史渊源的美学概念。而意境的理论却不同,它虽然和《周易》、《庄子》等有关系,但它的诞生,主要是佛教输入中国后,佛教的哲学、塑像、绘画等影响的结果31,其萌芽阶段在魏晋南北朝,较为普遍使用于文学艺术,是唐以后的事。
其次,就意象和意境的内容说,意境这一概念,指的是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能够把读者引入充分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而意象虽也具有这方面的含义,但它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意”与“象”,及其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以上只是笔者关于意象理论的初步认识。从以上的事实里,充分地说明了:意象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一个专用的术语,并非只是英语image的译名;关于意象的理论,我国古代美学中早有丰富而精辟的论述,把它视作纯粹外来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