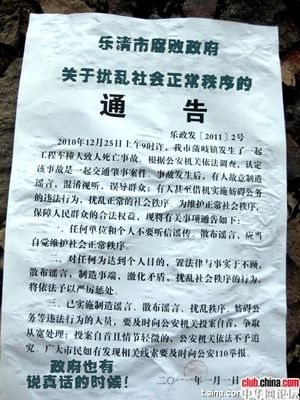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對於“古代”各依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有不同的斷年,從殷周之際,兩周之際,春秋戰國之際到東漢末,甚至唐代,不一而足。我個人主張古典社會的崩潰始於春秋中晚期之間,直到秦帝國的建立,或嚴格地說到漢武帝時代,傳統社會於是形成。大約從公元前600年至前100年,這五百年可以說是“古典”到“傳統”的轉型期,它的基本性質,可以概括為“編户齊民”,構成秦漢以下兩千年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骨幹。
衆人皆知在各種學問知識之中,歷史學特别重視時間的流變,我尚不至於愚蠢到將兩千年作為一個不變的單位來看,而陷入“停滯論”的謬誤。即使遥遠的夏商周三代,我所謂的“城邦”也不當作一個模式。雖然過去史料缺乏,受到儒家聖王理念的影響,這段兩千年的歷史難免形成刻板的史觀;而今因考古新资料不斷充實,我們的理解逐漸深入,城邦形態也可以指出幾個發展階段。[1]至於秦漢以下史料豐富的時代,歷史轉變的痕跡是至為顯明的。不過,如果歷史家探索的目標朝向社會文化的本質,有些特色是可以經久而少變的。所謂秦漢以下兩千年社會特質的“編户齊民”要放在這樣的脈絡中來理解才有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城邦形態的發展階段參看拙作《夏商時代的國家形態》;《關於周代國家形態的蠡測——“封建城邦”說芻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從考古資料論中原國家的起源及其早期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1分,1987年。以上皆收入《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我所論編户齊民形成的時代即是中國傳統史學認為古代大變動的時代,近代一些研討中國古代社會轉變的理論也把轉變放在這時期。傳統史學側重政治層面的改變,如中央統一政府的確立,郡縣制度的完成,也發現諸子百家澎湃思潮和周代封建的王官學術具有絕對的差别。然而近人研究毋寧更重視社會層面,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謂奴隸制轉為封建制,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東洋史學者所謂中國古代帝國之形成皆是;我的“編户齊民論”雖然也從社會出發,但整體著重的焦點以及個别的論證意見與他們頗有出入。本文分疏鄙論與他們的歧異,目的在於對照說明,以讓我的意見表達得更清楚而已。這種對照比較是拙作《編户齊民》一書所未嘗論及的。
1992年春天蒙韓國東洋史學會之邀,指定報告我的編户齊民論,[2]而草就此文,使我有機會對四十餘萬言的《編户齊民》自我剖析。除比較過去數十年中國古代晚期研究的一些大理論外,因為在韓國研討,本文特地舉李成珪氏的“齊民論”來砌磋商量。李先生是韓國知名的東洋史學者,與我以文會友有年,但他倡導的“齊民論”與我的說法名同而實異。這也是《编户齊民》一書所未涉及的,或可提供讀者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韓國東洋史學會1992年1月27~29日在木浦大學召開“第11回(國際)東洋史研究討論會”,會議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的統治結構與社會變動之諸問題”宣讀論文六篇,按時代順序是臺灣杜正勝的《中國古代晚期的‘編户齊民’》、日本谷川道雄的《中國中世社會と“豪族共同體”》,韓國李範鶴的《北宋後期之政治與新舊黨争》,日本森正夫的《明末清初“社會變動論”》,中國大陸王曉秋《十九世紀末維新派的“帝國主義論”》,和韓國尹世哲的《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論”》。這次會議議題的設計和報告人的甄選實在值得中國歷史學會效法。
二、“編户齊民”釋義
“編户齊民”是漢初文獻常見的語彙,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剛過世,吕后深恐諸將乘機叛立,與密友審食其計謀時就說:“諸將故與帝為編户民。”(《漢書·高帝紀下》)“編户民”也就是“編户齊民”,或謂“編户之民”(《史記·貨殖列傳》)、“編户”(《淮南子·齊俗》、《漢書·貨殖傳》),或是“齊民”(《史記·平準書》),基本意思都相同。
誠如“編户齊民”字面所顯示的,此詞含有兩層意思,一是編户,顏師古云“列次名籍”(《漢書·高帝紀下》注),也就是以户為單位,登記同户成員名字身份的籍帳。另外一層是齊民,如淳說:“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漢書·食貨志下》注)所以“编户齊民”就是列入國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以劉邦為例,起義之前,他最高行政職務擔任過亭長,諸將有職位比他高的掾史僚吏,也有比他更低的市井之民,但吕后說他們同屬於“編户民”。另一方面,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論述貧富不均時也說:“凡編户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列傳》)可見编户齊民的“齊等”是政府相對於被統治人民而言,只具備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統治意義,與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富没有關係。
我採用“编户齊民”這個古籍術語來描述古典社會到傳統社會的轉變,並非因為怠惰,不想轉换成現代習用的語言,而是現代史學界流行的術語多半來自西方,它們的產生自有其歷史條件,也許可以恰當地展現西方(或西歐)的歷史、社會,但移植於中國,不一定貼切。譬如秦漢以下的社會成員,我稱之為“編户齊民”的人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主張“奴隸制”者認為即是“奴隸”,主張“封建制”(非中國古籍之“封建”)者認為即是“農奴”。所謂奴隸或農奴都指當時主要的勞動力而言,其實缺乏統計學的證據。但“編户齊民論”可以避免統計學的尷尬,每隔三年户口總普查,國家登記的全國總户口數可以確定為當時全國絕大多數的人口。因為從制度上說,户口普查要求“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周禮·秋官·司民》),官員不可包庇遺漏,人民不可逃脱不録。包庇遺漏謂之“漏户”,逃脱不録謂之“亡命”,都是犯法的,所以承平時期大部分的人口應該都編人户籍的,以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為例,登記的民户12 233 062,口59 594 978(《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一》引《帝王世紀》略異)。一個正常社會,亡命之徒總是占少數的。
奴隸制論者儘管列舉奴婢買賣,或從事生產的事實,甚至强調一般人家也可能蓄奴,而誇張全國奴隸的總數,但對於上述元始二年的人口數是否皆屬奴隸,抑或奴隸另有其人,而且人數還更多,皆未明確交待。如屬於前者,需要更全面的論證,比如這些被編人户籍的人口是不是可以任意被剥削生命或財產,而他們的主人(奴隸主)又是哪些人?如屬於後者,當時漢帝國統治區登記的人口已接近六千萬,再加上遠超過六千萬的奴隸,能不能經得起後世人口資料的檢驗?
“農奴”是外來語,不但很難從中國古代文獻找到典據,内涵也不易確定。“封建制”論者的“農奴”乃指當時大多數從事農作的人口,姑且視作編户民,在統計數據上不會遭到如“奴隸制”的質疑,但問題仍在。按照西歐中古時代的農奴,他們身份不自由的一個要素是人身與所耕種的田地結合在一起,田地易主,耕種者也隨著變换領主。束縛誠然是不自由的標誌,相對地說,卻是一種保障。根據漢代學者一再指陳的,農民之苦痛在於他們不得不抛棄土地而流亡(賀昌群《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頁38~42),可見秦漢農民非束縛的“自主性”是很明確的。擅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史學家侯外廬也不能否認他們是“自主的良民”,但“作為諸種課税的對象”,遂為“自由民其名而農奴其實的有名數田人”(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頁88)。侯氏承認秦漢農民是有名數的(户籍記録),有名田的(地籍記録),有自由的(身份),因為各種課税,經濟壓榨太甚,所以定作“農奴”,所以那時的社會是“封建制”。其實這派論者忽略了西歐中古的“農奴”是一種法律身份,侯氏既肯定秦漢農民的法律身份是自主良民,卻以不自由的另一法律身份“農奴”來命名,所謂“封建制”的根本理論已經動摇,這都是為配合馬克思理論而不得已的扭曲議論。
以“齊民”二字解釋古代歷史不是我始發軔,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東洋史家木村正雄氏研究中國古代帝國就提出“齊民制”的理論(《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前面說過,與我大約同時,韓國東洋史家李成珪氏也揭舉“齊民支配體制”之說(《中國古代帝國成立史研究》)。由於採用的名詞幾乎雷同,但内容不一,須要多加說明。其實我的“編户齊民論”和這些“齊民制”内涵差異是相當大的。木村氏所謂人頭支配的“齊民制”,以國家占有和支配治水灌溉機構作基礎,但據可靠的新舊資料證實,中國古代比較大規模的水利灌溉不會早於戰國。如果强調統治結構的經濟基礎,春秋戰國之際的前後兩階段應該相當不同,但木村氏雖劃分第一次和第二次農地的土地所有和土地耕作(第一次指先秦,第二次指秦漢以下),卻統稱作“齊民制”。如果再參酌其他政治社會因素,封建城邦時代的人民的身份顯然是不齊的,所以我認為齊民之“齊”只在戰國秦漢以下才出現,這是我和木村氏不同的第一點。其次,他承認作為國家主要生產者的“齊民”對所耕田地擁有所有權,但編入本籍地貫,禁止自由遷徙,征課賦税,隸屬國家統治,故所謂“齊民制”其實是一種不同於希臘、羅馬古典奴隸制的“奴隸制”(木村前引書,頁7~59)。那麽木村氏的“齊民”不過是“奴隸”的另一種說法,當然和我的“編户齊民”大異其趣。
李成珪氏最近新作《秦統治體制結構的特性》(1991)確認“齊民”既非奴隸,亦非農奴,比木村氏固然進步,但把“齊民”作為一種等級(階级?),介乎有爵者與謫民或奴婢之間,則值得商榷。“编户齊民”包含各種等級的人口,所謂齊等只就國家行政與法律觀點而言,不能用社會階級的觀念來分析。首先,李氏將秦國的有爵者和齊民分開是錯誤的。秦國爵位分二十等,《商君書·境内》曰:“軍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雖無軍功也可能授予一級之爵位。根據我的研究,韓非所謂斬一首者爵一级,斬二首者爵二級,只能累積到四爵不更為止,也就是一级至四級的有爵者都還是齊民(《編户齊民》,頁335~345)。因此,把“齊民”和“有爵者”分作兩種社會階级並不適當。秦爵二十等的階層秩序,五級以上條件甚嚴,所以七級公大夫和八级公乘以上就算是高爵了,在秦代甚受禮遇。但高爵之人似乎並未構成另一社會階級,故劉邦統一天下後發現高爵者“久立吏前,曾不為决”的窘境,詔令“諸吏善遇高爵”(《漢書·高帝紀下》)。即使高爵也可能受到官吏的侮辱,正反映有爵者也是齊民,不宜視作兩個階級。
李氏之論上有“有爵者”,下有謫民或奴婢,中間薄薄一小撮是齊民,我戲稱作“夾心三明治式”的齊民論。按照他的說法,若無謫民這種賤民階級,齊民勢必瓦解,當然也就不可能有“齊民統治體制”了。但所謂賤民的證據則很難成立,如他舉證的《管子·輕重己》的“賊人”、“不服之民”、“下陳”、“下通”或“役夫”都不是身份階級的詞彙;《逸周書·大明武》的“十藝”並非十種身份等級的人,隸臣妾乃齊民犯法後受處分的刑名,而他舉以說明所謂比隸臣妾還低一等的“工”與“赦罪人”、“免臣”都是謫民,顯然也是誤讀文獻的結果。第一、二兩項比較清楚,可以不論,[3]先說“工”。
睡虎地秦簡《軍爵律》曰:“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其不完者,以為隱官工。”秦國官造的兵器或秦權鑄有“工城旦某”、“工鬼薪某”或“工隸臣某”之銘文,還有更多刻記“工某”(王輝《秦銅器銘文编年集釋》;《編户齊民》,頁297~299),當是《禮記·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制度。單稱“工”者是自由民,加上城旦、鬼薪或隸臣者則是一定刑期的徒刑,工表示其職務。兵器銘文也都鑄有“工師某、丞某”,是他們的上司。所以工隸臣是指服隸臣之刑而專司工之職務的刑徒。工隸臣自己斬首有功,或别人斬首立功,以這種功勞换取工隸臣的自由,他便可免除刑徒的身份,但仍執行工的職務。如果肉體有所虧損,像黥、劓之類,便作隱官工。這條《軍爵律》應如是解,但李氏誤把“工”和“隸臣”斷開,再按某些學者的講法把隸臣解釋作官奴婢,於是創造出齊民與奴隸之間的謫民階級“工”,是不可信的。[4]至於《史記·秦本紀》的“赦罪人”或“免臣”按文義是秦政府赦免罪人或臣妾,移民去充實新征服的地區。這是秦在征服六國過程中的一種策略,逐漸在東方安插秦人,被赦免的罪人當然相對地獲得自由的身份,也就是齊民。而不是“赦罪人”“免臣”(名詞)形成一個低於齊民的“謫民”階級;實際情形則是罪人或奴隸(臣妾)一經政府赦免便成為齊民,在地方行政體制之下,做為國家公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管子·輕重己》論冬至後九十二日春分,全國開始農作,“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張佩綸云作當任)之地,上作(任)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理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隋農不勤農事,遂蒙“賊人”“不服之民”之惡名,賊人者謂賊害農業生產,不服者謂不服南畝。這種人在鄉里遭到鄙視,在軍隊降為下等(“下等”從安井衡說)。如果他努力樹藝了,這些惡名當可免除,這樣算不算賊民呢?又《逸周書·大明武》論戰陣,“城廓溝渠,高厚是量,既踐戎野,備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赦,十藝為明,加之以十因,靡亂不荒。”所謂十藝,“一大援,二明從,三餘子,四長興,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八閑書,九用少,十興怨”。朱右曾《集訓》云,大援,與國也;明從,使能也;餘子,卿大夫之庶子;長興,長於興積者;伐人,長于擊刺者;三疑,虚虚寅實莫測;閑書,離間之書;用少,簡其精銳;興怨,使衆怨之。可見“十藝”涉及戰争之人員及方法,不是十種社會階級。
[4] 李成珪又說一般隸臣妾用上绞爵贖免為庶人的條件大概是爵二级,從同樣的隸臣妾等級,上絞爵一級所能達的工與上絞爵二級才能獲得的庶人(即齊民)等級之間有爵一級之差。這段話不太清楚,上絞之“絞”或即是“繳”。他的意思是繳爵二級,隸臣妾可免為庶人;繳爵一級,隸臣妾可免為工。其根據當出於上引《軍爵律》的前半段:“欲歸爵二級以免親父母為隸臣妾者一人,及隸臣斬首為公士,謁歸公士而免故妻隸妾一人者,許之,免以為庶人。”秦律意思是說,父為隸臣,母為隸妾,其于歸爵二級,父或母可免為庶人。另一種情况是身為隸臣,斬首有功,授爵為公士,可以將一級公士之爵還給政府换取身為隸妾的妻變成庶人。不是還二級爵隸臣妾便免為庶人,還一級免為工。“工隸臣”或“工隸妾”是一個專名,不能分開。
秦始皇遣往南北邊徼的“謫戍”,身份上也不是賤民。發遣的對象包括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和治獄不直的官吏,使他們去充實郡縣。《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徙謫,實之初縣”,顯然是成為邊疆新郡縣的人口,在法律上是國家的公民。個别地分析,逋和亡是兩種罪名(王毓銓《萊蕪集》,頁65~70),逋是逋事,睡虎地秦簡《律說》云,應當服徭役,已發出徵集令,但逃避不會者謂之“逋事”(《睡簡》,頁221);亡是亡命,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云,“籍亡”,“去亡以命”(《睡簡》,頁250、252),脱離户口名籍而流亡。嘗逋亡人即曾犯“逋”或“亡”的前科。從法律觀點言,罪犯服刑届滿,仍然應該恢復齊民的身份。贅婿,按《魏户律》“贅壻後父,勿令為户,勿鼠(予)田宇”,魏國的贅婿不列入户籍。秦國“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書·賈誼傳》),是否如魏國不屬籍,没有旁證,但如果没有户籍,國家恐怕也無從征斂吧。認定“賈人”的標準是市籍,由鼂錯所舉七科謫的“嘗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漢書·鼂錯傳》)可以證明,賈人是現行登録於市籍之人。賈人的身份向來極具争議,主張低於平民者多徵引漢高祖的詔令:“賈人毋得衣錦綉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此令發佈於高帝八年,其背景是經過秦末大亂,楚漢相争,國家貧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但另一方面“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史記·平準書》),故漢高帝運用政治手段壓抑經濟勢力,不是把賈人貶為賤民。何况公元前199年這道詔令並不能影響到十幾年前秦朝末的賈人。相反的,戰國至秦,商賈的身份地位绝對不低,且不論吕不韋、烏氏倮、巴寡婦清等特例,一個商業極其發達的時代,從事商業者大概不可能是賤民身份的人吧?即使在政府刻意壓抑商人的漢初,市籍也不一定表示身份低賤。[5]最後七科謫還有一種所謂“間左”的人,自古以來釋義紛歧,但不論“人間取其左”(《漢書·鼂錯傳》),或“發閭左適戍漁陽”(《史記·陳涉世家》),閭左只能如司馬貞《史記索隱》或顏師古《漢書·食貨志》注的解釋,謂居閭里之左,不是一個表示身份的法律名詞。秦時住在閭里之左的人,據司馬貞說是復除者,准予免除兵役;按應劭的說法,“戍者曹輩盡,復人閭,取其左發之”,顏師古最贊同此說。也就是到秦朝末年,正規軍征調完盡,原來不服或免服兵役之人亦不能幸免。所謂“七科謫”並不是秦帝國軍隊的主力,即使謫戍,他們也都屬於齊民,而非介乎齊民和奴隸之間的賤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鼂錯的七科謫,其中四科是具賈人背景的人,嘗有市籍者,父母、祖父母有市籍者,可見市籍既非世襲,本身也可改變,不是一種身份制。漢初政府壓抑商人,高帝禁止賈人衣絲乘車馬,景帝禁止有市籍在仕宦(《景帝紀》),武帝禁止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平準書》),但皆時弛時緊,不是嚴格定制。譬如宣帝時期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漢書·何武傳》)。何顯的户籍屬於市籍,既不影響他的兄弟仕宦,自己也是郡府豪吏,而且有田產,還拒納租税,所以我認為“有市籍者”也是齊民。
编户齊民的時代當然也有奴隸,睡虎地秦簡仍然沿襲古代的稱呼,謂之“臣妾,”[6]漢代以後逐漸改稱作“奴婢”。據《睡簡·司空律》和《封診式·封守》爰書(《睡簡》,頁85、249),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他們如果犯罪,政府施以肉刑,不科以徒刑(《睡簡·律說》,頁152),也因為奴隸之勞動力屬於奴隸主、而非屬於國家的緣故。秦律有同居連坐之法,所謂“同居”,《律說》曰:“户為同居”,屬於同一户籍者謂之同居,有連坐責任。不過《律說》有一條但書,“隸不坐同户謂也”(《睡簡》,頁160)。奴隸不因主人之罪而連坐,可能因為他們不和主人同一户籍,也就是他們不是编户齊民,雖然國家對奴隸的生命擁有最後决定權,奴隸主須報告政府然後才可以殺,法律謂之“謁殺”。
我的“編户齊民論”並不否定當時有奴隸或賤民,目前也不能提供编产齊民佔居全國總人口的比率數據。但不論從傳統史籍或新出簡牘來看,維持政府機構存在的必要條件,如兵役、徭役、賦税等等並不是臣妾或奴婢來負擔的,而是编入國家户籍、法律身份大抵齊等的人民;秦漢政府得以存續,間接證明編户齊民實佔全國人口的绝大多數。我們從長程結構來分析,“編户齊民”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傳統兩千年政治社會結構的基礎,其意義在此。秦至漢初,齊民雖有爵位,但到西漢中期以後,平民之爵級已喪失社會意義。所以我的“編户齊民論”和李成珪氏上有有爵者下為賤民而且只存在於嬴秦一朝的“齊民論”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根據《睡簡》,臣妾和隸臣妾截然有别,後者是一種刑名,前者才是身份制的奴隸。《司空律》曰:“人奴妾居贖貲債于城旦,皆赤其衣。”又曰:“百姓有貲贖債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馬若一牛,而欲居者,許。”(頁84~85)秦簡只見以人丁贖代隸臣妾(《倉律》,頁53~54),没有隸臣妾替人居贖貲債的,因為隸臣妾本身已是罪犯,應服徒刑也。秦律曰:“有投書,勿發,見輒燔之,能捕者購臣妾二人,繫投書者鞫審*[氵+獻]之。”(頁174)政府以臣妾二人賞給捕得投匿名書信者,臣妾如貨物般被當作贈品,但未見政府拿隸臣妾來賞人,因為隸臣妾只是一時喪失自由身份的罪人,刑期一滿仍然恢復自由民的身份。秦律有“臣妾牧(謀)殺主”(頁184),《律說》有“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頁159)的討論,隸臣妾無主可謀殺,亦無主可盗,因為他們不是奴隸。同樣的,秦律的“非公室告”包含主擅殺、刑臣妾(頁195~197),臣妾屬其主人所有。隸臣妾没有這種法律,因為隸臣妾是國家公民,不是奴隸。奴隸屬於其主,秦律遂有“人奴妾”之名(頁84,197),“隸臣妾”則不可能加一“人”字。總而言之,睡虎地秦簡凡言“隸臣妾”决不可改作“臣妾”,反之亦然,有些學者把隸臣妾解釋成奴隸(臣妾)是錯誤的。
三、編户齊民的出現
本文序言提到“編户齊民”是繼“城邦氏族”而起的另一歷史階段,關於它的出現還是先從這名詞本身涵蓋的兩個基本要素——編列户籍與身份齊等說起。先論户籍。
春秋以前的封建城邦是否如戰國秦漢以後的政府,將管轄區域内的人民都登記在國家的户籍上,截至目前為止,除《周禮》系統外,我們還找不到積極的證據。《周禮·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有一項職責是掌其轄區的民數。這個“民”包括男女老幼,按《秋官·司民》,是自生齒的嬰兒就開始記録的,死亡則删削其名。關於《周禮》年代的推定,長期以來,中外學者的意見非常分歧,我個人贊成完成於戰國時代,但承認其中保存更早的資料。不過對於登録户籍這點,似乎没有早於春秋戰國的資料。相反的,在此之前的資料顯示,人口記録的觀念或方式與後代截然不同。
西周晚期宣王對江漢邦國用兵,打了敗仗,於是“料民於太原”以補充兵源。舊注云,料民者數民也,“數民”就是清查人口。當時仲山父反對料民,《國語·周語上》記載他的議論說: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终,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廪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搜于農隙,耨穫亦於籍,彌於既燕,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仲山父的話與本題相關者,有三點值得討論。一是封建城邦時代各種職官都可從其職守而知道一部分的人口,如司民記録死事者及其遺孤,司商掌賜族授姓,司徒掌糾集軍隊,司寇記録罪犯。同時生產部門各别掌握一些勞動力,如牧人手下的畜牧,工官手下的百工,場人手下的栽培者以及廪人手下的耕種者,也都可以知道一部分的人口數。故知當時人口附著於官府各種部門,並没有全國性的記録,更無專門管理人口簿册、生録死削的部門。在這樣的體制下,國君無法了解全部人口之多寡,於是再借助於全國性的集會活動如藉田禮、收成禮時參與藉田和收成的勞動力,或四時狩獵來圍獵的人口。第二,不論政府部門所轄的勞動力或全國性集會時參加的人口,大概都以一家一人的“正夫”為主,不包括全家男女老少的總人數。第三,封建城邦儘量避免公開宣示勞動力流失,否則是為政的大忌,可能因此引發更大的震蕩,甚至亡國。所以除非萬不得已,不應該清查人口。
然而戰國以後,不論清查人口的觀念,管理人口記録的組織以及記録的内容都截然改變。首先,政治理論肯定精確的人口記録是穩固政權的基礎,列國都努力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商君書》說:“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境内》、《去彊》)《管子·度地》篇引齊國法令也說:“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别男女、大小。”其他國家恐怕也不例外,後來劉邦攻入咸陽,諸將皆争相搶奪金帛財物,唯獨做過縣主吏掾的蕭何收取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司馬遷說:“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史記·蕭相國世家》)圖書的“書”當是户籍。人口記録成為施政的根本,《周禮》且有司民之神,據占星術是屬於文昌宫的星座,管理人口的司民官和治安的小司寇在孟冬十月祭祀之(《周禮·司民》、《周禮·小司寇》)。而秦律《效律》也明白規定登記人口的官吏若發生一户以上的差錯,便犯“大誤”(《睡簡》,頁125~126)。人口記録關係國家盛衰强弱,漢末三國時徐幹所著《中論·民數》篇已提出理論性的陳述,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史翠一貫的見解,但它的歷史意義要和封建時代相比較才能顯現出來。
我並不認為封建時代没有人口記録,上引仲山父的話可以為證,甲骨文也有“登人”、“共人”等征兵的記録。但不論征兵、籍田、狩獵或各部官司的人口記録可能都是一家一人的“名籍”而己,不是包含全家人口的“户籍”。從名籍到户籍的轉變(參《编户齊民》,頁1~10)是春秋戰國以下人口清查内容有别於封建時代的主要特色,目前發現較早的資料是公元前589年楚國擴充軍隊而“大户”的記載。《左傅》成公二年云,該年楚莊王卒,晉伐齊,戰於鞌,楚欲另闢戰場以牽制晉,將徵集軍隊,令尹子重說:新君弱小,群臣不如先臣,必“師衆而後可”,於是“大户”。大户,杜預注云:“閱民户口。”這次發兵,晉避楚,據《左傳》說是“畏其衆也”。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師衆”和“大户”的關係。“大户”的字面意義是擴大户口,登記户口而使每户擴大,應是在政府記録的簿册上增加人數,結果使得徵集的兵卒衆多。按照封建制度,每家只有一名正卒,提供政府兵、徭役的負擔,我疑心楚國這次“大户”,可能把原來没有賦役責任的“餘子”也列入簿册予以徵發,而且以“户”為單位制作名册。但是否已經包含老幼婦女,現在尚難證實。
封建城邦時代,各國内政基本上獨立自主,某一國家的改變並不意味其他國家也隨之而變。不過歷史趨勢也有它的普遍性,城邦之間既非老死不相往來,共通的時代要求難免有一定的感染性。楚國“大户”顯然是擴大征兵,而擴大征兵則是春秋中晚期(公元前第六世紀)各國普遍的新政,見諸記載者雖少,如魯國的作丘甲,用田賦(《春秋》成公元年、哀公十二年),其他各國恐亦不例外,比較春秋早晚期的兵力自然明白。當春秋前期齊桓公稱霸時,他的兵車不過八百乘(《國語·齊語》),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晉軍也只有七百乘(《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即使晉齊搴之戰,晉國也只出八百輛戰車而已,雖然這不是晉國全國的兵力(《左傳》成公二年)。但到春秋晚期,各國兵力卻完全改觀。公元前537年晉國大貴族每家都出得起百乘,國君管轄的縣,每縣亦有百乘,全國四十縣,可出四千輛戰車。同時南方的楚國,其附庸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左傳》昭公十二年)。大約半個世紀之後,連魯、邾這種三等小國也有八百、六百乘(《左傳》哀公十二年),可與春秋前期的霸主相比。各國增加的兵力還有别的來源,下文將會討論,但和清查人口,整理户籍應有直接關係,等到人口記録如《周禮·司民》所說的:“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時,傳統的户籍制度便確立了,最晚可能不遲於戰國前期。
戰國文獻論及户籍的资料雖然簡略,但都提到分辨男女大小,也有歷史意義的。不論封建城邦時代官府屬下登記的勞動力,或春秋中晚期因擴大征兵而增録的人口,大概還没有包括女性及老幼。然而國家進一步控制人口時,所有的成員皆——記録,以便分别利用,“編户”的意義在使國家得以徹底掌握、運用人力資源。自戰國以下,歷代户口帳册在每一成員之下多有“大”“小”“中”“丁”“老”“黄”或“使”“未使”等的注記,表示每人隨著年龄的變異,對國家提供不同的負擔,這是户籍制度成立以後,人口記録内容與封建城邦時代絕大差異之處。因為人的年龄年年增長,於是促成“編户齊民”另一特點——按時清查户口,整頓户籍。這在封建城邦時代是“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為政之大忌,但戰國以下卻是政府的必要措施,若不定時料民反而成為亂政亡國的徵兆。根據《周禮》,清查人口分歲時的“小比”和三年的“大比”,小比是地方性的,由鄉大夫、族師、遂人分别舉行;大比是全國性的,由中央政府的小司徒主持,實際執行還是鄉遂。從《管子·地度》篇所引齊令來看,齊國的確每年季秋(會計年度的歲末)閱民,當時必不限於齊一地而已,故漢代“八月案比”遂為全國的通制(參《编户齊民》,頁427~428)。
當各國推動全面性的人口登記,以掌握人力资源,作為中央集權政府基礎之時,這些列入户籍的人口同時產生身份的變化,成為“齊民”。“編户”與“齊民”不能分開,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同時進行。 所謂“齊民”的“齊”,上文說過,是指法律身份平等,相對的,“編户”之前的封建城邦時代,天下人民的身份是不等齊的。封建統治的本質在於明確的階级秩序,一旦秩序動摇或混亂,封建制度便難以維繫。楚國芊尹無宇說,人有十等,自王、公以下,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及圉、牧,形成上下隸屬關係(《左傳》昭公七年);戰國經學家也將封建貴族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近人講述這段歷史,往往不相信太仔細的階級區分,而籠統分成封建貴族、平民和奴隸三大階級,其實歷史實情的複雜程度速超出我們想象之外。即使同屬於卿或大夫的階級,其間身份的高低也随國家大小(即在天下秩序中的地位)而有所不同,絕非一律的。按照魯國大夫臧宣叔的說法,西周以來的制度,次國的上卿相當於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相當於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左傳》成公三年)。《周禮·春官·典命》則以接受天子册命之次數分辨位階高下,雖同樣具備卿、大夫、士之身份,王畿、公侯伯國與子男國的貴族命數是極其懸殊的,譬如王之卿六命,大國(公、侯、伯)之孤卿四命、衆卿三命,小國(子、男)之卿再命。命數不同,身份亦異。
封建城邦的一般人民,身份有没有差等呢?現在缺乏足够的直接史料,但我們可以從間接證據來推論,最明顯者是“國人”與“野人”的身份差别。根據我的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形態是城邦,所謂城邦是以版築城墙的“國”作中心,連同城外四周圍的田莊“野”,而構成一個國家。《周禮》天、地、春、夏、秋之叙官都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封建城邦分成“國”和“野”這兩大景觀,不獨天子王畿,大小封國,甚至附庸莫不皆然。居住在城裏的人民稱作“國人”,住在城外者謂之“野人”,他們之間的身份差别,我從寫作《周代城邦》時已有所討論,大要不外以下數點。第一、兵役權力不同,封建城邦時代當兵是一種榮耀和權利,據《尚書·費誓》魯侯征伐徐淮戎夷的誓辭,國人準備甲胄、弓矢、戈矛,是組成軍隊的重要成員,城外的野人則負責修築城壘和飼養牛馬等勤務。第二、徭役年限不同,《周禮·鄉大夫》說國人服役年龄從身高七尺開始到六十歲截止,野人始役提前為身高六尺,終役延後到六十五歲。舊解以為七尺二十歲,六尺十五歲,那麽野人一生比國人多服役十年。第三、復除條件不等,國中享受免除賦役之優待的情况比較多,包含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鄉大夫》),野外只限於“老幼廢疾”而已(《遂人》)。[7]第四、參政權力不一,《左傳》記載春秋時代國人參與政治决策、國君廢立、外交和戰、國都遷徙的事件,不一而足,顯見城邦這種國家形態的特質,西周史料雖然缺乏,仍可發現一些類似的痕跡(《周代城邦》,頁29~35),但我們絕對看不到野人享有這些權力。最後在一個强調“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時代,國人也准予參加鄉飲和鄉射的禮儀活動,年老的國人對於只有一命的貴族還可以不必讓坐,這種禮遇恐怕不是野人夢想得到的(參看《編户齊民》,頁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國人與野人的身份差别,在禮書其他方面也有一些痕跡。《儀禮·喪服傳》說:“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别也)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都邑之士即國人。然而這些分别是否如《周禮》户籍登記,是戰國的現象呢?從擴大征兵,全國皆兵的發展情形來看,戰國應無國人與野人的差異,而更重要的,基本上到春秋晚期,城邦時代已經結束了(參看拙作《周代城邦》),戰國的國家已無國野居民身份差别之分,所以我把《周禮》國人野人負擔的記述視為城邦時代的制度。
“國人”和“野人”都屬於國君管轄,封建時代各級貴族領有大小不一的采邑,其領民和國人、野人的身份是否齊等,不同貴族采邑的領民身份是否一律,尚缺乏史料證明。理論上貴族都鄙的地位次於國君的國野,其人民的身份應該有異,而根據現存少數資料來看,當時情况則極其分歧。譬如春秋晚期齊國大貴族陳氏給他的領民種種好處以收買人心,而齊侯治下的人民只能保存三分之一的生產所得(《左傳》昭公三年),遠比董仲舒批評的“或耕豪民之田,見税什五”(《漢書·食貨志上》)更加苛酷。晉國的情形也類似,晉侯剥削過甚,人民一聽到國君的命令,就像躲避寇雠一般地流亡(《左傳》昭公三年)。這是國君“公”民與貴族領民的差别。貴族之間,最有名的例子是魯國三桓的差異。公元前562年魯作三軍,三桓瓜分魯侯“公”民,重編為自己的領民。三家待遇各不相同,季孫禁止人民向魯公服役,否則加倍征斂;孟孫捨其父母,僅取子弟之半;叔孫則盡取之(《左傳》襄公十一年,參用竹添光鴻說)。即使同一家族的父子兄弟也可能因所屬領主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從法理講,待遇雖然不等於身份,但現實上對領民而言是没有什麽分别的。由於封建領地自西周中晚期以來以小塊土地的封賜為主,加上各種方式的轉移,一個農莊有多位田地領主,譬如裘衛自邦君厲取得的四田,其北界、西界的田主是厲,東界是散,南界為散和政父(《五祀衛鼎》,《文物》1976年第5期),顯然的,在同一農莊生活的農民,負擔很可能不一樣。
然而到春秋中晚期,城邦時代各色人的身份(或待遇)之差異逐漸泯除,首先是國人與野人的分劃消失了。上文提到户籍制度之建立,肇因於擴大征兵,其對象從每家的“正夫”擴大到“餘子”,除此之外可能也從國人擴充到野人,將原來没有當兵“權利”的城外人也納入正規軍系統。根據我對這時期兵制改變的研究(參看《編户齊民》第二章),不僅各國車乘數量增加,每車配備的士卒員額也膨脹。中國古代戰車每乘配置三名甲士,從殷周至春秋,此制未變,但隨車的徒兵,西周十人,春秋早期約二十至三十人,到春秋中晚期累增至七十二人。車乘總数及配置員額之膨脹,所需要的兵卒非“國人”所能完全供應,乃起用原來不服兵役的“野人”。那麽城邦時代國人、野人的身份界線自然泯滅。此時作戰方式也逐漸改變,封建城邦時代,戰場主力是車兵,勝負决定於車上的甲士,甲士與徒卒之間有身份的鴻溝。公元前541年晉國為對付山戎群狄,魏舒臨陣放棄以車兵為主力的傳統作戰方式,改編成步卒,引起某些貴族反對(《左傳》昭公元年),是可以理解的。但進入戰國,陣線拉長,時間持久,笨重的車兵不如機動的步兵更能適應各種突發狀况,戰争方式乃改採步兵為主,傳統的車兵和新興的騎步只居於輔助的地位。戰國七雄動輒數十百萬的常備兵不論車、騎、步,都是“編户齊民”組成的。
在國人野人身份齊一之時,貴族都鄙領民則隨著采邑之收歸中央而齊民化。漫長的封建城邦時代,有些貴族不斷凌替,有些則不斷興起。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西周中晚期的裘衛銅器(《文物》1976年第5期),依《周禮》系統,位居中士的司裘竟然比邦君、矩伯還富厚,矩族見於周初銅器,正顯示某些舊族世家的没落。尤其兩周之際的大遷徙,詩人感歎“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個别家族的竄昇或沉淪必定非常劇烈,然而這也没有形成結構性的社會變遷。真正發生結構性的改變是在春秋中期以後,封建貴族之間的鬥争日亟,有的家族“降在皁隸”(《左傳》昭公三年),有的家族流亡外國變成“寓公”,他們的采邑被中央政府收歸國有,直接統轄。上述春秋晚期晉國至少有四十個縣,大概有不少是没收失勢貴族的領地的吧!而這時的中央政府其實被幾個大家族控制,國君也日趨勢微,齊的田氏、晉的六卿、魯的三桓、鄭的七穆等等,都是最有名的例子。因此,相對地促使掌權貴族争相吞併式微貴族的采邑。公元前544年吳季札聘於齊,就勸晏嬰趕快將采邑和政權還給中央政府,“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采邑對於弱勢貴族正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璧玉,在此風氣之下,采邑領民自然而然成為國家的“公”民,也就是中央政府下的齊民。同時封建城邦時代層層疊疊的貴族,也因武裝鬥争失敗或和平轉移缴還采邑和政權而“齊民化”。
中國古代社會從封建城邦轉為郡縣制的統一政府是全面性的政治社會變革,各階層都在此潮流中發生過一點力量。不過,最根本的改變在於“編户齊民”的出現,論其原動力則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不是由下而上的革命。唯物史觀的歷史家往往利用少數幾條似是而非的資料渲染奴隸革命改造歷史,其實是没有根據的。《莊子·胜箧》篇有個比喻,小盗打開人家的箱櫃提曩偷取財物,大盗可不如此費心,乾脆將整隻箱子搬走。《胜箧》說:“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盗其國”,他真正是大盗之尤。那隻箱子就是齊國的人民、土地和財富,這時齊國全國的人都變成“齊民”了,其他各國“齊民化”的過程應與齊國差不多。
單就政治法律身份的齊等還無法確切了解新社會的性質,下文將根據史料建構“編户齊民”的内涵,提出我對傳統中國社會本質的一些看法。
四、編户齊民的内涵
關於編户齊民的内涵可以從軍隊組織、地方行政制度、土地權屬、法律制度、聚落社區與身份爵位六方面來說明。
上節說過政府為擴大征兵而登録户籍,不論國人或野人,不論國君“公”民或貴族領民逐漸成為軍隊成員,所以“編户齊民”第一種特性是國家武力的骨幹。
原先以封建武士主導的車戰進入戰國後失去舉足輕重的地位,戰車淪為臨時陣地防禦之工事;而春秋晚期新興起的騎兵因為馬鐙尚未發明,馬鞍可能也尚簡略,無法發揮攻擊威力,一般只用於騷擾奇襲;戰場上殲敵的主力便落在弩射、戈擊的步兵身上。大軍團堅固凝重,適於野戰,個别士卒輕便靈巧,適於攻城。但從當時各國軍備、各家兵書或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來看,新形式的戰争是以步兵為主、車騎為輔的三軍聯合作戰,《六韜·戰車》所謂“三軍同名而異用”。步、車、騎各有妙用,以長補短,所以他們之間没有身份之别,都是“編户齊民”(《編户齊民》,頁83~95)。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我所謂的“编户齊民”的人口分别定作奴隸或農奴,就國家武力骨幹而言,恐怕是說不通的。
由國家武力骨幹而引發的第二種特性是嚴密組織的國家公民。户籍制度一旦建立,中央政府掌握全國户籍檔案,這是經由各級地方政府清查、登録人口所得资料的總和,所以户籍制度與地方行政系統互為表裏,前者的完成也就是後者的建立。地方行政系統就像中央政府撒下的大網,所有被統治的人口都在此網絡中成為國家的公民。
地方行政系統的根本在縣和里,分别源自封建城邦的“國”、“都”和“里”、“邑”。縣里之間的“鄉”以及縣以上的“郡”都只是行政階層的單位,不是具體的聚落,鄉的公署必依附於里,郡府也必依附於縣城。所以分析國家公民的性質不能不落實到縣城内外的聚落,也就是“里”。
上文討論促使編户齊民出現的根本原因是擴大征兵,因應戰争的需要而起,所以戰國的“齊民”帶有濃厚的軍事性。《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軍隊組織與地方行政兩種階層體系並行,《周禮》夏官大司馬的軍隊階層也和地官大司徒與遂人的行政組織同步,其根本精神在於“作内政而寄軍令”(《國語·齊語》)。漢初鼂錯建議募民徙居塞下,模倣古制設立新社區,“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和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正定於外”(《漢書·鼂錯傳》)。這種組織國家公民的方式我稱作“以軍領政”。既然以兵法部勒居民,軍隊什伍制乃引入聚落,於是產生什伍連坐。這種制度在春秋中晚期已有些端倪,鄭子產推行新政,有一項“廬井有伍”(《左傳》襄公三十年),因而遭到人民的批評。近人討論閭里什伍制往往沿襲傳統史學的觀點,歸咎於商鞅虐政,其實是不正確的(參看《編户齊民》,頁131~133)。
政府嚴格地組織編户齊民,實行類似於軍事化的管理,兵學家遂有“農戰論”,耒耜視同行馬蒺藜,車輿視同營壘蔽櫓,鋤續如矛戟,蓑笠如甲具,钁鍤斧鋸作為攻城器,牛馬運糧草,鷄犬作警戒,婦人織布製旌旗,男子平地如攻城,田里相伍形同約束符信,里吏官長即是將帥(《六韜·農戰》)。戰國發展成全民皆兵,兵農合一不應該僅指出戰入耕、亦兵亦農的壯丁而已,全社區是農戰合一的整體。
被統治者服兵徭之役,相對的統治者給予土地作為報償,這原本是封建城邦時代的傳統,謂之“受田”。編户齊民的出現既然是政府對全國成年男子徵發兵役,自然也會授給他們田地,今存戰國文獻還保存不少這方面的記載。臨沂銀雀山《孫子兵法·吳問》篇謂之“制田”,《孟子》或說“為民制產”(《梁惠王上》),或說“分田制禄”(《滕文公上》),《商君書》說“制土分民”(《徠民》)“為國分田”(《算地》),《吕氏春秋》稱魏國“行田”(《樂成》),說法稍異,其實是一樣的。據睡虎地秦簡保留的《魏户律》,我們也知道魏國明令授予人民田宇(《睡簡》,頁293),銀雀山《田法》說齊國“州鄉以地次受田於野”(《銀雀山漢墓竹簡》,頁146),都可證明戰國普遍存在授田予民的制度。然而關於“编户齊民”的特性,我們要追究的是齊民對於耕地擁有的權屬,這也是甄别郡縣與封建兩個時代之農民的不同所在。直到最近,學界雖承認受田,但土地所有權問題依然非常分歧,大體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土地所有權國有,一派主張私有;前者可以做為“封建制”的基礎,而我是主張後者的。雖然現在有些“封建制”論者亦承認私有(林甘泉、童超《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但對土地私有制的意義,我與他們不同。“編户齊民論”係以土地私有做為“編户齊民”的第三種特性。
在雙方都承認受田的前提下,要解决土地國有和私有,最直截了當的方法是檢查農民受田後有没有還田,可惜目前雙方都缺乏直接資料以定是非。但我主張私有的理由是(一)土地可以買賣,其例證可以早到春秋戰國之際的范蠡,范蠡去越赴齊,“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累貲至巨萬(《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他以一個外國人到齊國從事大田地的農業經營,土地很可能是買賣得到的。其他證據如從戰國早期中牟之人的棄田耘,賣宅圃(《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到戰國末年趟括“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以至漢初蕭何“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史記·蕭相國世家》),不一而足,證明買賣的土地是私有的。(二)土地可以繼承。《荀子》述說魏國對武卒的優待辦法,通過體能戰技測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數年體衰,田宅並不收回。而從荀子批評這種制度使魏國“地雖大,其税必寡”(《議兵》)來看,可能武卒死後,其田宅是傳諸子孫的。韓非慨歎韓國的戰士“身死田奪”(《詭使》),係批評豪門侵漁平民,不是政府規定死後歸田。蕭何也認識到這種弱肉强食的情勢,故他“置田宅必居窮處”,理由是“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史記·蕭相國世家》)。至於秦大將王翦向秦王政請求美田宅“以為子孫業”(《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則是土地世襲最明確的證據。而且也因為國家授给人民的田地變成私有財產,才有“恒產”(《孟子·梁惠王上》)或“經產”(《管子·重令》)的說法。(三)田地租賃。湖北雲夢龍崗近年發現一批秦簡,報告者公佈兩條殘簡:“黔首錢假其田已……”和“諸以錢財他物假田……”(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綜述》)。文字雖殘,大意仍然清楚,這是百姓以錢財或他物租借田地的法律,租賃對象不論國家或私人,應該不是徹底受田再歸田的國有制,它所反映的土地私有權的性質應比國有濃厚得多。(四)維護土地私有的法律措施。睡虎地秦簡《律說》解釋“盗徙封贖耐”的律令,田間阡陌謂之“封”,按青川“為田律”木牘,阡道、陌道廣皆三步,合一丈八尺;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文物》1982年第1期),封可能是小於阡陌的田間道路。但即使是高寬四尺(約一米)的道路要整個搬動恐怕也不容易,我懷疑“徙封”可能是侵蝕田間道路,即削小封界,擴大耕地面積。龍崗秦簡也說“盗徙封,侵食家□,贖耐”;“侵食盗阡陌及斬人疇企,貲一甲”。報告者考釋“疇企”猶今言田埂。以上禁止侵削田間道縣與别人田界的律令,恐怕只有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才好解釋。(五)確定土地私有權的行政措施,即“名田”。所謂名田就是在田籍上記録所有者的姓名,封建時代貴族領地皆記録他們的名字,理論上土地雖是“王有”,事實上是“私有”的(《編户齊民》,頁168~174)。現在名田之齊民對田地的所有權具有如同封建貴族的地位,就法理而言,土地最後主權雖屬於國家,但“國有”“私有”的討論應當不是這種意義,否則後代任何繳税的田地豈不都是國有地了?然而如果說戰國秦漢的土地國有,漢武帝征收民田擴充上林苑,何必計其價值以償於民呢?(《漢書·東方朔傳》)秦始皇統一天下,“使黔首自實田”(《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令全國人民申報田地,顯然人民主要的田地都私有了。劉邦初定天下,詔令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漢書·高帝紀下》)秦末大亂,許多人民流亡山澤之間,成為“亡命之徒”,劉邦勸令他們回到故鄉,恢復原來的爵位和田宅。此時認定人民田宅的根據當然是政府登録有案的田籍。
戰國秦漢政府一直掌握相當大面積的國有田地,但與私有田地相比,孰多孰寡,則亦缺乏數據。國有論者大概無法否定大量漢代買地券所記載的土地交易(《編户齊民》,頁142~146),至於戰國或秦,睡虎地秦簡幾條所謂國有制的證據也都可以做别解釋,[8]不是絕對的證據。根據我的研究,即使在封建城邦時代,土地制度也有多種形態,某種意義的私有其實已經存在(《編户齊民》,頁150~174),“編户齊民”出現所帶來的土地私有制是有淵源的,不是突然的劇變。
戰國時代追求富强,鼓勵生產,開闢草萊是列國的基本經濟政策,土地國有論者所謂先受田後還田以均財富的推测,恐怕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相違背。政府對编产齊民授田固然承襲封建時代的傳統,提供賦役者獲得耕地,主要目的也在鞏固國家的勞動力,《商君書·墾令》篇表達得極其明白。所以這時的文獻只見受田未見還田。受而不還,私有權於是誕生。因為齊民土地私有,才有兼并。土地兼并的問題早在戰國時代就存在,趙括“視便利田宅”而買之,蕭何“賤强買民田宅”,甚至韓非所控訴的戰士“身死田奪”,基本上都同一性質,只是兼并手段温和或蠻横有别而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土地國有制論者常引睡虎地秦簡《封診式·封守》,認為政府財產不包含田地,正是土地國有制的明證。我的看法是第一,《封診式》是公文格式,不是實例,公文内容雖然可以反映一般情况,但不能作為必然的實例。第二,以《封守》的個案來說,它的目的是鄉吏點清人員財物交付给里人輪流看守,這些財物往往是可以移動的。如子女臣妾畜產,即使不動的屋室也特别注明建材、設施以及四周栽植的桑樹。防入侵佔。田地是不動產,政府存有田籍檔案,不怕改易。既然不是點交給里人看守物品,自然不會寫在封守公文書上。李成珪還舉《睡簡·傅律》來支持他的土地國有論。《傅律》曰:“匿敖童,及占癃不審,典、老贖耐。百姓不當老,至老時不用請,敢為酢(詐)偽者,貲二甲,典、老弗告,貲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遷之。”敖童者雖未到服役年龄,但身長已達服役標準的青年。這條律文第一部分關係課役,戰國始役普通以身高計(參《編户齊民》,頁17~19),敖童當役而不申報,或有廢疾但尚未達到免役的程度而認定可以免役,里正、伍老皆須受贖耐之罰。第二部分關係退役。退役年龄曰“老”,尚未到達“老”而認定作“老”,或已到“老”而不替他申報,主事的官吏罰二甲,里正伍老不報告,罰一甲,同伍之人每户罰一盾,都加以流放。這是關係賦役的法律,和田地耕作權或國家收回土地無關。

編户齊民的第四種特性是他們乃國家法律保護的主體。封建城邦時代雖然以禮作為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但也有法律,稱作“刑”(所謂“法”則泛指國家社會制度)。當時雖有刑書,但舉凡先王之遣訓及前朝之故實也都包括在刑律範圍内(《編户齊民》,頁230~235)。這兩點都是封建城邦時代和郡縣制國家所謂法律的差異,此外還有一點重要區别,即是執行法律的程序不同。《尚書·吕刑》說:“上下比罪”,蔡沈《集傳》云:“罪無正律,以上下刑而附比其罪。”所以《吕刑》又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解釋云:“輕重有權,隨世制宜。”罪名輕重之審判没有固定的科律,随各種客觀情况而調整,春秋中晚期晉國名臣叔向謂之“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左傳》昭公六年)。叔向反對鄭子產鑄刑書公佈成文法,故引述古代制度教訓他。
法律既是政治社會的規範,也是它的反映,所以新法律的產生多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革相關。公元前543年子產整頓户籍、田籍(《左傳》襄公三十年),五年後修訂賦役,普遍徵兵(《左傳》昭公四年),再過兩年而公佈成文法(《左傳》昭公六年),這一系列的改革說明成文法典的公佈是因應社會的需要,用他的話說就是“救世”。户籍、田籍、賦役都是形成编户齊民的根本條件,所以子產公佈的成文法可以說是编户齊民的法律。
春秋中晚期的法律改革,典籍還保留晉國“鑄刑鼎”(《左傅》昭公二十九年)的記録,從孔子的批評來推測,可能與子產鑄刑書之性質相近。當時列國大概也採取相似的措施,到戰國初期,最强盛最先進的魏國便公佈更完備的法典,即是李悝编著的《法經》。李悝《法經》的史料價值曾經引起懷疑,但從睡虎地秦律出土後,以往的疑慮應可消除,因為《法經》六篇的分類都可在《睡簡·律說》找到對應的證據(參看《编户齊民》,頁440~441、249~260)。《法經》分作盗、賊、囚、捕、雜、具六篇,其中具律是名例,囚、捕兩篇可能是關於官吏囚禁或逮捕罪犯的規定,如《居延漢簡》有一條《捕律》曰:“禁吏毋或入人廬舍捕人,犯者,其室毆傷之,以‘毋故入人室律’從事。”(圖版104,395.11)雜律包含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等規範(《晉書·刑法志》),相對於盗律和賊律還是次要的。偷竊或搶劫財物曰盗,殺死或傷害人身曰賊。前者關係財產權,後者關係生命權。所以《法經》六篇是以人民的財產和生命為主要對象,正如《晉書·刑法志》云李悝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賊”;和劉邦人關中,悉除秦苛法,與父老約定“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的三章法律(《史記·高祖本紀》)也完全吻合。所謂三章其實就是盗、賊二篇,但二篇不能獨行,必包含囚捕及名例,至少五篇。太史公說,劉邦使人與秦吏巡行縣鄉邑,告諭約法,秦人大喜。可見李悝《法經》是因應“編户齊民”社會而撰著的法典。
编户齊民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既然成為國家制法的主要目的,也是國家法律的主要内容,所以國家法律的功能是在維護編户齊民的存在,可以算是編户齊民的重要内涵。
以上所論編户齊民四種特性皆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角度而發,現在再從社會本身檢討編户齊民的第五種特性——休戚與共的“共同體”並不限制個人的發展。
按說“共同體”(Community)是原始社會的特徵,由於聚落人群對外交往稀少,高度保存同族群的單純性,才容易維繫“共同體”。自春秋以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經濟社會的因素使農村人口流向城邑,城邑紛紛擴建(參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頁637~646);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亡國之民往往被任意遷徙,聚落族群遂日益複雜。這種情形進入戰國以後更加劇烈,嚴格說很難找出一個單純血緣族群的聚落。但從文獻上看,古代聚落“共同體”的性格並未消失,這要從聚落本身的結構分析才好解釋。
戰國秦漢聚落四周都築有圍墙,中間一條主要街道,兩端設置閭門,由專人看守,定時啓閉,檢驗出入。當春秋晚期以後,鐵器逐漸普及,為個體小農的耕作提供可能的基礎,商周時期集體勞動的方式雖然消失,但由於農作受自然環境及節氣的限制,同里的農業勞動一直是很密切的,基本上還維持古代同居、共耕的形式。其次是同祭共飲,春秋祠祭,里社嘗新,聚落之人共同出錢,買酒群飲,如戰國淳于髠所述的州間盛會到漢代仍然延續不絕(《編户齊民》,頁196~210)。秦漢政府每逢慶典,往往令“天下大酺”,賜给人民的酒肉都以里做單位,以供全里暢飲(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頁395~429)。因此我認為戰國秦漢編户齊民的里邑聚落,從外形建築到生活勞動,合成一體,不是單靠血緣或地緣因素造成的。所以對於古代帝國之形成,我也不贊同血緣結合轉成地緣結合的理論。
聚落的領袖人物,根據我的研究(《編户齊民》,頁210~228),不全是憑藉血緣或地緣因素而起家的。譬如劉邦長於大梁,成年以後逢秦滅魏,被遷到沛縣豐邑中陽里,十足是一個外來的編户齊民。他的族人甚少,成功以後想分封宗親以鎮天下亦不可能。既缺乏血緣,又缺乏地緣,但靠著他的才能和Charismas性格(借用Max We- her的觀念)而成為地方領袖。類似例子亦見於同時代的項梁與漢武帝朝的任安。項梁避仇,亡命於吳中,當地賢士大夫皆出其下(《史記·項羽本紀》);任安為人將車到長安,占籍關中,首先代人為求盗,轉為亭長,後為里邑領袖(《史記·田叔列傳》)。類似這種傳奇事蹟秦漢之際尚所在多有,如張耳、陳餘即是(《史記》本傳),都充分說明編户齊民雖住在“共同體”性的聚落内,但並不封閉,個人仍具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可能性。
總之,戰國秦漢國家主體的编户齊民,在政治社會結構中,至少具有五種特性:(一)構成國家武力骨幹、(二)是嚴密組織下的國家公民、(三)擁有田地私有權、(四)是國家法律主要的保護對象,以及(五)居住在“共同體”性的聚落内,但個人的發展並未被抹殺。這些内涵也是探索此時期社會性質的主要憑藉。經過上文的分析,讀者當可理解我對戰國秦漢社會是“奴隸制”或“封建制”之争辯的態度。對於中國歷史的解釋,“编户齊民論”企圖提出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當不同的架構,能不能成功,當留待學者批評,但我誠摯地相信歷史家只有面對客觀史料,具體分析,才可能接近歷史的真相,否則被理論框架所束縛,難免變成教條的注疏家。
附帶一提的,有些學者討論戰國秦漢的國家結構,特别重視二十等爵制,這個問題在我的《編户齊民》專門有一章解答(第八章《平民爵制與秦國的新社會》)。平民爵制是秦國特别的制度,商鞅變法多承襲戰國前期東方列國的改革,唯獨二十等爵是新創,為東方所未有,故秦能激發民心士氣,終於統一天下(參《編户齊民》第九章)。終秦之世,爵位的限制仍相當嚴格,但漢代以後,賜爵買爵之途多端,爵制開始浮濫。到漢武帝時,原來的爵位對人民已無吸引力,他為籌措財源,於是另設“武功爵”,爵制破壞益甚。西嶋定生氏研究秦漢國家權力結構,把皇帝與人民的統治關係建立在以爵制作基礎的所謂人身支配上(《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如單就秦國軍功爵而言,大抵是可以成立的;但他研究的重心卻放在漢代的民爵,想要證成他的理論是愈發不可能了。
五、餘論——“編产齊民論”的發展
我提出“編户齊民”這概念,目的雖然為解釋中國古代晚期(春秋中晚期到秦漢之際)政治社會的大轉變,但它的效用希望不限於這短短三四百年之間,毋寧試著把它放在更遼闊的中國史脈絡之中,以對照過去兩千年的封建城邦,並且解釋秦漢以下兩千年的深層社會結構。
封建崩潰,介於天子與人民之間的各级貴族的朝廷紛紛没落,代之而起是中央政府統御下的地方行政機構;原來王畿、邦國、采邑等内部行政相當獨立的政治社會單位消失,代之以郡縣鄉里的隸屬體系;同樣的,以前生活在各種政治實體的各種身份的人,除奴隸之外,也都轉為編户齊民。中國傳統的帝制時代,儘管多方面皆有長足進展,但上面第二圖所呈現的統治結構,兩千年來基本没有改變。安定時期,中央王朝透過各級地方政府利用户籍制度掌握全國絕大多數的人口,人民固定地向政府繳纳租税,提供賦役(兵、徭),孟子所謂的粟米、布帛和力役之征,即如唐代的租、庸、調。因為編户齊民貢獻了物资和人力,中央政府才可能組織軍隊,豢養官僚,也才可能執行統治。漢末三國徐幹指出“民數周,為國之本也”(《中論·民數》),治國根本之道首在於健全的户籍制度,可謂“千古慧眼”的史識。中國傳統時代以皇帝為首的中央政府如果比喻作巍峨堂屋,編户齊民便是堂屋的地基和樑柱。我用“編户齊民”的概念解釋傳統中國歷史,理由即在於此。這個概念可以做為一種理論架構,它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從上文分析編户齊民的内涵來看,至少涉及行政、兵制、土地、法律、社群等層面,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側重生產關係而衍生的理論不同。
本文序言已經申明我不是停滯論者,作為國家基礎的编户齊民在歷史上有過數度沉浮,上述架構最為脆弱的恐怕是在魏晉南北朝吧。中國學者所謂的門第世族或日本某些史家提出的“豪族共同體論”(參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の共同體》),都說明此一時期之國家,由於編户齊民受到門第或豪族等社會力量的侵蝕,中央政府遂積弱不振。但不論“門第”或“豪族”,都不能拿中國古代封建或馬克思主義的“封建”來解釋,當時中央政府統治編户齊民的形式並未解體,只是式微而已。我們觀察中國傳統兩千年的歷史發展,不難發現國家的强弱、社會的治亂是和政府掌握編户齊民徹底的程度成正比的。我也希望這種觀點能得到不同時期歷史學者的指正。
然而我的“編户齊民”還有一部分工作未完成,那就是齊中的不齊,忽略這一層面,“编户齊民論”將有極大的缺陷。上文說過編户齊民的“齊”只就政府的統治而言,具備行政和法律的意義,不是人民經濟財富和社會地位皆齊等。在編产齊民形成時,已蘊藏了經濟性、社會陸不齊的種子,主要表現在新興工商資本家和喪失封建特權但仍擁有大量土地的豪門。戰國新興豪富分成兩類,第一種是囤積居奇、賤買貴賣的“輕重”商人,壟斷農產品市場和金融,第二種是控制齊民必需品的鹽鐵资本家。這些問題我發表的《戰國輕重術與輕重商人》已有所論述。至於戰國的豪門,可能有不少是封建貴族的後裔,由於封建貴族對其領地實際上是私有的,和平轉變的貴族雖不一定能在新政府享受政治利益,先人傳下來的土地大概還可以部分保有,他們也可能憑藉這種經濟優勢再進入政治權力圈。從財富觀點而言,商業和農業二者相輔相成,太史公總結戰國秦漢營利手段是“以末致財,以本守之”(《史記·貨殖列傳》),新形式的豪富與個體小農名義雖同屬编户齊民,但實際上由於財富相差過於懸殊,社會地位遂變成近似主奴的關係,太史公謂之“千則役,萬則僕”。這股社會力量正逐步吞噬中央政府的基礎,引起當政者關切,先有漢高祖之折辱商人,最後漢武帝利用國家機器的方便予以痛擊,拙作《羡不足論》(未刊稿)即是討論從春秋戰國到西漢前期編户齊民中的不齊。西漢政府同時利用鄉舉里選吸引另一股社會力量進入王朝,成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固不一定排斥商業,但自此以後,商人不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則是不争之事實。歷代的官僚地主雖然多在國家約束之下,而且寄生在現行政治體制之中,但二者的緊張關係卻一直存在(參許倬雲《求古編》,頁453~482)。這是中國歷史發展長期存在的問題——不同時代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但追根究柢則是皇帝的中央政府與地方上的社會勢力在争奪國家基礎的编户齊民。
統一的集權中央政府以編户齊民做為社會基礎,而在此基礎之中產生不齊的分化,有所謂的“豪强”、“門第”或是後來的“地主”,形成可觀的社會力量,伺機瓜分編户齊民,往往危及中央政府。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著社會力量與政治權力或即或離的模式,個别課題過去不少學者頗有傑出研究成果,“編户齊民論”也許可以做為深層基礎,統攝諸多歷史現象,並進而更寬廣地解釋中國社會的特質。
“編户齊民論”除涉及政府與社會(含經濟)兩大歷史單元的互動關係外,也有生活文化史的意義,它應該還有文化的意義。根據我的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特質因編户齊民而形成,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也可以在這裏找到源頭。所以“編户齊民論”應該擴展到生活史、文化史的領域,中國人(社會)的歷史研究才稱完備。這方面的開展起源於我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不滿意。
歷史研究雖然脱離不了政治、社會和經濟三大環節,但不能以此為限。我曾把遣三大環節比做人的骨骼,如果只有骨骼而缺乏血肉靈魂,還是不能成其為人。生活、文化的研究便是要填補血肉,賦予精神情感,使歷史研究能真正達到“全史”(Total History)的境界。中國歷史家鼓吹研究人民的歷史,也隨時隨地肯定人民的貢獻,很可惜的,長期以來都懷抱唯物史觀的幾個命題不放,致使歷史研究僵硬乏味。我想從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開始,涵蓋個人或社群的禮俗活動,以至社會倫理、超自然信仰和人生追求,都應該是構成人民歷史的重要部分吧。等到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能與政治、社會、經濟三大骨幹配合,有機的編户齊民全史才算完成。這是我另一階段的工作,最近幾年雖陸續撰寫一些論文,唯個人生命短暫,歷史奥秘難求,如果有更多的秀才俊彦攜手同行,也是人生的一大樂趣啊!
參考文獻
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杜正勝《羡不足論》(未刊稿),1987年。
杜正勝《編户齊民——傳統統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杜正勝《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3分,1990年。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2年。
林甘泉、童超《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賀昌群《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綜述》,《江漢考古》1990年3期。
木村正雄《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特にその成立の基礎條件一》,東京:不昧堂書店,1965年。
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の共同體》,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年。
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1年。
李成珪《中國古代帝國成立史研究》(韓文),漢城:—潮閣,1984年。
李成珪《秦統治體制結構的特性》,收入《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東洋史學會第十届研討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東洋史學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年1期。
《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5期。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
※ 本文原題《中國古代晚期的編产齊民》,1992年2月在韓國東洋史學會第十一届“國際東洋史研究討論會”上宣讀。1994年4月修正;後載《清華學報》新24卷2期,1994年。
※ 杜正勝,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