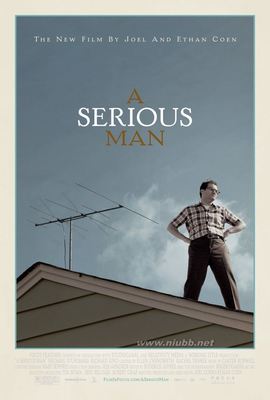沿街的树抖落去一冬的尘,新新崭崭地立在地上,像待命的兵士,只等有人一声令“发”,就要晶晶亮亮地泛出光来。那小小的尘飞舞着她的翅,吸吮着大地的气息,这光与影的和鸣,就浅浅地打着春的旋儿。
春来已多时,而冬的余威仍在。衣服裹紧了,阳光下闷得慌;松散了,晚来的风“嗖嗖”地,衣袖里、脖子上,钻进去,灌下来,从头到脚逼人的冷。
儿童中心一角,可爱的孩子们,已像初生的蝶漫天飞舞,但很快,又齐齐地进了相应的教室。这等待的空间里,家长们多半百无聊赖,因着空气的冷,在屋外呆久了,万万不得。索性倚靠在椅子上,看书的看书、阅报的阅报、聊天的聊天、瞌睡的瞌睡,打发这闲置的光景。
而坐在场子里的就有这样一个倦怠的男人,阳光斜斜地披在他的身上,竟没有一点知觉。他一个人独坐着,眼皮耷拉的样子,不说话也不抬头。头发蓬松而杂乱,像是很久了都没有修剪。头发下雾状的眼镜搭在鼻梁上,有气无力的松松垮垮,脸低下去,看不清具体的年岁,不过由他坐着的姿态和坐着的时间,及他无所事事的模样估计,他也是座椅上众多父亲中的一员。
这当儿,他的孩子正被他或他的妻怂恿着,关进去了。学什么不知道。或许是音乐,或许是舞蹈,或许是绘画,或许是……都不重要,反正是关进去了,有一个下午或者晚上,或者……反正是一个日子。要老老实实呆在他(她)愿意或不愿意的地方,楼下同样呆着的还有他(她)的爸。这个引人注目的男人,哪里知道他的孩子正满脸的怨坐在老师的面前,想说话又不能够,不说呢,心底满满的无比的憋闷,小孩的火发出来,也是不得了,他(她)的脑子早已揪死前桌漂亮同学漂亮的发。但或许大家都猜错了,他的孩子是满心满愿跑来的,也说不定。谁叫他(她)偏就爱死了这样的日子?
这个男人坐在那里,没有知觉。他的脸已不油光,脸上的褶子随意爬着,像施了一层薄薄的粉状的尘,模样就算在斜阳下也是灰的。他的西装也不时新,白白的条纹配着大块的黑料裹了他的身体,衣袋口却有一条闪亮的滑稽的皮质镶边,令光从他的打着斜阳的角落冲出来,很惊了旁边观众懒懒的目光。他竟不觉知,他的腿上摊着一本书,仿佛是嵌了“职称”什么的字样。他把书翻开一会儿,看一看,合上;再摊开一会儿,再看一看,又合上。他还拿了笔,有时做点圈圈点点的事。这样周而复始,慢慢就很吸引了旁边的人。
但予这吸引中,关书翻书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有趣的是这个男人穿了双,叫人难忘的夺目的红袜子。红袜子其实并不新,也不是鲜见,兴许还洗了好几水,红的地方都泛起淡淡的浮动的白。或许这袜子是他妻穿的也说不定,因为红的尽头绣有一朵绿的花,几瓣绿绿的叶悄悄的展开。这个穿红袜子的男人的西装裤脚极短促,因此让这抢眼的“红”露出来,又让观众欣赏了去是极其自然的事。由这红袜绿花里,不能不叫人联想如果他戴了红的帽子,穿来红的西装,脚上蹬了红的皮鞋是怎样?尽管在场的观众绝不会这般刻意辱没他。
但是他的穿了红袜子来,一定是穿了他的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如果这男人没有特别的癖好,脑子清醒着,也还算做着没有退休的活计,多半是不会在这敞亮的白日,如此打扮出来的,不过偶尔特立独行也说不准,他穿了红袜子,在儿童中心一个角落,又是休日。他大约可以抛掉平日的伪装不去顾忌,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认得他。
但更可以打包票的是,他的家里,有一个悍然的妻,呼气呵责,大势嚷嚷,逼迫他滚了出来接他的孩子。他是惧内的,又不善言说,他也曾拼了命似的跟妻甩威风,而妻抖一句,“你横,怎临了还在馆子里做牛做马?” 就让他趴下了。他极自尊,妻的话触动了他的痛处。想当年同学少年,如今哪个不意气风发?偏就他……这般田地。他诚惶诚恐,闭了眼,摸了她妻的红袜子,就穿了出来。他的妻并没有看到,她正气头上,日子一天天过去,恨自己当初瞎了眼,跟了这窝囊废般的男人。官提不上去,而今连职称都渺远得很,怎不令她怒火中烧。
他妻真没有看到她男人穿了她的红袜子,又跳着她的红袜子在冬去春寒的围墙里转圈,顾不得许多人看了他的笑话,直到他来到这个面西的座位,愁容满面的坐下来。他差不多要将头栽到脖子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