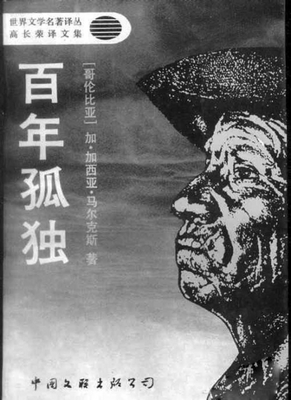前些天,从收藏的字画中挑选了几幅裱好,其中有幅作品名曰《雄赳赳》,是画的大公鸡,笔墨韵味十足。但是,这幅作品不是画家所为,而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凌元女士在晚年创作的。她习画年头不短,但是成品却很少,这幅作品是1999年冬天所画,我登门到她老人家的小院取回的。如今看到它,在百感交集之时,又觉乎着那么亲切和温馨。
总有朋友看到这幅《雄赳赳》会问,凌元是谁?其实,她演了好多好多电影,她也把全部的心思和心血都给了电影,她把电影中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以至于人们只是记得她在电影里的形象,而忘却了,甚至不记得她姓氏名谁。这里,我想请朋友们记住她,她叫凌元,是我的忘年之交。
凌元女士1917年出生于北国。从1937年入满洲映画协会表演训练班学习算起,到2012年辞世,从影七十余年。她在近百部电影中饰演过主要角色,随便例举几部:在《平原游击队》中饰演李向阳之妻、在《锦上添花》中饰演胖大嫂、在《黑三角》中饰演女特务于黄氏,以及大家熟知的《红旗谱》、《甜蜜的事业》、《邻居》、《向阳院的故事》、《小铃铛》等电影中都有精彩而深入人心的表演。
但是,也许是人们对她的过于熟悉,所以在许多的场合,人们见到她都会报以微笑,以示打招呼和尊重,少有人会问起她的名字。尤其是在演过《黑三角》之后,所饰演的女特务狡猾多端,以至于在京城人们都习惯在背后称之为“《黑三角》里的老太太”。她的模样深入人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名字却萎缩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她才不管这些,活的踏踏实实。
我和凌元女士的交往贯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讲学、演出、饭局常会有我们一老一少的身影。她住在后海畔,我们相距只是几分钟的步行,所以司机接送的时候,不是先她后我,就是先我后她,我们总有更多的一些机会谈天说地。她每次见到我先是什么都不说,就是笑,笑得阳光灿烂。其实,她的心里很苦,却从来不会向别人说半个字。她努力用笑淹没和躲闪她的苦,用笑等待每一次太阳的升起。笑,成了她应对内心苦涩与外界疑虑的砝码,也成为了她的符号和她的名片。
从茫茫白雪的北国走到刚刚建国不久的北京,这一路上的风尘还没有来得及掸去的时候,她就与一部又一部电影的拍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交错着打着交道。直到文革,她被打压、看管、劳作,然后是失子之痛,再就是刚刚迎来阴雨连天之后的阳光,又承受起失夫之苦。然而,她依然是把苦楚掩埋,去笑着撬起生活的重压,做孝顺女,做慈母。
我理解,这笑中的不简单。
1996年夏月,我回国拍戏。首演是在保利大厦剧院,临近开场,我看到凌元女士在李唐先生和耿莲凤女士的搀扶下,手捧着鲜花前来捧场。她说:“小子!怎么也不告诉我你的戏首演呀?我看到报纸以后才知道!”我本想说,怎么敢惊动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艺术家呢?但是话还没说出口,便已是泪水夺眶而出。
散戏后,她打电话给我,像是一家人一样,有鼓励,有批评。
此后,我们常常通话,或者见面。她还是那样笑,直到有一天,她不再笑了。
我却总是落泪,每每想起她的时候。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