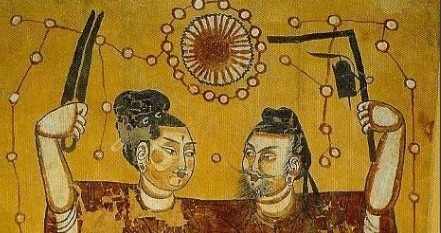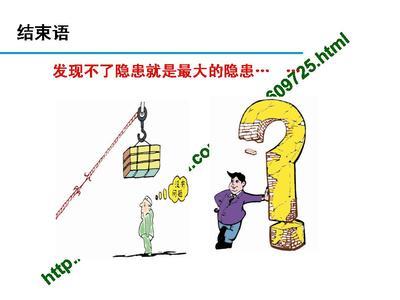慈母爱永驻
——浅谈琦君散文中的母亲形象
[摘要]琦君笔下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淳朴、善良、隐忍坚强。大爱无声,说的就是母亲这样温柔无悔的情感,琦君不管是行文或为人的温婉低调,都能够看到她那位慈爱的母亲的影子。琦君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她的慈悲、平和,与她的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琦君散文;母亲形象
[引言]在台湾当代文坛,琦君被誉为当代散文家中最负盛名的二三健笔之一,并被称是20世纪最具中国风味的散文家。有台湾的“冰心”之称。她的文字清丽雅洁、如梦如烟,清逸朴实之中见秀美,平淡自然之中有深沉。对中国大陆普普通通的广大男女老少来说,是从由其小说《橘子红了》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而知道琦君的名字的。[1]然而,琦君的创作,功在散文。[2]而在其散文作品中,最上乘的则是她的怀旧散文。在这些怀旧散文中,最好、最为动人的几乎全部写的是她的母亲。母亲的形象,可以说是琦君散文中最为耀眼的发光点。
(一)传统质朴 教子有方
琦君笔下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淳朴、善良、隐忍坚强。“母亲是位简朴的农村妇女,虽然没读过多少诗书,可是由于外公外婆的教导,和她善良的本性,她那旧时代女性的美德,真可作为全村妇女的模范。”(《母亲》)身为官太太,却整日劳作,喂猪,缝补衣服这些生活杂物都是亲力亲为,还要为长工烧饭做菜,有什么好吃的总不忘与邻居分享。琦君在很多散文中都称赞过母亲的绣花手艺。“母亲的绣花手艺是村子里闻名的。村子里若有姑娘出嫁,都回来向母亲讨花样,请她叫道她们配丝线颜色……母亲都一一仔细地指点她们……叶子也是一样,浓浓浅浅的,看上去才有远远近近,母亲不是个会画画的艺术家,可是竟然懂得现代的所谓‘透视’与‘立体感’呢。”(《绣花》)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在教育孩子上也表现出那样一种简朴的温柔。“我”被父亲带往杭州去上学,母亲十分不舍,“在临别的千叮万嘱中,她还说:‘真恨不得给你一大缸的酸咸菜去,让你顿顿都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好好求学’。”(《妈妈炒的酸咸菜》)在母亲去世后,“我”在整理衣服时,才发现母亲“把它们(虎爪和心经)和我的短袄包在一起,要虎爪为我避邪,求菩萨保佑我平安。”(《虎爪》)而母亲疼爱我之余,却并不一味宠溺,小时候作者在门边摔倒后,吵闹着耍赖不起来,母亲鲜有地变得严肃了,“走过来大声地说:‘起来,是你自己不小心跌跤的,怎么怨门槛,再赖着不起来,我就要打你了。’”过了很久,才“把我拉到怀里,慢声细气地说:‘走路要小心,做什么事都要小心,做错了就想想看,是怎么错的,不要怨别人。’”(《妈妈,我跌跤了》)一个朴素温柔的母亲,不溺爱不纵容孩子,也不轻易打骂,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让人感到心暖。
(二)大爱无声 温婉谦顺

作家白先勇在《橘子红了》的序言中曾经写道:“琦君塑造成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段。”[3]琦君的父母是远房表亲,从小就定了亲,他们的婚姻应该说是典型的就是婚姻,两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琦君的父亲任职军界,事业有成,而母亲则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子,相貌也不出众,沉默老实,也没有念过书。这样的她自然不受父亲的喜爱。起初父亲留下母亲在村里出外闯荡,后来避乱回乡,也难得才和母亲说一两句话。之后,父亲有纳了一房妾,“皮肤好喜好白,一头如云的柔发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梳各式各样的头……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漂亮时髦的姨娘自然博得了父亲的欢心,母亲在父亲眼中更加失色了。在《髻》中,琦君描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母亲和姨娘在廊前背对背坐着,互不说话,让包梳头的佣人梳头。姨娘那边总是有说有笑,梳着各种花哨的发髻,而母亲总是闷声不响,梳着老式的鲍鱼头。两个女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和敌意,在这一刻以最平常不过的方式表达着。
无论母亲是怎样自甘淡泊的人,婚姻中的不幸终究令她变得郁郁不乐,“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但她终究是隐忍和善良的。她始终爱着自己的丈夫,当女儿问她因为什么而满足时,母亲回答说:“有你爸爸从前对我的好处。”这是一个有怎样心怀的妻子啊!连少时的女儿都为她抱不平,她却始终带着安详、沉静的笑容,无怨无悔地过着平淡的生活,竭心尽力为丈夫打点生活。父亲在新婚时送她的金手表,当有人想要见识一下时,“母亲就会把一只油腻的手,用稻草灰泡出来的碱水洗得干干净净,才上楼去从枕头下郑重其事地捧出那只长长的丝绒盒子,轻轻地放在桌面上,打开来给大家看。”(《金手表》)父亲送她一支镶着宝石的梅花发簪,事隔十八年,母亲忆及此事,“眼神中流露出对父亲无限的感激与依恋”。(《一朵小梅花》)
母亲无声的爱与守候没有落空。父亲得病后的最后几年,终于懂得了母亲的好,“ 她一生都是那么宁静淡泊”(《杨梅》)“他一天天的更怀念旧日淳朴的农村生活,也一天天的更体验到母亲对他宽大无底的爱。我时常看待这一对两鬓苍然的老伴儿,泪眼相看,却又相视而笑。”(《一朵小梅花》)大爱无声,说的就是母亲这样温柔无悔的情感,琦君不管是行文或为人的温婉低调,都能够看到她那位慈爱的母亲的影子。
(三)宗教情怀 佛性博爱
琦君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琦君散文中不时可以见到母亲诵经念佛的场景。“自幼跟外公学了不少经,《金刚经》、《弥陀经》她都背得很熟。”母亲每天一大早,都要在经堂里上香拜佛念经,每逢不得已杀鸡宰猪时,她就会念往生咒,每当“我”生病时,就为“我”念白衣咒,而自己心烦意乱时,则会念心经。“月亮好的夜晚,母亲就为我唱《月光经》”,“母亲最后总是以一首《孩儿经》催我入梦”。(《母亲》)母亲正是在拜佛念经之中,化戾气为祥和转烦恼为菩提[4]。依靠着佛家的信仰,安然淡定地接受这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也正因为信佛,母亲宅心仁厚,生性仁爱。她作为官太太,却一直信奉众生平等,从不摆架子。对于乞丐的孩子,她说:“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地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罪过呢?”(《粽子里的乡愁》)她同情贫苦的人,时刻想着帮助救济,每逢过节,她总要建议村里一起捐钱捐粮给穷人。她有着宽大的胸怀,以德报怨。长工的女儿偷了琦君的零钱,母亲对女儿说:“不要声张,她不像你,有妈妈疼,一声张,就没有人理她了。”她的心是慈悲的。连对使她婚姻陷入痛苦的姨娘,在丈夫去世后,也与她“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对于骗了她钱的叔叔,母亲依旧没有仇恨,更在其困难落魄之时给予了接济。她的慈悲、平和,与她的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结语]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重的记忆与怀念……琦君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5]琦君散文构建的一直是一个飘散着“烟愁”的世界。那一丝愁绪,若有若无,似真似幻。在她对于故乡,对于曾经的回忆里,母亲这个形象一直存在,是作为如烟如梦的惆怅中一个永不转移变换的爱的美德而存在的。
[注释]
[1]楼肇明,素心笺(序言)[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魏赤,台湾女作家琦君的散文世界[A].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
[3]白先勇,弃妇吟——读琦君《橘子红了》有感[A].《橘子红了》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楼肇明,素心笺(序言)[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5]白先勇,弃妇吟——读琦君《橘子红了》有感[A].《橘子红了》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琦君,素心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琦君,水是故乡甜.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3]林薇,琦君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4]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5]贾植芳,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辞典,2003.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