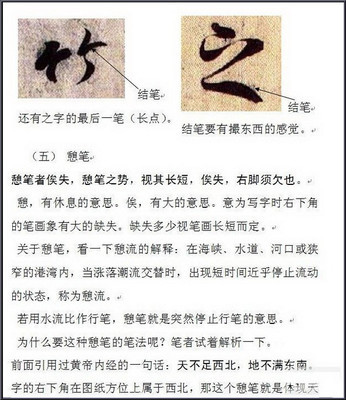“锤子去沧州了,揣着斧子去的。”小庙台的三旺眉飞色舞地说。“揣个斧子?拿个枪,他也是软蛋。”富绅闭着眼,慢条丝里地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哩!”三旺说话扯嗓子,脖子上的筋不由自主地又跳了起来。“兔子可是红眼,也有性子。”富绅说完,揣了揣手,不再吭声了。三旺想再接着往下说,见一群人不吭声,自己一时也没词了。
这次,锤子是真红眼了。
九德媳妇茹荷花到街上磨面粉,碰见锤子。“他婶子,你也磨面呀!”锤子给茹荷花打招呼。“磨面!”茹荷花接腔时,表情很不自然。“哟嗬!您俩搭上桥了!”磨面的张国增开玩笑说。“扯哩!”锤子尴尬地呵呵二下。“你别说,一会儿让锤子给你送回去!”一旁的青枣又给茹荷花来了一句。“鳖样!让他给我送回去,除非天下的男人死完了。”本来有些不好意思的茹荷花被青枣这么一将,装做不屑地说。“嘿嘿!”锤子仍没有说什么。“听人说,九德和三妞在沧州生意红火得很。”青枣也不看人的脸色,又接一句。“红火,有一天非死在外面不行。”荷花开始上脸了。“球!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干脆,你和锤子也合伙算了。他们俩个在外面,你们在家里。”国增说着,手里的活没停。“呸!”荷花虽然这次没有说话,但让锤子有些受不了了,脸由红变黑,由黑又变白……
国增正感觉这个玩笑开得有些过火时,锤子憋出来一句:“他俩在外面合伙做生意呢!”轰一下子,国增与青枣忍不住笑出来了。“没见过你这么死鳖的男人,媳妇给别人跑了,你还装得……”荷花被国增与青枣的笑声激垮了,压抑几年的愤怒找着锤子使出来了。“你!”因为这个事,锤子虽然被人涮过很多次,但没有如此当面羞辱的。“你啥你!你媳妇给别的男人跑了,你还装聋作哑,你是个男人不?”水冲开闸后,关都关不住。这时,荷花怒目圆睁,把一肚子委屈朝锤子倒来。“你不也没有管住……”锤子想说九德哩,有些不好意思提。“我是一个妇道人家。我要是男人,早就把他俩给收拾了。”荷花心里真有恨。“哪!哪!哪!”锤子有些结巴了。“那啥那!哪有男人指着自己女人的屁股挣钱的。”荷花的压抑爆发出来惊人,话像掷砖头一样,扔了出来。“你!”锤子像被雷击了一样,颤了一下。“你啥你,是男人,就把他俩弄回来。别丢人现眼。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呢!”荷花流泪的眼充满了愤恨。“你,你,你等着。他们不回来,我把他们的头拎回来。”锤子忍无可忍的火蹿了上来,“腾”的一下,把架子车往地上一甩,车上的小麦袋滚了下来。锤子看也没有看一眼,甩手走了,弄得国增与青枣一脸尴尬……
锤子真的揣个斧子去沧州了,到汽车站被工作人员没收之后,就不想去了,怕村里人笑话,硬着头皮去了。离沧州还有一百多里,锤子的气已经全消了。最初,九德和媳妇三妮一起去沧州开饭馆时,锤子真接受不了——自己的媳妇和别的男人一起走了,面子没有地方搁。锤子去沧州找三妞时,九德正在租的店里忙活呢!“我可以回去!你爹的病还看不?女儿还上高中不?儿子还……”三妞很平静,很理性地说。“那你和九德!”锤子头皮发紧。“你也知道九德,在咱那儿远近有名的厨子。他蒸的包子,那个香呀!在这儿一定好卖。”三妞确实和九德商量几次才出来的。“那荷花!”锤子想说荷花同意不?但说不出口。“就她那邋遢劲……别说卖包子,不要钱看有人吃不!”三妞这么一说,锤子不敢说什么了。锤子不但有疝气不能干重体力活,也不太会算账。三妞给锤子生活十多年了,对锤子太了解了,平心静气地把锤子给打发回来了。
九德和三妞的生意做得很红火,两个人的账也分得很真。锤子就是靠三妞拿回来的钱把父亲伺侯老了,把女儿送去上大学,儿子上高中了。这几年,茹荷花也去过沧州几趟,虽然有些风言风语,家里还是盖起了楼。
锤子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有没有意思都得活。现在,锤子经常这样想,也这样安慰自己。锤子心里很清楚,九德和三妞这几年在外面,别人都认为他们是俩口子,自己也早就习惯了这个事实。锤子赶到沧州时,天还没有黑。锤子不好意思大白天过去,一个人在沧州街上转,直到路灯亮了才进店。“锤子来了!”正在忙着和包子面的九德打招呼。“你来时,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三妞正在算账,看锤子那有些落寞神情,责怪地说。“嘿,嘿。”锤子没有接话,憨笑了一下。“你等一会儿,我和好面,去买酒。”九德抡起胳膊,吧吧吧地甩面,那熟练的程度,像玩杂技一样,让锤子好生羡慕。
酒是河北的衡水老白干,菜是有名的叫花子鸡。三妞知道锤子好吃蒜苔炒肉丝,亲自做了两个菜。“外面不好混……”锤子喝得舌头发硬说。“男人,男人,生下来就是作难的。”九德说话时,也前言不搭后语了。“我喝的差不多了。”锤子好久没有喝这么多酒了。“我也不能喝了,明天还得做生意。”九德摇一摇头,睁一睁眼说。“睡觉,明天您还要做生意。”锤子喝了最后一杯,不让九德给他倒了。“好,睡觉。明天还得做生意。”九德也抿了一口,把酒瓶盖柠上了。“你给我拿个铺盖,我今晚看店。”锤子醉熏熏地说。“不,你好久不来,今晚我看店。”九德歉让地说。“日子还要和往常的日子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锤子一句话说完,堆在哪儿睡着了。
三妞看着锤子那喝得有些发呆的神情,高一声低一声像打雷一样的鼾声,叹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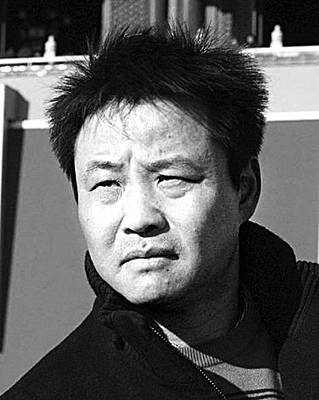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